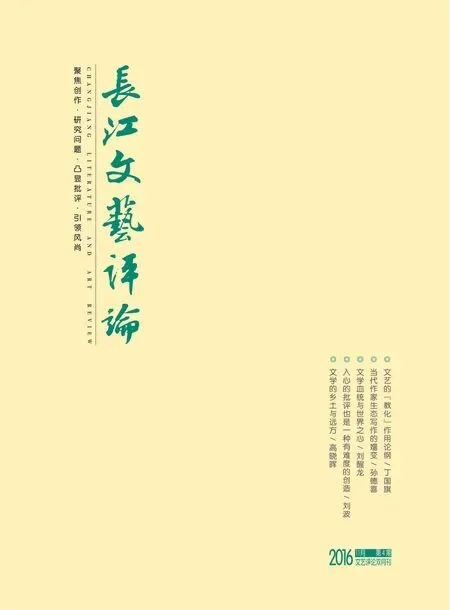“汉派文学”与都市审美
◎ 李俊国
“汉派文学”与都市审美
◎ 李俊国
在中国都市中,武汉是一座都市历史含蕴丰富,文化层积驳杂,都市文化性格显豁的现代都市。其“开埠”的时间及其现代都市构建与规模仅次于上海;此后,新学、新政、新军,共生于武汉,成为辛亥时期的“首义之都”[1];再加上武汉地处长江中游,长江汉江两江交汇,东西南北互通的地理优势,“九省通衢”“华中重镇”,成为武汉在中国都市群落中的标签。
新时期文学以来,武汉作家逐渐形成了以武汉都市为题材的写作风尚。从任常写汉正街第一代创业者的长篇小说《风流巨贾》至今整整30年,武汉都市文学创作作家辈出、四代同堂;文类齐全、体量巨大。在以乡土文学、战争文学、历史文学为主要成分的当代中国文学格局中,武汉都市文学创作是一个特别的文坛现象。当代武汉都市文学创作几乎可以与北京上海鼎立为“三”。基于此,武汉学术界早有“汉派文学”或者“汉味小说”的提法[2]。
不像当年的“京派文学”,作家虽然居住京城,却返回故乡写出大量的乡土文学,如沈从文、师陀等。“汉派文学”直接以武汉为对象,多角度、多层面、多样态地展开了文学对于武汉的都市审美。因此,从都市文学审美路径研究“汉派文学”,既符合“汉派文学”的创作实际,也深化“汉派文学”的文学批评尤其学术研究的学理需要。
一
本文所论的“都市审美”是指文学创作“把都市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3];以多样化的都市书写样式,表现出特定的都市经验和都市文化理性,传达出相应的都市审美意识,体现出独特的都市审美艺术特性。[4]
从都市书写类型概而论之,“汉派文学”已经具备五种书写类型。
一、武汉市民日常生活的样态写真。
池莉无疑是武汉市民日常生活的样态写真第一人。90年代初,《烦恼人生》《太阳出世》《不谈爱情》三部中篇,构成武汉市民日常生活的“人生三部曲”。此后,《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等大量作品奠定了池莉“汉派文学”的领军地位。池莉的都市聚焦,直接对准像印家厚、赵长天、吉玲、来双扬这类武汉市民,正是池莉小说提供的“仿真经验”与都市读者的日常经验,“艺术”与“生活”之间、“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同构”和“仿真”,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消费”[5]。
紧随其后,魏光焰、冯慧、姚鄂梅、李榕、宋小词等一大批武汉作家,纷纷游走武汉街头巷尾,寻觅都市小人物的细碎人生。《街衢巷陌》《吴嫂》(魏光焰);《彩虹的颜色》《放心的蝴蝶》(冯慧);《忽然中年》《你们》(姚鄂梅);《汉口之春》(姜燕鸣);《深白》(李榕);《谁带我回家》《声声慢》(宋小词)……武汉作家大有40年代海派作家张爱玲的“状日常之态,写人性传奇”的遗韵。她们大多认为,“较之波澜起伏,大起大落,生离死别,离合悲欢,惊险曲折的传奇式生活图景,日常生活才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领域,是我们无时无刻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活动”(姚鄂梅语)。但是,张爱玲的“日常”是“表”,“人性传奇”才是它的“魂”;而武汉女作家们,过多地关注日常的表面,对于武汉市民人性之“魂”的开掘,用力不足。
二、武汉都市历史文化的长篇书写。
从都市审美层面看,池莉们是在都市的物态层面和日常维度,平面铺排着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样态;彭建新、钱鹏喜、董宏猷、姜燕鸣却沉入武汉历史文化的纵深层积,书写着武汉都市的生成史及其武汉文化风情。
彭建新《红尘》三部曲(《孕城》《招魂》《娩世》),叙事绵密,结构宏阔。小说以1904—1949为时间之经,以汉口建城、辛亥革命、民国之都、御敌抗战为主体构架;以洋行买办、教会神父、文人雅士、军队政党、市井百姓、民俗风情、码头帮派、青红帮会、赌场妓院、地痞无赖的百业人生为空间之纬,宏阔而饱满地描绘武汉都市的生成历史与风云际会。都市文化繁杂茂密描的用力状绘,《红尘》不让茅盾的《子夜》;都市风云诡谲与都市人性裂变的传奇表达,《红尘》不逊老舍的《四世同堂》;都市空间与市井百态的开阔密匝,三教九流的谐趣智慧,《红尘》不输王安忆的《长恨歌》。因为彭建新不是静态刻板地“搬运”历史,而是沉入都市历史的层积和都市文化的肌理,鲜活地发现一座城市的生命史。
钱鹏喜的长篇《花会》,在都市历史文化肌理书写中特别有意义。“花会”是一种特殊的“赌场”。与上海赌场不同,旧时武汉的“花会”有严密的组织形式,神圣怪异的开场仪式,公开的报纸传媒信息传播和广泛的参与人群。“花会”是武汉城市建制之外的“组织”,“它几乎网络着城市社会的每处空间多个阶层,构成了旧武汉隐性的都市神经网络”。钱鹏喜以“花会”的权利争斗欲望博弈为节点,“以花会兴衰,写出雅致仪式包裹中那刀光剑影的武汉赌场文化,及其粗豪但狡黠,势利却文雅,嗜赌如命又愿赌服输的旷达人性的鲜明特色”[6]。由某一特殊的隐形的都市文化结构,作为文学的都市书写路径,钱鹏喜开启了一种异质于主流文化显性事件的,隐形而且特殊的都市文化与都市审美的文学空间。缘此路径,董宏猷和电影导演钱五一联袂推出长篇小说《汉口码头》,把码头叙事与武汉城市史的重大事件相关联,以辛亥革命前夕至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沦陷为历史背景,以大码头、汉正街为城市描写的主要空间场景;围绕码头工人黄天虎由码头工成长为一位杰出“汉口商人”生命经历为主线,形象地反映了汉口码头及其武汉都市近40年的历史风云。
姜燕鸣钟情于“老汉口的气质和性格”[7],创作了《汉口的风花雪月》和《倾城》。“汉口”不仅只是区划名称。在近现代中国,“汉口”是唯一有资格与“上海”并称的都市。《汉口的风花雪月》由四个中篇连缀而成。姜燕鸣“一直以为,设置为三四十年代的背景是最有韵味的,可以写到极致。”[8]长篇《倾城》延续着《汉口的风花雪月》刚刚触摸到的以仕女爱情切入“汉口韵味”的创作路数,并有意强化着1938年“武汉抗战”的重大事件及其“意义内容”。“那四个女人的爱情都执着而凄美,人物又显有各自的主色调,徐瑷风情、佳莉青春、香菊泼辣、云素忧郁……无论她们展示出的个性和面貌如何,她们都只是一个个小女人,追求纯真美好的爱情,过自由自在的小日子。然而战争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在经历了生死离别的伤痛之后,几个女人都相继投身于抗战洪流之中,她们也无从选择。”[9]
二
“汉派文学”对于武汉都市描写的第三种类别,是对于都市隐匿者和边缘人人性的先锋实验。
现代都市往往是现代艺术的诞生地和大本营。相对于传统乡土社会而言,都市空间的多重性与分裂感,都市生活的流动性与变异性,都市生命的撕裂性和异化感,容易形成文学艺术的“现代性美学”。“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近年来的武汉文坛,有如武汉那些日渐密集的建筑物态风景:对外在物事细密绵长的铺排,以表象化的‘唠叨’复述市民生活的日常。给人以密密匝匝的拥挤感,终究少了几分灵秀钟毓,缺了些许超验和怪诞,沉醉与张扬。武汉文学创作一直缺乏一种与大都市气质相匹配的‘另类’或‘先锋’”[10]。因为有了张执浩和李修文,武汉都市文学的书写方式有了新变。
作为诗人的张执浩,写过《去动物园看人》的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入土为安》《天堂施工队》。张执浩写武汉,避开了城市的高楼、街道、巷子、里弄,撇开了过日子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都市隐匿者”的生存状态尤其他们的精神心态,是张执浩小说的重心。朴(《盲人游戏》)、马太(《替我生活》)、张望(《马路上什么都有》)、何为(《毛病者也》)、秦天(《去动物园看人》)……这群都市隐匿者们的真实身份,是90年代转型期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蜗居斗室却心系广宇,超然物外。他们很少出门(“我对远方感到失望”);弃绝时间,拒绝都市物欲,以慵懒幽闭的存在,体现人与都市的孤独虚无,人的存在与世事变幻之间的荒诞和悖谬,还有几分睿智与清醒。
如果说池莉们是“敞开”武汉市民的生活样态,张执浩则是“隐匿”式潜入武汉知识人生命中“那些令人灵魂疼痛的生活碎片”。“隐匿”是都市写作的良好姿态和特殊视角。因为,人与都市的“隐匿”关系,使作家对都市的关注多了几分从容和理性,机智和深刻。如果说池莉们描绘的主要是都市市民的“公共经验”,张执浩则是传达都市人的“私我经验”;池莉们是对实在生活样态的真实呈现,张执浩则是对都市人“隐匿”状态的“想象虚拟”;池莉们给读者呈现一份生活报告,张执浩则为读者提供一个个有关当代人都市生活的“精神寓言”。文学史家把前者命名为“新写实”,把后者命名为“先锋”或者“现代派”。当代中国,先锋作家们多以“先锋”写远古,张执浩最早用“先锋”意识和现代派手法写当代武汉的都市人性。在都市审美层面,它承袭着30年代海派文学如刘呐鸥等人的都市审美方式,有着多方面的开拓意义。
李修文的出场有着横空出世的姿态。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将唯美审美风尚,灌注在武汉都市写作的之中。都市边缘人超越生死的情爱绝恋,是李修文精心叙述的都市爱情故事。带着养父留下的遗产从武汉只身到日本游学的武汉籍青年,随马戏团去日本寻找母亲的北京女孩(《滴泪痣》);住在东湖边废园荒冢旁,“患有再生性贫血绝症”的编书写作的武汉青年;从乡下来武汉一天打四份工的沈园园(《捆绑上天堂》);都是城市的边缘人却有着超越一切世俗意义的“生死绝恋”。
李修文把19世纪欧洲唯美主义审美方式导入武汉都市的情欲叙事,极致地张扬都市边缘者们的情欲亢进和情爱纯净。相对于吉玲(《不谈爱情》)、来双扬(《生活秀》)的势利狡黠,蓝扣子、沈园园们倒近乎王尔德作品中的“莎乐美”。[11]有着欧美文学“恶之花”的女性标记;但她们又具有了超拔俗世的纯净与高贵,诗意与神圣。在放浪中写纯净,在恶俗里写神圣,在病态里写高贵,是李修文都市书写的审美特性。
张执浩的“都市隐匿者”,李修文的“都市边缘人”,都是我们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普遍的都市人性状态。相对于城市市民生活样态的写实而言,他们的都市书写,越来越浮现在可视性的都市物态底层处的不可视的人性空间,是对都市神经的细微触摸与深度的现代性文学表达。
三
“汉派文学”对于都市审美的第四种类型,是都市思想者的武汉文学书写。
胡发云的文学创作,一直显示出特别的气质:沉思者的忧郁。早年的《老海失踪》《死于合唱》,后有长篇小说《如焉@sars.come》。茹嫣,一位独居的中年女子,儿子出国以后因为寂寞而进入网络生活。在网络里,她结识了民间思想者达摩和人生导师卫老师,被他们的强大思想所震撼。在世俗生活中,经同事的撮合,副市长梁晋生进入了茹嫣的家庭生活。与达摩们的思想交流和与副市长的情感纠葛,茹嫣面临着灵与肉的矛盾。梁晋生同样面临着与茹嫣的情感生活和副市长的仕途发展之间的两难。作家依托一个常见的都市言情故事,以达摩、卫老师们的精神出场,洞开了都市网络世界的民间思想空间,及其胡发云关于中国两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深邃思考:关于生命的情怀理想与人的生命常态;关于人和时代的“罪与罚”,痛苦与安宁,情怀的高贵与俗世的平和……从文学的都市言情叙事看,《如焉@sars. come》并无太多新鲜,但它的沉思者气质及其巨大的思考空间,远远超过了小说文本的边界。
长篇新作《蟠虺》,标志着刘醒龙创作进入“都市思想者”的写作状态。早年的《大别山之谜》,是人与故乡的自然性写作;此后的《秋风醉了》《凤凰琴》《天行者》,可视为乡村知识分子写作;《分享艰难》《政治课》,体现了刘醒龙“公民写作”的理念和实践。移居武汉以后,刘醒龙先后从熟悉的乡土题材转入武汉都市题材写作,如《城市眼影》等,但大多属于都市情爱光影的捕捉。直到《蟠虺》,刘醒龙成功地实现了由乡土文学到都市文学的转型。在武汉这座城市,刘醒龙的锐眼盯上了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青铜器,被誉为“国之重器”的“曾侯乙尊盘”。小说《蟠虺》,“围绕着国宝‘曾侯乙尊盘’构设的悬念庞大而细密。上则关乎历史与科技,下则系于野心与阴谋,旁及楚学与玄学,市井与俚俗;加上学识渊博的考古宗师、情比金坚的痴情女子、技艺精湛的青铜大盗、雄心勃勃的政治狂人,兼及龟甲卜卦、墓室陷阱、死人传书、山歌留信等等这些,冶于一炉”[12]。重要的还在于,围绕国宝曾侯乙尊盘的真伪,刘醒龙把历史与现实贯通,把国运与时运链接;在学术文脉学统的坚守和变异,知识者气节德性与野心势利的博弈,爱情与事功,文物与政治纠缠的时代语境中,塑造出曾本之、马跃之、郝文章、郑雄等一大批知识者形象。小说《蟠虺》将武汉地理风情,楚国青铜文化,当代知识者的人格,时运与国运的蜕变交融互汇,将《达芬奇密码》式的悬疑推理与民间文化的神秘怪诞穿插渗透,将“公民写作”理念和都市审美方式衔接,体现出一位当代社会观察者和思想者的感时忧世情怀。
五、武汉都市婚姻爱情的“夜半歌声”。
女性与爱情是文学的母题之一,这个文学母题被女作家不断复写。40年代上海,流行的就是张爱玲的《传奇》、苏青的《结婚十年》,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因为时空变了,语义杂了,形态多了,问题也来了,文学与都市情爱的书写也就没完没了。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似乎可以概括武汉女作家们的都市爱情书写基调。借用女诗人阿毛《午夜的诗人》的意象,她们的创作可以看做都市婚姻爱情的“夜半歌声”。因为,面对人世间林林总总的情爱婚姻,午夜适合咀嚼爱情品味婚姻,也适合舔伤口慰心灵。汪忠杰曾经把自己大学毕业后的武汉生活写成长篇《依稀如梦》,既呈现日常生活的琐碎,也流露出女性婚恋的怅惘。陈冰有长篇小说《狂欢森林》,近乎自传性的写作,展示着都市青年情爱婚姻的过程和样态,其中不乏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和都市男性文化虚伪品性的呈现,有着都市情爱表达的现代气息。阿毛真正写出了女性在婚恋城堡中的“孤独疼痛”。她的中篇小说集《杯上的苹果》,长篇小说《谁带我回家》,显现出一位都市女性对于爱情的执着及其“那种飘零与伤残的美感”。
自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有着或“情爱神圣”或“情欲剥离”,或“爱情启蒙”或“让欲望飞”等多样性书写及其复杂多样的男女人性[13]。经过中国几代作家对于都市情爱婚姻的文学表达,仍然存在着武汉女作家们的写作空间。
四
三十年间,四代作家、五种书写、作品众多、体量庞大是“汉派文学”已经成熟的都市文学风貌,它们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地形成了“汉派文学”对于武汉都市的立体性审美格局。从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文学与都市的关系维度考察,几乎没有哪个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像武汉/文学这么紧密这么繁盛。“汉派文学”与都市审美的确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现象,一道风景,一种可以成为文学史的事实。
人类文明史表明,都市的兴盛发展既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期,也是文学艺术繁荣的“黄金时代”。都市文学在以乡土文学、历史文学、战争文学为主要体式的当代中国文学语境里,是一个后起的次生的文学类型,而“汉派文学”却成为这后起的次生的文学类型的“先行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汉派文学”的称号不仅能够成立,而且意义明显。
当我们标示“汉派文学”旗帜并高张它的文学意义的同时,仍然不能回避这样尴尬的事实:当众多作家汇聚为“汉派文学”并且集中对武汉都市进行“都市审美”时,“汉派文学”的意义才得以彰显;当我们逐一检视武汉作家作品时,绝大多数都影响不大。问题根底在于,“汉派文学”如何从事“都市审美”?
文学的都市审美,从表面形态说,是文学对都市生活的描写与反映;从深层意义看,是文学对都市的“再发现”。在文学与都市的互动关系中,发现新的都市人性存在方式,新的都市经验和表达都市的新的美感形式。说到底,是作家如何从传统的文学审美方式中从事“现代审美方式”的转型问题。比如,当我们对都市生活的“日常样态”的“仿真”描述时,“日常”如何“审美”?怎样从“日常之态”中写“人性之奇”?当我们沉入都市历史时,如何触及一座城市的文化肌理文化经络?武汉历史叙事怎样体现文学的“在场性”以及如何避免历史体认的“共名性”?都市的先锋实验如何寻找作家自我表达的独特形式?都市的女性书写如何建构真正属于女性的文学感知方式和符码体系?由此看来,“汉派文学”与都市审美的未来,是一个仍需提升必须努力的文学空间。
项目来源: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都市审美:汉派文学叙事方式研究”,项目号:2 0 1 5 A A 0 1 6;江汉大学2 0 1 4年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武汉都市文学研究”。
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冯天瑜:《武汉:从中古重镇到近代都会》,《建筑设计研究》,2016年第3期。
[2]樊星:《“汉味小说”与汉味文化》,《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3]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李俊国:《都市审美:海派文学叙事方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5]【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李俊国:《〈花会〉:城市欲望的传奇叙事》,《长江文艺》,2003年第11期。
[7]李鲁平:《书写老汉口的气质与性格》,《文艺报》2011年8月24日。
[8][9]姜燕鸣:《当爱已成往事》,《倾城·代序》,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
[10]李俊国、卢轶婷:《都市隐匿者的睿智与限制——谈张执浩小说的“先锋”意识》,《长江文艺》,2001年第10期。
[11]李俊国:《唯美审美者的生命舞蹈——李修文小说解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279页。
[12]马兵:《〈蟠虺〉里的技术,精神与情怀》,《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
[13]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