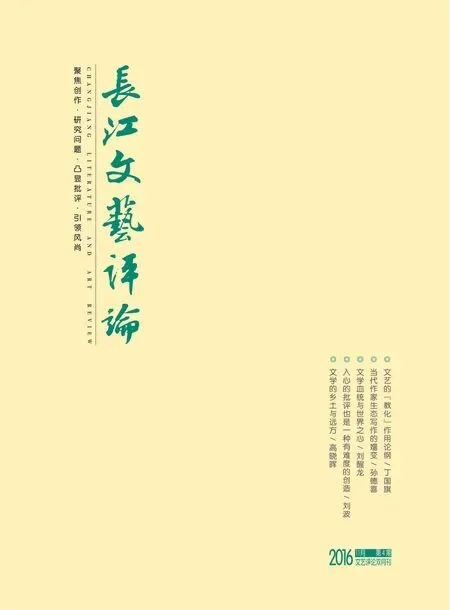文学的乡土与远方
◎ 高晓晖
文学的乡土与远方
◎ 高晓晖
一、关于文学的乡土
每一位作家都属于他自己的乡土。这一片乡土,是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可以是乡村,可以是城镇,也可以是都市。这一方水土,可大可小,大,可至乡俗的边界,小,可限于出生地之一村一街。严格地说,作家的乡土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它只是一种天然的存在。作家的乡土是作家成长的根本,是养分,是资源,是流贯始终的血脉。乡土是作家的“文学之脐”。
文学的乡土,是作家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地域。这种地域,当然离不开作家的乡土,但已不是作家生长的那片乡土本身,而是被作家文学化的乡土。作家的乡土被文学化的过程,大致是要经过“平正—险绝—平正”这三重转换的。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书谱》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平正—险绝—平正”,也可视为文学由低到高的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正好与禅家所谓“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相吻合。
最初的“平正”重在求真,追求的是摹写乡土惟妙惟肖,呈现的是同质同构的效果,即所谓“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平正”之后的“险绝”则是重在求异,使乡土陌生化,呈现的效果是同质异构或者是异质异构的。即所谓“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险绝”之后复归“平正”,重在神似,呈现的效果是形同而实异的。即所谓“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专辟一节论述了乡土小说的现代审美特征。首先,丁帆强调乡土小说是有文体边界的,他认为,“如果没有较为明确的题材阈限,乡土小说便名存实亡。”为此,他划定了乡土小说的题材范围:“其一是以乡村、乡镇为题材,书写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生活;其二是以流寓者(主要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也包括乡村之间和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流寓者)的流寓生活为题材,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其三是以‘生态’为题材,书写现代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丁帆把乡土小说划分为三种形态:乡土文化小说,乡土性格小说和乡土精神小说。在对乡土小说作了题材和形态限定之后,丁帆概括出乡土小说现代审美特征为“三画四彩”:即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
我所说的作家的乡土与文学的乡土,外延上,应该是大于丁帆关于乡土小说的题材和形态限定的。作家的乡土有地域的区分,但没有严格的界限,更无所谓乡村与都市的区分。而文学的乡土,则不限于小说一种文体,而是涵盖虚构与非虚构各种不同的文学样式。总体说来,作家的乡土与文学的乡土有共通的地方。这种共通,丁帆概括为“三画四彩”,还有的学者表述为: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我觉得,自然物象、人文风物、人情世故(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等),都属于乡土的标志物,是文学乡土的素材、能量、或者依凭,作家的乡土是文学乡土的根。
脚踏实地,是作家对待乡土应有的态度。只有脚踏实地,作家与乡土的血脉沟通才不会中断,也只有与乡土血脉沟通的文学才是“有根”的文学。作家关于一乡一土的体验和记忆,关于一乡一土的爱恨情仇,不论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它都会充当作家创作的素材,并对作家的作品内容和风格产生深刻影响。
我们习惯指称某一位作家是乡土作家,或者某一部作品地方色彩浓郁,实际上,强调的是作家的乡土与文学的乡土之间的同一性较为突出。正因为作家的乡土与文学的乡土的同一性,作家的“地方色彩”很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不自觉的。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认为,“地方色彩一定要出现在作品中,而且必然出现,因为作家通常是不自觉地把它捎带出来的。他只知道一点:这种色彩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和有趣的。”同时,他强调“地方色彩”对文学至关重要。他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1]这里,加兰是把“地方色彩”与文学的差异性相提并论的。我倒觉得,文学的差异性并非完全取决于“地方色彩”,相反,一味地摹写乡土外在表征物的(如风景、风俗、风情等)“平正”状态的乡土作品,倒不一定带来文学的本质差异。只有经过“险绝”的求索之后复归“平正”的乡土作品,才能获得本质意义上的差异,如鲁迅、沈从文等,他们笔下的乡土才是不可复制的“乡土”。鲁迅笔下的乡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愫濡染过的乡土,是以阿Q、闰土、孔乙己、祥林嫂等这样一些乡土符号,对“国民性”的生动演绎。鲁迅通过对“乡土”的回望,“引起疗救的注意”,以期达到启蒙的旨归。沈从文笔下的乡土,是对湘西酉水流域人情风俗的审美再造。这种再造的朴素、澄明之境,寄予着作家类“桃花源”式的乌托邦情怀。“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沈从文很清楚他“故事的真实”与这种世界“消灭”的现实构成了某种“互文关系”。正是一种朴素、澄明世界的消灭,成就了作家笔下“真实”的想象,从而“乡土”获得想象的美化与补偿。
二、关于文学的远方
我们承认作家的乡土与文学的乡土,从“根”的角度,二者是同一的,但从叙事或者表达的角度,作家的乡土与文学的乡土,是有本质区别的。丁帆说,“风景画不等于风景。风景,是乡土存在的自然形相,属于物化的自然美。风景画,是进入乡土小说叙事空间的风景,它在被撷取被描绘中融入了创作主体烙着地域文化印痕的主观情愫,从而构成乡土小说的文体形相,凸现为乡土小说所特有的审美特征。”要区分“风景”和“风景画”,关键在于是否居于“叙事空间”。我曾把这种区分理解为“照葫芦画瓢”。作家的乡土,是现实存在的“葫芦”,不在“叙事空间”之内;而文学的乡土则是作家以“葫芦”为依据,画成的“瓢”。“葫芦”在客观范畴之内,“瓢”则在主观范畴之内。“瓢”的审美价值,取决主体的创造力,取决于作家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或者说,取决于作家是否具备远方意识。
远方意识,从本质上说,是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德国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康德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道德律的敬畏与持久思考,其实就是一种远方意识。
远方意识体现在空间上,是作家对故乡的超越,对国家、对族群的超越,对人类的超越,视野穿越地平线,穿越大气层,进入外太空,进入未知的宇宙世界。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以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他认为,“现在的宇宙,对人类来说还是一个待开发的巨大未知空间,但对高等级的外星智慧来说,早已是一片狼藉加一片废墟的战场,是一个已经被空间战争逐渐低维化逐渐扁平化的濒临枯竭的河床。”《三体》是一位中国作家对外太空的想象,虽然作品中有关于中国乡土的时空指称,但作家的想象却远远地飞越到了“乡土”之外。
远方意识体现在时间上,是作家对历史的超越。作家要突破时代的局限,必须熟练运用“思接千载”的功夫。面对历史的长河,作家既可以逆流而上,也可以顺流而下。
有两首短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家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表达远方意识。一首是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首是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想象一下,如果《敕勒歌》只有“风吹草低见牛羊”,而没有“天苍苍、野茫茫”的空间描述,《敕勒歌》就只能见到眼前的风景,无法获得它特有的宏阔苍茫的大气象。如果《登幽州台歌》仅限于写“独怆然而涕下”而没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间视角,它也无法获得如此动人心魄的历史沧桑感。
文学的远方有多远,是相对作家的乡土而言的。从乡土出发,定位于乡土,才有远方的空间与时间。如果没有乡土的定位,只有远方,那不是如大树生长般“有根”的状态,而是流云飘浮般“无根”的状态。如果《三体》只有外宇宙空间的想象,而没有关于中国的时空指称,作为中国作家的“根”就会缺失。
李敬泽为甫跃辉的小说集《动物园》作序,题为《独在此乡为异客》,在这里,李敬泽发现甫跃辉揭示出了一种“无远方”的困境。从云南“流寓”上海的甫跃辉,他的小说和他的人物似乎一开始就被禁闭在这个地方,这个庞大都市,这个此时此刻,没有远方—空间和时间之远,有的仅仅是某种来路不明、模糊不清的气息。”此乡异客,是无“根”的,不回忆,无历史,只是此时此刻的“飘萍”。甫跃辉笔下“无远方”的困境,正好成为“文学远方”的一个反证。
文学远方所蕴含的时空距离感,有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层面。可从空间位移和时间延展两种状态进行理解。空间位移就是丁帆指出的作家“流寓”状态。沈从文离开了湘西,再写湘西;艾青离开了大堰河再写大堰河。因空间位移,作家有了对乡土的回望,故乡因此置换成了远方。时间延展有回望和前瞻两个向度。回望是作家对乡土的记忆,如废名的《桥》,关于乡土的“反刍”,如梦如诗;前瞻则是作家对乡土未来的期许;如食指的《相信未来》。
二是精神层面。作家对乡土作文学的表达,总是要思考如何回应心灵的呼唤。心灵的呼唤来自空间意义上的远方,也来自时间意义的远方。唐代画家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美国作家爱默生说:“必须远离尘嚣,离群索居,一个人与自然独对,领承天启和福音。”“心源”“天启”,都应是心灵呼唤的一种表述。
一般说来,传统现实主义作家,都会表现出很强的对乡土的风景、风俗、风情的摹写功夫。但当代文坛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家,笔下的乡土与作家的乡土少有关联或根本没有关联,比如那些关注“他乡”题材的作家。方方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却创作出了《闲聊宦子塌》《奔跑的火光》等优秀的乡土小说。2014年,一个法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湖北,5位当代法国作家,竟有3位写异域题材,最有趣的是,这几位法国作家在作品中呈现的地域,作家从来就没涉足过,更谈不上是他们的乡土了。勒·克莱齐奥是喜欢写异域的作家,他的创作更多的是关于异域生活的记忆与想象。比如他的小说《乌拉尼亚》,有很浓郁的墨西哥风情。作家放弃“地方色彩”而追求异域风情,构成了作家的“弃乡现象”。
一种情形是作家应心灵中对远方的呼唤,追奇逐新、遗弃乡土、钟情异域。这种情形下,有一种现象应该警惕,就是阿来指出的“奇观化写作”,像《藏地密码》一类,有意将异地文化“奇观化”,作为一种消费文本,消费他人的生活。也就是只追逐生活的表象和碎片,而并不在意揭示生活的本真和本质。阿来认为,边地书写与边地消费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而这种“共谋关系”足以消灭表达和书写的真实:“真实不真实是不要紧的,但是我要契合他们的心理,投其所好,满足他们的想象,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满足了他的想象,构成了那种共谋关系,那么我就能成功。[2]
另一种情形,作家为表达主观的认知,移花接木,且把他乡作故乡。陈应松的家乡是荆州的公安县,但他标志性的文学乡土却是神农架。他说,不是他对荆州没有感情,而是他把荆州的许多东西都移到神农架去了。至于陈应松为什么要这样“移花接木”,他自己的解释有点玄,他说那是因为“神农架离我的实际距离和心灵距离,不远不近,恰好够那个距离,既亲切又陌生,既遥远又近在咫尺,是我心中所想象的乡土,也是现实生活中非常真实的乡土。”
实际上,陈应松为回应远方的呼唤,找到了神农架这样一片乡土,刚好成为他的心中所想象的乡土。
归结起来说,作家的乡土是作家的根和魂。文学的乡土更要具有远方气象。陈应松说:“远方的气象,就像是一个背负很重行囊的孤独朝圣者,有着无法预知的命运和谁也不知道的心事,走在天地之间。”[3]这种“行走”是“大兽孤行”,是“独往独来”,而不是“群鸟噪林”,抱团取暖。文学有乡土并不难,难在有远方气象。谈到地域和乡土,贾平凹有一个观点:云层上面都是阳光。就是说,作家在关注乡土的差异性的同时,更要清醒地意识到乡土中所蕴含的人类的同一性。用《圣经》上的表述,即为:“太阳底下无新事。”拘泥于一时一地的乡土,为一时一地的乡土的差异与精彩陶醉,却无暇顾及更宏阔的时空背景里昭示的人类命题,这无疑会局限作家的视野和格局。文学的乡土与远方,相互依存。没有乡土,无所谓远方,因为远方是由乡土来标示的。没有远方的乡土是肤浅的,因为远方才能让乡土获得时空意义或者心理意义上的深度和广度。
高晓晖:湖北省作家协会
注释:
[1]【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转引自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2007年版。
[2]阿来:《消费社会的边疆与边疆文学》,《长江文艺》,2015年第11期。
[3]陈应松:《小说的远方气象》,《长江丛刊》,2016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