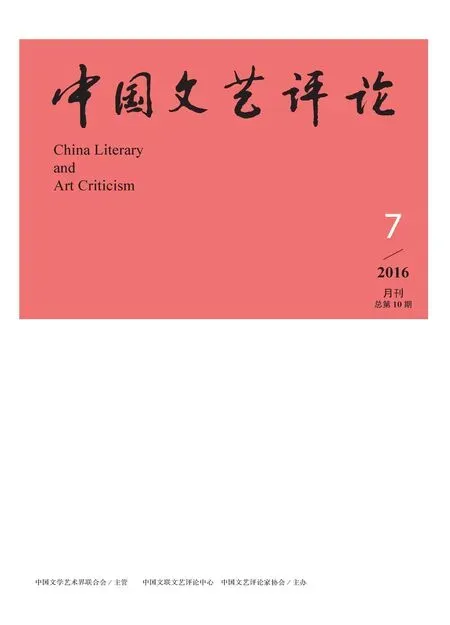中国当代戏剧中文学精神的缺位与重拾
陈建忠
中国当代戏剧中文学精神的缺位与重拾
陈建忠
编者按:如何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用艺术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是当前文艺界和文艺评论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上,青年文艺评论家们围绕舞台艺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国精神”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温度、有力度、有锐度的见解,本期刊发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冲突固然是戏剧的核心,但直面现实却应该成为戏剧的灵魂”。继2014年、2015年携3小时长度的《假面·玛丽莲》和5小时长度的《伐木》来华演出引起巨大轰动后,2016年,波兰当代著名戏剧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携立陶宛国家剧院演出的新作《英雄广场》亮相于第三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再一次引起了业界的震动。《伐木》和《英雄广场》均出自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之手。与两部戏剧漫长的演出同样著名的是剧作中对现实强烈的关注和介入。这种关注、感受和介入已经不再是在舞台演出中空泛地提出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人物,全都因为历史的浸淫,政治与文化的逼迫,在现实生活中徘徊、迂回、踟蹰、焦虑、痛苦。《伐木》中始终未出场的教授约瑟夫·舒斯特因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剧中的三场戏,也全部是与其生活有关或者无关的人在收拾遗物、送葬和聚餐时候对其的追忆。生活裹足不前,每个人心中却暗流涌动。及至全剧最后,教授夫人与一群朋友吃饭时,来自楼下英雄广场上的声音慢慢传来,从隐隐绰绰变为震耳欲聋。这是1938年3月15日希特勒宣布“德奥合并”并将坦克游行的广场命名为“英雄广场”时,奥地利民众发出的欢呼。在“德意志精神”的蛊惑下,奥地利大部分人放弃了独立和民主,宁可屈从于某种盲目和狂热,正像剧中约瑟夫弟弟说的“人类真正害怕的是人类的精神”那样。此后的几十年里,人们的生活就在疼痛与平庸中日复一日,一如舞台上所展示的那样。很明显,这种戏剧已经不再是人与人的冲突,或者人与社会的冲突,而是“戏剧”与社会的冲突。它带给中国观众的感受是:戏剧,有着直面现实,抵达现实“深处”的无限可能性。
近年来,随着国外戏剧不断被引进,《撒勒姆的女巫》《死神与少女》《死无葬身之地》《纪念碑》和近两年才亮相中国舞台的《丽南山的美人》《黑鸟》《十二公民》,甚至来自中国香港的小剧场话剧《最后的晚餐》这样轻巧、细致,生活流的作品,都具备了某种抵达社会和现实“深处”的力量。当《丽南山的美人》中,一边是母女两代人与生俱来的刻骨仇恨和对抗,一边是爱尔兰人在英格兰整个政治格局中存在感的微茫;当《十二公民》以一种辩论式的表达,探讨“公正”如何能在惯性思维和政治偏见纵横交错的社会秩序中得以抬头、生长,最终实现对生命的尊重;当《最后的晚餐》,儿子从厨房里把母亲用以自杀的炭包拿出来,母子两人不约而同选择“自杀”来成全对方的“计谋”,被以最后一顿晚餐,用既温情又尴尬的状态呈现……我们会不自觉地与中国本土原创戏剧进行比较:我们的戏剧偏“浅”、偏“窄”。这种“窄”,体现在对题材的选择上,更体现在对生活的展现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戏剧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宏大叙述。这一类作品,因为多数停留在对题材意义的高扬而未进入到人物的心灵层面,从而缺少情感共鸣。戏剧的一大重要功用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实现观众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深度反观、思考和探究。这些打着史诗旗号的作品,因为无法进入到人物内心,距离戏剧本身的意义相去甚远。甚至,有些不应该称作创作,而应该划为宣传。另一类是近年来流行的白领戏剧,以减压为理由,将戏剧舞台出让给段子和杂耍。令人忧虑的是,我们面临着一个物质、观念和思潮极大丰富的时代,但戏剧艺术并不因此显得丰润饱满,反而类型简单、内容干瘪、意义直白,其中不乏有对政治的谄媚和对市场的匍匐,让我们的舞台,既少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欧阳予倩、曹禺、老舍等为代表的剧作家群创造的戏剧“黄金时代”,又远离了改革开放之初对人与社会的种种发问与思考,显得苍白和俗气。
产生这种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对体制的过分依赖,对市场的屈从;舞台上新鲜力量很难进入,自我造血功能不足;戏剧原创力量被影视界和其他行业分流和吸引;国家层面对于戏剧的重视程度远远达不到民众对戏剧艺术的多层次要求;社会还没有提供给戏剧蓬勃发展的多种力量……但我想,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戏剧人对戏剧艺术所能抵达的现实深处的“可能性”缺乏信任和想象。上述提到的国外经典剧目最可贵的地方,恰恰在于这种从社会到政治,再到人心层层递进、层层剥离,“到达深度”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比其他所有的创作技术加起来都重要。戏剧精神,也正体现在这种对“可能性”不懈的追求之中。
以主旋律戏剧来说,这一类戏剧固然大多是政府出资,有的甚至就是命题作文。但并不意味着,这一类题材就一定是唯上的、虚假的、宣教式的。“主旋律”本来应该是一个褒义词,是一个民族和群体中精神、品格、秉性与气质中主要部分的概括;国家倡导主旋律作品,也是因为热气蒸腾的生活中,的确有太多可以书写、值得书写的题材。它们,或者存在于英雄人物的隐忍、克制与奉献中,或者存在于普通人群的苦痛、渴望与梦想中。历史与当下,时代与价值观,都会作用在这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使他们面临选择,面对内心,也面对世界。而这,正是戏剧创作应该着力的地方。然而,我们对待主旋律的理解和态度往往是片面的,单一的,是由宏大叙事、虚假宣教、口号标语杂糅成的“伪主旋律”:描写官员两袖清风时,一定会写到在其简陋的行囊中珍藏着履任过的地方的一把把泥土,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主人公的心系苍生表现得最为直接;描写英模人物,多半会有一个岌岌可危、贫病交加的家庭。更有甚者,在一部描写人类在悬崖峭壁上开掘河流的主旋律作品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当剧中人几乎被重重困难压倒时,是一个小女孩在送水过程中的意外死亡,让场上人物在挫败和悲痛中转变为奋起——这种戏剧技巧的运用背后,暴露的是对“人”和“生命”的轻视。我们的舞台上还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只探讨一种可能性,只有黑白两种分法。或者,将所谓“大爱”和“大善”作为消泯和跨越一切矛盾和障碍的力量,而不管这种矛盾和障碍是源于个人,源于群体,还是源于历史。许多即使是打着“人性”幌子的主旋律作品,也更多的是在政治图景下对于个人缺陷的修补性描写。因此,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小奸小坏小毛病,但总体“三观”正确的人物,并将其作为戏剧文学发展的一大突破和进步,被反复运用和模仿,这些人物背后所可能存在的社会动因、文化投射却从不被深挖和提及。太多的人物都像是臆造出来或者架空的,关于戏剧,我们能谈到的更多是某一部作品的“技巧”,而不是人物的多义和复杂,人性的幽深与可感。
文学即人学。舞台上的虚假、空洞与平庸,暴露出文学精神和作家独立表达的精神在戏剧艺术中的缺位和退场。对文字本身的敬意,对文学纯度的追求,对舞台这一空的空间所能架构和达到的时代宏阔、历史厚度、人性深度、哲学思考和美学追求,在舞台上越来越难以见到;与此对应的是,创作者独立表达的意识和愿望也在不断衰减。以至于,很多创作者到了最后,已经很难分清楚作品中的那些局限,哪些是真正来自政府和官方的限制,哪些是来自自我束缚。比起有形的限制,主动放弃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权力,对于戏剧艺术发展而言更可怕。因此,需要重新认识文学对于戏剧艺术的重要,认识戏剧精神对于舞台的支撑,呼唤戏剧精神重回舞台。
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戏剧对社会的功能。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在著作《诗学》中定义“悲剧”:“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3页。——摹仿成为戏剧的基本功能。随着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和表现主义、荒诞派戏剧等现代派戏剧的出现,戏剧的功能被大大拓宽。之于人类社会,戏剧是有着与文学同等的表达力的。如果说,文学是民族隐秘的历史,那么,戏剧就是将民族历史与个人世界具象展现在观者眼前,更为直接的立体的文学样式。因此,人类对世界、对社会有怎样的实践和探索,戏剧就应该能伸展和抵达,甚至走得更远。因此,今天的中国原创戏剧,需要重新认识戏剧对于社会的作用和可能性。它绝不仅仅是好人好事的讲述,也绝不只是一件事件的起承转合,甚至不仅仅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人、社会与世界的一种链接。以前苏联话剧《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国内一般翻译为《青春禁忌游戏》)为例,该剧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在最近的十几年里,它几乎被搬上了欧洲所有国家的舞台,中国许多高校的艺术院系将其作为毕业大戏。这是俄罗斯女作家柳德米拉·拉苏莫夫斯卡雅创作的一部作品,取材于苏联解体前的那段历史:社会动荡、政府腐败、经济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孤独的数学女老师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秉承着自己教书育人的理想,单纯地活着。直到四名高三学生,因为数学考试失败登门拜访,打着为其庆祝生日的名义,一步步实施着自己的“计划”,从欢笑和哀求中透露要叶莲娜老师给他们存放试卷的保险柜钥匙,到原形毕露后的恫吓和穷凶极恶的搜身,直至整个事件的策划者瓦佳对唯一的女孩拉拉施暴,以胁迫叶莲娜老师投降……整个事件,发生在一天一夜,像是一个恶毒的玩笑,又像是一个残酷的游戏。但这玩笑和游戏,却展现了整个苏联解体前夜的真实情况:传统和美德摇摇欲坠,主流价值观面临土崩瓦解。社会阶层固化,贪污腐败横行,这一切如病毒一样侵入到孩子们的身体和心灵中。他们像是小兽一样横冲直撞,却坚定地认为:存在,即合理。正像剧中平民的儿子巴沙讲的那样:“我恨用自己胸膛去堵枪眼儿的英雄们!恨那些需要人的胸膛去堵的枪眼儿!凭什么,凭什么永远该我们堵枪眼儿!为了争取一份好鉴定,我们在学校里个个都得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现在我们在您家,把自己作践成社会的败类、无赖,为的是把毕业成绩提高一档好考大学。也许就是差这一分,我们被淘汰了,到时候,为了一张免服兵役卡,我们就得假装是白痴进精神病院。为了满足我们最基本的要求能从事自己心爱的事业,我们付出的精力是否也太多了?愚蠢的傻瓜可以拿这种游戏当真,稍稍有一点儿脑子的人只是玩玩而已。您还不明白,您捍卫的不是什么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只不过是官僚主义机器连同它彻头彻尾虚伪狭隘的道德?”——戏剧到这儿,已经不仅仅是长幼之间的冲突,也不仅仅是观念之间的对弈。它跨越了事件本身,成为一种利器,插在俄罗斯民族历史进程的褶皱之中,也对当下,泛着警示和诘问的幽光。
其次,当代戏剧舞台文学精神的缺失,对写作者提出了严格要求。戏剧文学,向来被认为是文学中的文学。在有限的时间内,它需要凝练、浓缩、提取与精粹。这固然需要对文学语言的熟稔和运用,更重要的,却是政治、历史、哲学、美学、宗教等人类史中优秀的文化结晶的强有力支撑。经典作品,一定是建筑在理性上的感性。感性是一个作品的外形,而理性恰是这个作品的内在。也正是这一点理性的光芒,使其具备穿透能力和再创造价值。因为,人类历史上的理性之路尽管曲折逶迤,但想要解决的基本哲学命题从未改变。我们被《萨勒姆的女巫》中约翰临终前的表达深深震撼的时候,支撑作品精神高度的,是剧作家阿瑟·密勒对萨勒姆小镇“驱巫”事件历史的深刻解读;我们为《丽南山的美人》人与人之间永无沟通可能的困境叹息和震惊时,英国剧作者马丁·麦克多纳将本国历史中英格兰、爱尔兰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放置在了剧中母女两代人身上;话剧《最后的晚餐》表面上讲述的是母子两人在父亲的家庭暴力下人生尽毁的故事,背后却是整个香港的后殖民心态:落寞、无根、尴尬……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同样,在戏剧舞台上展现的“人”,也应该是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属性的人,也只有拥有这样人物形象的作品,才可能传达出历史厚度和社会容量,才不会让观众觉得“浅”,觉得“窄”。这就要求戏剧写作者拥有深厚的文学积累、哲学和美学修养,以及良好的诗性表达。惟其如此,才可能塑造出生动、传神、复杂的人物,也才可能写到观众的心里。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是剧作者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敏感。剧作者在写作时,理应扮演着上帝的角色:以理性的目光穿越历史和当代,透过生活的表层,探究人性的隐秘,最后,以感性的笔触书写。因此,具备真诚和悲悯的写作态度至关重要。尤其是当下,浮躁气息涌动,作为剧作者,很容易被市场热点所吸引,也很容易让笔滑进世俗和庸俗。那么,在写作中就要时刻提醒自己:捕捉热点、焦点。这是剧作者应该有,而且必须有的能力,但对戏剧而言,更需要深究的是这热点、焦点下的众生与个体。只有进入到人物层面,进入到个体精神世界,这种写作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文字本身、文学范畴的。这同时涉及到写作敏感问题。艺术家需要具备比常人更敏锐、易感、丰富的内心,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看待事物的眼光、角度和深度。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不断训练和保持这种敏感,不至于因为写熟了某一类题材,吃惯了某一类饭菜,而让感觉钝化,味蕾麻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将剧作者的这种退化归罪于种种限制,这就又回到文中探讨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禁忌都不存在,你还具备不具备“写作”和“表达”的能力?
陈建忠:国家一级编剧,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