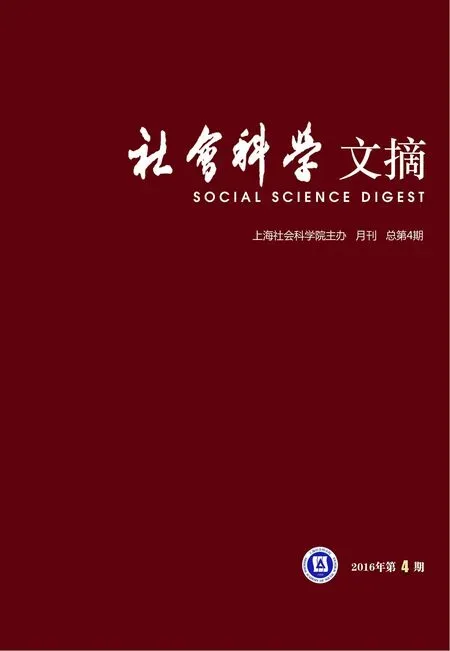性别与革命:近代以来秋瑾形象的转换(1907-1945)
文/夏卫东
性别与革命:近代以来秋瑾形象的转换(1907-1945)
文/夏卫东
秋瑾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人物。她的政治形象在近代先后经历了“男女革命”、“革命先烈”、“女革命家”等三个阶段;这种形象转换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民族战争密切相关,早期往往只强调她其中一个侧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的女权主义思想被替换为男女爱国平等,革命思想被替换为积极抗战,两种改造过后的思想第一次统一到“秋瑾形象”之中,成为当时国民党领导妇运的精神象征。
“男女革命”的悲剧人物
“秋案”发生以后,秋瑾的形象是女权主义运动倡导者,遭当地官府冤杀的无辜受害者。秋瑾死后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为秋瑾鸣冤喊屈的声音,认为秋瑾并非是革命党,只是兴办新学的知识分子而已;秋瑾的“革命”是“男女革命”,追求妇女独立,并非是旨在推翻清政府的“种族革命”。这种解释与事实还是有相当大的出入。不过,秋瑾以女性解放倡导者的形象出现,与晚清社会环境、政治局势变迁是密切相关的。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学在中国广泛传播,民权主义裹挟着女权主义开始进入国内。女性解放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的一股潮流。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女学归入家族教学法。1906年,清政府明定官制,将女学列入学部职掌。1907年,清政府定女学章程,各省设立女师范及女子小学。秋瑾长期以来主张“男女革命”,倡导女性解放,至少在表面上契合了清政府的“新政”。秋瑾主持的绍兴明道女学在开学之时,绍兴地方官员前往学校致辞,表示地方政府对“兴办女学”这一朝廷政策的支持。其实也是对秋瑾作为“男女革命”社会形象的一种无意识强化。“秋案”发生之后,各种社会传言随之涌现。当时许多人将秋瑾只是定格在“男女革命”的层次,不认同政府将其视为“种族革命”的角色。
之后由于省城常备军在绍兴大肆搜捕各处学堂,使全城人民惊恐,并导致社会舆论迅速脱离对“秋案”本身的关注,开始怀疑地方政府的真实用意。随着对政府批判的深入,部分社会人士对“秋案”处决程序也表示怀疑,社会舆论也再度从质疑地方政府的动机,升华到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催促。在“秋案”的处置上,浙江地方当局做事仓促,秋瑾被捕次日,便被当地官员在轩亭口处决。许多人甚至提出地方政府在“秋案”中的处决程序,还不如义和团时期的拳民;如果政府继续专事杀戳立威,“则立宪之望终虚,而革命亦永无消除之一日”,只有“宣布实行立宪之诏书,消除满汉不平之分界”,才能从源头上消除革命的产生。舆论的关注已经脱离案件本身,成为借机要求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的社会声浪。在晚清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关于秋瑾是否是真正的“革命党人”这一话题已淹没于社会舆论对清政府的话语围攻,很少有人去关心“秋案”事实本身。
浙江地方当局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为了说明案件的真实性,不得不在上海的《申报》上公布了“秋案”的部分材料。在各种舆论的围攻批判之下,社会还是深信秋瑾是被冤杀的,甚至怀疑清政府在《申报》公布的秋瑾口供是伪造的。总之,秋瑾以主张“男女革命”的形象出现在清末,有关“秋案”社会舆论的焦点切换,导致她最终以“被冤杀”的悲剧人物呈现,而其革命党人的真实身份却很少有人去探究。
“革命先烈”的政治形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上海发起举行纪念革命烈士的追悼会。在上海明伦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除了有杨衢云、史坚如、郑承烈、秦力三、蔡蔚之、张沛如等6人的纪念图像外,还加上了秋瑾的纪念图像。在这次纪念活动中,秋瑾正式作为“革命先烈”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中。1912年,湘浙两省“争葬秋瑾”的举动,引发了社会对秋瑾的进一步关注,更是抬高了秋瑾作为“革命先烈”的政治形象。
秋瑾并非是最早牺牲的女革命党人。之所以她能成为“革命先烈”,除了女性的性别优势外,主要还在于她对辛亥革命的实际贡献,以及革命党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加强内部团结的政治需要。秋瑾在绍兴活动期间,接手了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积极在浙江各地发展革命力量。大通学堂是浙江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这也是当时革命党人的普遍认识。秋瑾在同盟会成立以后,便加入同盟会,成为加入该会的第二个浙江人,后又成为光复会成员。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随着革命胜利的形势发展迅速,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原先的意见分歧逐渐公开化。这种政治分歧早在辛亥首义之前就存在,光复会主要领导人陶成章就于1909年发表过《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以陈其美为代表的同盟会势力,还曾与光复会成员关于沪军都督一职发生过激烈争夺。秋瑾既是光复会成员,同时也是同盟会成员,许多浙籍人士加入同盟会多为她的引荐。从这个角度而言,革命党人纪念曾作为光复会主要领导人的秋瑾,客观上亦能缓和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冲突。
作为“革命先烈”秋瑾形象出现,当时的文学作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秋案”发生以后,就有人根据此案的社会轰动效果,马上就推出《徐锡麟》一书,其中就涉及秋瑾的内容。这是秋瑾的事迹第一次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秋瑾作为“革命先烈”在政治上受到各地广泛纪念以后,又出现传播广泛的《斩秋瑾》的带唱半新戏剧。该剧本把秋瑾描绘成为深具革命思想的女子,因徐锡麟案受到牵连而被清政府残酷杀害。《斩秋瑾》充满了浓厚的反满思想,同时也带有明显的形象过渡色彩,延续了清末秋瑾被冤杀的无辜形象,但同时也将秋瑾“男女革命”的主张以及倡导女权主义的个性印记加以消除,仅仅呈现了其革命爱国的人物特征,使其更符合“革命先烈”的政治形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秋瑾的“革命先烈”政治形象再度得到重视。在这一期间,国民党的宣传刊物中多以“革命先烈”宣扬秋瑾。1930年,蔡元培在秋瑾纪念碑记中称秋瑾为“先烈”;国民党中宣部的《革命先烈传记》,就将秋瑾与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十三人收录其中。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转函,要求所属机关购买由上海百代公司灌制大戏唱片《总理伦敦蒙难记》和《秋瑾就义》两种,认为“该片为宣传革命等事项之良好工具”。1935年10 月14日,国民政府正式明令褒扬“先烈秋瑾”。
“女革命家”的妇运形象
在辛亥革命以后及国民党的党史叙述系统中,秋瑾主要是作为“革命先烈”而存在的,性别色彩并不突出;但是在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时期妇女运动中,她更多地是作为“女革命家”形象出现,强调政治与性别的重新结合。
中国国民党成立之初,比较重视妇女运动,曾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分别建立了“妇女部”或“青年妇女部”。1927年,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出于对民众运动的顾忌,曾经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逐渐消沉。到三十年代中期,社会上更是开始宣扬贤妻良母的“妇女回家主义”,复古主义回潮,对新女性的批判日益增长。1935年,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国民党重新加强了妇女运动的领导工作,先是在“社会部”下设“妇女运动委员会”;此后又改组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此领导全国妇女工作。
作为“女革命家”形象出现的秋瑾,就成为了当时国民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最佳政治符号或精神象征。妇女运动与政治活动结合是当时一大特色,全国各地妇运组织的中心工作是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战。当时集中宣传妇运与政治的关系,认为“(中国)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运动相辅相成”,国外的妇女运动只是为了妇女本身的利益,“把国家民族的危机反而淡然视之”;中国的妇女则是意志集中、目标一致,“很纯洁的为了国家民族而奋斗牺牲,没有丝毫自私自利的观点”;并称秋瑾是“中国第一个女革命家”,突出强调秋瑾作为女性的性别。将“妇女运动”与“国家民族”揉合在一起,反映了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一种社会因应。
秋瑾作为革命先烈无疑符合国民党的政治需要;又因她性别的缘故,也是各地妇女值得仿效的对象。秋瑾“对一般人所认为只有杀身之祸的革命事业,毫不畏怯地努力参加”,充分体现了女性在识见、能力方面与男性平等。秋瑾当年主张“男女革命”的女权主义色彩进一步被淡化,取而代之是“女子爱国”的新内涵。同时,作为妇运宣传载体的秋瑾,被注入积极抗战的时代新内涵,“秋瑾假使生在抗战的今天,将是一个能驰骋沙场、挥戈斩敌的英雄好汉了”,纪念秋瑾最好的形式就是以“中华民族解放”来告慰这位“侠骨柔肠的英雄”。
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是叙述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客观地认识历史具有积极的意义。秋瑾的形象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质。这种阶段性质恰恰说明政治因素对历史人物形象塑造起决定性作用,文学作品、社会舆论等在这一过程中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共同将历史人物的形象烙入人们心中。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摘自《民国档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