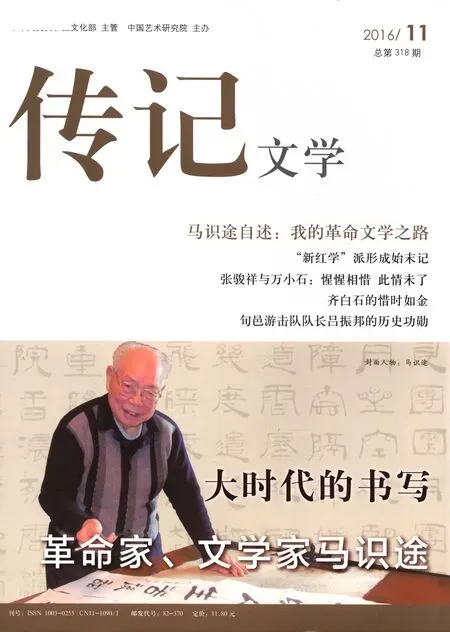传记家的报复
文|〔美〕约翰·豪尔普林 译|杨正润
传记家的报复
文|〔美〕约翰·豪尔普林 译|杨正润
后现代主义发明了“作者死亡”的概念,无视写作行为和作者可能要表达的意义;他们认为,文本的语言只能指涉其他语言和文本,决不能涉及真实的超文本的实体,因此读者、批评家变得比作者也比文本更重要;这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形式,试图摧毁传统的价值观、社会契约和自然法则这样一些概念,拒绝对作者的道德或非道德行为作任何规定。事实上,任何创造性的活动都起源于艺术家和那个时代的汇合,作家写作时总想说出某种特殊的和特定的东西,没有一个作家写作时不参照自我,而一切传记作品必然是缩影,包含着传记家对事实的选择。因此,如今“作者得以复活”,而随着文学批评中纯文本学派日益丧失信誉,历史和传记的方法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回归。由此看来,如果反传记的文学理论最终是由于发现其领袖人物有严重问题的传记事实而被打败,那倒是一种“诗意的正义”,或者说,传记的报复。
后现代;作者死亡;传记价值;作者复活;正义
诗人的一生是他的作品。
——〔美〕田纳西·威廉姆斯
一
米歇尔·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一文里把故事的叙述者从人降低为一个形容词。这位后现代的高级祭司不说作者,只说“作者功能”。他问道:“谁在说有什么意义呢?”他认为作者是“写作游戏中的死人”。
结构主义者,特别是罗兰·巴特,宣称批评的任务并非阐释作品和作者的关系,也不是通过作者的思想和经历分析作品,而只是通过结构分析作品的构建、内在形式及其语言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发明了作者的死亡和消失,避免涉及他或她,无视写作的行为和作者可能要表达的意义。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想象出文本的一般状况,即这一文本分散于其中的空间和它展开的时间。他们跨越了作者既是看不见的也是没有关系的论断,进而试图对作者死亡所留下的空缺加以占领和描述,追随作者的消失所分布的裂缝,寻找他的消失所打开的空洞。
福柯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作者已经停止存在,为什么不把他的名字从作品中完全去掉呢?他说,一封私信、一份契约、一张贴在墙上的无名告示,也许都有一个签名者、一个担保人或一个写作者,但是这些“文本”没有一个有作者。同样的,文学作品也应当看作没有作者。福柯的结论是:全部的作者概念不过是读者造出来的设想。
尽管被宣布死亡,对福柯来说作者仍具有潜在的“重大危险,虚构的东西就以这种危险威胁我们的世界”。他宣布,我们必须“把传统的作者观念完全撤除”。他坚持认为:作者并不“先于”他自己的作品,“它是某种虚构原理”,以此强迫读者限制、排除——最恐怖的是选择意义。福柯说,作者“阻止虚构作品中的自由流动、自由操作,以及自由写作、拆散、改写”。换句话说,作者是一种麻烦,批评家完全可以无视其存在。在福柯看来,一部小说的作者, 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品”或阻挠“添加意义”的角色。承认他的存在减少了批评家希望获得的解释途径。最后福柯预言,作者和全部著作权概念都将消失,这给了批评家一条到达“多义”文本的明确而简单的道路,文本可以“体验”而不必涉及其作者。福柯希望一切文本最终都可以用他所说的“低低咕哝的无名氏”来包括。归根到底,他不想知道“谁在说”,也不想知道作者写的哪一部分表达了他最深刻的自我。福柯问道,既然作者不能说得真实,也不能说得独创,“谁在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解构主义者争辩说,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循环流动的,只能指涉其自身,不能指涉其身外的任何东西。解构主义者想知道,词语到底是指涉事物,还是指涉其他词语,还是指涉这两者?他们说,因为文本的语言只能指涉其他语言和其他文本,决不能涉及什么真实的超文本的实体,从总体来说,作品总是具有多重含义,它们可能相互抵触,互不相容,使“意义”难以确定,最终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他们喜欢的观念。极而言之,文本可以看作它自身多重意义的祭品。阅读文本就是一切,作者和他们实际生产的文本什么也不是。语言不再是一种风气或历史习惯的产物,反而仅仅变成一种隐喻——或者更明白地说,关于诸隐喻的隐喻——最后不但是不可认识的,而且也是无法解释的。读者变得比作者、也比文本更重要,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独自任意解释文本。比如,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①实际上就在某个地方说过:“没有什么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只是一种文本效果。”奥斯卡·王尔德的说法可能更正确一些,他说:“因为(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里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他自己,所以他的戏剧彻底地向我们显示了他,把他的本性和气质向我们展露了出来。”
按照解构主义的说法,语言不能表达任何东西。他们愿意不断向我们举例说明他们的方法。这里就有一个。按照批评家莫瑞·克里格②所说,对于“你看到我的要点了吗”,一个女性主义解构者会认为这句话是用来破坏这位说话者的目的的,因为说的形象里包含了阳物崇拜的象征。我只能假设说一个以击剑为消遣的男同性恋解构主义者会对“你看到我的要点了吗”有另一种解释。毫无疑问,文学批评家的职能是解释普通人同他们自己语言的互动这一过程,而非让人无法理解。你理解我的要点了吗?
按照解构主义者的说法,我们不但不能确定词语的意义,最终我们也不能知道词语是什么。极而言之,解构主义者可以看作是坚持这样的观点:阅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读的是什么。
解构主义者的高级祭司告诉我们,任何作品都可以被解构。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这个僵死体系中的领头大蟒——喜欢解构《独立宣言》作为练习。希利斯·米勒说过,“他说一种语言”是“语言通过他来说”,他解释说《独立宣言》里“我们人民”这个短语“在现实里没有指涉”,因为人民在那个文献中第一次被规定前并不存在。一个悲哀的事实是——解构主义者总是倾向于寻找让人沮丧的事实——“我们人民”这个短语没有在《独立宣言》里出现,而是出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序言”里;如果说这个短语对于米勒教授而言“没有现实指涉”的话,这倒是一个理由。事实上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之前很久,“人民”这一概念就已经存在了。希腊文里“demos”一词就是“人民”的意思,拉丁文里“populus”也是这个意思,事实上“人民”(people)一词就是从此而来。“罗马元老院与罗马人”(SenatusPopulus que Romanus)这样一个短语——缩写是SPQR——写在罗马军旗上,至今仍然在许多意大利古建筑上可以看到,即使对解构主义者来说,读起来也很容易。不过解构主义者对历史不感兴趣,他们喜欢把历史说成是同小说一样讲故事。因此如果在朗福德夫人③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威廉·柯林斯④的《白衣女人》之间,或者在《烹调的乐趣》和《裸体午餐》⑤之间分类,解构主义者会感到不快。
解构主义者对历史事实并不聪明的蔑视还有一个例子:德里达对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叙述所做的叙述。德里达争辩说,柏拉图用了一个希腊词“pharmakos”,这个词既有“治疗”也有“毒药”的意思,这就证明,柏拉图作品的含义根本是“无法确定”的。柏拉图实际上使用的不是“pharmakos”,而是“pharmakon”一词,这个词在柏拉图那里确实“治疗”和“毒药”的意思都有。人们确信,柏拉图和他那个时代的读者,对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同德里达把握得一样好,当柏拉图称苏格拉底喝下的“pharmakon”为毒芹汁时,他们完全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而不必去解构他的语言。我很乐意说一下:“pharmakos”的意思既不是“治疗”,也不是“毒药”,而是“替罪羊”,或是为了治疗人的什么病而向神做的献祭。
对于后现代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雅克·拉康来说,作家不过是一些被哄骗的动物,当他们数小时处于无意识的疯狂时,意象和冲动通过他们偶然地被放进词语之中。
解构主义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形式,它试图摧毁传统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契约和自然法则这样一些概念,以便不必再去对付它们。在德里达之前有生活,在德里达之后也有生活。德里达、福柯、拉康、罗兰·巴特,这些法国人要为很多东西负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已经取得搅乱和抹杀一切类别界限的效果,所以《独立宣言》(确实是《独立宣言》而不是其他什么作品)同《失落园》《大使们》可以用同一种方式阅读,它们否定文学同现实的任何联系,并最终拒绝关于一部作品有好的和坏的解释这种麻烦的看法。
弗里德里克·克鲁斯⑥曾评论过他称之为新“理论主义”的东西。他在《可疑的婚约》中对当代批评有一个出色的评论:我们在过去一代人身上看到的一个主要变化,不是对重大观念不断增长的体会,而是不断增长的先验论,喜好用理论判断来解决问题,甚至连证据都不装着要。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罗纳德·沙蒙克·莱恩⑦的观察:优秀学者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对未加证明的东西()有着习惯性的怀疑,就是说,怀疑在确凿的证据之前就得出假定具有相关性和权威的特殊结论的所有方法,怀疑理论教条或其他总体性的命题。但是在今天,正如克鲁斯所说,我们被一种理论主义所包围:直接依靠那些没有得到证明的理论,不是只把它们只当作研究的工具,而是当作自认为正当的反经验知识。克鲁斯提醒我们,德里达的门徒杰弗里·哈特曼在《拯救文本》一书中承认,他对理论同经验证据之间的联系没有兴趣。克鲁斯指出,哈特曼似乎相信我们的时代里唯一有意义的文学样式是文学批评本身,他还主张在批评家身上培育一种精致的含混。求得明确的文学知识,考察任何一种事实,在他看来正是这种观念要为全国性的危急状态承担责任。
福柯的认识论里排除了事实的概念。他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要求为疯癫说话——准确地说,这是我的看法,后现代主义的莫里亚提教授⑧则说他希望自己的著作是汽油弹,使用过就毁灭。克鲁斯提醒我们,这种暴力的意象就是理论主义的典型,它们和一切极权主义体系一样,都是拒绝信任读者有权向各种观念发出理性的质疑,它要的是征服而不是辩论。许多法国批评家以及他们在美国和英国的门徒,倾向于把希特勒的一位早期支持者、已故的马丁·海德格尔放进解构主义神灵的圈子,这并非一种巧合。毫无疑问,解构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其他观点不能被容忍。1940年至1942年间,保罗·德·曼在比利时为主张纳粹主义的报纸和刊物写作并发表了将近200篇文章,其中许多篇把犹太作家对文学的“污染”当作主题。他的许多反犹文章中有一篇晚期作品现已无人提及,其中宣称犹太作家都很平庸,把他们全部赶走也无损欧洲文化。“豹子变不了斑点”,德·曼在文中说。“犹太人属于亚洲,他们对于接受他们的民族是一种威胁,应当被赶走。”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希特勒主义”许诺“对发现自己被号召在欧洲实行霸权的人实施最终的解放”。大卫·雷曼⑨写过,解构主义(德·曼是其中的大执事长)总是干扰那些明确地高度评价人文主义的人,因为解构主义拒绝在文学中对道德行为,或是对作者的道德或非道德行为作任何规定。正如雷曼所说,如果反传记的文学理论最终是由于发现其领袖人物有严重问题的传记事实而被打败,那倒是一种诗意的正义。德·曼,这位政治学上的法西斯主义者、后现代主义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⑩,在解构主义中发现了对艺术的一种抚慰式的、非道德的、反人文主义的方法,这符合他的气质,事实上也代表了多数解构主义评论的特征。
1980年,法国结构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勒死了他的妻子,他被判定没有接受审判的精神能力。我忍不住怀疑今天他有多少门徒能够通过同样的测试。如同福柯理想的批评家那样,理论家们在用尽能力之后,倾向于自我毁灭。他们中有些人进入其他时髦的思想派别,有些人则被监禁以实行社会保护。我在考虑,阿尔都塞杀死妻子的同时,又在雅克·拉康的手中接受精神分析,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吗?拉康只允许他的病人每次来访限定在5分钟;阿尔都塞显然需要更多时间。难道整整一代批评家都走向了疯狂?后现代主义在消灭意义和身份的愿望中,只关心他们会引起的爆炸:记住福柯的汽油弹。当代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确实让我们想起了一位匈牙利谋杀犯兹尔韦茨特·马图斯卡⑪,他只有看到列车相撞时才会体验到性兴奋,只有在造成戏剧般的铁路灾难时才会激起性欲。
二
对我来说,所关心的是为批评职业进行辩护,这种关注有时能使批评家为他的同时代人做出一种贡献,即在对文学名著进行阐明的问题上,不是去研究文本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去研究历史和传记背景,文本正是在这种背景中生成,它的本质也被这种背景所决定:简单地说就是研究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能帮助我们懂得我们在阅读什么的,是承认文学同它写作的那个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它被那个时刻塑造成型,两者都是必然发生的和可以理解的,两者都是“决定性的”并可以解释的。
我对这类批评不感兴趣,据说它要告诉我们文本是用一些什么东西构成的,但却不打算解释为什么用那种方式构成。对我而言,任何创造性的活动都显示出它起源于艺术家和那个时代的汇合。当文本被聪明而又沉闷地解构成它们的组成部分,并显示出这些部分相互联系起来的途径时,这种自我限制的批评方法以其虚无主义、最后是完全不分是非而使我震惊。后现代主义者对待文学同物理学家对待粒子的方法是一样的:把它当作毫无生气的东西来观察。后现代批评家对文学是什么、甚至对文学在说什么都不感兴趣,唯一感兴趣的只是它看起来如何。他有一个仆役总管的灵魂。
我认为语言总是有目的地使用的,即是说,作家写作时是想说出某种特殊的和特定的东西。作者总是在表达什么。语言没有说,是人在说。文本的意思就是作者的意思,而不是评论家的意思,它可以同读者分享。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那又为什么阅读呢?评论家的工作是,也始终是寻找作者的意思,而不是为了找到作者忘了告诉我们的意思而绞尽脑汁。解释学的虚无主义者相信,正如德里达所说,白纸黑字构成了文本,意义却永远“没有”,对于他们的罪过,我称之为荒诞主义者的恐怖主义。更应当注意的是,这些人还犯下了一个巨大的背叛罪:当他们急急忙忙解构意义的时候,他们取消的不仅是阅读的快乐,而且是同人文主义相关的东西,以及我们对生活的人文主义研究。
让我们进一步考虑一下意义的问题。意义总是难以接近或无法揭示的吗?不同的批评家在同一个作品中可以发现不同的意义,可是这些意义也可以相互包容:就是说,各种阐释或者解读虽然可能互不相同,但看来也都有道理(因此是“正确的”),因为在某方面,它可以被我们理解这一文本的方式所支持。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仍然必须是尝试着告诉我们文学的意思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就不可避免地一次次回到作者而不是读者,因为作者是意义最重要、最持久、最可靠的源泉。因为它存在于作者的人格和作者的观点之中,形成它的力量并不总是不能发现,意义的钥匙可以找到;然而每一个读者,正如后现代主义承认和证明的,却把他自己高度个性化的观察方法带到了文本之中。当“意义”可以被定位时,应该是在作者而不是批评家身上发现。批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弗里德里克·克鲁斯通过聚焦于读者与文本的冲突、这被批评家视为要着重解决的论题,提醒我们,后现代主义者企图把文学批评变为某种完全主观的东西和手淫;对他们来说,意义如果还存在的话,并不是存在于文本,而是存在于评论家自身,由他所使用的批评方法显示出来。这样批评变成了它自己的目的,不是作者也不是文本,而是批评家自己成了批评的焦点和主体。意义被视为属于评论家而不是属于作者。其实质就是,批评家变成了作者。作者的位置被评论家所霸占,他用这种方法让作者似乎消失了。在此批评体系中,批评家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意义的唯一源泉,它宣称,意义在此体系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存在。正如克鲁斯所说,后现代主义者的罪过不仅是谋杀了作者,他们还企图自己占据作者的位置。他们是文学批评中的克劳迪斯⑫。批评家要求我们研究他们和他们做了些什么,而不去研究作者和作者做了些什么,不去研究文本和文本实际上说了些什么。文学由此迷失于对批评家及其批评方法要义的探寻之中。批评家变成了他自己的主题,作者死亡了,在大学课程设置中,文学理论课取代了文学课。
读者反应批评的大祭师斯坦利·费什⑬也许是这个将死的体系最臭名昭著的执业者。他曾经说过,文学批评中的客观性被取消后,不再要求批评家一定要正确,但要求他富有趣味性。在《为罪恶所震惊》中,费什教授宣称,弥尔顿希望我们误读他那舒缓而精美的诗句,并在我们费力地、一节一节往下读的时候过早形成结论,他就能不断地让我们感到惊奇,以此提醒我们处在堕落的状态。如果这真是弥尔顿的目的,就如同克鲁斯在《可疑的婚约》中所说,真正让人惊奇的是300年来居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后却由一个读者发现了。
对于解构主义者提出的文学系是不是应该存在的问题,我不是太关心;我更在乎他们许多人的一个假设:没有文学这样的东西,而且由于无法用他们的术语得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关于文学的定义,因此就无需存在这种正式的机制,它能在学习文学的过程中给许多人带来乐趣和享受。当然,说没有文学这样的东西那是胡说八道,不如说没有后现代主义更适合。人们会回想起普鲁斯特说过的话:唯美主义注定的命运是以吃掉自己的尾巴结束。在《追忆似水年华》靠近结尾的时候他继续评论道,好像同这里说的有特殊的关联:
许多人缺少审美感,许多家伙身上缺乏……顺从现实的能力……他们也许有能力阐释艺术理论,直到被命运打断……他们愿意相信文学是一种智力游戏,将来会被逐步淘汰。对我来说,他们的文学“理论”清晰地表明了那些赞成它们的家伙的自卑感……真正的艺术不是用作宣言的,它在沉默中完成工作。而且,那些制造理论的人……翻来覆去用一些词语,与被他们称为笨蛋的人所用的词语很奇怪地相似。
三
无视作者,似乎其作品从无到有的生产过程同他无关,似乎每当他拿起笔的时候,艺术创造的疯狂就向他袭来,他就进入拉康说的昏迷状态,文字就以某种方式落到纸上,似乎真如魔术一般,这种观点实在是幼稚。这样的观点透露出对艺术家实际功能的无知。我们怎么能把舞蹈家同舞蹈分开?一切艺术家,甚至坏艺术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无论他们所做的是不是他们想做的、原来打算做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脱离历史时代和个性的外壳,即使他想脱离也不可能,他的创造力正是源自于此。后现代主义者实行的文学批评,大部分变成了自传体,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另一类小说虚构——一种编造的东西、一种没有规则的游戏,但是艺术的历史和传记特性则被故意排除了。
作者是什么、作者想什么,文本就是它们的产物;无论是不是意识到,没有一个作家写作时不参照自我。没有一个作家能生活在他的时代之外。只要我们前面放一本他的书,作者怎么可能就死了呢?照福柯所说,把他的名字从封面上去掉,也改变不了什么。我注意到,福柯和他的同党丝毫没有把自己的名字从作品封面上去掉的意思,当他们写作的时候,“谁在说”显然很重要。
已故的理查德·艾尔曼教授在他的《乔伊斯传》中写道:
艺术家的生活——同其他人生活的不同在于,当生活中的事件要求他注意的时候,就成为艺术的源泉。他不是让过去一天天倒流,陷入含糊不清的回忆,而是重新形成这些体验,正如这些体验曾经形成过他。他既是奴隶同时也是解放者。反过来说,重新形成生活体验的过程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如同起床和睡觉一般成为每天重复的事。传记家在每一时刻都必须估量艺术家对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的参与。
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必须研究艺术家,才能了解他的作品。
我并不是想说传记可以成为一门精密科学,总是纯粹的事实。在此有必要作出免责声明:传记作品的好或坏与书写它们的作者是一样的。一部传记,同其他任何文字作品一样,必然有部分的自传性。柯勒律治在他的《笔记》里说:“当一个人试图描述另一个人的性格时,他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是有一件事他总是成功的:描述他自己”。事实上托马斯·哈代试写过自己的传记,签上他第二位妻子的名字作为作者——而他一死,这位妻子就把书中有利于第一位哈代夫人的东西全部删除了。哈代生平的各种版本都是由哈代先生和夫人这个写作组制作出来的,他们写了有趣的小说片段,但是很难说是传记。奥斯卡·王尔德宣称:“只有人们相信的画像才是画像,那里模特儿很少,艺术家很多。”里顿·斯特拉奇着手写《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时就贴切地遵从了这个公式,书中大多是斯特拉奇自己对祖父那代人的态度,却同他所写的四位传主的真相很少相似。斯特拉奇作为剑桥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并无出色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作品是他用来对大学主考官的一种报复,因为他们只给了他历史学的二等荣誉学位。
埃勒·B·奈德尔⑭的《传记:虚构、事实和形式》对传记的科学性作出了出色的评论,他就这样认为:大多数传记家懂得,事实本身不足以写成一部可信的传记——在他们叙述传记家的故事时,事实可能被调整、选择、删节、遗忘。当事实同他们对传主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坏传记家就会改动或消除事实:我想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米歇尔·米尔盖特⑮的哈代传记。好的传记家对于他选来介绍给读者的事实,会尽力保证其准确、可靠和恰当。“选择”在这里是个适合的字眼,因为一切传记作品必然是缩影,包含着传记家对事实的选择。在传记家和他的传主之间,用王尔德的术语说,艺术家和模特儿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关系:友好或不友好,很少是中立的。
传记家同传主之间的认定和互动,如奈德尔教授所说,可以发生在几个层次中的任何一个。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历史层次;如果传记家实际上认识传主——比如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夏绿蒂·勃朗特⑯——就不可避免地在叙述中包含了自己的观点。传记家发现自己的叙述必然会遇到干扰,她通常是宁愿这不可能发生,因此对任何一位想当传记家的人来说,服从我称之为“死者较好”的原则,是最安全的。正如普鲁斯特所说:“总的说来……最聪明的事是跟随已死的作家……一个死了的作家可以很出色而没有任何脾气。”距离使人更容易做到客观。哈代当然不可能真实地写出他自己;斯特拉奇当然不可能没有偏见地写他厌恶的那一代人。弗吉尼亚·伍尔夫亲身感知的罗吉·弗赖伊⑰的个性,同对他生平事实的研究产生了矛盾,这妨害了她,正如奈德尔告诉我们的,她为这位朋友兼导师写出了一部呆板、僵硬的传记。她在自己的《日记》里曾这样抱怨:“怎么才能摆脱那些同我的理论相矛盾的事实呢?”
承认传记可能既是创造的,又是自传性的,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必定始终是不可信的,其中的虚构并不比解构主义者评论的少?传记家必然在他的作品里出现,这同小说家会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一样无可否认,这是不是破坏了传记的可靠性?传记是否无法同小说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者拒绝在文学类型之间做出区分,不想弄清楚“谁在说”,他们是正确的吗?《烹调的快乐》和《裸体午餐》归根结底是同样的书吗?
如果传记家配得上他的职业,那么答案必定始终是“不”。奈德尔教授发现,传记家意识到了他们所写作的人生的杂乱性质和形式的不完美;任何人的生活都必定如此,传记家中最优秀的那些人会从混乱中找出某种秩序和完整。传记家的前面有一捆书信:他应当引用哪一封呢?他选择了一封信,应当引用其中哪一部分呢?“好”的传记家会做出尽可能客观的选择,而不是做宣传和为自己服务。“坏”的传记家知道,只要有足够的删节,任何事情都可以得到证明,他从私人信件中只引用他希望读者看到的东西。
乔治·D·派因特尔⑱在他的《普鲁斯特传》中宣称:“传记家的任务是……发现艺术家日常面具下面的客观生活与秘密生活,他正是从中提炼出了自己的作品;显示他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平淡无奇的人物和地点中是怎样发现隐含的、普遍的意义的,而这正是其作品的主题;展示他的日常存在和他作为一个创造者隐秘的内心生活之间的对比和互动的戏剧性。”我们看到,理查德·艾尔曼在其《乔伊斯传》里说过几乎差不多的东西。人们对传记的标准决不能不现实地高。奈德尔在《传记:虚构、事实和形式》中提醒我们:传记的读者应当尽量记住,他面对的是写下的、而不是实际的人生,文学作品不可能是人生权威的或完全精确的记录,因为传记家总是在被迫做出选择——他有时做出好的选择,有时做出坏的选择,同其他文类的作家相比这种情况并不更少。在任何传记中,我们决不可能避开传记家的出现,正如我们在小说中避不开小说家。这是必然的,正如要理解一部小说、一幅画或一首交响曲,途径在于通过理解制作它的人,也要通过试图理解它的人。这些人当中的第一位就是制作它的人、就是艺术家,而后现代主义者最希望摆脱的就是他们。历史学家和传记家都知道,对模特儿和艺术家两者的评估必然是对作品本身评价的组成部分,也是对有关批评的质量评价的组成部分。奈德尔教授无疑说的很对,传记家如果失败了,应当责怪他自己运用传记方法的错误、他的才能和敏感度不足,而不是责怪方法本身。
尽管传记难免犯错,但我认为,对作家笔下可能的意义,同后现代主义者的方法相比,这是更可靠的途径,因为后现代主义者谈论读者同文本关系的时候不考虑作者,他们是在写自传。批评如果主要是关于自己,当然它就难以发现自己之外的意义——比如作品里的意义,更别说生活了。好的历史学家/传记家懂得过多的主观性会引起的问题,并且试图避免或尽量减少。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文本中既然不能发现客观真实或意义,他们就不再去寻找它,而是通过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精神来四处闲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那么不可思议,同时又那么迟钝。
四
很显然,我的兴趣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取消的对象——或者用他们喜欢的说法:省略的对象,即始终与我们读者在一起的:作者。作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了临时性的死亡,90年代得到重生。只要看一看这个年代公众对传记、自传、日记、书信、笔记的兴趣的爆发,就可以看到作者重新复活了。在90年代,通过不同形式呈现的历史比其他文类更多地被阅读。
后现代主义者无视作者,假设他或她并不在场,比如说,小说是客观的戏剧化作品,却不知道什么人写成,他不一定是在讲一个故事,而只是在写同墙上的海报或法律契约难以区分的某种东西,后现代主义者不但把批评这种职业歪曲得面目全非,他们还力图取消阅读的巨大快乐之一:认识作者的快乐。为什么人们一旦读过一位特定作家的作品,常常会一部一部地继续下去呢?答案很清楚,就因为他的书与众不同,它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享受。我们寻找某些作者、而不是其他人的作品,并不主要是因为作品本身,更多的是因为封面上的姓名——这个正是福柯要删除的东西。当某人走进一家书店,询问最新的厄普代克或勒卡雷的作品,或者问还有没有特罗洛普的其他平装本小说时⑲,他当然是在找作者,其品质是已知的,他不找文本,因为直到实际阅读之前,文本对他来说是未知数,他只能通过封面上那位作者的其他作品间接了解;人们不会那么急切地期待着新的评论。读者打开一本书之所以能读到底,是因为欣赏作者的其他书。归根结底这就是绝大部分人阅读、再阅读的方式。没有一个为了快乐而阅读的人,会去寻找墙上最新的海报或最新的法律契约,或是解构主义最新的评论。讨论一部小说而不讨论其作者,那就是删除掉了一个人阅读小说的经验中最关键的方面:小说家的个性。
正如韦恩·布斯在其《小说修辞学》里说过的,读者知道,他也必须知道,他是被某个人告知一个故事。是作者决定了写谁、写什么、怎样讲他的故事,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决定了读者可能作出反应的方式。这样我们就得出了关于所有小说的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它们是一个隐含的作者所讲述的,这个作者又是被传记作者所创造的,他必然是小说阅读经验的形式部分。你不可能在讨论形式的时候不讨论作者。
在书信、日记、笔记中,在任何有意识的自传形式中,作者必定有某些隐瞒,一部自传可能有歪曲,事实可能被修改或省略。但是小说毕竟不会说谎;它从总体上展示写作者。康拉德完全懂得这一点。“一位想象性散文的作者——会在作品中被认出”,这是他在《个人记录》(1912)中说的,“他就站在那里,这是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在各种想象性事物、事件和人物中唯一真实的东西。他写他们,只是写自己——确实如此,任何人把笔落在纸上的时候——除自身之外无可言说。”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王尔德告诉我们:“一个人谈论自己的时候最不真实。给他一个面具,他就会告诉你真相。”塞缪尔·巴特勒⑳在《众生之路》中欣然宣称:“任何人的工作,无论是文学、音乐、图画、建筑或其他任何东西,总是在给自己画像,他越是试图隐藏自己,他的性格就越是清楚地显示出来。”
一切虚构都来自作家的意识,因此也总是以意识理解的方式形成。这样来看,小说家也许是唯一说真话的人。而且,作家的观念和意识必然深深卷入他的文化所共有的假设中,即使他拒绝。王尔德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生活模仿艺术而不是相反,这反映了他的理解,即艺术始终是艺术家的产品,反映了他的个性。
萨默塞特·毛姆在其《十部小说及其作者》里告诉我们,小说家总是听任他的偏爱。主人公是他选择的,人物也是他虚构的,他的偏爱决定了他对他们的态度。“无论他写的是什么,都是他个性的表达,这是他天生的本能、他的感情和他的经验的显示。不管他多么地努力要客观,他仍然是他的气质的奴隶。”不管他多么地努力要公平,他还是免不了偏袒。如果我们问,一位作家的创造性本能必须同什么结合起来,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答案必然是:个性。作家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观察事物。即使最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也不只是“抄袭”生活:无论生活怎样,他都要进行调整以适应他的目的。一位男人或女人,虽然写出一部伟大作品,但还是一位男人或女人。毛姆写道:“有人说著名(作家)的缺点应当忽略,我不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我认为知道这些(缺点)比较好。这样我们虽然意识到自己也有那些显著的缺陷,但也相信这并不妨碍我们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就。”
毛姆认为传记能够作为一种伟大的工具,就如乔治·艾略特或特罗洛普的小说,用以实现维多利亚时代人所说的“道德现实主义”,我倾向于同意毛姆所说的。亨利·詹姆斯实际上把他的小说看做传记,如同“真实的”男人和女人们的“真实的历史”。我们知道,贝多芬有着令人讨厌的性格,这并不减少我们对他音乐的欣赏;相反,这可以教导我们,某些人和我们一样,虽有缺点——或许正因为有缺点,也能取得某种成功。这样对于更多的读者,传记可以使艺术更容易接受、更容易理解。
毛姆在《总结》中说过,他写作那些东西是为了心灵的解放。“如果艺术家是一位小说家,他用人们在各种地方的经历,自我的忧虑、爱和恨,最深刻的思想,曾经有过的爱好,在一部接一部的作品中描绘出一幅生活的图画。这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他诚实的话,最后他必定也要做另外一件事:给自己画一幅图像。”
托马斯·哈代把艺术界定为艺术家所认知的事物的模式。正如画家以他的画笔和色彩思考,小说家以他的故事和人物思考,艺术家对生活的观点和他的个性,虽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以一系列创造出来的人物行动而存在。
如毛姆所说,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一部传记出版以后,人们发现了艺术家的生活和他的作品之间的矛盾,有时会感到愤怒。对于贝多芬的理想主义同他精神的卑贱、瓦格纳的天才同他的自私和不诚实、塞万提斯的道德缺陷同他的温情和宽宏、简·奥斯汀的出色才智同她的冷酷和恶意、哈代的伟大诗艺同他的极端自私和虚伪、狄更斯的喜剧天才同他对人的绝对狠毒、丁尼生的公德纯正同他的私德败坏:人们很难把它们协调起来。人们有时在事后消失的气愤中会试图说服自己:这类男男女女的作品不可能具有他们曾经想过的价值。当这样一些东西引起他们的注意时:伟大诗人留下一大堆淫荡的诗句;家庭美德的颂扬者诸如考文垂·巴特摩尔㉑收集色情作品;看似纯真的小说家伊迪丝·华顿㉒屈从于乱伦的幻想,这时人们受到了惊吓。他们会有一种心神不定的感觉,好像整个生活是个骗局,或者谴责他们的偶像是骗子,或者责怪传记家不该多管闲事。但是正如毛姆在《十部小说及其作者》里所说,艺术家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创造出许多人,也许衡量他是否伟大的一个尺度是看他的作品里包含多少个自我。当一位作家塑造出一个无法让人信服的人物时,通常是因为那个人物没有他自己身上的东西,他只得退回去观察或研究,所以他是描述而非生产出这个人。
五
没有不受历史影响的东西。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时刻之中,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偏见、我们的观念,都必然是那个历史时刻和社会历史所积累的智慧的产物,也必然是我们特有的精神的产物。一个男人或女人,无论选择做什么,其中必然可以找到两个原因:个性和历史时刻。个性和历史时刻允许和鼓励对某种情境做出某种反应,同时也阻止另外一些;一个人的行为被其他人视为恰当或不恰当,取决于当时的价值观和风气。每个时代都从不同的前提做出解释。亚历山大大帝被某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是邪恶的野蛮人;在他的时代采用必要的手段获得尽可能多的土地,则是衡量一个伟大君王的主要尺度。每个人都应该用他自己时代的标准来判断。我们不可能不被环境所限定;因此我们越是研究历史,我们就越可能对死者的行为作出聪明的评价。
历史常常作为现时的镜子来研究,在这镜子里可以反映出过去的意义,也可能看到将来的进程。人们还可以为同样的理由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生活的外部标识——我们的住房、书籍、我们的通讯手段和旅游——这些东西可能改变,但是我们的本性仍然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力量所限定。这始终是正确的。被作用的东西总是在变化,这是受到作用的直接结果;人类的本性自身就是历史的产品,也可以进行同样的研究。我所说的历史,不仅是指编年的记录,也是风气的历史、价值观的历史,尤其是观念的历史。
这些日子,我们对社会史和知识史的研究似乎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对文学个性的兴趣不是减弱而是增强。我们决不能忘记:一切艺术作品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心灵的产物,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获得研究它的工具,这个心灵就能够被研究;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去研究,这个心灵存在的时代就能够被研究;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评价,这个时代对心灵的影响就能够被评价。我想,我们这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人中有一些已经忘掉怎样去做这些事。
随着文学批评中的纯文本学派日益丧失信誉,文学的历史和传记的方法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各种各样的回归。德里达相信写作中没有在场、没有历史、没有原因,它同任何东西无关,它没有主体、没有主题、没有目的。但是这种写作如果存在的话,那只是胡言乱语,一片没有一个人物的土地,没有一页文本的空白。难怪今天残留下来的解构主义大都以拙劣的自我模仿的形式存在。要解构某件东西就去杀死它,让它消失,强迫它自杀。所以解构主义的终极目标似乎是艺术的一去不复返。
戴维·洛奇在他的戏剧《压力锅》中描述过一种适合后现代批评的最理想的小说:一个导论,后面跟着250页的空页。洛奇的观点同我的一样:是时候了,把作者和真实的文本——同被解构的文本相反——放到文学研究中去。那么,晚安,雅克!晚安,米歇尔!晚安,罗兰、斯坦利、希利斯、保罗、杰弗里、墨瑞!“如果你找到工作就写吧!”㉓
注释
本文译自《文学传记:问题与对策》(John Halperin, “The Biographer’s Revenge”, in Dale Salwak ed.,The Literary Biograph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p.149-166)。本文的两个不同版本,分别发表在《澳大利亚大学语言文学协会学报》1988年第LXIX期和《传记》1989年第XII期,这里采用的是经过修订的最新版本。内容摘要与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①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1928- ),美国文学批评家,解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代表作有:《理论今昔》《小说与重复》《他者》等。
②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 1923-2000),美国文学批评家,教授。
③朗福德夫人(Lady Longford, 1906-2002),原名伊丽莎白帕克南,后为朗福德伯爵夫人,英国历史学家、传记家,著有《维多利亚女王》《拜伦爵士》等。
④威廉·柯林斯(William Wilkie Collins, 1824-1889),英国侦探小说家,著有《白衣女人》《月亮宝石》等。
⑤《烹调的乐趣》是美国妇女厄玛· S.罗姆鲍尔(Irma S. Rombauer, 1877-1962)写作的一本谈烹调的书,1931年初版,此后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食谱之一,迄今已经发行1800万册以上。《裸体午餐》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威廉·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 1914-1997)的小说,后被改编为电影,风行一时。
⑥弗里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 Crews, 1933- )美国文学批评家,教授。
⑦罗纳德·沙蒙·克莱恩(Ronald Salmon Crane, 1886–1967),美国文学批评家,芝加哥学派的奠基者。
⑧莫利亚提教授是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中的一个虚拟人物,被称之为罪犯中的“拿破仑”,这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⑨大卫·雷曼(David Lehman, 1948- ),美国诗人,主编《美国最佳诗歌》丛书。
⑩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 1918-2007),奥地利外交家,曾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奥地利外长和总统,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奖”。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纳粹的关系被揭露,受到舆论的批评。⑪兹尔韦茨特·马图斯卡(Szilveszter Matuska, 1892-1945),匈牙利匪帮首领、机械工程师,1930年代初期曾在匈牙利、德国和奥地利制造多起火车相撞事故。
⑫克劳迪斯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中杀死兄长篡夺王位的奸雄,即哈姆莱特的叔父。
⑬ 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 1938- )美国文艺批评家、法律学者。
⑭艾拉·B·奈德尔(Ira Bruce Nadel, 1943- )美国传记家、文学批评家、加拿大哥伦比亚-不列颠大学杰出教授。
⑮米歇尔·米尔盖特(Michael Millgate, 1929- )英国文学批评家、传记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语系教授。哈代专家,著有《哈代传记》等有关哈代的论著多种。
⑯ 伊 丽 莎 白· 盖 斯 凯 尔(Gaskell Elizabeth,1810-1865)是19世纪英国的一位女小说家,她为自己的好友、《简·爱》的作者夏绿蒂·勃朗特写了一部《勃朗特传》。
⑰罗吉·弗赖伊(Roger Fry,1866-1934),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美学家、艺术批评家。同伍尔夫是好友,都是布鲁姆斯伯里文社(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他死后,伍尔夫为他写了一部《罗吉·弗赖伊传》。
⑱乔治·D·派因特尔(George D. Painter, 1914-2005),英国传记家,以两卷本的《普鲁斯特》知名。
⑲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 ),美国作家,写作长、短篇小说和诗歌,以《兔子四曲》闻名。勒卡雷(John le Carré)英国小说家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nwell)的笔名,以间谍小说闻名。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英国作家,写有大量长、短篇小说和传记。
⑳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英国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众生之路》在20世纪产生重大影响。
㉑考文垂·巴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 1823-1896),英国诗人、批评家,其代表作叙事诗《家中的天使》描写了理想的、幸福的婚姻。
㉒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美国女作家,出身于纽约上流社会,写作风俗小说,其作品文笔优美。
㉓这是美国著名喜剧演员鲍伯·艾略特(Bob Elliott , 1923- )和莱·古尔丁(Ray Goulding, 1922–1990) 1973年出版的合著之名,书中这句话被不断重复。
责任编辑/于溟跃
约翰·豪尔普林(John Halperin),美国传记家、学者,克莱蒙研究大学教授,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荣誉研究员,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美国会员之一(1984年),两次获得古根海姆奖。主要研究领域:传记,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与文化。著有《乔治时代名人传》(1995)、《小说家的青年时代》(1990)、《简·奥斯丁传》(1984)、《吉辛:书中人生》(1982)等。
- 传记文学的其它文章
- “孤岛”儿女(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