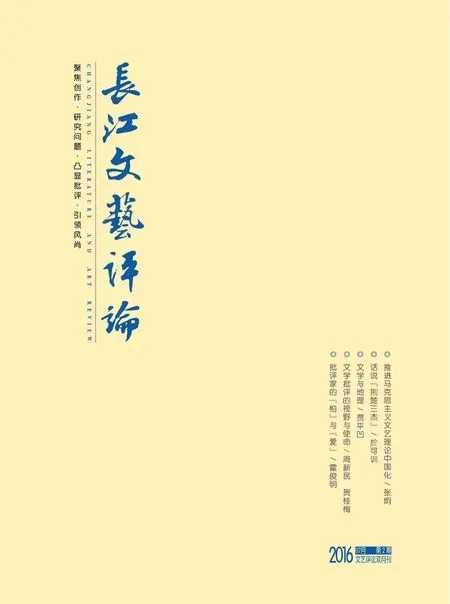“微长篇”与《禾木》
——评张好好的长篇小说
◎ 王春林
“微长篇”与《禾木》
——评张好好的长篇小说
◎ 王春林
我们注意到,70后作家张好好的长篇小说《禾木》在《中国作家》2015年第10期发表时,编者所特别标明的栏目名称竟然是“小长篇”。我不知道《中国作家》的编者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小长篇”这个概念的,又或者,他只是因为这些作品的篇幅体量不够大,灵机一动便想出了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早在《中国作家》的编者提出“小长篇”这一概念之前的若干年里,类似于张好好《禾木》这样的“小长篇”文本在中国文坛就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现象。
其实,《禾木》并不是张好好的第一部“小长篇”,她先于《禾木》完成的另一部作品《布尔津光谱》,严格说来,也同样是一部“小长篇”。而且,二者之间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内在关联。正如同小说标题已经显示出的,这是两部与遥远的新疆边地关系密切的作品。我们都认为小说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与作家的真切人生经验联系紧密的一种文化想象方式,由此来观照张好好,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她小说写作的文化想象方式何以总是会与禾木或布尔津这样的北疆小镇联系在一起。一种可信的结论是,尽管张好好的祖籍为山东牟平,而且现在的居住地又重新回到了内地,但因为出生并在布尔津度过了自己的童少年时期,布尔津反而成为了滋养其小说写作最重要的一种文化想象资源。这样,一旦她试图打开自己的经验之门展开小说叙事的时候,率先进入其艺术视野的,自然也就是她的布尔津生存经验。虽然说张好好初始踏上文坛不久,虽然她的小说写作尚且处于刚刚展开的阶段,但我想做出的一个预言是,不论其小说写作面貌在未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布尔津作为其文学想象的文化资源这一点,却不可能发生变化。张好好此后的小说写作,都将会从布尔津这个北疆小镇出发,会与这座不起眼的小镇发生千丝万缕的各种联系。
除了共同的文化想象资源这一点,《禾木》与《布尔津光谱》也还有书写对象上的某种关联。正如同《布尔津光谱》带有一定的自传性因素一样,《禾木》中自传性因素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文本事实。居于《布尔津光谱》中心的,是一个生活于布尔津的五口之家。其中,父亲海生是个来自于山东的木匠,母亲小凤仙来自四川,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已经成为当地很有名的一个裁缝:“这时候小凤仙已经成为布尔津的资深裁缝。许多哈萨克妇女要穿萨拉凡,便会来到海生家里量体。”不仅如此,关于这一家的三个女儿,作家还暗示性地写到:“再过几年她们会一个一个地离开这里,去遥远的乌鲁木齐甚至更远的地方。那时候我和小白猫,还有绒绒,都不在这里了……”到了《禾木》中,位居文本核心的依然是一个五口之家。祖籍山东的“你们的父亲”同样先是辗转东北,然后来到布尔津。他所赖以谋生的也一样是木匠手艺。而母亲,则开了一家裁缝店:“两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一个熨衣服的案子,她的身后是一个货架,顾客送来的布料塞得满满的。她的生意好极了,她是这座小县城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万元户。”而他们的三个女儿,也都先后离开了布尔津:“反正出去读书就再也不用回来了。你们都这样想。无情地,最终,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由以上的比较即可以看出,《布尔津光谱》与《禾木》最起码在故事原型的层面上有着突出的共同性。尽管我不知道张好好在写作《布尔津光谱》的时候是否就已经有了关于《禾木》的进一步写作设想,但这两部“小长篇”之间存在着书写原型的同构性,却是无可置疑的一个事实。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虽然张好好的两部“小长篇”存在着文化想象资源以及书写原型等方面的共同性,但作家所实际完成的这两个文本之间,却存在着太过明显的差异。鲁迅先生当年谈到陶渊明的时候,曾经特别强调老先生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一面,却也有类乎于荆轲一样的“金刚怒目”一面。我想,这种评价方式某种程度上也完全可以被移用来评价张好好的两部“小长篇”。《布尔津光谱》是一个缓慢的文本,“在张好好的笔下,不论是作为故事核心的海生小凤仙一家,抑或还是他们家周围那些民族肤色不同的邻居,虽然物质生活谈不上丰富,但一种相对贫瘠生存条件下的相濡以沫,一种亲情的温暖与谐和,却是无可置疑的。除了无法回避的死亡之外,出现在张好好笔端的布尔津,可以说是一个无冲突的世界。如此一种无冲突的谐和状态,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世界。”也正因此,我把那个文本归结到了一种“田园叙事”与“方志叙事”兼而有之的叙事传统之中。就其基本叙事节奏而言,《布尔津光谱》毫无疑问是舒缓、松弛而又自然的。这样一部“小长篇”的基本艺术品格,肯定属恬淡一类。但《禾木》却明显属于一种“金刚怒目”式的批判性文本。如果说前者是缓慢的,那么后者就是峻急的,前者的叙事节奏舒缓、松弛而自然,后者的叙事节奏紧张、激烈而对抗。
相对于《布尔津光谱》,《禾木》叙事形式方面最显著的变化约略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你”这样一种第二叙事人称的征用。张好好此举显然并非故意别出心裁。正如同第一人称“我”与第二人称“你”相对应而存在,二者之间有一种突出的彼此参照作用一样,就我个人的理解,张好好的第二人称叙事其实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人称叙事的某种变体,有一种十分突出的自我分身效果。作家对于“你”的征用,显然有着一种拉开距离之后的“我”与“你”甚至包括整个世界之间的潜对话意义。之所以要拉开距离,乃是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自我审视的客观效果。这里,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心理前提即是,不管多么富有理性的智者,在涉及到与自我紧密相关的话题的时候,总是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自我掩饰与自我美化的倾向。张好好之所以要在规避第一人称之后,使用作为其变体的第二人称,其根本意义正是为了能够更加冷静客观地呈现主人公之一“你”的基本生存与精神状态。
其二,是对叙事时空彻底打破后的重组。《布尔津光谱》基本上是一种顺时序的叙事,张好好从海生与小凤仙这两个“盲流”从内地流窜至北疆小镇布尔津落脚写起,一直到后来的结婚生子,到三个女儿的成长过程,乃至关于三个女儿未来命运走向的某种预叙,所遵循的是一种自然的时间顺序。到了《禾木》中,自然时序被彻底打破后,呈现为一种现象层面上的凌乱情形,叙述者的思绪与讲述始终不断地游走于现在与过去之间。“你不知道为什么,年轻时会那样荒唐,那几年断断续续进山三四次,次次的晚饭都要喝醉,及至走到夜色的山谷里,天已经完全黑了。你所要寻觅的——那个人呢?”《禾木》开头第二自然段的这些叙事话语,就奠定了小说的两种叙事基调。首先,尽管全篇并非一味地简单倒叙,而是采用了一种时而现在,时而过去的彼此穿插互嵌式叙事,但从总体上说却保持了一种回望往事的姿态。其次,从“年轻时会那样荒唐”一句,即不难判断出某种“觉今是而昨非”的忏悔式叙事基调的具备。更进一步,如果说《布尔津光谱》的顺时序叙述与整部小说那样一种无冲突的谐和状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那么,《禾木》之所以要打乱叙事时空,进而呈现出一种显豁的时空凌乱感,就与整个文本情节结构堪称紧张激烈的内在矛盾冲突密切相关。
其三,是一种充满内在紧张感的箴言式叙事话语的自觉运用。很可能是与作品那样一种无冲突的谐和状态有关,《布尔津光谱》的叙事话语不仅总体感觉平和、柔软,一点也不张牙舞爪咄咄逼人,而且通篇皆保持了一种平稳正常的语序结构。其中,日常生活气息的渗透与缠绕,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但到了《禾木》中,所有的这些感觉却都已经遭到了根本的颠覆与重构。不仅平和的长句为短促紧张的短句所取代,叙事的节奏与频率明显加快,而且,整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也都完全被打碎切割成零散的93个带有醒目小标题的断片,不断地闪回跳跃,然后被作家根据主体表达的需要而进行重组拼接。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禾木》的叙事话语在拥有日常生活气息的同时,更增加了一种具有形而上思辨色彩的箴言式语句的穿插互嵌。“艾蒿那么高,溪水那么清,木头房子是明黄色的,被亿万只草虫的呐喊包围,月亮在东山升起。那个充满魅惑力却纯洁的少妇的脸,和东山的月亮一样美,仓央嘉措如是说。”如此一个富有诗意色彩的小说开头,在写实性地单刀切入禾木这样一个北疆村落的同时,也象征性地寄寓着张好好对于理想生态世界的艺术性想象。其中,箴言式的段落与话语可谓随处可见。“伟大的事业只能是自己的良心和最终的爱情,还有纯洁这个单词,这个随时能把你掐死的单词。”“他以着天意,向你伸出手,拽你从泥浆里起来。他说,你是怎样的,我就会把你当怎样的人看。”“你们已经知道,每一次都要抉择,选了这一条,命运的终点是一个样子;选了另外一条,就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可怕的,步步惊心。”正因为有着类似箴言式话语的普遍使用,所以我们才断定“小长篇”《禾木》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箴言式写作。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