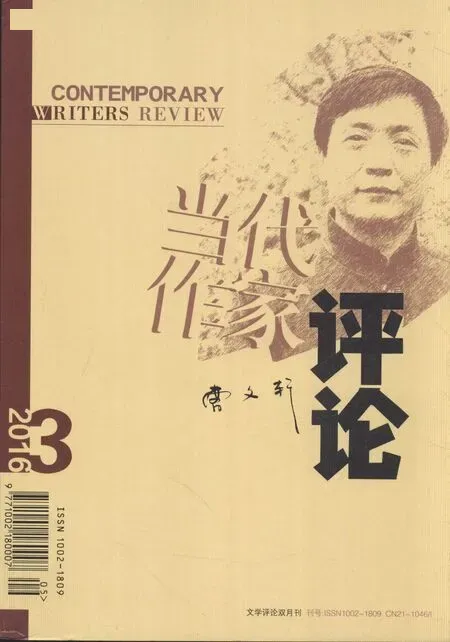冲突:宗教、文化抑或文明
——重读《穆斯林的葬礼》
李晓峰
作家作品评论
冲突:宗教、文化抑或文明
——重读《穆斯林的葬礼》
李晓峰
一九八○——一九九○年代,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张承志的《心灵史》塑造了“中国穆斯林”群像,揭示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部冲突以及穆斯林内部的文化冲突。这些作品在当时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议。在今天,伴随着中亚、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动荡,新疆“暴恐”的升级和扩散,“伊斯兰”、“穆斯林”已然成为社会生活热点和敏感的词汇。上述回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中的不同文明的冲突以及作者们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特殊形态也再一次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玉”与“月”:两种文化的并置、交融与冲突
《穆斯林的葬礼》由“序曲”、“尾声”及十五章组成。包括序“序曲”、“尾声”在内的各章,均有章目标题。“序曲”、“尾声”的设计体现了非常典范的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设计规范。如果我们把“序曲”、“尾声”也看成是两章的话,那么,小说的章目就很有意味。十七章的标题均为二字,分别由以“月”和“玉”作为核心词的主谓结构的词组,交错推进。“序曲”至“尾声”的偶数章节分别为“月梦”、“月冷”、“月清”、“月明”、“月晦”、“月情”、“月恋”、“月落”、“月魂”,共九章;偶数章节标题分别为“玉魔”、“玉殇”、“玉缘”、“玉王”、“玉游”、“玉劫”、“玉归”、“玉别”,共八章。前者构成了一个“月”系列,后者构成了“玉系列”,两个系列呈现出并置、对应并且交叉的结构形态。
这种结构形成在今天看来,实质上是一种隐喻修辞,暗示着两种文化的关系——并置与交融中的冲突、冲突中的交融,也表达着一种宗教和文化观念,即,冲突和交融,构成了伊斯兰宗教(文化)与汉文化内在关系的整体结构形态。
然而,长久以来,人们的关注点仅仅些局限在小说中的“月”和“玉”所隐喻的文化本体意义上,特别是由于缺乏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国玉文化的了解,因而未能揭示二者之间的张力与冲突的结构形态。
例如,有人认为“月”象征了韩新月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徐冰:《悲凄的美学意蕴——赏析〈穆斯林的葬礼〉中‘新月’的意象功能》,《飞天》2009年第1期。吕豪爽:《多情的月亮多重的象征——〈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月亮意象再解读》,《时代文学》2010年第2期。,有人将“月”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诗词艺术相关联,认为“新月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象征着美丽,如‘新月如眉’,让读者从美如新月的娥眉展开联想,想象到她的明眸皓齿。新月又象征希望,如新月如芽,使人联想到它由新月至半月、圆月和残月的无可限量。‘新月’意象与主人公韩新月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其明净、清秀和凄楚的特点与新月的聪慧、美丽与不幸构成异质同构。”*刘凤娟:《〈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概念隐喻研究》,黑龙江大学,2011年硕士研究生论文。也有人将“月”和“玉”看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重要的两大象征物”,同时又认为“在穆斯林世界里,玉是事业的象征、国家文明的象征;‘月’是神性的象征、幸福的象征。但是‘月’与‘玉’的美好意象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却透着无穷无尽的悲剧意蕴。”*李晓玲:《穆斯林的葬礼篇名、章名、人物名和相关语篇叙事的修辞分析》,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研究生论文。张建成则认为“月”与“玉”两条时空线索平行推进又交叉铺叙的对奏式的复式结构。徐其超认为“‘玉’字系统,主要抒写‘博雅’玉器世家第一代、第二代人梁亦清及韩子奇和梁冰玉、梁君璧的社会人生悲剧故事,‘月’字系列主要抒写韩新月以及韩天星的爱情悲剧故事。”*徐其超:《回民族心灵铸造范型——〈穆斯林的葬礼〉价值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马丽蓉认为,“‘月亮’的色、形、质,分别负载了中国回民尚洁、喜白、思乡、念亲与坚忍内隐等独特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月亮’意象便成为回民心象的最恰切的载体”*马丽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第10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等等。
可以说,在对《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月”和“玉”进行的解读中,单纯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伊斯兰文化角度进行的挖掘,或者将“月”和“玉”与小说人物的爱情悲剧进行简单对照,都偏离了小说所要表达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平行并置的外部结构下的“交融中的冲突”以及“冲突中的交融”所产生的彼此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内在张力及其复杂关系。
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均是塞缪尔·享廷顿所划分的人类主要文明中体系的两大重要文明体系,而且是两种各有其生成历史、传统和文化体系以及文化特质的不同文明。
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而言,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月所不能比的。中国的玉文化有八千多年的历史,玉文化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而且也与个人的地位等级、权力层次以及人的道德、情操、人格密切相关。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周代,玉就不仅成为国家官制体系中诸侯等级的标识物,而且还是性别的标志。《周礼·春官·大宗伯》载,周代“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植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浦璧。”《周礼》还依据玉的颜色,来规定祭祀的等级顺序:“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四方、玄璜礼北方。”*吕友仁:《周礼译注》,第24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这样,“六瑞”与“六器”表明玉已经被纳入国家礼制之中,成为权力地位、身份等级的标识物。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后来人们所说的“玉乃国之重器。”、“君子比德于玉”是对玉的在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和道德价值体系中的地位的高度概括。
玉文化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崇玉、佩玉、赏玉、鉴玉、藏玉、玩玉等等,作为一种重要文化事相和传统,无关朝代更迭,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成长。
中国传统器物文化也支持这一观点。从考古发现的上迄于旧石器时代的种类繁多的玉器文物便可见一斑。相同的情形我们在伊斯兰文化史中并未见到。
与玉相比,月文化却没有进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之中,而且也没有明确的对应意义系统的生成。尽管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月的神话传说,《诗经》以及历代文学都有“借月抒怀”的传统,但文学作品中的“月”意象仅仅作为审美对象化和人性化的自然物,或道德、情感的投射物而具有道德和审美意义。“千里共婵娟”是其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模式。而且,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也鲜有关于月崇拜的记载,更没有将其神圣化提升到文化体系的核心层面。所以,玉文化与月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体系性的,一个是非体系性的,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在伊斯兰文化里,如同十字架之于基督教、“卍”字符号和法轮之于佛教,新月则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
《古兰经》里不仅多次记述月亮,而且有些章节就用月亮命名。如第五十四章“盖迈勒(月亮)”,并且还与“太阳”、“星辰”、“黎明”等,构成完成的伊斯兰教的意义体系。其中,新月是指每月第一天初升时的月亮,象征着伊斯兰教的新生力量。一五六六年奥斯曼帝国赛利姆二世在伊斯兰清真寺的穹窿中竖起高三十米的铜制新月,从此,清真寺大都用新月作为伊斯兰教的标志性装饰。现在世界上五十七个穆斯林国家中,有十二个国家的国旗上都有新月的标志。所以,新月在伊斯兰文化中的意义与中国文化(准确说是中国诗词中)中的月亮有本质的区别。
而玉在传统伊斯兰文明中,同样没有上升到文化的最高层,没有进入其文化体系并成为其核心价值的一部分,更没有像月那样成为宗教符号。尽管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朝圣老人吐罗耶定说:“穆斯林与美玉珍宝有缘啊!和阗玉出自新疆、绿松石产于波斯,猫眼石源于锡兰、夜明珠来自叙利亚……”。*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第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这完全是因为是面对雕玉高手梁亦清时,为交流而寻找的“语言”,况且,玉的产地并不能代表出产物在该民族中文化体系中地位,况且,这段说出自中国的穆斯林口中,也代表不了伊斯兰文化。事实也是如此,玉在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正如新月一样。
因此,玉和月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乃至文明。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或者文明相遇时,互动中的彼此接纳、融合、冲突也成为一种正常的、规律性的现象。
霍达在谈及《穆斯林的葬礼》的写作目的时,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她说,此书“写了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的撞击和融合,这种撞击和融合都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延续发展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霍达:《我为什么而写作——〈穆斯林的葬礼〉获奖感言》,《文艺报》1991年4月2日。这无疑告诉了我们破译“月”与“玉”神秘之门的密码。
然而,与塞缪尔·享廷顿所讨论的伊斯兰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冲突不同,《穆斯林的葬礼》所展示的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的“撞击和融合”的地点在中国。
我们知道,无论是最早的波斯商人还是阿拉伯商人,无论是海上香料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无论是以经商名义跋涉而来的移民,还是蒙古后因战争被迫移民到中国西北的大批中亚穆斯林,对中国而言,他们都是异质文化的闯入者。这些穆斯林把伊斯兰文化带入中国,同时也以积极接纳的态度,主动融入中国文化。对此,他们别无选择。
伊斯兰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对中国文化中与伊斯兰教核心教义并不发生冲突和矛盾的那些文化——语言、习俗、制度与器物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语言。无论是波斯语还是阿拉伯语的携带者,他们要想真正生存下来,实现财富梦想,首先要获得与本土中国人交流的工具——接受中国的语言。在此,从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位势上说,穆斯林们的母语是“少数者”的弱势语言。然而,从文化心理上说,主动接受中国汉语,这是一种心理的强势。而且,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主动接纳那些并不与其宗教精神相龃龉的异质的当地文化,才能够生存下来。所以,他们不但要认同当地文化,也不能阻止当地文化也以各种方式融入到穆斯林们的生活和文化之中。再如,从文化的角度说,世界各民族文化总有一些相通的为人类所共有的价值标准,正是这些在今天被称为普适性的文化观念、价值才使不同种族、肤色、国家、民族的人在总体上呈现出“共同发展”的趋向。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的道德理念,恰好契合了伊斯兰对身心清洁的追求。同样,中国人(主要是文人骚客)将月亮纯洁化、圣洁化的审美的诗意想象,也契合了伊斯兰教投射在新月上的圣洁与新生的宗教理念。
所以,在《穆斯林的葬礼》中,穆斯林梁亦清不但完全融入了京城文化,而且因“琢玉高手”成为“奇珍斋”的主人,以琢玉、收玉、藏玉、赏玉、卖玉为生,尤其是他的雕工更是名震京城。“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小说中并没有形成直接冲突,相反,“玉文化”已经成为梁亦清的生存和精神依托。特别是经过了漫长的“融合”,在公共生活中,梁亦清身上已经没有了波斯人或阿拉伯人的任何印迹,这也是中国穆斯林们共同的生命历程。
进一步说,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也许未必是穆斯林们心甘情愿的。而融合也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冲突,有些冲突是显性的,如禁忌等,而有些冲突则是隐性的。
例如,霍达《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新月”以及多次描写到的天空中的“新月”在本质上并不是中国文化中的月,而是伊斯兰教的象征,是对“麦加”这一圣地和真主“穆罕默德”崇拜和信仰的具象化和情感化。小说中新月所说的“我叫新月!就是刚刚升起的月亮……”*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第5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是典型的伊斯兰话语,是中国穆斯林对自己文化(宗教信仰)的坚守和表达。这本身就与中国文化中审美化对象的“月”相龃龉,构成内在张力。所以,中国的穆斯林文化在融入中国文化语境时,并没有迷失自己,并没有象有些民族那样被完全同化。
二、身份建构与禁忌守护
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从蒙元开始,中国的穆斯林不但认同“回回”的他称,而且也乐意以“回回”自称。命名最大的功能是把一个事物同另外一个事物区别开来,这种命名等同于身份认定。因此,回回的命名,从中国非回族身份的角度,区分了本土人与小说中被称为“外来人”回回的身份。其实,穆斯林也有同样的身份区分的诉求。这是隐性冲突的表现也是避免显性冲突的有效方式。所以,回族主动认同“回回”的命名,也借此将自己建构成独立的民族、宗教、文化的共同体。因为,在来源不同的穆斯林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靠伊斯兰的宗教信仰作为认同的标准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他者”(“外来人”)的弱势地位,“穆斯林归顺真主,接受真主通过穆罕默德所晓谕的启示,虔诚祈祷,老实做人,宽厚仁爱,生活简朴,不骄傲自大,不诽谤他人,捍卫信仰,遵循‘逊奈’——圣行,穆罕默德之路。他们相信人生有‘后世’,相信‘末日审判’,每个人的灵魂被接纳进天园或是火狱,一切将由真主判定。他们相信善行必定得到报偿,邪恶必定受到惩罚。”*②③④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第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可见,融合的背后,是以“信仰”的在场和文化主体性身份意识做支撑的。而“回回”这一民族命名,使他们获得了独立的族群身份。
族群身份认同与宗教认同在强化中国穆斯林独立性的同时,也成为文化冲突的根源。
正如小说所讲述的那样:“由于历史上难以避免的融合,回回民族当中也糅进了一些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和犹太人的成分,但回回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存在。而不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②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霍达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也就是说,在霍达的价值标准里,回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融合是生存的需要而被动做出的选择。但被动之中的主体性不但没有缺失,反而得到了加强。
在霍达看来,对于中国的回族而言“真主至大而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穆罕默德,主之使也”③的宗教信仰是回族民族认同的核心价值,这使他们无论“被派遣、被迁徙,甚至被征讨、被杀戮,为了生计,流落四方……尽管他们是少数”,④但真主一直在他们心中,信仰维系和支撑着他们、凝聚着他们。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强化了他们的文化认同,由于宗教信仰总是与宗教禁忌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的回族不与外通婚(融入外族)、不食不洁净的动物等禁忌,成为整个民族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并被严格遵守。在主观和现实性上,这种民族核心价值体系和规范的确立,与其说保护了民族血缘的纯粹性,不如说捍卫了回族的独立性。这样,中国回族的宗教信仰实际已经被转化成民族认同和民族核心价值,成为回族民族主义的重要特征和表现。正因如此,回族成为一个“只进不出”*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亦有回族女嫁入其他民族的个案,但不具有普遍性。的民族。于是,独立性与封闭性是回族文化的一大特点。而在坚守本民族价值观和独立性这一民族主义的基本点上,回族不仅是最坚决的,同时也是最成功的。
然而,对外部与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内部的独立、坚守和封闭,并不能回避文化及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这种坚守和封闭同样代表着对冲突的防范和应对,这本身就是冲突的隐性表现。
小说中的新月是韩子奇与梁冰玉的女儿,本是穆斯林与汉族的混血,但却一直被当成纯洁无瑕的穆斯林的后代名正言顺地纳入到穆斯林的家族谱系,因此她要严格遵守被民族化了的伊斯兰宗教禁忌。尽管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公共社会空间和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新月从未感受到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包括与老师楚雁潮自然而然产生的纯洁的爱情,与世界上所有非功利的、纯粹建立在两情相悦的人性基础之上的爱情并无二致。然而,对新月而言,她与中国大多数的穆斯林一样,是生活在两个文化语境中的人,一是社会多元的公共政治文化语境,他们以学生、商人的公众身份参与社会一切活动。但在家中——一个小的封闭的伊斯兰文化语境中,他们是穆斯林,他们的活动——礼拜,他们的语言——伊斯兰教原始的阿拉伯宗教语言,他们的习俗——清真饮食,等等。
新月之所以没觉得不适,是因为她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两种身份行走于两种环境之间。甚至爱情来临时,她都没有一丝的冲突感和危机感。但她的爱情显然触撞了穆斯林的禁忌。即使是在新月生命垂危之时,梁君璧的态度也没有丝毫改变和妥协。当楚雁潮亲吻了已经死去的新月时,梁君璧仍然仿佛受到了巨大的不可忍受也无法接受的玷污。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以梁君璧强烈的过激反应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此,并非梁君璧不近人情,也并非因新月不是自己亲生女儿而报复。恰恰相反,从伊斯兰宗教禁忌的角度,梁君璧的过激反应恰恰是一种理性的表达,她是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禁忌在替真主卫道。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的巨大冲突就是这样以戕害爱情和人性的形式呈现出冲突的严重性。由此看出,当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价值受到挑战时,它会以主动进攻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实际上,千百年来伊斯兰文化正是以禁忌守护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才保持了自己民族和宗教信仰的纯洁性和民族的独立性。
无独有偶,在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中,尽管这些西北的穆斯林们已经学会用中国西部方言作为交流工具,甚至他们在高兴和悲伤的时候也会像地道的西北汉子们一样唱“小曲”和“花儿”,但是伊斯兰的禁忌在他们心中始终是神圣不可触犯的禁区。这种禁忌是他们避免冲突和自我保护的重要方式。而当这种禁忌受到破坏的时候,文化之间的冲突便会演化成暴力冲突。所以,当生产队强行让他们每家每户都养猪时,暴力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穆斯林们操起了鸟枪、铁叉、斧头和菜刀,与手拿步枪的民兵们发生的武装冲突。结果可想而知:海文的父亲被打死、马存惠受伤被俘(后被判处死缓而保住了性命)。
《穆斯林的儿女们》里的这场冲突比《穆斯林的葬礼》更为直接,而且在一九六○年代被纳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冲突的范畴。但在本质上,却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拉雷恩在谈到文化冲突中身份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权力发挥作用,其中一个文化有着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时尤其如此。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的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形成,或与其他文化有关时,更是如此。”*〔英〕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194-195页,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查舜《穆斯林的儿女们》中的冲突的双方,显然与身份和权力有关,作为穆斯林的生产队长杜石朴在更大的权力掌控者韩维民的“支持”下,“行使”了他所掌握的行政和意识形态合法权力,才把十三队做了“回回人养猪的试点”。在这里,并不是杜石朴有意去背叛伊斯兰教义和禁忌,而是杜石朴作为“队长”的政治身份和这个身份所拥有的权力发挥了“魔杖”作用:一则因为“养猪”的命令来自于“上面”——更强大的政治权力及至国家意志,二则他本人对权力的诉求,而其权力的对象,则是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普通的穆斯林们,二者无论是权力还是文化,在其势力上都是不对称的。因而在“破旧立新,易风易俗”的社会政治语境下,在政治与宗教信仰两种选择中,杜石朴坚定地选择了前者。
这场冲突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结果,一是杜石朴们被认同为穆斯林的叛徒,二是马存惠等底层穆斯林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得到了强化。这一方面说明,在穆斯林的内部,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冲突,也使穆斯林内部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和坚守出现的裂缝和分化,从而导致伊斯兰文化的更大认同危机与信仰危机,并引发民族内部的冲突。
从这一意义上说,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揭示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冲突带给穆斯林们内部的文化认同危机、焦虑和现实冲突。
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所揭示的伊斯兰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对穆斯林们来说也许更加可怕:一直被当成穆斯林并因此继承了梁亦清家业并娶了梁君璧做妻子,同时还与梁冰玉生下了新月的韩子奇,并不是穆斯林。虽然他已经融入到这个家庭里,但他从不做礼拜,他的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异质化的他者”,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什么民族。这当然是霍达心中的“融合”,两种不同文化,无论如何融合,也总有无法融合的部分——那是一个民族文化最坚硬的内核。这一内核如果被融化,民族文化的防线将彻底崩溃。对这一点,霍达既警觉又没有自信,因为,在她看来,异质文化的偷袭与渗透是无所不在、防不胜防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文化乃至其他冲突。
三、当宗教成为一种文化
安东尼·史密斯曾说:“民族主义是将民族作为关注焦点,力求促进民族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对每一个民族而言,它都具有所有成员均能(至少潜在地均能)而非成员均不能分享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独有的思想、行动和交流方法……民族主义者的任务就是重新发现本民族的独特的文化才华,为人民复兴其真正的文化认同。”*〔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9、30页,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无疑,霍达和查舜都将自己的民族作为关注和表达的焦点。无论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还是在伊斯兰内部因为权力、政治诉求所引发的冲突,都是因为是否和如何捍卫伊斯兰文化的纯洁性和民族信仰所引发的,当然也是这种纯洁性和民族信仰受到挑战和危机所引发的。《穆斯林的儿女们》中的杜石朴、韩维民、张佐铭是作为被否定的被政治权力异化了的穆斯林的“叛徒”身份出现的,查舜把自己对伊斯兰文化的纯粹情感投射在这些“不配有好命运”的人身上。对霍达而言,她把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融合与冲突的“痛苦”投射到梁亦清、新月、韩子奇这些好人的悲剧命运上,尽管“我已经舍不得和我的人物分开。当我把他们一个一个送离人间的时候,我被生离死别折磨得痛彻肺腑。心绞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吞药。我甚至担心自己的葬礼先于书中的葬礼而举行。”*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后记》,《穆斯林的葬礼》,第6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然而,所有的悲剧都是为了“新月”不再坠落,为了穆斯林们能够象穆斯林一样的活着。他们的伊斯兰文化在他们心中的那份圣洁、独特是无法被替代的,为了在伊斯兰文化危机四伏的当下,重建伊斯兰文化信心,他们只能以悲剧的形式和文学的方式让回族全体成员意识到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潜在的危机,重新开启民族文化的复兴之门。
霍达说:“我认为应该把宗教当成一种文化,宗教信仰应该是奉献,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只拘泥于形式。”*霍达:《写作让我连死都不怕》引自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11/03/content_1156670.htm“我无意在作品中渲染民族色彩,只是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民族之中,它就必然带着自己的色彩。我无意在作品铺陈某一职业的特点,只是因为主人公从事那样的职业就必然顽强地展示那些特点,我无意借宗教来搞一点‘魔幻’或‘神秘’气氛,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某种气氛之中。……必须真正理解‘历史无情’这四个字。谁也不能改变历史、伪造历史。”*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后记》,《穆斯林的葬礼》,第6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这段话对理解霍达对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以及如何避免冲突、化解冲突的设想非常重要。可以说,在回顾和反思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融合以及其中的悲剧之后,霍达试图为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和化解异质文化间的冲突,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将伊斯兰教的神圣性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表达自己对于这种文化的认同的同时,审视、观察这种文化最核心的内容,诸如信仰的建构对于维系穆斯林文化共同体的作用等等。这一点,也恰如塞缪尔·享廷顿所说:“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美〕塞缪尔·享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4页,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而宗教认同则不一样。因为宗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自愿性、群体性和向内性,不同宗教有不同的宗教教义。两种宗教很难融合,是因为宗教的“殊别主义”总是把自己信仰的宗教视为唯一正当的宗教,通过该宗教的优越感来提高教徒们的信仰度。如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就是因为仅仅把宗教当成了宗教,或者为了宗教而宗教。
从这一角度说,我以为,霍达的理智和高明之处,恰恰就在于她将笔下的冲突转化了一个观察的角度,将宗教上升到一种文化,将不同宗教的冲突纳入到文化冲突的范畴,从而,远离了敏感而极易落入的极端宗教冲突的泥沼,让人们在文化层面来思考宗教问题而不是宗教的本身。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将回族与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区分开来,她思考和展示的是中国回族穆斯林,而不是伊斯兰的全体穆斯林。也就是说,她是站在中国回族的民族立场上揭示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来寻找在中国语境下化解两种冲突的可能性,而不是世界性语境下的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冲突,因此,小说所表达的是霍达特定的文化和民族主义立场,而不是她的宗教立场。
而对于作为文化的宗教,在霍达看来,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信仰的功能,而不是信仰的形式。因为信仰解决了人的心灵归属、寄托和行为的目的性以及原动力。这也正是宗教赖以生存并还将生存下去的原因。
对当今世界特别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危机正是信仰缺失的危机。缺少共同的信仰,民族会分离、国家会解体,人类也将陷入更大的以现实利益为追逐对象的更大的灾难之中。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末日图景。在这一点上,正如霍达所说:“宗教信仰应该是奉献,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只拘泥于形式”,这也与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埃斯波西托与他的合作者达丽亚·莫格海德对伊斯兰所做的调查不谋而合。在约翰·埃斯波西托与达丽亚·莫格海德的《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中,他们指出的:“宗教和文化一直是穆斯林政治和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政治激进派和温和派来说,宗教认同的问题都同样重要。在被问及自身值得称许的是什么时,对此最常见的回答是‘忠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与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相关的最高宣言是‘恪守自己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是进步的关键。’”*〔美〕约翰·埃斯波西托、达丽亚·莫格海德:《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第126页,晏琼英、王宇洁、李维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而安东尼·史密斯在评价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时也指出:“浪漫主义者认为民族就是一种精神原则,一种‘民族的精神’(Volksgeist);并且每个民族都有它的特殊命运与使命,以及它的独特的文化,即‘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被韦伯视为民族主义标记的信仰。”*〔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42页,叶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这里的信仰不是宗教此外,霍达将宗教信仰视为文化,无疑也是想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回族的民族精神秘码:是什么支撑着回族在异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顽强地走到今天,成为一直葆有自己民族个性的民族。
信仰,而是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的忠诚和坚守。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伊斯兰教的独特性,也窥见了中国回族千百年来之所以一直葆有自己民族独立性和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即:正是文化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不是宗教化的伊斯兰教信仰凝聚了回族。既然韩子奇除了不礼拜已经与传统的穆斯林别无二致——不礼拜也是可以接受的;既然伊斯兰禁忌无法阻止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阻止本身是对人类最新圣洁的情感的戗害,这也不是宗教本义所反对的,那么,如何“去宗教”而文化,使不同的宗教信仰回到信仰的本体,去完成其守护美好、守护圣洁的使命,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而至“天下大同”,这恐怕正是霍达的信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当代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思潮研究(1949-2009)”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ZW134〕
(责任编辑王宁)
李晓峰,大连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