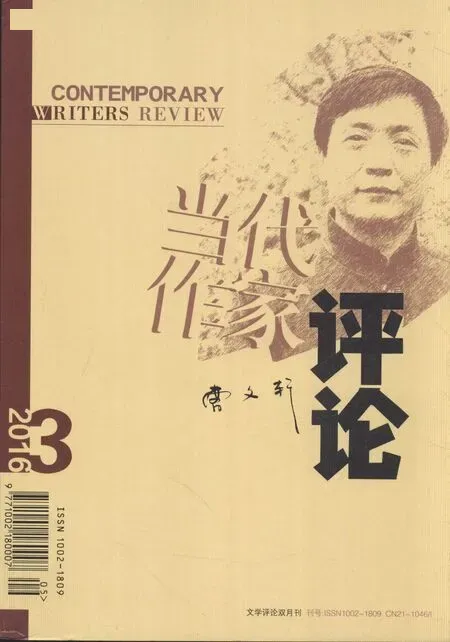儿童视角与审美想象
——曹文轩短篇儿童小说评论
钱淑英
曹文轩研究专辑
儿童视角与审美想象
——曹文轩短篇儿童小说评论
钱淑英
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曹文轩是一个站在高台上的作家,其身份地位和创作影响力,使他备受关注。无论我们对曹文轩的文学创作抱以怎样的态度,都应该承认他代表中国儿童文学高度的事实。因此,在中国文学整体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在童书出版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
论及曹文轩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我们首先会想到他的长篇小说。《草房子》《青铜葵花》《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大王书》等作品,的确代表了曹文轩儿童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准,成为我们探讨其创作特点的主要文本。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长篇写作之前,短篇小说为曹文轩提供了最初的美学准备和艺术蓝图,它们同时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曹文轩短篇儿童小说进行脉络梳理和类型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初期形成的文学理念,进而触及他的写作内核以及可能包含的问题。
一、儿童视角:一种美学策略
实际上,文学的经典性与儿童文学的特性之间并不是无法调和的矛盾关系,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的幻想小说《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就证明了这两者完全可以实现完美融合。但或许正是与其他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刻意强调儿童性却难以抵达文学的经典性不同,曹文轩在将儿童文学特性高高悬置的同时,通过文学性的偏执坚守,使其作品恰恰显示出同时指向儿童与成人的文学感染力。这也是儿童文学发展至今天,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可的儿童文学的理想接受形态。
曹文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国儿童文学界的视野。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说《弓》获得《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之后,他以极大的爆发力创作出了一系列高水准的短篇儿童小说,受到关注。一九八八年,曹文轩以短篇小说《再见了,我的小星星》摘得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显示了他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界的重要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曹文轩并不刻意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性,但他为孩子写作的意识是明确的。曹文轩获奖后接受《文艺报》采访时说:“我的写作选择了儿童视角,它所带来的是特别的美学效果,让我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很不一样。我比较向往诗性,儿童文学、儿童视角能帮我实现、达到我向往的目标,满足我的美学趣味。”*《“站在水边的人无法不干净”》,《文艺报》2016年4月8日。
儿童视角未必一定指向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核。在中国当代成人文学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儿童视角的运用,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这些小说里的儿童,以奇特的方式跨过迈向成人世界的门槛,走进真实而复杂的生命世界。聚焦曹文轩的短篇小说,我们会发现,儿童视角也并非是曹文轩走向儿童文学艺术内核的自觉运用,而只是他实现自身美学目标的一种策略或手段。不过,借助儿童视角,曹文轩在自我表现与儿童接受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由此形成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路径。
通过儿童视角与成人经验互为交织的复调叙事,曹文轩在小说中吟唱着来自童年和生命的诗意歌谣。其中虽然同样夹杂着苦难和忧伤,但他始终用文字维护着精神世界的洁净,玩味着“一种高贵的美学享受——忧郁的甜美或甜美的忧郁”。*汤锐:《印象:一束浪漫主义者的心灵之光》,《暮色笼罩的祠堂》,第6页,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发现当我站在儿童视角,投入到那个语境之中,整个故事的走向就全部改变,而这些故事一旦用成人文学的视角考虑,其中的同情、悲悯等就会全部改变。”*《“站在水边的人无法不干净”》,《文艺报》2016年4月8日。曹文轩的短篇小说,正是经由儿童视角与成人经验的交互结构,实现了对成长和人性的深刻揭示。
二、三种人物关系与结构
当我们从儿童视角出发,细细梳理曹文轩短篇小说的人物关系时,会寻找到一些基本的脉络和结构。作品中的儿童,总是在与他者心灵交集的时刻,打开认知世界的大门。这样的交互,大概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即儿童在与祖辈、父辈、伙伴交往的过程中,通过过去、当下与未来三个维度,显示出迈向成长的精神力量。
1.孩子与老人:在过往的故事里相遇
曹文轩在短篇小说中塑造了诸多老人形象。《第十一根红布条》中用独角牛救活落水孩子的麻子爷爷,《蓝花》里一辈子为人帮哭的银娇奶奶,《蔷薇谷》里独自居住在峡谷的老头儿,《大水》中那个拉手风琴的行乞者,《城边有家小酒店》里用喝酒来化解丧妻之痛的老人……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和境遇,大都是边缘者的角色,内心充满了孤独感。在小说中,作家常常透过孩子的视线,让这些逐渐被人们遗忘的老人,在生命的暮年向人们印证他们不可忽视的生命价值。
比如《蓝花》这篇小说,作者以女孩秋秋的视角讲述了银娇奶奶的一生。秋秋在自己奶奶的回忆里,了解了银娇奶奶的辛酸过往,同时在与银娇奶奶相伴的日子里,体会到了老人内心的苦痛。当银娇奶奶去世后,秋秋在静静的田野上,为她响起了幽远而纯净的哭声。小说最后,当一老一少两个形象交叠在一起,过去和现在互为映照,银娇奶奶令人动容的一生就被笼罩上了一层美好的光晕,在人的心里荡开层层涟漪。
中国南方汉族人群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C677T多态性与脑出血的关系 …………………………………………………………………… 江东东,盛文利,罗曼 10
祖辈的经验、智慧和境界,是应该予以尊重的精神财富,曹文轩在这一类作品中,表现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意识。作品里的孩子,往往是观察者和倾听者,而老人才是潜在的主人公。在很多时候,老人化身为讲故事的人,他们用时光的距离丈量过去的岁月,以平静的语调诉说往事,带给孩子心灵的启悟。
2.孩子与父亲:在当下的目光中交集
在曹文轩的短篇小说中,父亲形象也是十分常见的。通过父亲身上男性气概的彰显或缺失,来激发主人公的男子气概,是曹文轩在以男孩为主人公的作品里常常采用的一种叙事方式。
《金色的茅草》中的青狗在父亲的逼迫下,放下学业,来到海滩割茅草。儿子无法理解这个吝啬、乖戾、暴躁、不近人情的父亲,父子俩常常在荒无人烟的海滩静默地对峙着。直到大火把他们打了三大垛的茅草全部烧光,在父亲歇斯底里后的平静诉说里,青狗才终于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青狗的妈妈跟一个唱戏的走了,父亲曾向她许诺,用三年时间盖出三间茅草屋。然而,他用十一年的时间等待兑现的这个承诺,最终还是被一场大火毁灭了。《野风车》中的二疤眼子,则是在父亲盼望的目光下,实现了对父辈的超越,他用一种近乎原始的野性的力量,征服了狂风中那架孤独傲慢的风车。
而在有的作品里,如《荒原茅屋》《海牛》《叉》等,作家是通过父亲缺席的情境设定,来激发主人公身上的男性气质。主人公之所以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中爆发出力量和意志力,是因为始终有父性目光伴随左右。这种父性目光,或者是来自不在孩子身边的父亲或兄长,或者是作家在文字里所传达的对于男子汉形象的期待,它们与儿童视角相交,带领主人公直面现实的困境,迸发出成长的勇气。
3.孩子与伙伴:在未来的希望里对话
还有一类作品,作家是以更为纯粹的儿童视角来构建童年的世界,让孩子从自我的内心深处生发出抗争的力量,同时通过与伙伴的冲突与和解,经历一场近似于成长仪式的精神洗礼。《埋在雪下的小屋》中的四个孩子在灾难面前,凭借强大的生存本能,逃脱险境,其中的两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化解了家庭间的怨结。《甜橙树》通过主人公弯桥讲述的四个梦境,指引孩子们实现顿悟,最终以游戏的方式消除恶作剧后的尴尬与不安。
不过,即使在纯粹的孩童视角中,依然交织着成人的视线。有时,曹文轩甚至将儿童放置复杂的人性网络,让他们在黑暗中艰难地寻找希望。《阿雏》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提起这个作品时,曹文轩说:“从头到尾我都在想改变成年人的世界,想让那个世界恶更少,善更多一些。”*曹文轩:《曹文轩如是说——在日本NHK教育电视台〈现代问题·来自亚洲的发言〉节目中的讲话》,《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第105页,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8。
善终于战胜恶,这是儿童文学追求的普遍原则。然而,儿童改变成人世界的希望是无比微弱的,如同曹文轩在《红葫芦》中所描写的那样。尽管破除旧有的道德体系是如此艰难,但曹文轩的短篇小说却通过孩子的视角,向我们揭示了构建理想社会的意义,这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愿望。
三、眺望式的审美想象与缺失
以上基于儿童视角所划分的三种主要人物关系类型,自然无法完全涵盖曹文轩所有短篇小说的创作形态。*比如《再见了,我的小星星》《白栅栏》《泥鳅》等作品所表现的姐弟情感,就难以纳入以上三种类型,而这也是曹文轩短篇小说值得研究的一种叙事模式,可以对此进行单独讨论。不过,它们作为基本的结构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曹文轩所说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这一创作理念。
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评价曹文轩的创作时,称他“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原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曹文轩的短篇小说,尤其着力于儿童成长瞬间的艺术描摹。无论是与孤独老人的默默相伴,父辈引领下的现实抗争,还是伙伴之间的心灵交流,在生命交集的时刻,我们都能看到人性激荡的美丽光芒。与此同时,曹文轩常常借助色彩、声音等象征性意象,强化灵魂交互形成的精神力量。蓝花、红葫芦、白栅栏、金色的茅草,寂静的山谷里、田野上、河水边流淌的歌声,无不散发出古典主义的浪漫情调。它们构成的一幅幅风景写意画,在大量留白中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这种诗意化的想象,与作家眺望的姿态不无关系。吴其南认为,曹文轩常常“以过来人的身份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回首眺望”,“不仅从成人眺望童年,也从现在眺望过去,从城市眺望乡村”,因此,“生命中的许多经历、感情都借故事诗化了。”*吴其南:《曹文轩:为儿童提供人性基础》,《守望明天——当代少儿文学作家作品研究》,第212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曹文轩的短篇小说,虽然是以儿童视角为统摄,但背后始终存在着作家眺望式的目光。这样的眺望,会因为距离的存在而产生审美的想象。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距离,过去时光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距离,乡村生活与都市文化之间的距离,都被曹文轩统一在了一起,他“不仅将其作为一种创造美感的手段而且将这些距离本身也审美化了。”*吴其南:《曹文轩:为儿童提供人性基础》,《守望明天——当代少儿文学作家作品研究》,第212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将儿童视角作为满足自我创作理念和美学趣味的途径,用审美想象去填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沟壑,会不会使曹文轩笔下诗意化了的童年世界显得不那么真实呢?当作家过于强大的成人自我遮蔽了儿童主人公的视线,属于孩童自身的内在主体性就会被弱化。例如《再见了,我的小星星》中小男孩对女教师身体的感受里,就加入了作家的成人经验和想象,又比如《弓》这篇小说,作者用小提琴家的眼光去表现一个从乡下来的弹棉花的孩子的内心世界,仿佛隔着一层朦胧的面纱。而且,这两个作品所暗含的性意识和阶层意识,会对儿童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是需要讨论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为追求审美空间的洁净,曹文轩短篇小说对于成人世界的描写,因整体写意而缺少复杂多样的现实面向,影响了儿童与成人心灵交互所能抵达的深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曹文轩充分调动短篇小说的素材,不仅将很多人物形象和美好“瞬间”进行巧妙融合,而且把心理意象和行动线索较好地组接在一起,使作品显示出更加真挚动人的艺术魅力。《草房子》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短篇小说作为最初的文学准备,孕育了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理念和艺术胚胎。直至今天,曹文轩仍用一种近乎倔强的态度,坚守着原有的童年观和文学观。这种倔强的姿态,为其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提供了强大的信念支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缺失。我们期待着,拥有悲悯情怀的曹文轩,在未来可以写出更加饱含童年精神和现实力度的作品,为中国孩子的心灵成长注入无限生长的力量。
(责任编辑高海涛)
钱淑英,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