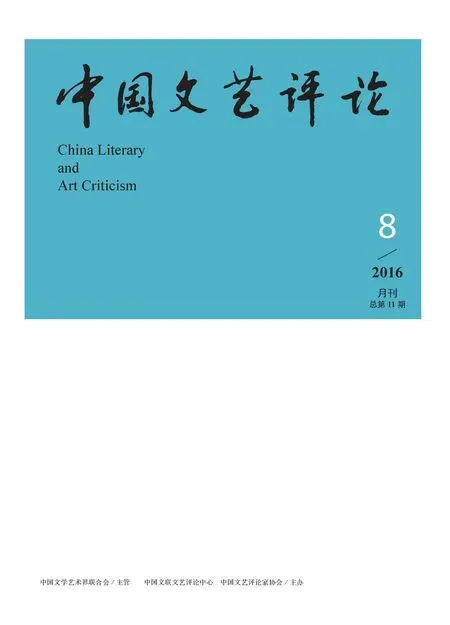诗心禅境了相依:禅宗诗学内容研究
皮朝纲 潘国好
诗心禅境了相依:禅宗诗学内容研究
皮朝纲 潘国好
金人托梦,释氏幻化中华文化韵味。一叶五花,禅宗涵养传统信仰品格。不离文字,文学成就禅宗诗学精神。与诗学精神相联系,禅宗以独贵心源、提倡心性修养,构建其人生论哲学;以崇尚禅悟、获得境界般若,构建其境界论哲学;以接引众生、注重开示法门,构建其实践论哲学。作为禅宗哲学的文学化,禅宗诗学理论的内容包括以心为源、胸襟修养、生命体验、艺境追求、像教悦情、禅艺互释六个方面。
一、以心为源
所谓“心源”者,乃心为一切万有之根源也。
禅宗又名佛心宗。“佛心”,一指如来慈爱之心,一指不执著于任何事、理之心,一指人人心中本来具足之清净真如心。从客观之心到主观之心,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为以心传心的传道方法提供了依据。憨山老人因此说:“佛法宗旨之要,不出一心。由迷此心,而有无常苦。以苦本无常,则性自空。空则我本无我,无我则谁当生死者?此一大藏经,佛祖所传心印,盖不出此六法。”[1]在禅宗看来,佛性和智慧皆人心固有,因而佛法要旨,不出一心。若悟得离思虑分别之心识,即是真知见,此“真知见”与智慧同义。获真知见,即得佛心。然而参修者常常依照自己的思虑分别,只是口诵佛经,在文字口舌间卖弄经义教理,心不悟佛法,徒增诸烦恼,所获者为“知见”,而非佛知见、非知见波罗蜜,故曰“心迷”。“心迷法华转”者,获有漏之果报,故称为苦;世间皆因缘所生灭,而无固定不变之实相,故称为空。抛却知见,见苦、见空,则达到远离二执、断灭烦恼之无漏境界。无执则可无我,可了知诸法因缘所生,实无自性实体。一旦悟入,则知心性即真如。离迷得悟、离染得净,成就自性清净心,即得本源。
以心为源,首先契合了楞伽师“以心为宗”的禅风。
从达摩到弘忍,禅宗五祖皆以《楞伽经》为根本经典,他们的思想和宗风一脉相承,故称为楞伽师。《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共四品,每品皆名为“一切佛语心品”。《宗镜录》说:“所以《楞伽经》云:‘一切诸度门,佛心为第一’;又云:‘佛语心为宗,无门是法门’”。[1]马祖道一认为:“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何故佛语心为宗?佛语心者,即心即佛。今语即是心语,故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者,达本性空,更无一法,性自是门,性无有相,亦无有门,故云无门为法门。”[2]由此可见,楞伽师十分强调“以心为宗”的禅风。
以心为宗,先悟后修,是修行的法门。云谷把禅学之悟引入诗歌创作,认为包括诗歌在内的百工伎艺也各有悟门:“譬如诸子百家百工伎艺,亦各有悟门。若得悟去,自然脱白露净,便有精妙之理。”[3]经过长期实践,禅与文字建立如下关系:“不可离文以为禅,即不可离禅以为文,此石门老人文字禅之所由作也。”马端临因此说:“(禅宗)本初自谓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灯总一百二十卷,数千万言,乃正不离文字耳。”[4]
既然以心为宗可以不离文字,那么诗文、禅意结合,就能相得益彰。禅宗思想从以心传心到以文字传心的过渡,推动了禅宗“以心为宗”诗学观的形成发展。
道燦就有“以心为宗”的诗学观:“或问诗以何为宗?予曰:心为宗。苟得其宗矣,可以晋魏,可以唐,可以宋,可以江西,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有本者如是,难与专门曲学泥纸上死语者论也。”[5]在道燦看来,以心为源,师心独造乃诗歌创作之根本。在师心和师古、师今之间,师心是师古、师今的基础。道燦的“以心为宗”的诗学见解,与后世很多主流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主张相一致。王世贞在批评李梦阳文必西京、诗必盛唐之后说:“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后来,麾之而后却,已落第二义矣。”[6]以心为源,如若外求,则会师古、师今、师自然;如若内搜,则会独抒性灵。袁枚因此说:“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7]禅宗“以心为源”的诗学观,体现着儒、释两家诗学观的融合。
儒家倡导诗言志,觉浪道盛禅师也有用诗写志之说:“予叹赏其风神,亦步十诗之韵为忆嵩诗,以写吾志。”[8]在禅宗诗学著述中,专门论诗的专论极少,觉浪禅师的论诗专论《诗论》就显得弥足珍贵。他论诗,乃充分吸取儒家的诗学观。如曰:“诗者,志之所之也,持也,时也”;如引“六义”说、“兴观群怨”之“四可”说:“诗有六义,实是比兴赋,三互而风转,古今之轮焉。诗有四可,实是哀乐之两端,感于中而相生者也。风写情景,雅叙事理,颂称功德,用之乡国朝廷宗庙。其概也,约言之,雅颂皆兴于风,而比兴所以为赋,三自兼六,而三自互焉。古今之轮,转而不已,就海洗海,圣人因之。四可者,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是远近一多之贯也。惟兴乃观,惟观乃群,惟群乃怨。”他提出诗是“传心光”之论:“声气实传心光,心不见心,以寓而显,故诗以风始,是曰心声。”[1]
儒、禅诗学融合的直接表现,就是诗文创作“情性说”的提倡。
作为诗歌艺术本质规律的内在组成,“情性”是“诗道”观研究的重要内容。皎然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崇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2]在皎然看来,情性是道之极则,如儒家之六经,如释家之空王。因此,他认为诗歌只要吟咏情性,就不以用事为贵。如果说“诗道”重在研究诗歌的创作规律,那么“诗教”则重在强调诗歌的宣传教育作用。两者的轻重问题,引起了禅门中人的探讨。释斯植从诗道观出发,主张诗歌要“乐情性”,就要关注诗歌的“言志”功能,而不是它的教化作用:“诗,志也,乐于情性而已,非所以有关于风教者。”[3]与之相对的是,永觉元贤禅师则持诗教观,推崇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引庄子诗论,赞成“诗以道性情”之说,又引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之论,赞成“诗惟在得其性情之正而已”。他批评有的诗论家“反是专以雕琢为工,新丽为贵,而温柔敦厚之意,索然无复存者。是岂诗之教哉?”他赞赏潭阳立上人之诗,“有古之道焉,其情宛而至,其气肃而和,其辞雅而温,其趣清而逸,无非率其性情之正发其所欲言者而已。”[4]
性情有正有邪,禅师们往往强调诗歌吟咏性情之正。
通门主张,诗的“触境命词”,应“皆得性情之正”[5]。道霈禅师论诗,吸取儒家诗学观(如“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看重“诗得性情之正”者:他认为觉非先生之诗,“得性情之正,匪徒事风云花鸟求句之工体之肖而已”,“夫人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情。天赋全者得其正,则形诸语言,见诸行事,皆足为天下后世法。”[6]道燦吸收儒家诗学观:“诗主性情,止礼义,非深于学者,不敢言”,他因此肯定营玉涧“本之礼义以浚其源,参之经史以畅其文,游观远览以利其器,反闻黙照以导其归,由千煅万炼以归于平易,自大江大河而入于短浅,轻不浮,巧不淫,肥不腴,癯不瘠”。[1]以此类推,就可以得出一个“性—情—文”的诗学言说逻辑:“文所以达其情者也,情所以极乎性者也。”由此可见,情之极至为至正之性。
二、胸襟修养
方立天认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是禅师们提出的心性修养的重要命题。[2]“平常心是道”源于禅宗公案:“南泉因赵州问:‘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3]从南泉普愿接化赵州从谂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禅林中人认为,日常生活所体现出的根本心,见诸于喝茶、吃饭、搬柴、运水等日常琐事,都与道连为一体。平常心内连道体,外显为行、住、坐、卧等四威仪举止。如果不放逸懈怠,常肃穆庄严,那么四威仪中就能显示真实的禅意。“明心见性”指明了自性清净心,彻见自心本然之佛性。修行人抛开一切颠倒妄想而达到明彻境界,即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说,在六祖慧能那里,就是“见性成佛”之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机缘品》云:“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4]禅宗强调“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惟作心求。
但是,顿悟之宗离不开渐修之教。严格意义上的胸襟修养,在禅宗那里,就是修行。论及修为之准则,佛教有所谓“八万四千法门”之称,然其主要者,即包括以上的三学、四谛、四禅天、四念处、八正道等条目。所修阶级,从声闻、缘觉、菩萨之修行,至最后果位。其修行时间各有不同,声闻须三生六十劫,缘觉须四生百劫,菩萨须三祇百劫。
对于很多禅僧而言,其胸襟修养可以实现“文学化”的转化。中国禅宗文学活动,可以说是禅宗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现。禅宗诗学的很多内容,都涉及到胸襟修养。
首先,禅学修为是诗文创作的前提条件。天隐和尚指出,诗颂创作的先决条件,是超脱一切“圣凡迷悟三乘学解”,成为一个“依真道人”:“实乃圣凡迷悟三乘学解一齐超脱活脱无依真道人也!”[5]基于此,禅师在进行诗文创作中,要诗品、人品合一。牧云通门禅师认为“人乎近诗”,人品即诗品,诗品即人品。他认为“懒亦能感人”,即是说“懒”作为一种人生态度,也有感染人的力量。“懒”者,优闲也,闲适也,无事于心,无心于事也。[6]基于同样道理,牧云评价“梅谿庵主”之诗,有沁人心脾之力,可使人脱去尘俗:“非诗不洩梅之神,非梅不发诗之韵。诗乎,梅乎?殆莫可分矣。”牧云所言之“懒”,并非真懒,而是相对于方外之人役役不休,为身所患的“勤”而言,是一种超凡脱俗的逸境;牧云所言之“梅”,并非是仅指梅溪庵主,而是包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梅花神韵和精神修养。懒以喻逸,梅以喻德,其中比德韵味浓郁,展现出胸襟修养之美。
其次,文学活动是提高禅僧修为的重要方法。禅宗中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活动。禅门中人在“游戏翰墨,作大佛事”的同时,也让文学活动走进佛事,使得文学步入禅境。这种境界为修行者身心愉悦地参禅悟道,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法华经》有“开示悟入”之说。开,开发之意;即破除众生之无明,开如来藏,见实相之理。示,显示之意;惑障既除则知见体显,法界万德显示分明。悟,证悟之意;障除体显后,则事(现象)、理(本体)融通而有所悟。入,证入之意;谓事理既已融通,则可自在无碍,证入智慧海。禅门诗歌因为充满禅意,而成为“开示悟入”的方便法门。憨山老人特别欣赏《法华经歌》的开示悟入功能:“余少时即知诵此歌,可谓深入法华三昧者。每一展卷,不觉精神踊跃,顿生欢喜无量。往往书之,以贻向道者。”[1]在禅宗初创的时候,菩提达摩即强调文艺活动的无功利性。梁武帝萧衍问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祖答曰:“并无功德,此乃有为之善,非真功德。”[2]之所以无功德,是因为“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3]后来灯录记载“了无功德”一句,指出禅祖已超越有无对待的妄执,也指出造寺、度人、写经、铸像,自认有功德,即一无功德,唯有不计较功德,不求回报的功德才是真功德。
禅宗的这种不求回报的功德观,要求禅门中人在进行文学活动时,要秉持无功利的胸怀。道燦论诗,提出心路绝、静参禅、万象显的创作方法,以及“胸中清气”的人格修养。所谓心路绝,就是指好诗、至文的成功秘诀,在于“学之无他术,先要心路绝”,即要摒去思维,摒去分别心,有一个澄澈空明的心胸。所谓静参禅,就是要“兀坐送清昼,万事付一拙。如是三十年,大巧自发越”,参禅静坐,无思无虑,做一个无事于心,无心于事的如拙如愚之人,长期坚持,大巧顿显。所谓万象显,即是说,经过前两个过程之后,作家创作就会百怪万象纷至沓来,供驱使、陶铸。[4]他还提出要怀清气于胸的人格修养主张:“诗,天地间清气;非胸中清气者,不足与论诗。”他因此批评当时诗家之弊:“近时诗家艳丽新美,如插花舞女,一见非不使人心醉,移顷则意败无他,其所自出者有欠耳!”他们是“不以性情而以意气,不以学问而以才力甚者,务为艰深晦涩,谓之托兴幽远”。[1]
在胸襟修养上,禅宗诗学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才情的涵养。
在诗文创作中,才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天王水鉴海和尚充分肯定天童悟和尚的诗才:“不事翰墨,而动笔皆是竹圣;不精诗书,而开口便成章法。”其《登金山诗》有“独自出手眼”,“玉韵惊人”之说:“和尚万历丁未春,自燕还南,是时尚未受嘱,气宇已自不群,偶登金山,辄成是句,不独自出手眼,尤且玉韵惊人,其绘文琢句者,曷能有此哉?”他提出观赏天童悟之诗的原则:“然则读之者,幸毋作文字诗句观,当眼豁心开可也。”[2]这说明,才情利钝,可以从诗文中观见。
由于才情难固,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在不同评论者那里,所见才情也可能不同。拿寒山诗为例,雪峤信禅师充分肯定寒山诗:“我见寒山诗,字字言真实。”[3]真可与他有类似见解:“世之高明者,无论今昔,皆味之而不能忘”。这是因为寒山诗“天趣自然”:“岂不以其天趣自然,即物而无累者乎?”[4]在解寒山诗时,无明慧性禅师却认为寒山也执著“解脱”,是“坐在解脱深坑”,并未达到能所双忘之境。[5]
在胸襟修养上,禅宗诗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识的养成。
才情属于先天禀赋,学识属于后天修养。禅门中人有人强调学识的重要性,提出“既精本业”又通“外学”的观点,主张精通“诗礼”“诗式”等“外学”,佛门弟子应“既精本业”,又应“钻极以广见闻,勿滞于一方”。应懂得“学不厌博”之理,因在“魔障相陵”时“必须御侮”,而“御侮之术,莫若知彼敌情”。主张者举习凿齿、道安、宗雷、慧远、陆鸿渐、皎然等人为例,说明他们“御侮”之法,“皆不施他术,唯通外学耳”[6]。即非禅师认为,非胸中洞澈,笔底玲珑,焉能并露。他评《山居合咏》:“句含蘸碧之渊,韵协五音之洞,俨然一座敛石山,飞来海外,与五岛争奇矣。非胸中洞澈,笔底玲珑,焉能并露?山身谿舌,不惟调高一时,抑道合千古,诚足传也。”[7]即非的“胸中洞澈”,在道霈那里就是学问淹博,道霈禅师肯定“湛菴禅公”“游于诗余”且“日臻其妙”,是因为“阅世日久,闻见益亲,学问淹博,性地愈明。故发为诗辞,意句俱到,情境皆真。匪徒留连风月雕刻字句已也”。[8]
无论先天后天,只要胸襟修养达到,就能才长工熟,离形得神。元叟行端禅师评价赵子昂诗:“韵高而气清,才长而工熟,非韦苏州、柳河东,则不能为也。”[1]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偈颂)中呈现的胸襟修养,是作者精神境界的外化。觉浪禅师指出:“吾故谓天下有真人,始有真性情;有真性情,始有真知见;有真知见,始有真事业;有真事业,始有真文章。”[2]明确指出只有真人,才有真诗。
三、生命体验
禅宗诗学的生命体验,和禅宗哲学的“悟”理密切相关。禅宗以“悟”为要义,“悟”也是贯穿禅宗诗学的主题。禅门宗人借助诗学化表达,首先感悟天然美景,其次可以感物以寄情,最终可以体悟到天真性情。
禅宗哲学之“悟”,与“迷”对应,如称转迷开悟或迷悟染净中之悟。有证悟、悟入、觉悟、开悟等名词。悟能生起真智,反转迷梦,觉悟真理实相。佛教修行之目的在求开悟,菩提为能证之智慧,涅槃为所证之理,佛及阿罗汉为能证悟者。佛教由于教理之深浅不同,悟之境界亦有区别;小乘断三界之烦恼证择灭之理,大乘之悟界乃是证见真理,断除烦恼之扰乱,圆具无量妙德,应万境而施自在之妙用。在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间、天上、声闻、缘觉、菩萨、佛等十界中有迷悟之分,前六界为迷界,后四界为悟界,称六凡四圣。若以九一相对来说,前九界为因,后一界为果,圆满之悟界唯有佛界。又从悟之程度而言,悟一分为小悟,悟十分为大悟。若依时间之迟速,可分渐悟、顿悟。依智解而言,解知其理,称为解悟;由修行而体达其理,则称证悟。
禅宗诗学之“悟”,是哲学之“悟”的诗意化表达。正所谓“世间文章技艺,尚要悟门,然后得其精妙”。[3]在大慧看来,一切“世间文章技艺”都崇尚“悟门”,只有证悟,“然后得其精妙”。持相似观点的,还有齐己。他说:“道自闲机长,诗从静境生”,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道(禅心)与诗(诗思),都只能在生命体悟的“闲机”、“静境”中产生。[4]齐己认为,吟诗作画,均可传心悟道,所谓“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5]诗心、画心、书心及一切文艺之心的传达(抒写、表现),必须通过诗、画、书及一切文艺创作来实现,而诗人、书画家及一切文艺家,也只有在观察、体验审美对象中,有了深切的感悟(证悟)时,才会有审美兴会的爆发,审美意象的形成,才能有诗、画、书及一切文艺作品的产生。其创作过程中的证悟的获得,同禅家参禅悟道中的证悟(其证悟是在般若观照即禅体验中获得的)是相似相通而相同的。
《老子》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过在道家著作中,“自然”更多简称为“天”,即自然天成、不假人为、本真固有的存在。禅宗也讲自然,指的是不假任何造作之力而自然而然、本然如是存在之状态。禅宗诗学认为,佳诗出于无意为之,乃出之自然。牧云指出:“绝无思虑于其间,任天而已矣”。[1]
禅宗诗学观照的“自然”,又分为几个层次。
首先,是自在存在的审美客体。契嵩认为自然美景,有待人之发喧昭著:“然物景出没,亦犹人之怀奇挟异者,隐显穷通必有时数。若此十咏之景,所布于山中,固亦久矣弃置,而未尝稍发,今昼师振之,众贤诗而光之,岂其数相会亦有时然乎?”[2]在来复看来,自然山水往往倚人而重:“夫山岳之雄丽,必有不世出之材而镇之,故其云霞水石草木禽兽,亦得托名不朽,往往倚人而重”。[3]与此相对应,山水为诗家创作之助:“水阔山高对日华,山嵘水艳助诗家。”[4]大自然有“天开画图之妙”,“频观兴愈清”,“快意乐天真”[5],诗歌的上乘之作,总是写即目所见。禅诗崇尚不假任何造作之力而自然而然、本然如是存在之状态。入就瑞白禅师曾作《又题四景(并引)》,内有“任运禅人搬木回,至五龙湫憩息。举目偶见一水瀑布,喷珠而下,遂有瀑布泉五龙湫之诗。”[6]这个序说明,禅门宗师主张诗歌创作应写即目所见。诗歌的上乘之作,总是写即目所见。“即目所见”是在追求诗境,“诗境”何来?吹万禅师云:“何事与君堪敬节,何境与君共题诗?”那就是千姿万态的大自然:“唯有白雪乱山巅,梅花依旧吐寒枝。”[7]也就是说,诗境源于自然。达到这种状态之后,就会“天机所至,不期然而然”。
其次,是感物寄情的审美境界。“物”至少应有两层含义,一指客观事物,二指客观事物在人头脑中的映象,也就是陆机所说的“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8],客观之物与主观映象交相凑泊,是产生新的审美特质的过程。刘勰则把“物”与“自然”并举,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9]陆机和刘勰把创作过程看作是由感物生情到情物交融,再选义择声,物化为美的作品的过程。禅宗诗学继承了这种建构在外物之上,对观物方式、文人精神生活的深切思索,把感物寄情升华为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妙声说:“离则思,思则咏歌形焉,咏歌既形,则凡物之感于中者,皆足以寄情而宣意,此风人托物之旨,而陶渊明所以有停云之赋也。”[1]正因为物我相召,才有将自然美人格化的表达,才有了“比德”之说。妙声就欣赏这种“比德”式的物我关照:“古之取友者于一乡,于一国,于天下,犹以为未也,又尚友古之人。古人远矣,求之于今而未足也,又取诸物之似者而友之。盖友者所以成德也,苟可以比德焉,虽草木之微,在所不弃之。”[2]契嵩也表达了一种对“比德”式观照的偏好:“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遥有正,视其物,则其人之贤否可知也。若石之为物也,其性刚,其质固,其形静,其势方。方者似乎君子疆正而不苟也,静者似乎君子不为不义而动也,固者似乎君子操节而不易也,刚者似乎君子雄鋭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峰拒似乎贤人严重而肃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虚心而合道也。今无以吾道为禅者师,以翰墨与儒人游,取其石而树之于庭,朝观夕视,必欲资其六者以为道德之外奖、操修之黙鉴也。”[3]契嵩把人的禀赋气质和石之存在状态进行类比,再将这种对人和物的观照寄托在翰墨之间强调了道德节操的人格境界对于文学家的重要作用。
第三,是心性天真的人生追求。所谓心性,指心之本性。自性有清净、染污,天真可以使它去染得净、去污得清。在禅宗哲学那里,所谓“天真”,是指天然而不假造作之真理。《摩诃止观》卷一说:“法门浩妙,为天真独朗,为从蓝而青。”[4]禅宗有“天真独朗”之说,即是了悟不生无作之本体,超越生死差别而朗然大觉。在禅宗诗学看来,天真是一种适意而为,是对闲淡之趣的抒写。鄂州龙光达夫禅师追求一种“适意辄吟诗”的境界,即认为“吟诗”出于“适意”。[5]禅宗诗学对生命体验的表达,常常显现出适化无方的特征。这是一种随机教化众生,而不拘泥于特定方式。菩萨出入生死,教化众生,令悟性空,乃权巧方便之智,亦为如来适应众生机缘所施设之法门。所谓“适化无方,陶诱非一”。[6]这恰如寒山之诗,无意于诗而似诗:“寒山诗,非诗也,无意于诗而似诗,故谓之寒山诗。”[7]诗之本质:“皆所以歌咏性灵,阐扬道妙,欲使众生去妄归真,舍凡入圣,厥旨微矣。”[8]闲是佛道修行的有暇境界,佛教鄙薄俗套之“闲”,反对落入闲尘境,成为诸闲不闲之人。所谓闲尘境,就是指无意义、无价值之外在诸条件。尤指不用之文字、言语。尘境之“境”,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之对象六境(色声香味触法),以其有染污心之性质,故称尘境。《临济录》“示众”说:“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总上他闲尘境,都不辨邪正,只如有祖有佛,皆是教迹中事。”[1]所谓“不闲”,指有八难等而无暇之境界。所谓“诸闲”,指于人天趣中无障难者;反之,堕于难处者,称为不闲。《无量寿经》云:“悉睹现在无量诸佛,一念之顷,无不周遍,济诸剧难,诸闲不闲。”[2]禅宗诗学中的生命体悟,不是要人步入闲尘境,堕落成诸闲不闲之人。它是“以音声文字而作佛事”,体现出随缘适化的特征。
四、艺境追求
在佛学看来,从消极意义上说,境是心与感官所感觉或思维的对象。它能引起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感觉思维作用,产生色、声、香、味、触、法六境,以其能污染人心,故又称为六尘。从积极意义上说,境可指胜妙智慧之对象,即是佛理(真如、实相)。境界般若,五种般若之一。五种般若,指照了法界、洞达真理之五种般若圣智。其中,境界般若指般若所缘之一切诸法。
禅宗浑简锋利、超然特立之思想,为中国文坛开启一种笔随神具、气韵有致的禅诗之风。禅宗诗学所言之艺境追求,其实是对禅门诗歌(诗偈)审美属性的思考。禅宗诗歌的艺境追求,可以分意义层、意蕴层和哲理层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在意义层面上,首先是诗歌用词和音韵问题。真可云:“夫机缘者,活句耳。”[3]凡富有生命力之诗句,即是活句;凡无丰致、无寄托、无韵味的诗句,即为死句。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须参活句,勿参死句。”[4]曾几在《读吕居仁旧诗有怀》中说:“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5]人们往往有一个片面认识,那就是活句不是寻常语,常语多是死句。乾隆年间学者张问陶却不这么认为,他在《论诗绝句》中说:“跃跃诗情在眼前,骤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6]禅僧修睦和张问陶有相似见解,强调写诗多用常语:“常语亦关诗,常流安得知。”[7]写常语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就会进入牧云所说“意圆词爽,旨深格高”的境界。
用词往往和音律结合起来。有人认为,诗偈创作,是“兴到随腔信口歌”,并不留心于什么“协韵”与否。明方云:“我无玄亦无奥,相逢只唱渔家傲。更问如何性与心,断拂一枝当面挫。也作诗,也作偈,协韵何曾有文字。兴到随腔信口歌,记取是名雪书记。”[8]也有注重诗歌音律的,吹万禅师强调诗应协韵。他说:“怛闼老子大圣人也,尚美频伽未出之卵,盖重其音也。夫音借韵以成句,续句以成章,章之长短即言之长短也。是而有风焉,有雅焉,有三颂焉,复又稽之乐经之五音也,析显刚柔之声,一之六律也。潜通岁时之气,故音变则声变,律变则气变,所以毛诗之后有离骚,离骚之后有十九首,十九首之后变辞为绝敲乐为律。”[1]
用词和音律是诗文创作的语言问题,诗歌的体制形式与用词、音韵的关系,也每每被人论及。
雪关高度评价寒山之诗:第一,寒山诗不拘时人窠臼,打破程式束缚,“我爱寒山诗,不入时人调”。第二,寒山的诗意句清新,勿事华藻,句句能涤除尘情忘识。第三,寒山的诗能让人玩味,“乍看意句新,转玩滋味好”[2]。同是评价寒山诗,吹万禅师则充分肯定寒山诗通俗流畅,“拈语不粘唇”;有强大的感染力,有如“风吹野火”,可以燎原;有很强的审美教育作用,能“唤醒众生心”[3]。
在意蕴层面上,禅宗诗学强调禅体诗用的体用结构。憨休禅师指出,佳诗有很强烈的感染力:孝廉公之《风穴游记》并诗“读之,如钟闻午夜,俗耳顿清,似剑淬丰城,星河耀彩,盖缘思超而才俊,兴远而语雄”。其使人“俗耳顿清”,缘于“思超而才俊,兴远而语雄”。[4]高泉强调写诗唯求适趣:“诗不求工唯适趣”[5]。齐己指出,在参禅悟道外,也寻求诗之妙趣:“禅外求诗妙,年来鬓已秋。”[6]而对意蕴的强调,往往强调诗偈的美育功能。居简吸收儒家诗教说,重诗“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功用,批评“末流着工夫于风烟草木,争研取竒,自负能事尽矣”之风[7]。
大汕论诗,既提到兴会,也参杂五位君臣,论述诗禅关系,从而论证了禅宗诗学意蕴产生的哲学基础。他认为,第一,写诗起于兴会,无容心于诗:“偶兴会所至,信口发声,侍者记录成帙,无容心于其间也。”第二,以“重离六爻、偏正回互”论诗、论禅:“惟吾洞上一宗,言禅而不离五位”。“吾宗之五,为君臣道合,君不偏于正,臣不正于偏,如银盘盛雪,明月藏鹭,混然而分明,斯为向上一路。知斯旨者,始可以言禅,并可以言诗。”[8]第三,禅不离诗,诗不离禅:“以为禅则离诗非也,以为诗则离禅非也”。第四,然而,诗禅有别。它们是“合之未始合,则离之亦未始离”,不即不离。把五位君臣学说引入禅宗诗学,便于形象地认识禅诗意蕴的现象和本质。大汕借禅宗的五位君臣之说,将诗禅之偏正关系,对应于事理之偏正关系,强调了禅诗以禅为正,以诗为偏的诗禅关系。
在哲理层面上,禅宗诗学主张“融文心为禅思”。天隐和尚指出了诗颂创作的先决条件,超脱一切“圣凡迷悟三乘学解”,成为一个“依真道人”:“实乃圣凡迷悟三乘学解一齐超脱活脱无依真道人也!”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参究公案,应“吃紧须看古人无义味语,种种因缘,密密体究,看他是个什么道理,一一俱要透过,不被他瞒,直至无疑无悟之地,七穿八穴,拶到古人不到处,则所悟既真,所行必到,所学既实,所证要明,最亲切处更加亲切,然后苏醒得来,掀翻窠臼,扫绝踪由,把从前学解的、见闻的、悟证的一抛抛向那边更那边”。只有到此田地,有了今人所说的“前理解”“前结构”,做到了“见在机先,意超言外”,那么,“飞泉落涧,清韵长吟,可以激扬般若之真机;空谷行风,玄音和雅,可以提挈纲宗之妙诀”。只有如此,“汝欲颂耶,不拨舌而松风浩然,岂非颂也?汝欲诗耶,未启唇而云鸟悠然,岂非诗也?”[1]
五、像教悦情
所谓像教者,首先指像法之教化。像法即于佛陀入灭经500年正法后之教法;像教即指此时期佛法之总称。其次指佛像与经教。相对于儒教之称“名教”,而以佛教拜佛像,故称像教。唐末,以临济宗的汾阳善昭为开创者,禅宗内部逐渐兴起通过研究经文、语录、公案、偈颂等文字来习禅、教禅,进而相互讨论,启迪和勘验。惮门宗师也常以文字的方式,表述自己对宗法的理解和接引学人的经验。具有“文字禅”性质的诗文创作活动,因其描摹佛像、涉及佛事、弘扬佛法,因而具有了像教性质。于是,诗文创作是做魔事还是做佛事,一直成为争论的焦点。
有禅师认为,诗文创作是在做魔事。其中缘由是,悟禅须正信、三业犯罪业、文字是葛藤。
但是,也有不少禅师说,诗文创作是在做佛事。
第一,诗文创作是游戏三昧。三昧乃三摩地之意,为禅定之异称,即将心专注于一境。游戏三昧者,犹如无心之游戏,心无牵挂,任运自如,得法自在。亦即言获得空无所得者,进退自由自在,毫无拘束。《坛经》云:“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2]首先,诗文是否符合禅理?三祖有《信心铭》、永嘉有《证道歌》,是否与禅宗“直指”之宗旨相悖?回答是:“不悖”,“盖有以助显其直指之道者也。”[3]其次,吟咏诗词,是否是在做佛事?在智及看来,“达人大观”,吟咏诗词,乃“游戏翰墨,无非佛事”,其旨在:“盖欲咨决大事因缘,碎尘劳窟宅,拔生死根株,岂吟咏云乎哉?”[1]再次,禅诗具有怎样的启发作用?如净明确提出“借诗说教”,这是禅宗诗歌美学的重要观点。他用“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等绿竹的三种状态,来比喻“序品第一”“正宗第二”“流通第三”。[2]所谓“序品第一”“正宗第二”“流通第三”,是指佛学大师对佛典经论的内容作适度的区分,通常都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等三部分。如净禅师引用杜甫《严郑公宅同咏竹》之诗句,解说佛典经论。杜诗云:“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此首咏物诗,是着力描绘“竹”的形象。首联即着力描写竹的新嫩和勃发的生机。这是从视觉的角度描绘竹的两种形态:幼竹,竹子的初生形态;成竹,竹子的成熟形态。如净以之分别比喻为“序品第一”和“正宗第二”:第一句“绿竹半含箨”,有一半还包裹着笋壳的嫩绿之竹,正是竹子的初生,她会节节向上成长,正如“圣人造论,必有由致,故初明序分”;第二句“新梢才出墙”,其新长的枝梢,才刚刚伸出墙外,它是竹子的成熟,恰如“序分既彰,必有所说故,次明正宗”。此诗的第三联是描绘竹子经雨洗刷后的洁净,以及竹子的清香。这是从嗅觉的角度描摹竹子缕缕清香,使人心旷神怡的感受。如净以之比喻为“流通第三”,正如“正宗既终,劝学流通故,后明流通”。
第二,诗文创作是禅宗摄受众生之法。菩萨摄受众生,令其生起亲爱心而引入佛道,以至开悟的布施摄、爱语摄、力行摄、同事摄等四种方法。其中爱语摄,又作能摄方便爱语摄事、爱语摄方便、爱言、爱语。谓依众生之根性而善言慰喻,令起亲爱之心而依附菩萨受道。[3]基于这种认识,禅宗诗学主张禅诗功能,是弘扬佛法的重要手段。在云外云岫看来,好的山居诗,可以成为展示、传播佛法的经典:“陈年佛法无人问,黄叶堆金不转官。一卷山居诗更好,焚香只可作经看。”[4]
第三,诗文创作促进儒释道融合。儒释道经过长期发展,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觉浪禅师对孔子的诗学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作了阐释,他认为“怨”之一字,乃是“造化之玄枢,性命之秘藏”:“予以‘怨’之一字,尤为造化之玄枢,性命之秘藏。凡天下之事,到于‘群’处,不能无怨,到‘无邪’处,乃能归根复命,贞下起元也。此非千圣不传之玅密乎?须知有性命者,必有形色,有形色者,须有造化,有造化者,须有事功,有事功者,必有文章辞令,为天下之风教。”道盛的“文章辞令,为天下之风教”的观点,表明他对诗文功能作用的重视[1]。禅门往往明确标举孔门的诗学观:“不学诗无以言”。并明确提出“弘道须习文翰”的主张[2]。《一贯别传》提出:“诗书六艺亦有成佛之种子”。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十住位中,自在主童子者,所修书数算印等法,即得悟入一切工巧神通智慧门。可见诗书六艺,亦有成佛之种子,此即心中发明,如净琉璃之治地住也。”[3]像教足以悦情。的确,诗歌的上乘之作,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人们欣赏之,“如啜萝岕于酩酊,令人眼目一新”。而一些山居诗,并无真情实感,因为他们不食人间烟火,心中不存丘壑烟云:“近代禅讲,集必有诗,诗必有山居,多屐不食丘壑,杖不饱烟云,纵描写十分,何异矮子观场,而因人啼笑哉!”[4]
六、禅艺互释
以禅喻诗,是一个古代诗学命题,借佛家禅理以比喻创作与批评。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5]“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6]以禅喻诗,并非严羽首创,北宋苏轼、叶梦得与吴可等已开其端。如吴可《学诗诗》提出“学诗浑似学参禅”之说,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7]这些论述,均为严羽“以禅喻诗”之先河。
就禅宗诗学而言,禅艺互释有以下几个表现形式:
第一,以禅喻诗。诗歌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形之于心之时,禅寂可以诱发诗文创作。齐己认为,心机的兴起,诗思的涌动,只能在禅寂中产生:“日日只腾腾,心机何以兴?诗魔苦不利,禅寂颇相应。”[1]在行之于手的时候,禅思可凝练出玄旨。林昉指出,诗与禅都重参与悟:“诗有参,禅亦有参;禅有悟,诗亦有悟。”因而,诗与禅之悟是无差别的。文本一旦形成,就会出现诗中有禅的现象。何谓“诗中有禅”?是“非有关于性命”,不是讲禅理,而是“奇幻绝人”,是“融文心为禅思”,如严无敕居士,因他“老于林下,听水二三十年”,能“叩大事因缘”,领悟了生死事大,进入了禅境,获得了禅思,从而能“融文心为禅思”,因此,其山居诗“语语遒迈,复多警人心意,如流水细听看念断”[2]。在这种状态下,诗情必须近禅。此时,以诗喻禅是表面,以禅喻诗是宗旨。[3]
第二,以诗喻禅。以诗喻禅(教),往往为宣扬佛法的方便。方便又作善权、变谋,指巧妙地接近、施设、安排等,乃一种向上进展之方法。禅家往往引诗说法,以为禅学方便。普融所作藏主《颂》,是追问什么是“本来面目”,这是借颂(诗)说教(禅)。他作《渡桑乾》,乃是回答什么是“本来面目”。这是用诗释颂,是二度说教(禅)——是用《渡桑乾》解说普融藏主《颂》之“意”而说教(禅)。前者(藏主颂)是直说式,后者(《渡桑乾》)是曲说式。[4]普融指出,人的本来面目(真实生命)是难以把握的,它“从来往返绝踪由”,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也是难以领悟的,“行人莫问来时路”。普融之意,在于截断学人的分别心,不要在葛藤里纠缠,而要返观自心,直下承当,以直探内在生命。
第三,禅、诗互释。以禅喻诗和以诗喻禅理论的提出,为禅、诗互喻理论奠定了基础。觉浪禅师引憨山“诗禅一也”之说。“吾宗以之接机,山川烟云,竹水飞跃,感物造耑,不即不离,而协在其中矣。”[5]皎然认为,诗禅不相妨:“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6]他还说:“儒服何妨道,禅心不废诗”,诗心禅思两相依。[7]不仅禅不废诗,诗也不废禅。
禅和诗不仅不相离,而且相互渗透。智舷提出理论:“诗夺禅者言,禅夺诗人髓。”前句,讲其诗无禅语(“诗夺禅者言”,乃诗语非禅语);后句,讲其诗有禅意(“禅夺诗人髓”,诗人已有禅心、禅意)。[8]林昉从思维方式上,提出了禅、诗互释的原因。他指出,诗与禅都重参与悟:“诗有参,禅亦有参;禅有悟,诗亦有悟。”因而,诗与禅之悟是无差别的。他引英上人之论:“诗悟必通禅”,“妙处如何说,悟来方得知”[9]。牟巘认为,诗人往往既逸而之禅又逸而之诗的重要原因,是禅与诗有共同之处,是二者都能超然物外,摆脱世俗烦恼的束缚,使胸襟放旷逸荡:“往往逸而之禅,又逸而之诗,二者实能外事物,旷荡可喜,故人亦乐为之称道。”[1]
第四,禅、诗两妨。在禅、诗互释理论大行其道的同时,也有理论认为,禅、诗不同,乃至禅、诗两妨。王庭言认为,偈颂与诗,“虽诗体不殊,而理趣各别”,“偈颂之深谈(‘理’),或不如诗之玄寄(‘趣’)。若将景物会,差之毫釐。”景与物会,诗则擅长。[2]元叟则从作家的不同,区分了禅、诗的关系。他说,“诗禅”者,诗人之禅;“禅诗”者,禅人之诗。[3]行泽则指出:“夫诗文之学,非博学强记,殚精敝神,则不能工也。不工则不足以示人,工则徒丧光阴,于无补之学。外以无益于人,内以无益于己,故虽穷年参学,皓首无归者,滔滔皆然。是唯非特于生死无益,又从而滋甚之,可不为大哀欤!”[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4XZW008)、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5A738) 阶段性成果。
皮朝纲: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潘国好: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韩宵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