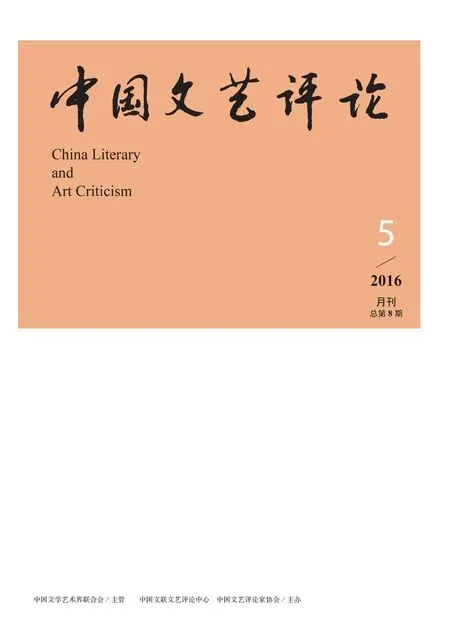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略论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中的实际地位
陈传席
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略论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中的实际地位
陈传席
编者按:为进一步推动文艺评论繁荣发展,深化对文艺领域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从本期起,本刊开设“一家之言”栏目,为艺术界学术界评论界思想碰撞、观点交锋搭建平台,欢迎各方专家踊跃赐稿。来稿请发zgwlplzx@126.com。
一、中国书画对世界艺术的重大影响
毕加索、马蒂斯、梵高、莫奈、塞尚等人是西方最关键、最重要的画家,若缺了他们,西方美术史甚至世界美术史将有大片空白。但这几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学习了中国艺术而成功的。且看史实。
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早期的油画,基本上和欧洲传统绘画一样。他自己说他在少年时临摹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和当时的大师们的作品完全一样,一样就没有发展了。他1901年画的《横躺的裸女》,也仍然是欧洲传统式油画,用面表现而不用线表现。还有他的《自画像》也是以面表现的。还可以列出很多事实。但他后来临摹了中国画,有五大册,每册三十多幅、四十多幅不等。当然用毛笔画,其中线条不可能是地道的中国画传统线条,大抵都和他在1956年在法国南部Nice赠送给张大千的《西班牙牧神像》中的线条相类。有些线条也暗合于中国传统的提按方圆轻重之变化。有的线条也有圆润感,但这都不是自觉的。有的人物画是用水墨画的,也颇有点韵味。后来,他又用毛笔学齐白石的画,画了二十本。他学齐白石的画学得并不像,但他学了中国画后,便改面为线,他的画变为主要用线来造型了。有的是用线勾好后,表现质感的部分也用面,但他的“面”也是中国化的,似中国画的写意笔法,不是传统欧洲油画式。他1907年创作的《阿维农少女》被公认为第一幅立体主义绘画,其画法主要即是用线,尤其是那幅《阿维农少女》的油画草稿更明显是用线造型。愈到后来,他愈重视线的造型。有时用粗线,有时用细线。他的《弹吉他的男人》《扶手椅中的妇人》《三个音乐家》《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三个舞者》《镜前少女》《庭院中女人》《戴红帽子的坐着的女人》《生之喜悦》等等,他后期几乎所有画都是用线造型。他1923年画的《恋人》,实际上就是用油画画中国画,线条也好像是用细毛笔勾写似的,实际上是用小油画笔勾的。1937年他创作的著名的《格尔尼卡》也全用细线造型,这是传统欧洲画中所没有的。但毕加索学中国画用的是毛笔,他送给张大千的那幅《西班牙牧神像》,也明显的是用软毛笔画的,线条有圆润粗细的变化。但他用油画笔画油画时,线条便无变化了。因为油画笔的棕刷子很硬,缺乏弹性,画不出粗细的变化,只能画出直线条。所以,他后期形成他个人特殊风格的画几乎都是用直的、或圆的、或各种几何形的线条为主画出来的。其画属于立体派也好,现代派也好,但画法来自中国画。形成他的绘画风格的部分来自中国画,若没有中国画的启发,便没有毕加索后期的成功。毕加索也十分感谢中国画对他的启发。他对中国画的评价也十分高,远远高于欧洲画(详后)。
张大千在丙申(1956年)也回赠毕加索一画,上画两株竹子,前浓后淡。据张大千的叙说,他见毕加索用毛笔学中国画,但不知用笔之法,他画竹子告诉毕加索应该怎样用笔。如果张大千的话对毕加索有影响,那么这影响仍然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因为张大千是研究中国传统的画家。
毕加索还说过:我最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的,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的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1]包立民:《张大千艺术圈》,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
看来,毕加索对艺术史的研究也颇有见解,他说“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是非常正确的,这比很多美术史研究家的看法高明得多。日本艺术对世界产生影响是“浮世绘”,全用长线条造型,日本人说是学习中国唐代的绘画,其实主要是学习中国明代的陈洪绶。早期“浮世绘”中的人物造型多来自陈洪绶的人物画,画法更是来自陈洪绶。当然,同时也学习了中国唐宋传统和其他一些优秀的中国画家的作品,总之都是“源自中国”。因而,凡学浮世绘者实际也是受了中国画的影响,不过是中国画的再传“弟子”而已。白人早期用面表现物像的油画乃是来自古希腊,后期用线表现物像的油画来自浮世绘和中国的写意画,归根结底是来自中国。毕加索还说:中国画真神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2]包立民:《张大千艺术圈》,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崇尚西方画和现代派的人提起毕加索,无不五体投地,他的每一句话都比圣旨还要严重。那么毕加索如此崇尚中国画,论之为世界上第一等艺术,怎么又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了呢?难道一些根本不懂艺术的画商能高于毕加索吗?
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也是欧洲最重要最有特色的画家之一。荷兰有梵高美术馆,还有很多梵高大画集。从画集中梵高的作品和其生平介绍可知,梵高只活了37岁。他早年学画也是传统的欧洲式油画,毫无特色。他30岁之前一直临摹荷兰画派和法国巴比松画派的作品,尤其是米勒的作品。他的画卖不出去,可能也和他的画既不美又无特色有关。如果美而艳俗,可以投合一般俗人的口味。如果有特色,则收藏家必光顾。这两点,早年的梵高都不占。
梵高在学习素描时,成绩是全班最末一名。如果他这样学下去,他永远不能出人头地,也许他最终只能成为一个不入流的普通画人。
1885年,梵高购买了一些日本浮世绘的版画。他在给他弟弟特奥的信中说:“我的画室不错,尤其是由于我在墙上钉上了一批小幅的日本版画。我非常喜欢这些画,在花园里或海滩上画得很小的仕女、骑马的人、花朵、多刺的荆棘枝。”从此,他喜爱上日本的浮世绘。
在荷兰梵高美术馆里,收藏(挂在玻璃柜中)梵高曾学习过的日本浮世绘画三张作品,其中有他1887年临摹的《开花的梅树》(日本歌川广重原画),原作和临作放在一起,基本一样,只是梵高用油画笔画的,而歌川广重是用中国毛笔画的线条加重色而成,再刻印而出的。1887年,梵高模仿日本浮世绘用油画颜料和油画笔又绘制了另外两幅油画作品。从此,他改变了自己的画法,由用面表达改为用线表示。长线、短线。即使画上是面,也是用短线画成的面。他的独特风格形成了。以后三年多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以线为主的作品。
在《塞尚、梵高、高更书信选》中,梵高也多次论述到自己作画是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他说:“当你处处发现日本的绘画,不论是风景还是人物,色彩都是那样鲜艳夺目时,你一定会产生一种绘画革命的思想。提奥和我已搜集了数百张日本画的印刷品。”[1]《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选》,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请注意,我说的是那种日本画法中的色彩简化法……(反推日本画---有种色彩简化的特点---例如梵高就说过---他的作品----)日本画家就是采用这种手法的。他们在一张白纸上,三下两下一画,就奇迹般地表现出一个少女的表面粗糙而苍白的皮肤的颜色与黄色头发间趣味横生的对比。更不用说那星罗棋布般盖满了无数白花的黑色荆棘林。”[2]《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选》,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4页。“我敢预言,别的画家们会喜欢一种在强烈阳光下的色彩,喜欢日本绘画中那种晶莹澄澈的色彩。”[3]《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选》,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2页。“日本画家传授给我们的真正的宗教……我羡慕日本画家对作品的每个细节处理得极其清晰,从不使人乏味。”[4]《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选》,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5页。
他甚至说:“我的整个创作均以日本绘画为基础。”“日本艺术在他本国已逐渐衰落,却在法国印象派艺术家中生了根。”[5]见《美术译丛》1982年第3期,第411页。谈到色彩,梵高说:“你会察觉到,我是像日本的样式谈色彩的简化……就像我们在日本的套色木刻里见解到的那样。”[6]《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23页。
可见梵高的画来自日本浮世绘。但梵高因为收藏了日本的浮世绘,并学习它,而言必称日本画,但他不知道日本的艺术完全来自中国艺术。我再一次声明,梵高学日本浮世绘实际上仍然是学中国的艺术,因为原创来自中国。
可惜梵高死得太早了。他死后一年,他的画就被世人所知所赏。巴黎为他举办的遗作展览,尔后就是大量的出版、展览、回顾展等等。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建造梵高博物馆,正式向全世界开放。梵高如果不自杀,他会比毕加索还富有。
如果没有浮世绘,便没有凡高;没有中国画,便没有浮世绘。凡高的成就来源,便不言而喻了。
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也是欧洲和世界上最重要的画家之一。马蒂斯早期的油画也是欧洲传统式,用面表现而基本上不用线。如他1896年画的《女服务生》《工作室》,1899年画的《生病的女人》,1904年画的《裸像》等等,都是普通的欧洲传统式风格。1904年画的《静物》,1905年画的《撑伞的女人》则明显的是学点彩派,基本上没有个人特色,不过是点彩派中普通一员而已。
从1905年开始,他抛弃了点彩派画法。他开始学习浮世绘,改用线条造型。1909年到1910年,他创作的名作《舞蹈》(其中五个裸女拉着手在跳舞)、《音乐》(其中五个裸体男孩),全是用线勾括,再平涂颜色,涂色也完全是中国画的写意式。线条也是中国画式——柔曲而劲细。1916年和1917年画的二幅《常青藤、花瓶和雕塑》用粗而实、直多于曲的线条造型。马蒂斯后期的画,全是学浮世绘的线条,而色彩全是中国画的写意式,他的“野兽派”风格凸显出来了。
再晚年,马蒂斯学习中国的剪纸,创作出大量的剪纸作品。他的剪纸作品是学中国的,这事实,也是所有学者公认的。但学中国哪一个地方的剪纸呢?我作了对比,可以判断出他学的是中国徐州市邳县的剪纸。
马蒂斯自己也反复讲:“我的灵感常来自东方艺术。”“我的风格是受塞尚和东方影响而形成的。”[1]转自迟轲《西方美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390页。这东方艺术即日本浮世绘和中国的写意画。当然,浮世绘也来自中国的艺术。如是看来,马蒂斯由中国艺术的再传弟子变为入室弟子。没有中国艺术也就没有马蒂斯。
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法国著名画家,也是世界著名画家。莫奈的名作是《睡莲》。可是莫奈早年绘画,也是欧洲传统式,虽然也不错,但不足以十分的出人头地。1871年,莫奈31岁,他到荷兰并滞留到年底,发现了日本画浮世绘,他买下了数幅。从此,他开始了对东方艺术的兴趣和研究。1899年,他对浮世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且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藏画中还发现了两幅他十分喜爱的画,乃是中国画。所以,他画《睡莲》,用线勾出形状,用油画着色也是中国画的写意法。他画的芍药花、睡莲中的水草和很多色彩笔触,都完全来自中国画的大写意法,大异于传统的欧洲油画。尤其是画上的垂柳,更是中国画的传统画法,他成功了。而且,他画的《睡莲》是长卷式,高两米,长达数十米。欧洲传统油画受定点透视的规定,一般长宽比是5∶4或4∶3。没有长卷或长轴。中国画从不受定点透视的影响,像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高仅51.5厘米,而长达1191.5厘米,长是高(宽)的20多倍。莫奈的《睡莲》也是仿效中国画长卷式,打破了欧洲传统的定点透视法。没有中国画的影响,也就没有莫奈的名作《睡莲》。莫奈有了《睡莲》,才有了他在欧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
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法国人。他的画一直遭到官方沙龙的拒绝,多次送展均失败,就是因为他的画和欧洲传统绘画不同。传统的欧洲油画用笔用色一直是很严谨的,不敢随意。而塞尚的画显然是受了中国写意画的影响,用笔用色抒情、放纵,随意而潇洒。至少说它和中国的写意画相通。他的画解放了欧洲画家谨慎小心的精神状态,不在于描摹对象,而重在抒发个人的感情和意趣。塞尚成为了西方现代艺术之父。其实,塞尚写意式的绘画,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十分普遍。他只学了一点皮毛,便成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
杜尚虽然是有争议的人物,但他早期的作品也是西方传统式油画。如《薄兰韦勒的风景》《两个裸体》。后来他画《春天,抑或在春天的年轻女子们》,便用中国画式的线条。《下楼的裸女》等则用直线了,也改面为线了。
……
西方绘画和中国绘画的最根本区别就是:西方画用面去表现物像,而中国画是用线去表现物像,“骨法用笔”成为中国画的重要法则。包括空中的云,一片一片,本无线,而中国画也用线条表现;水也是无线的,中国画也用线表现。现在只要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各美术馆中去看看,西方的近现代画家的作品,凡有新意的,差不多都是用线去造型,都是受了中国画的影响而如此。
2013年、2015年北京举办的国际双年展中,很多外国画家的画都用线去表现,都酷似中国画。朱德群、赵无极在中国学习西画,跑到法国去,他的油画无法赶上西方的油画。走投无路中,他们又转向中国的传统,从中国画传统中找到了形式和灵感,于是创作出有别于西方传统式的新的艺术,成为法兰西艺术院士,他们的画也一直为法国很多画家所学习,成为一时风尚。在北京的双年展中,我们看到法国参加展览的画家作品,差不多都是朱德群式、赵无极式,从中也可见中国艺术的间接影响了。
还有很多的西方艺术家,借用中国书法的形式去创作新形式的绘画。那些满纸满油画布上重重的黑杠杠,深厚而有重量感,表达什么,我看不懂,但其形式都来自中国的传统书法,那是一目了然的。美国很多研究家都发现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现代艺术是受中国艺术的影响。2000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中,其展览前言中终于承认:美国很多现代艺术是受中国书法的影响而成功的。但美国和欧洲很多艺术家虽然借用中国书法的形式,而他们对中国书法的内涵和奥妙根本不知。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限于篇幅,便不再一一列举。但西方近现代艺术的成功,至少说西方重要画家的成功,是受中国艺术的启发,引导乃至示范作用已经十分清楚了。没有中国传统艺术,便没有西方艺术的现代局面。
当然,西方画家中也有不少不太重视借鉴中国画的线条法形式的,但其作品新意皆不大,绘画成就也非太高,至少说不能和毕加索、梵高、马蒂斯等相比。
二、中国画论一直居世界画论之先
中国传统艺术一直居世界艺术潮流之先,也一直引领着世界艺术的发展。公元初至5世纪,亦即至今2000年至1500年间,中国的艺术家就知道:模拟真实(自然)非艺术的本质。汉人就知道“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1]杨雄:《法言》。书画表现的是自己。更早一点,《庄子》就知道,作画者必须身心自由,不为权势所迫,不受各种约束,方为“真画者”[2]参见《庄子☒田子方》。。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便认为“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3]刘安:《淮南子☒修务训》应该以神写形,神比形更重要。到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期间,画论上对传神的认识,刻画人物内心世界,表达人物的身份,对道、理、情、致、法的认识,书画是传达自己的感情,写的是自己等等;画可见之物简单,重要的是画人能想象到的,但看不到的境界等等;都有深刻全面的认识。一直到现在,全世界的绘画理论都无法超过中国那时候的理论。[4]详见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
在西方,绘画就是写形,仅供眼睛享受,后来变为视觉冲击力。而中国画重在“写心”“写情”“写趣”“畅神”等。丹纳说:“绘画是供养眼睛的珍馐美味。”[5]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71-172页。还有:“画只为眼睛看,音乐只为耳朵听,不这样做,就等于没有完成任务。”[6]《欧美古典作假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李健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78-180页。而中国画家认为“目”是“陋目”。画的是“道”,是为了“畅神”,为了“媚道”,不是只画见到的东西,还要画见不到的东西:头脑中想象的东西。唐代符载云:“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知夫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在心中),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与神为徒。若将短长于隘度,算研蚩于‘陋目’,凝觚舐墨,依违良久,乃绘物之赘疣也。”[7]《唐文粹☒观张员外画松石序》。“目”是“陋”的,看不到全面,更看不到背后的东西,尤其看不到人头脑中想象的东西,但中国画可以,画家要“与神为徒”,朱景玄说:“伏闻古人云:‘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8]《唐朝名画录☒序》。在西方,画家必须重目,目无所见,笔无所画,形便无以立。如是,则没有立体派和现代派也。宋·欧阳修《盘东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吴昌硕说:“老缶画气不画形。”这都是西方画家在文艺复兴及以前所不知的道理,当然也画不出来。
早在1600年前,宗炳就说:“山水以形媚道”,“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1]见宗炳《画山水序》,载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王微则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2]见王微《叙画》,载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太虚”之体是看不到的,因为“目有所极”,但却能画出来,而且绘画“岂独运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3]见王微《叙画》,载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王微还大谈,“画之致也”,“画之情也”。[4]见王微《叙画》,载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这都是古代西方画论中所无的。
中国画不是以画形为尚,宋人陈与义还说:“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5]陈与义《和张矩臣水墨梅五绝》之一,见《宋诗钞》卷四十二《陈与义简斋诗钞》。九方皋相马,把马的毛色都看错了,把黑马看成黄马,把公马看成母马,其实他不注意这些细节。但却看到了马实际是个千里马。画中国画也如此。一眼看去,雅?俗?不必细看形色,也不必细看用笔,便见到格调高、雅、低、俗,雅就高,俗就低。当然这要很深的功力,尤其要很深的文化修养。形、色弄错不要紧,关键在内涵,内涵就是修养,表现出来的就是雅和俗。写作、作画,重在人格的修炼,性情的抒发,思想的表达,有时还要“载道”。 而西方画家到了14世纪,还在讨论画家要做大自然的儿子,还是孙子,而且结论是孙子。最有名的画家达芬奇说:“绘画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唯一的模仿者。……因为它是从自然产生的。为了更确切起见,我们应该称它(绘画)为自然的孙子。因为一切可见的事物一概由自然生养……所以我们可以公正地称绘画为自然的孙儿……”[6]《达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17-18页。西方人最崇尚的苏格拉底说:“绘画是对所见之物的描绘,……借助颜色模仿凹陷与凸起,阴影与光亮,坚硬与柔软,平与不平,准确地把它们再现出来。”[7]《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朱光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0页。
达芬奇阐述:绘画要像镜子那样真实的反映物像。他说:“画家……他的作为应当像镜子那样,如实反映安放在镜前的各种物体的许多色彩。”[8]《达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镜子为画家之师。”[9]《达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安格尔是法国古典主义画派的领袖人物,1829年起任美术学院副院长、院长。他的言论影响颇大,也十分有代表性。在《安格尔论艺术》中,他说:“只有在客观自然中才能找到作为最可敬的绘画对象的美,您必须到那里去寻找她,此外没有第二个场所。”[10]《安格尔论艺术》,辽宁美术出版社,1970年,第20页。他又说:“造型艺术只有当它酷似造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把它当成自然本身了时,才算达到高度完美的境地。”[11]《安格尔论艺术》,辽宁美术出版社,1970年,第22页。他更说:“眼前没有模特儿时永远不要画。无论是手,还是手指头都不该仅凭记忆来画……”[1]《安格尔论艺术》,辽宁美术出版社,1970年,第179页。而中国画则是主张画主观的,不主张对着模特儿作画,主张“目识心记”。而中国画家认为画由画家心生,由个人意识重铸而成。西方画家还在复制真实。从希腊到文艺复兴到安格尔,那么多画家,虽有天才之质,但并无天才之迹,他们的作品只是真实,充其量是“天能”。后来,他们从中国画中找到出路。
西方各类现代派所画的不同于传统的画,立体派把“目有所及,故所见不周”的地方也画出来;老虎、蜘蛛、女人画在一起。女人的乳房放在抽屉内,头长在胳膊上,人的面上有一飞鸽等等,这些都不是目所周见的。早在中国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就有“无形因之以生”“万类由心”“太虚之体”。到了毕加索才知道“我不画我看到的东西,我画我想到的东西”。西方的理论显然大大落后于中国,落后了一千多年。
三、西方大画家和大理论家早已推崇中国画和理论
其实,西方画家中卓越者,早已认识到中国画的先进性。法国巴黎曾被人称为是世界艺术的中心,那里确有一批真正有卓识的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他们的看法颇值得重视。他们是怎样评价中国画的呢?林风眠在1929年发表《重新估定中国绘画的价值》一文,并不止一次地介绍法国第戎国立美术学院耶希斯对他讲过的一段话:你可不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的传统啊!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当时法国真正的艺术家几乎都持这种看法。常书鸿的老师就告诉他:“世界艺术的真正中心不在巴黎,而在你们中国,中国的敦煌才是世界艺术的最大宝库。”常书鸿就是在法国了解到中国艺术的价值和地位,他毅然回国,投身于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的。
我在少年时代读过很多苏联艺术家对中国艺术的评价:“那惊人的中国画”“那伟大的中国画”之赞,至今犹记。苏联艺术科学院通讯院:B.H.彼得洛夫教授曾惊叹:“喜马拉雅山般宏伟的中国画。”并说,“中国画是哲学、是诗歌、是寓意的顶峰。”推崇之高,已无以复加,凡是有相当造诣的艺术家无不对中国艺术刮目相看,推崇备至。
贡布里希(Gombrich)是西方最著名的美术史家和美术评论家,中国画界现在正掀起一股贡布里希热。贡布里希谈到中国书法艺术时说:“有位女士在宴会上问,要学会并能品味中国的草书,要多长时间时,韦利(Arthurwaleg)答道:‘嗯——五百年。’注意这并不是相对主义的回答。如果有谁懂行的话,那就是韦利。”[2][英]贡布里希著:《艺术发展史》,范景中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400页。可见其对中国艺术的心仪程度。
前面说过,毕加索认为“中国的字都是艺术”,而法国的真正大家认为中国画理论十分精妙,连六祖的《坛经》都是绘画理论(按中国最早的绘画理论实是玄学理论)。1949年,著名画家吕无咎女士在高雄举办个人画展,招待会上,她说:当年她在巴黎留学时,因系学习近代印象派的画,故与法国新派画家往还,经常互相观摩,共同讨论。因为她是中国人,也时常谈些中国画理,大家都非常尊重她,视之为中国画理的权威。一次,有位年事甚高、名气颇大的印象派老画家前来移樽就教,拿了一部六祖《坛经》请她讲解。吕女士翻阅一遍,十分茫然,讷讷不能置一词,只好推说不曾学过。那位画家大吃一惊,问道:“你们中国有这么好的绘画理论,你都不学,跑到我们法国来,究竟想学甚么呢?”[1]引自《禅宗对我国绘画之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1987年,第227页。
这个“名气颇大的印象派老画家”也确实深懂中国的《坛经》和中国的“艺术”。《坛经》中说的皆是深懂艺术真谛的艺术家所应该进一步知道的理论。如《坛经》中说的:“不离自性,自是福田。”(《行由品第一》)“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行由品第一》)“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行由品第一》)“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行由品第一》)“自悟自解”(《行由品第一》)“自悟自度”(《行由品第一》)“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顿渐品第八》)“道由心悟”(《护法品第九》)“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付嘱品第十》)“安闲恬静,虚融澹泊。”(《付嘱品第十》)吕无咎为了去法国留学,精力用在学习法语和西洋画上,对中国的理论反而不懂。可这位法国的老画家看到了中国的理论之高深处。他说:“你们中国有这么好的绘画理论”,说明他对《坛经》早有研究。一个画家学习绘画理论,连《坛经》都读了,其他画论想必也都研究过。
不但《坛经》是“好的绘画理论”,《金刚经》《心经》也是绘画理论。再早一点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更是“好的绘画理论”。《老子》书中讲:“五色令人目盲”,“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有无相生”、“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复归于朴”等等。《庄子》书中说:“五色乱目”(《天地》)“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刻意》)“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庄子》书中处处都是最好的绘画理论。后代文人画画,其实就是以老、庄思想为指导的。
四、由自信到自卑的原因
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2]这里说的“五四”,不是指1919年5月4日那一天,而是指“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画家对自己的艺术本来也是十分自信的,而且对外国的艺术也很看不起。按道理,中国写意画草草而成,两点便是眼,半似半不似,当看到外国的油画,精细而逼真,如镜取影,应该十分惊讶佩服才对。但是他们却不屑一顾。清代画家邹一桂论“西洋画”是“虽工亦匠”。他在其所著《小山画谱》中专列《西洋画》一节,谓之:“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3]邹一桂:《小山画谱》,《画论丛刊》下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806页。
这就代表当时画家对待西洋画的态度。西洋画不但“虽工亦匠”,而且“不入画品”。说明当时画家对自己的传统还是很自信的。
另一位清代画家郑绩著《梦幻居画学简明》,其中把“西洋画”视为“夷画”,古人将野蛮而无文的鄙人称为“夷”,他说或云:夷画较胜于儒画者,盖未知笔墨之奥耳。写画岂无笔墨哉?然夷画则笔不成笔,墨不见墨,徒取物之形影,像生而已。儒画考究笔法墨法,或因物写形,而内藏气力,分别体格,如作雄厚者,尺幅而有泰山河岳之势;作澹远者,片纸而有秋水长天之思……夷画何尝梦见耶。[1][清]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画论丛刊》下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55页-556页。
郑绩称中国画为“儒画”,认为“夷画何尝梦见耶”。也是对自己的艺术十分自信的。
松年是中国清代蒙古镶红旗人,善画花鸟山水,师法白阳(陈道复)、青藤(徐渭)诸家,其所著《颐园论画》,其中论到西洋画:“西洋画工细求酷肖,赋色真与天生无异,细细观之,纯以皴染烘托而成,所以分出阴阳,立见凹凸,不知底蕴,则喜其工妙,其实板板无奇,但能明乎阴阳起伏,则洋画无余蕴矣。”又云:“昨与友人谈画理,人多菲薄西洋画为匠艺之作。愚谓洋法不但不必学,亦不能学,只可不学为愈。然而古人工细之作,虽不似洋法,亦系纤细无遗……可谓工细到极处矣,西洋尚不到此境界。”[2]松年:《颐园论画》,《画论丛刊》下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623页。“板板无奇”“无余蕴”“匠艺”“不必学”“不能学”“不学”,这是松年对待西洋画的态度。
总之,西方油画自明代传入中国,虽经西方传教士的鼓吹,但在国内,还没有画家对它推崇。反过来,都是十分鄙夷的,谓之“不入画品”,“不能学”,以至于清代前期,西方的画家来到中国,如郎世宁(意大利米兰人)、王世诚(法国人)、艾启蒙(波西米亚人)、安德义(意大利人)等等,不得不放弃西洋画,而改学中国画了。
到了民国初年,一部分画家开始鼓吹或学习西洋画,但立即遭到一些遗老和国粹派的攻击。后来的金城也说:“即以国画论,在民国初年,一般无知识者,对于外国画极力崇拜,同时对于中国画极力摧残。不数年间,所谓油画水彩画,已无人过问,而视为腐化之中国画,反因时代所趋而光明而进步。由是观之,国画之有特殊之精神明矣。”[3]金城:《画学讲义》,《画论丛刊》下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742页。
其实“对于外国画极力崇拜”之现象,并没有绝迹,而且其势越来越大。康有为、陈独秀、吕澂等倡于前,徐悲鸿、林风眠以及岭南派等等弘于后。陈独秀在《美术革命》中说:“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徐悲鸿要以西方素描为基础,林风眠要“调合中西”,岭南派要“折衷中西”等等。正如林纾所云:“新学既昌,士多游艺于外洋,而中华旧有之翰墨,弃如刍狗。”[4]林纾:《春觉斋论画》,《画论丛刊》下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628页。
一时间,有能力的学人画家多出国留学,中国传统艺术渐渐被人冷落。留学回国者即教以外国技法,鼓吹外国画。不仅绘画、文学、医学、社会风气,都开始西化。中国固有之伟大而崇高的旧诗被西方式的简单的自由体新诗代替,伟大的传统中医被西医代替,人的服装、发式、用具、建筑等等都被西式所代替。新文化运动变为西化运动。
为什么一切都是西方的好,而中国的都是落后的呢?盖因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打了很多败仗。于是大家先是认为中国科技落后了,船不坚,炮不利。甲午战争后,大家又认为我们的制度落后了,继而,又认为我们的文化有问题,文化也落后了。民族虚无主义、自卑心理占了上风。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必须西化,甚至全盘西化。当然,科学、民主方面,西方是先进了。船坚炮利是他们打胜仗的原因之一,但文化也落后了吗?
实际上,中外历史上,先进文化的民族被落后文化的民族打败是常事。文化落后的民族往往崇尚武力,文化先进的民族崇尚文明,反对武力,儒家学问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去兵”,崇尚礼义。所以,中国打了败仗,而被当时的学者认为是文化落后了。这也是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
中国在世界上的先进,特别表现在文官治政,在西方最早实行文官治政的是英国。英国承认是学习中国的,并说中国的文官治政早于他们六七百年,其实早于他们两千年。西方一直由贵族和教会把持政权,学习中国的才改为文官治政,现在全世界先进国家都实行文官治政,中国是导先路的,当然,西方在文官治政方面又更加完善了一些。中国画从理论上、实践上也一直是先进的。前面已叙述清楚。
五、中国画应该怎样发展
如果说现代中国的艺术有些贫乏的话,那恰恰是因为丢掉了自己的伟大传统,生搬硬套外国的形式所致。日本当代美术评论家吉村贞司的一段话最可发人深省了,他说:“我感到遗憾,中国的绘画已把曾经睥睨世界的伟大的地方丢掉了。每当我回首中国绘画光辉的过去时,就会为今日的贫乏而叹息。”[1]《宇宙的精神,自然的生命》,《江苏画刊》1985年第5期。
这话讲得太确切,也太沉痛。学习外国是正确的,反之,外国也学习我们。譬如日本,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同时也保留自己优秀的传统(这传统也包括从中国拿去的传统)。日本人称为“和魂汉才”,后来学洋,又称“和魂洋才”。汉才、洋才,但魂必须是大和族(即日本),未尝丢弃自己的魂啊。西方人学习中国画,也保留自己的长处。而我们一学习西方,首先就要打倒自己的传统。“五四”那一批人要“全盘西化”,要把中国的线装书全都丢到茅厕坑里去。中医也不科学,文言文、格律诗也下流,而且甚至连汉字也要废除。钱玄同认为仅废除汉字还不行,必须把汉语也废除。陈独秀主张先废除汉字,暂保留汉语,胡适也赞成先废除汉字,然后再废除汉语。“凡事要有个先后”,差不多所有的新文化运动人物都主张废除汉字。
汉字废除,书法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中国人很奇怪,认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先破坏自己的,新的自然就立起来了。果能如此吗?旧的打倒了,新的未必建立起来。即使建立了新的,损失太大,也未必比旧的好。比如你住的很传统的宫殿,十分优秀,但你把它炸掉,也许你马上就无法居住,侥幸未被冻死,再去借债建起新的房屋,也许差之旧房甚远。“五四”以后几十年间,中国人大肆破坏自己的传统,以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五四”打倒孔子、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废除读经,到80年代,自己大讲中国画已“穷途末路”了。这在外国都是没有的。当然,外国某些势力也会行施一些阴谋,有人甚至提出世界艺术一体化,以达到文化侵略之目的,但关键在我们自己。20世纪30年代,美术史研究家兼画家郑午昌的一段话倒颇有启发,他说,外国艺术自有供吾人研究之价值,但“艺术无国界”一语,实为彼帝国主义者所以行施文化侵略之口号,凡有陷于文化侵略的重围中的中国人,决不可信以为真言。是犹政治上的世界主义,决非弱小民族所能轻信多谈也。盖实行文化侵略者,常利用“艺术是人类的艺术”的原则,冲破国界,而吸集各民族之精神及信仰,使自弃其固有之艺术,被侵略者若不之疑,即与同化。如现在学西洋艺术者,往往未曾研究国画,而肆口漫骂国画为破产者。夫国画是否到破产地步,前已述之,唯研究艺术者,稍受外国文化侵略一部之艺术教育之熏陶,已不复知其祖国有无相当之艺术;则中国艺术之前途,可叹何如!郑午昌这段话谈的是文化侵略问题,但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任何国家的艺术都和这个国家一样,如果要想在世界上出人头地,那就必须在牢固地守住自己的传统的基础上,再强烈地吸收别国的有益成分。如果丢弃自己的传统,一味地模仿人家,数典忘祖,那就永远赶不上人家。何况中国的艺术本就有伟大的传统和被举世公认的高峰。
而中国的艺术,只要文化在,它就永远在;只要人的性情不同,精神不同,所表现出的艺术就不同,虽然是很微妙的。“文以载道”,道在,文(画)也就永远在。
而且,西方的艺术每出现一种新的形式,总要解构他人,总要颠覆前人;而中国的艺术,凡有新意,凡有很高文化价值者必以继承前人为基础,然后再谈发展。解构、颠覆是有限的,颠覆完了,便无法再颠覆。而中国的继承也是无限的。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艺术也愈来愈厚,愈有文化内涵。
所以,当西方艺术终结时,中国艺术仍然会自然的发展,永无终结。
当然,中国画家也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和“曾经睥睨世界的伟大的地方”才行。
*本文根据作者近期系列演讲整理而成。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禾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