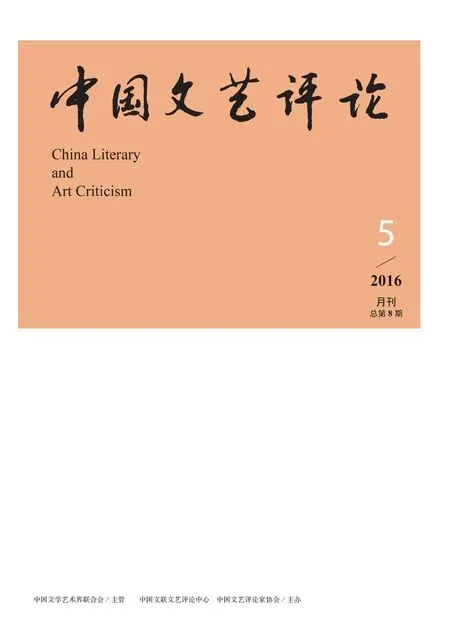近年来国产电影的表演美学及文化分析
厉震林 罗馨儿
近年来国产电影的表演美学及文化分析
厉震林 罗馨儿
一、2012-2015年国产电影表演美学谱系
2012年到2015年,是“疯狂”的电影的“疯狂”年代。国产电影在一种复杂的作用力场中,以空前的速率刷新着各项指标和数值的涨幅。或许从诸多层面来看,电影的新时代已然来临,许多新模式和新命名,在这几年里蔚然成风并逐步突显。
一是电影工业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和重组,尤其是电商资本的融入,以全产业链的方式,真正打通了生产和销售的命脉,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先后成立影业部门,将电影及其背后的生态圈纳为新一轮行业竞争的阵地;二是故事创意和艺术概念成广为争抢的电影创作的制高点,2015年影视行业内热门的关键词——“IP(知识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充分说明了下一步的产业趋势;三是电影的创作人员不再仅限于“科班”“专业”,风口浪尖的弄潮者们其原本的身份属性大相径庭,仍不妨碍“业余者”去“引领”专业人士;四是电影宣传、发行和传播形态的改变,互联网、跨文化、自媒体、全媒体、用户时代等改变当代人生活方式及思维模式的技术革命产物,也深刻地促进着电影市场的扩张和电影产业的转型。
在此,中国电影走过了市场复苏和市场膨胀的历程,成为“热钱”竞逐的文化产业支柱,成为深入大众生活方式的精神消费品,成为世界范围内传播国家形象和文化输出的通道。然而,日渐刷新的年度票房增长率和总值是否代表着中国电影的真正胜利?产业的一片涨势是否能够置换出等量的文化价值?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电影究竟在创造出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些关乎中国电影精神等级和市场品质的重要命题,依然亟待认知与破解。
电影表演是一个接通艺术形态和人文风貌的特定通道,它将具体真实的形象和人性镶嵌进工业生产和意识形态的“端口”,形成具有特殊质感的人文“模型”。2012年到2015年期间,电影表演美学的整体情况也是兼容和整合在文化、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国际因素、跨地域与跨文化等多元交织的“力场”之内的。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经历了六个阶段,即戏剧化表演、日常化表演、纪实化表演、模糊化表演、情绪化表演和仪式化表演。而近年来的国产电影表演,主体依然处于仪式化表演,是一种受到多元影响与多力竞合的末期阶段,充满交接效应和探索模式的动态呈现。仪式化表演是“使表演人偶化了,是仪式的一种形象手段。表演无需内心深度,使表演的演绎空间受到局限,而更重要的是明星身份,成为仪式图谱中的身份亮点以及东方人的脸谱代表”[1]厉震林:《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论纲》,《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85-89页。。在这样的表演美学总谱下,具体考察每一年的整体电影表演艺术,能够发现一条清晰的“精神成长影像”。
2012年是国产电影经受严峻外部挑战的一年,放宽的进口电影政策将国产电影置于更为自主也更为艰难的竞争环境里。面临来势汹汹的“对手”,国产电影表现出自觉意识和自我重估,向内探索的创作倾向使得电影表演也呈现出自我重塑的整体形态。对本体的审视和重估,具体表现为对质朴内向的生活化表演的回归,《搜索》《一九四二》《白鹿原》《我11》《万箭穿心》等影片代表了此年度电影表演美学的发展,代表着对先前夸张与浮华的仪式化表演弊病的纠偏。
2013年占据主流美学部位的电影表演形态是“轻”表演,这与时代的渴求与欲望有关,也是受到“台式”美学风潮的影响。清新简朴和爽朗明快的艺术风格实际上体现了“减法”的内在发展规律,《人再囧途之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图》《致青春》《中国合伙人》是“轻”表演的最佳注脚;同时,也不乏《一代宗师》《无人区》《厨子、戏子、痞子》《天注定》这样具有较重分量的力作。
2014年则涌现了较多人文化与内省化表演的突出成果,这是前几年“商业挤压”后在表演美学形态出现的必然。凭借《白日焰火》获柏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廖凡,凭借《一代宗师》荣获包括第5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等12座影后大奖的章子怡,在第51届金马奖中因《一个勺子》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以及因《军中乐园》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陈建斌等,都意味着人文化表演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文化输出和文化认同。此外,《归来》《推拿》《亲爱的》《黄金时代》《一步之遥》《太平轮》等重要影片也是体现2014年表演美学的重要样本。
到了2015年,表演则较为呈现出平民化身份和个人化叙事,具有较之以往更为强烈的“草根”情结和怀旧色彩。主要表现为《山河故人》《心迷宫》《刺客聂隐娘》《我是路人甲》等文艺片表演,以及《港囧》《夏洛特烦恼》《滚蛋吧!肿瘤君》《煎饼侠》等喜剧电影的表演。
从上述四年的电影表演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表演格局:相当一批成熟的优秀演员,能够在不同类型和氛围的表演中把持住自己,保持艺术创作的持续高水平,这其中包括陈道明、倪大红、张国立、张丰毅、葛优、陈建斌、冯远征、张涵予、黄渤、廖凡、王景春、王千源、王志文、吕中、巩俐、徐帆、郝蕾、章子怡、赵薇、周迅、赵涛、颜丙燕等;另外,还有一批演员在不断的类型化表演中重复与加深,也逐渐形成了带有个人身份标识的表演风格,比如徐峥、王宝强、郭晓冬、秦昊、孙红雷、刘烨、段奕宏、邓超、郭涛、张译、佟大为、余男、周韵、宋佳、白百何、王珞丹;然而,年轻演员相对而言表现则不够稳定,要根据具体作品或导演的“调教”来评价其艺术水准,个人风格也尚未稳定,如黄晓明、冯绍峰、郑恺、范冰冰、汤唯、张雨绮、倪妮、杨幂等。实际上,高速与批量化的工业式产出,必将会带来电影在艺术形态上的重复和文化情怀上的“悬浮”,演员在商业价值和明星效应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涨程度时,其“身价”与“身手”之间形成的“剪刀差”,也成为中国电影结构性问题的表现之一。
目前的表演艺术有着“两端运营”的美学倾向,具体可描述为互为反向的两种表演风格,在年代区间内此消彼长、彼此超越、互为补充,既无高低之分,也无前后之别,形成了双轮前进的态势。此前的六大表演形态,都可视作艺术发展的深层规律在不同社会、历史和人文环境下的外在表现。在2012年到2015年这个特定的区间里,具体呈现为纪实性表演与魔幻性表演、“轻”表演与“重”表演的这两对动态延展方向,共同构成了这一阶段中国电影表演的整体美学性格。
二、文化纵轴:纪实性表演和魔幻性表演
纪实性表演和魔幻性表演分属于纪实性美学和奇观化美学的不同范畴,在中国电影表演史上各有一条有迹可循的发展脉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关于巴赞、克拉考尔纪实理论的译介文章出现,对中国电影产生影响。80年代风行的纪实性表演,体现着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电影美学内部的强烈需求以及创新理想。而到了新世纪,在技术、文化和市场的三重推进下,中国电影出现了奇观电影的美学现象,魔幻性表演也走向了“大表演”的概念,体现了特定时代在数码技术催生下的表演美学“冲动”。从文化纵轴来看,纪实性表演和魔幻性表演始终呈现出了矛盾而又统一的格式,交织形成了中国电影表演的独特美学风格以及艺术方法,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东方美学交融而成的美学特征。
从电影表演角度而论,由民国时期多元混杂的表演形态,到“十七年”既朴实又概念的表演美学,发展到“文革”时期的“古典浪漫主义”表演状况,电影表演的非生活化的戏剧化倾向一直占据主体,因而20世纪80年代时期出现了纪实美学思潮下的“还原生活”的纪实性表演阶段。新世纪以来,仪式化表演占据了表演艺术的强势地位,并在不断升级的“中国式大片”中愈演愈烈,因而近年来对纪实性的反思与回归,也是出于拨乱反正的艺术需求和内在律动。梳理近年来的国产电影创作可以发现,新世纪前10年大量涌现的玄幻武侠题材的古装大片在数量和质量上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回落,此消彼长,一批反映人文现实、日常生活的影片一洗此前在市场上和口碑上的失落面貌,也让国产电影的表演艺术在通往深度模式及其历史隧道的进程之中,以一种保守和内敛的姿态,进行重新评估与出发。
从具体作品来看,纪实性表演有以下两种呈现形态。
一是时代背景下的真实个体。在这类用个体境遇的具体真实来折射时空特性的影片中,纪实性的表演被笼罩在整体情境的真实感之下,表演任务主要在于将“此时、此地、此人”的风貌准确并且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成为国民形象与时代人格的影像化记录。其中,很多演员的角色都有原型,在艺术创作中如何将人物的味道和生活的质感传达给观众,给演员功力带来了较大考验。较为杰出的代表作品,有以西南地区的“大三线”作为故事背景,讲述青春期少年成长历程和集体记忆的影片《我11》。以武汉这座都市为空间背景,借一个普通女性的悲剧命运折射市井万象的影片《万箭穿心》,其中,女主角颜丙燕凭借与角色浑然一体的高超演技,获得了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等8个奖项。用日记体的形式,客观真实地表现内蒙古鄂尔多斯因公殉职的公安局长郝万忠的传记故事的影片《警察日记》,主演王景春凭借对主人公人格的透彻展现,斩获第2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讲述“打拐寻子”社会现象的影片《亲爱的》,塑造了一批形象各异的年轻父母群像,黄渤、郝蕾、赵薇、张译等优秀的中生代演员用质朴而投入的状态,将各自角色塑造得具体可感,尤其是饰演村妇的赵薇,实现了表演生涯的突破。
二是架空背景中的人性标本。这类影片的时空背景通常被架空化或者模糊化,只作为一个寓言的情景,让故事中的人性得以相对独立以及自足自闭地充分展现。因此,相关的纪实性表演更为偏重艺术范畴里的真实,甚至较为抽离,只对呈现当下的某种具体人性负责,故而可被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观照价值的精神标本,在表现国民人格的集体无意识时,可以用抽象避免琐碎。描述一群老人任性地“逃离”老人院,追寻梦想的影片《飞越老人院》,由许还山、吴天明、李滨、田华、牛犇、管宗祥、仲星火等数位中国影坛重量级老年演员担任主演,这本身就是影坛的一桩“现象级”盛事。老演员们纪实化的表演中带有抒情与诙谐,将一个有些残酷的命题演绎得充满人情味和人性美。表现盲人推拿师生活的影片《推拿》,以职业演员和盲人演员共同塑造的人物群像书写出深厚而幽微的群体性人文内涵,影片进而具有了一种文化人类学的内涵。秦昊、郭晓冬、梅婷、黄轩、张磊用特殊的表演方式和呈现手段,配合导演高度风格化的镜头语言,赋予了全片独一无二的视觉质感,令人过目难忘,让这一特殊群体的真实人性和生命脉动为更多的观众所知悉。影片《一个勺子》讲述了一个具有循环结构的荒诞寓言。“勺子”是西北方言中“傻子”的意思,陈建斌饰演的农民“拉条子”淳朴、善良而又一根筋,打乱他平静生活的“傻子”(金世佳饰)突然到来又突然离去,“拉条子”在被动、茫然和不解中不断地发问,总是陷入“呆照”和“呆立”的表演,充满荒诞性和可解读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左右出现了一种新的纪实性表演分支,即综艺电影表演,如《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这些改编自综艺节目的电影,是近两年电视综艺真人秀收视火爆的后续产品,在呈现方式上介于综艺节目、纪录片和电影之间,也因其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与传统电影的差异而引起社会的争议与讨论,构成了一种新的现象以及命名方式。影片中的演员进行游戏参与者和自身明星身份的双重扮演,比起艺术创造,他们更多地是在社会表演学范畴内的加魅化行为。在更广博的艺术语境中看,综艺电影体现了当代艺术的交叉、跨界与融合的特点。这一类纪实化表演,也不能完全沿用传统的艺术发展体系和美学格式来裁断,而要纳入社会角色的文化建构性和规定性来考量。
与纪实性表演形成两极分立形态的是魔幻性表演。魔幻性表演是新世纪奇观电影的仪式化表演在近年的区间段中较为多见的一种形态,包括身体表演的极度奇观化和加魅化;演员的表演如同可以搓揉的“面团”以及魔幻的“神者”;演员与数码技术“融合”表演。由于东方民俗神秘的美学形态和功夫片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程度,能够为西方视野所注意,成为他们猎奇和欲望的对象。同时,古代题材与主流意识形态能够保持一定的时空上的疏离,这种分裂属性也是后来导致奇观修辞偏离了电影艺术核心本体部位的原因之一。同样,表演也就被架空为奇观声画的一个功能性部件,观赏性成为最大的考量因素,可以被色彩、构图和影调等其他声画要素所遮蔽、割裂与稀释。2012年至今,可以在魔幻性表演中看到动作电影以及喜剧电影在表演艺术上的“惯性”,也能发现一些将此类表演从技术语汇转化为美学肌体,从前卫姿态转化为传统形态,从平面态度转化为深度模式的尝试。这意味着中国电影发展到现阶段,逐步浮现出对精神定力、人格素养和文化等级的强烈诉求。具体包括以下两类:
一是动作电影的魔幻性表演。动作电影作为奇观电影的一大重要类型,将一直会占据国产电影票房排行前列,然而,过度堆砌与叙事无关的武术炫技表演和动作场面也成为此类影片为人诟病的“沉疴”。近年来,可以看到由动作身体转到人格世界及社会属性的策略倾向,如《一个人的武林》《战狼》等,发出了对武者灵魂的自问或者拷问,提高了动作演员对内心深度开掘的表演要求。但是,对于大部分动作电影来说,武打身体主要还是代表着一种身体的表现力以及诉求张力。管虎执导的影片《厨子、戏子、痞子》是一个抗日题材的动作片,处理得富有黑色喜剧感,影片的表演中杂糅着京剧表演、歌舞伎表演、舞蹈表演、民族表演、丑角表演等多元形态,配合惊悚的动作场面,造成目不暇接的观影感受。上映63天累计票房接近24.4亿的古装奇幻片《捉妖记》,是2015年最受关注和讨论的影片之一,也是一部艺术和产业大融合的超级文本。真人动漫CG技术的大量使用,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施法、念咒、捉妖、打怪等“伪民俗”动作包装下的好莱坞动画式的故事内核,增强了影片的神秘感和奇观效果。《捉妖记》中呈现出来的特效表演是影片整体创作效果的必然要求,较之以往的同类型影片,体现出了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为复杂的概念建构。
二是喜剧电影的魔幻性表演。这一类影片在表演上的共性,是要给主人公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最高任务或者贯穿的动作线,将表演重点放在情绪渲染和强烈的效果上,具有非自然主义倾向的风格化、技术化和魅力化的美学特质。内地电影的喜剧表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香港电影中“无厘头”表演风格的影响,多见夸张、脱线、自我解嘲等表现,有时甚至走入“癫狂”和“过火”。2012年到2015年期间,喜剧电影表演艺术形态上相对单一,多以闹剧或者浪漫喜剧为主,尤其是《泰囧》的成功,引发了诸多企图“复制”的尝试。冷幽默、黑色幽默、肢体喜剧、乖僻喜剧(神经喜剧)等其他典型的喜剧片形态尚属少见,也没有出现像曾经的“冯氏贺岁喜剧”那样具有人性温度和时代气息的感性力作。《泰囧》之后时隔3年问世的《港囧》可视作是一次电影文化品牌的“跟进式”创作,其产业上的意义高于艺术上的价值。徐峥、包贝尔、赵薇、杜鹃所代表的内地表演与王晶、林雪、葛民辉、李灿森、苑琼丹等极具“城籍”风格的港式表演相得益彰。“他者”视角中的港式表演承担着叙事与造型之外的怀旧功能和陶冶功能,与片中的诸多粤语流行乐插曲一样,代表着集体文化记忆。姜文导演的影片《一步之遥》则是艺术形态多元和美学追求较高的一部喜剧,影片的表演将诸多元素按照艺术需求拼贴、重构和虚拟一种想象性的现实,显得异彩纷呈而又特立独行,可以看到话剧表演、文明戏表演、默片式表演、纪录片表演、歌舞表演、海派清口等多元的美学痕迹。
三、时代截面:“轻”表演和“重”表演
同有着纵向文化轴线的纪实性表演与魔幻性表演相异的是,“轻”表演和“重”表演更多地反映为在时代截面上的一种相对形态。尤其是近年来“轻”表演的大行其道,与消费社会、产业趋势、流行文化、偶像经济等即时性因素的关联较大,因而呈现出横向延展开去的笔触与画法。这一方面是艺术美学内在律动的外在呈现,另一方面与大众审美诉求相符相应,是时代渴望的表情与表演。新世纪以来,电影行业整体“力学系统”被注入大量的能量,再加上对诸多“他者”电影艺术形态的“接收”和“误判”,投射到表演这一艺术局部时往往显得动能充沛而又激情饱满。“轻”表演与“重”表演,实际上就是两种对表演能量的处理和使用方式。
“轻”电影或“轻”表演伴随着中国电影类型化操作的日渐成熟而蔚然成风。但实际上,国产电影的“轻”形态的出现,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文化成因和社会心理,它与中国的文化发展前进步履和开放程度同步,从中可以看到与台式“小清新”、“韩流”视觉艺术、日系文艺片、欧美流行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态之间的交织现象;以及节约观念、“减法”美学、集体怀旧心理、“萌”文化、“都市病”、异域景观、身体叙事、“粉都(fandom)效应”、“男色消费”“眼球经济”等群体性的“有意识”以及“无意识”,因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系统与产业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轻”电影的概念,主要是针对具有“导演大多是新人、普遍为中低成本制作、主题都比较轻松、娱乐性强、能卖座、看电影的观众偏年轻”等特征的影片[1]连春华:《2013电影学术年会聚焦“轻”电影》,《中国银幕》2013年第11期,第12页。。较为典型的代表作品有《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一夜惊喜》《非常幸运》《青春派》、《小时代》系列、《被偷走的那五年》《后会无期》《匆匆那年》《我的早更女友》《撒娇女人最好命》《重返20岁》《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滚蛋吧!肿瘤君》《夏洛特烦恼》《左耳》《栀子花开》。通过以上事实还可以发现,“轻”电影往往成为跨界导演或者跨媒介电影的“试水”对象,成因可堪寻味。
“轻”电影的表演大致上具有两种形态:
一是作为想象性解决的途径。商业社会所生成的消费文化很直观地反映出社会的心理需求,“轻”电影出现的最大作用力之一是“社会趣味”。“轻”电影繁荣的文化成因和社会心理,是大众渴望在观影体验中得到想象性解决的内容,也是时代繁荣之下的大众对清新气息的渴求,因而“轻”表演在角色塑造和表演基调上,更贴近时下都市大众的欲望对象、生活常态和心理节奏。演员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主要是反映“80后”对大学生活的集体回忆和今昔对比,怀旧的基调下显现了一定程度的清新感。在主要演员的选择上,杨子姗、江疏影、刘雅瑟、韩庚等新人演员奠定了全片的表演风貌,即青春味道和热血气质。新人演员在演技上的不足,使得演员以生命体验为出发点,见天性、见自然、见真心。《北京遇上西雅图》则采用误入迷途的“白雪公主”被平凡的“毛驴王子”拯救的罗曼史内核,加之异国风景、异国生活方式和异国价值观的文化冲撞。“文艺女神”汤唯与“落魄大叔”吴秀波的设置和搭配,产生了一种幽默而脱俗的喜剧效果。汤唯的表演放松而灵动,吴秀波的表演含蓄而淡雅,整体上形成一个具有美学可读性的“轻”表演经典文本。
二是成为景观叙事的部件。“轻”电影的影像画面大多美轮美奂、赏心悦目,映射着现代人的生活图景,同社会风尚形成既迎合又引领的互文机制。很多“轻”电影都选择在国内外名城或者名胜取景,很多甚至将情节背景设置在异域景观下。如此使“轻”表演更加强调造型功能而非叙事功能,富有身体美学的观赏性,与景观美学和谐统一,显现出了一种较为显著的时尚感和美感。作为《小时代》主要情境的当代上海是一个超级都市空间,对奢华景观的展示与堆砌构成影片里所聚焦的“真实”。画面中的演员形象突出、造型精致、妆容艳丽,表演则以“走秀”和“作态”为主。全片整体艺术构思的特殊性和目的性,自然导致表演创作重点的位移。《后会无期》的散文化和片段化的智慧内涵,要优于影片本身的艺术水准。赛车手韩寒的“公路情结”和对野外空间的感受成为奠定影片开阔和寂寥的画面基调。演员的表演任务除了叙事和抒情之外,还应符合韩寒式的狡黠、清高与落拓感。另外,《非常幸运》中的新加坡都会地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中的布拉格风情,《重返20岁》中的身体年龄与心理年龄的反差错位,《栀子花开》中的女版“四小天鹅”与男版“四小天鹅”交织映衬等,这些与常规生活拉开距离的景观叙事,都是富有典型性的“轻”表演培养皿。
“重”表演并非与“轻”表演相伴而生的对立形态,而是具有严肃态度、学术重量和深度模式的表演现象的总合。“重”表演不是单指“用力”甚至“用力过猛”,而是一种向角色内在深处的探索、富有人文关怀、精神指向和哲学意味的表演形态。其在学术和理论方面的研究价值,往往高于娱乐价值和泛情价值。从表现对象的年代时期层面,可以将“重”表演归为以下两类。
一是对历史人物的“人文考古”。在“历史人物考古”的影视文化浪潮中存在着传奇化和文化型的两种不同创作策略,前者主要是追求故事性和可看性,其文化价值相对滞后;后者则是注重历史人物的重新阐释,甚至是颠覆性的解构和建构。“重”表演中,文化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主要表现在挖掘和塑造具有年代性的人物身上深层次的传奇色彩、时代质感、人格密码和文化价值。表现抗日战争时期河南旱灾的影片《一九四二》,集结了张国立、徐帆、张默、李雪健、陈道明、范伟、张涵予、冯远征等国内顶级优秀演员阵容的倾情出演,形成了一组分量厚重的角色群像,将灾难面前的人性种种演绎得令人动容,极富感染力。勾勒民国武林群像的《一代宗师》历时多年精心打磨,甫一问世就得到了观众和学界的好评。梁朝伟、章子怡、张震、王庆祥、张晋等主要演员用稳扎稳打的功力和沉静入定的表演,共同还原了特定时代和特殊身份的人物的精气神,显得血肉饱满而又气度非凡,配合富有智慧的台词和极具表现力的镜头语言,营造出全片高超的艺术境界。反映“文革”中后期一个普通家庭悲欢离合的《归来》,以洗尽铅华的面目,用一种摆脱了庸俗化的温情细腻的方式,塑造出一对在时代变迁和人情冷暖中坚定不渝的知识分子夫妇形象。众多实力派演员在平实而克制的总体美学路线下,对特定年代的人物质感拿捏准确、一步到位。
二是对当代人格的人文解码。在当代题材影片中,如何衔接地气、富有人文关怀和哲学形态地表现人物,是优秀的“重”表演需解决和说明的问题。优秀的演员,可以通过表演而触碰到现代人格中最微妙与最深刻的部位,甚至是一些“痛点”,从而使电影表演从艺术作品变成当代人文图景和精神面貌的形象标本。《白日焰火》是一部气质强劲、叙事精巧、元素杂糅、质感粗粝的黑色侦探电影。具有多年艺术积累的廖凡抓住张自力这个人物兽一般的形象本质,寻常状态的潦倒窝囊与职业生活的精悍老辣之间转换自如、逻辑流畅和情感到位。同样是犯罪题材的《烈日灼心》中,三位主演郭涛、邓超、段奕宏共同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奖,这种情况较为罕见,但也代表了业界对影片表演整体上的肯定。在这部充满了阴暗、焦灼和凶险氛围的影片中,每个人物的性格、状态以及诉求交错其中。三位主演分别完成了人物从平面到深度的多维立体刻画,互相之间的对手戏也充满张力,完整而饱满地将那种如临深渊的境地传递出来,具有感染力和凝聚性。
此外,一直以“重”表演为主的主旋律电影,在近年来的艺术创作中也显示出诸多“新配方”或者“新转向”。《钱学森》《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天河》《西藏天空》《永远的焦裕禄》《黄克功案件》《百团大战》《战火中的芭蕾》等,都在尝试以新的历史观和美学观来描述主流思想价值下的故事。在“重”表演和创意性的文化元素之间,建立传奇而又充满人性深度的有机人物性格,运用文艺化、类型化、加魅化、视觉化等多元表演风格充实主旋律人物的性格质感,达到更为深厚和微妙的人文内涵。
四、国产电影表演结构性问题
综上所述, 2012年到2015年是中国电影发展较为关键及其问题较为集中的时间段,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以及相应表演艺术呈现出一定的新面貌和新高度,但是,国产电影表演依然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的问题。
一是目前的表演美学形态中,整体上依然较为浮躁,娱乐型表演和煽情型表演较为普遍,思想型表演或有出现,启蒙型和哲学型表演更是凤毛麟角。对于演员来说,“艺人化”的思想倾向和行为方式普泛化了,所以生产出来的艺术只能是取悦于人,只有以“文人化”为人格坚守的演员,才能在目前文艺精神等级普遍下滑的状况中起到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启蒙的作用。
二是整体面貌较为模糊,尚未形成更清晰、更具有代表性和概括性的表演模式。近年来的电影表演中,电影人格还不能准确地提纯出存在于当代人意识和无意识中的精神面貌,以及形成对自我形象的体察、自我身份的确认等具有代际意义的艺术言语方式。
三是跨文化与“交织化”的特性越来越明显,但是,多停留在模仿和直接移植的阶段。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深入,多种多样的地域地区的艺术形态为国人所熟知和接受,但是,很多优秀的表演理论和表演实例还需要进一步消化和吸收,才能成为真正滋养中国电影表演的“养料”。
四是后劲略显不足,成熟演员表演水准趋向平稳,完成度虽高,但是重复多,突破少、惊喜少。中生代的青年演员发挥水准不够稳定,表演的亮点存在着偶然性和随机性。新人演员青黄不接,或者说更多具有才华的新人缺少能够施展和发挥的平台。当工业操控对于表演资源配置起到了绝对的决定作用时,只会多有明星阵容组成,少有演员人格构成;强调表演现象的片段享用,而不在意表演形态的集体沉淀。
厉震林:上海戏剧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馨儿: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