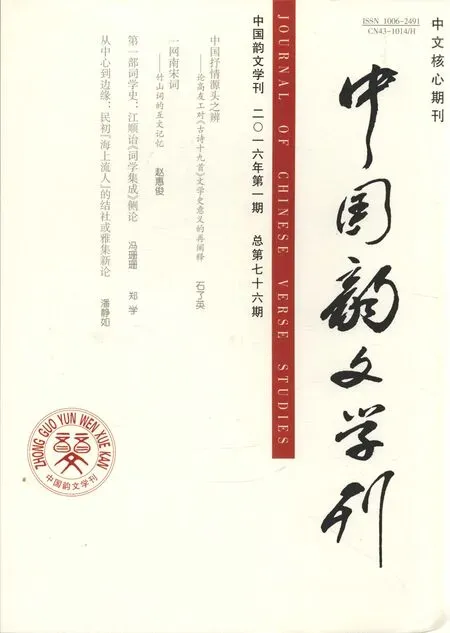杜甫从秦州到巴蜀荆湘的地理感知与文化体验
田峰
(伊犁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杜甫从秦州到巴蜀荆湘的地理感知与文化体验
田峰*
(伊犁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辞官离开关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西南漂泊生活,这段生活经历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使他的诗歌在题材方面颇多开拓,而且在艺术手法上更加高超。这当然与杜甫从秦州到荆湘独特的地理文化体验有关。杜甫对秦州的感知更多的是边塞文化,秦州的边塞气象在杜诗中较为独特,是清新秀丽与苦寒寂冷的矛盾统一;诗人对巴蜀的感知主要集中在成都和夔州,成都给诗人的感觉是气候宜人,环境优美,但作为军事界线与文化界线的西山一带令作者时刻觉得身处异域。杜甫对夔州的体验是地理的僻远与文化的疏离,这是诗人漂泊西南以来最为深刻的地理文化体验;杜甫对荆湘的感知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地理文化的南界。
杜甫;秦州;巴蜀;荆湘;地理;文化
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离开关中,途经秦州到达蜀川,后又辗转至荆湘。在这段漂泊的行程中,杜甫不断体验新的地理环境,文化心态也随之变化。诗人远离大唐文化的中心地带,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新的环境与国家、个人的前途命运交织在一起,使杜甫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应该说,在这段行程中杜甫始终体验着“边地”的地理风貌与文化疏离之感。这种地理体验与文化感知对杜甫诗歌的题材及其艺术创作手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杜甫对西北边塞的感知
“边”与“塞”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边”是与中原相对而言的,指的是靠近边疆的地域,基于地理方面的考量居多;“塞”主要指因国土安全需要而在边疆地带修筑的防御工事,基于文化方面的考量居多。关于“边”和“塞”的界定,时人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当以时人的地理感知与文化体会为主。杜甫作为唐代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中包含了诸多与边塞有关的作品,他对边塞的地理感知与文化体验自然与其他诗人相比有很多不同。
我们知道,唐代的边塞随着唐代疆域的盈缩不断变化,在杜甫的感觉世界里,疆域变化所带来的体验是明显的。从翻越陇山的那一刻起,诗人便感觉到了边塞的气息。这种感知既有基于前人的认识,又有新的认知。旧识新知叠加在一起,在杜甫的感觉世界里“边塞”有了新的内涵。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之地多陷吐蕃,唐代西北的疆域范围不断缩小,先前作为地理疆界的陇山一下成了非常重要的军事防御线,边塞的文化意味不断加强。陇山属六盘山南段,横亘南北,是关中与陇右的天然分界线,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界线。此处是杜甫西行非常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作为“塞”的意义是明显的。行到陇坂,杜甫显得极为犹豫,他在《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中这样写道:“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①(清)仇兆鳌著:《杜诗详注》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本文所引杜甫之诗皆出自该本。在度过陇坂关口的时候,诗人用了“怯”、与“愁”二字来表达自己忐忑不安的愁绪,而当看到“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的景象时,滞留这里的心思大打折扣。作者在过青阳峡时,陇山的高峻犹历历在目:“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华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壮观,已谓殷寥廓。突兀犹趁人,及兹叹冥莫。”(《青阳峡》)一旦听闻陇右的烽烟消停,杜甫便觉得“渭水逶迤白日净,陇山萧瑟秋云高”(《近闻》) ;杜甫在蜀川听到朝廷在边地打了胜仗,喜吟“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喜闻盗贼总退口号》) ;另一首诗《夕烽》写道:“夕烽来不近,每日报平安。塞上传光小,云边落点残。照秦通警急,过陇自艰难。闻道蓬莱殿,千门立马看。”显然,在杜甫的感觉世界里,陇坂具有地理与军事的双重意味,也是一道心理防线。陇坂地屏关中,通巴蜀,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读史方舆纪要》:“陇坻,即陇山,亦曰陇坂,亦曰陇首,在凤翔府陇州西北六十里,巩昌府秦州清水县东五十里。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汧、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1](P2464-2465)《元和郡县图志》载:“陇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每山东人西役,升此瞻望,莫不悲思。”[2][P982]陇山是兵家要地,关中门户,险要高峻,所以在杜甫的感觉世界里这里既是地理的悬隔,也是文化的界线。
处在陇山之西的秦州,向来是守卫这道屏障最为主要的城邑。杜甫到达秦州时,是吐蕃对河西、陇右争夺最为激烈的时期,杜甫所谓:“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卷七《遣兴三首》其一)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六盘山、陇山以西及四川盆地以西的大部分地区为吐蕃所占领。越过陇山,杜甫到达了秦州、同谷一带。初到秦州,诗人便感觉到地理人文环境的全然不同。秦州一带自古胡汉杂居,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杜甫的《寓目》这样写道:
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
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
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
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
诗歌首联写物产的不同,颔联写地气的不同,颈联写文化的不同,尾联写自己的感受。作者完全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总瞰秦州,初来乍到,这里的环境与作者先前所生活的环境差异极大,置身其中,感觉大为不同。
首先,秦州、同谷在安史之乱后作为边地,在杜诗中这里“边”与“塞”的意味非常明显,如:
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秦州杂诗》其四)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秦州杂诗》其六)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秦州杂诗》其七)
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秦州杂诗》其十)
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低。(《秦州杂诗》其十一)
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秦州杂诗》其十八)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月夜忆舍弟》)
数奇谪关塞,道广存箕颍。(《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其二)
水净楼阴直,山昏塞日斜。 (《遣怀》)
含星动双阙,伴月落边城。 (《天河》)
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
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 (《初月》)
宁辞捣衣倦,一寄塞垣深。 (《捣衣》)
塞上传光小,云边落点残。 (《夕烽》)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 (《病马》)
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 (《送远》)
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 (《别赞上人》)
杜甫在秦州一带深切感受到了边地的风物,诗中所言鼓角、胡笳、塞云、戍鼓、塞日、暮云、塞垣、关塞、关河等都是典型的边塞意象,这组意象给人以苦寒、凄清之感,与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所烘托的氛围大体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这里对边塞的体验与唐代边塞诗中典型的荒漠沙碛体验又不尽相同。秦州、同谷一带,降水量充足,植被丰富,气候宜人,在地理感觉上并非荒凉、苦寒,杜甫这里对边塞苦寒的感受更多是文化层面的。因为这里胡汉杂糅融合,所以杜甫诗歌中的胡笳、胡马、白刃、鼓角、羌笛、戍鼓、羌女、胡儿、骆驼、蕃剑、孤戍等意象,基于文化方面的感受居多。尽管诗歌中也出现的一些自然意象具有边塞意味,但这些意象并不是边塞所独有的,如,塞柳、寒菊、寒月、陇草、塞田、胡雁等意象,只是将文化感知叠加在了一些物象上,从而给人一种荒凉之感。
其次,从自然环境来看,秦州处在秦岭的最西段,自古以来以秦岭为南北方在西段的分界线,物产、植被、气候等既有南方特色,也具有北方特色,杜诗中又尽显秦州一带温婉秀丽的一面,如:
清溪含冥寞,神武有显晦。 (《万丈潭》)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
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秦州杂诗》十二)
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秦州杂诗》十四)
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
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秦州杂诗》十六)
檐雨乱淋曼,山云低度墙。
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秦州杂诗》十七)
溪回日气暖,径转山田熟。
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赤谷西崦人家》)
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 (《宿赞公房》)
出郭眄细岑,披榛得微路。
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屡渡。(《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
石间见海眼,天畔萦水府。 (《太平寺泉眼》)
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 (《山寺》)
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 (《空囊》)
隔沼连香芰,通林大女萝。(《佐还山后寄》其三)
这样的描写在杜甫秦州一带所写的诗歌中随处可见。这里清泉绕山,松柏苍劲,片云卷舒,菊院莲池,完全是一派风光旖旎的南国景象。但当作者听到远处的戍鼓羌笛,看到眼前羌女胡儿,才意识到这里是边塞。这种双重体验,在陇右的其他边城中并不多见。
可以看出,杜甫在秦州一带的边塞书写,与高适、岑参有关西域的边塞诗有所不同。高、岑之边塞诗所书写的重点是西域的苦寒、荒凉,风格雄浑壮大;而杜甫在秦州一带的边塞书写除了苦寒、荒凉的书写外,也有清新秀丽的书写。甚至在同一首诗中也能反映他的这种双重体验,他在《雨晴》诗中这样写道:“天外秋云薄,从西万里风。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此诗吟咏秦州的初晴景象,既有西风、胡笳、高雁等边地景象,也有雨后柳翠梨红的清新,读来别有风味。
在唐人的心目中,塞是非常重要的地理文化分界线,秦州、同谷等陇右之地,距离长安极近,又与胡地接近,因此在文化上甚为特殊。杜甫身在其中,一方面感觉着山峦叠秀的诗情,另一方面又体验着戍鼓狼烟的塞外荒凉,诸多地理体验事实上是一种文化感知。
二、杜甫对巴蜀的感知
巴蜀地处长江上游,是指大巴山及其以西的区域,北以秦岭为界,西以西山为界,南以大渡河及长江干流为界,包括山南西部和剑南道,是相对封闭的一块地理单元,文化上具有整体性。杜甫跋山涉水来到巴蜀,对这里开始了全新的认知。
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经过崎岖艰险的蜀道,到达成都寻觅安身之所。安史之乱后的蜀川,与北方相比这里的局面安定不少,杜甫除了在宝应元年(762年)避乱梓州、阆州外,大多数时间都在浣花溪边的草堂度过。初到成都府,杜甫对这里最为直接的感受就是山川之异,他在《成都府》中说:“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地理环境与关中和秦州又大为不同。在气候方面蜀地与北方差距极大。春夏湿润多雨,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风雷飒万里,霈泽施蓬蒿”(《大雨》) ;秋天凉爽雨多,所谓“飞雨动华屋,萧萧梁栋秋”(《立秋日雨院中有作》),“雨声传两夜,寒事飒高秋”(《村雨》) ;当然,最让杜甫印象深刻的是成都的冬天,所谓“季冬树木苍”(《成都府》),“甲子西南异,冬来只薄寒”(《重简王明府》),“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大雨》)。正因为气候宜人,所以这里的动植物也更加丰富,这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大量表现。
即使是物产丰富,环境优美的成都府,也常常使杜甫感到不安,因为在杜甫眼中这里依然是边地,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偏僻。他在诗歌中经常流露出这偏远的感觉,如,“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田舍》) ;“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遣兴》) ;“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寒食》) ;“卧病荒郊远,通行小径难”(《王竟携酒高亦同过》) ;“兵革未息人未苏,天子亦念西南隅”(《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 ;“乡关胡骑满,宇宙蜀城偏”(《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野望》) ;“层城临暇景,绝域望馀春”(《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 ;“白雪避花繁,结子随边使”(《甘园》)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天边行》)。杜甫用僻、偏、远、遥、隅、绝域、天边等字词表达着一个北客对成都的感受。甚至有时杜甫以“塞”来理解成都府的偏远,他在《立秋雨院中有作》云:“山云行绝塞,大火复西流。”这种偏远感觉的由来,一方面与成都远离中原,道路崎岖,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唐代在西南的疆界有关。
杜甫到达蜀川之后,对边界最直接的感知是西山,这里是汉蕃非常重要的军事分界线。唐代的西山通常被认为是成都平原以西,大渡河、岷江上游诸山的泛指,并非是具体所指,《资治通鉴》记载了陈子昂有关西山的上书,胡三省注云:“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统诸羌州,皆西山羌也。”[3](P6455)浦起龙《读杜心解》中说:“西山,即松、维等州诸山。”[4][P462]大体而言,西山包含了松、茂、维等州的诸多山脉,即今之川西北的岷山。西山是非常重要的界山,是西控吐蕃的要冲,《旧唐书》云:“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5](P4519)《钱注杜诗》引李宗谔《图经》云:“岷山巉绝崛立,实捍阻羌夷,全蜀倚为巨屏。”[6](P436)松州被围时杜甫作《西山三首》,对西山作为地理文化的界线感受尤为强烈,其一:
夷界荒山顶,蕃州积雪边。
筑城依白帝,转粟上青天。
蜀将分旗鼓,羌兵助铠鋋。
西南背和好,杀气日相缠。
西山险峻参天,白雪皑皑,而在文化上西山是夷夏的界山,界东界西判然有别,守卫此地自然是极为重要的,杜甫所言“辛苦三城戍,长防万里秋”正体现了唐代对这一边防线的重视。这一意象在杜诗中屡可见及,如,《军城早秋》:“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由于西山常年积雪,杜甫所在的成都府又很温暖,所以远在府西北的白雪在视觉上给诗人以强烈冲击,他在诗歌中以“雪岭”这一意象表达自己的感受,岭东的成都府与雪岭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其三),“西岭纡村北,南江绕舍东”(《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门前是绿水东流,透窗远眺却雪拥西山。《怀锦水居止二首》其二:“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雪岭与锦城在一线之间,然景观迥异,这种差异造成的结果就是昔日的形胜繁华之地,尽显寥落。当然,自然景观的差异背后是文化的差异,《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赠蜀僧闾丘师兄》:“青荧雪岭东,碑碣旧制存。”雪岭将华夷割裂,岭东旧制犹存,水通东吴。当吐蕃进逼之时,对雪岭的防守就显得极为紧迫,杜甫所言“雪岭防秋急,绳桥战胜迟”(《对雨》),“闻道君牙帐,防秋近赤霄。下临千仞雪(即雪岭),却背五绳桥”(《寄董卿嘉荣十韵》),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雪岭之急也意味着江城所急,《岁暮》:“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但当西山兵事稍缓的时候,在成都府确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有诗为证:“雪山斥候无兵马,锦里逢迎有主人。”(《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二)
永泰元年(765年)五月杜甫离开成都,沿岷江南下,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九月到达云安,因病在云安修养,到永泰二年(766年)春移居夔州,在夔州居住近两年,创作四百三十多首诗。夔州位于渝东北,临荆楚,控巴蜀东门,形势险要,为通吴之要塞。夔州虽与成都相去不远,但地理文化却差异很大。杜甫夔州诗涉及夔州的山川、历史、人物、风土、神话等诸多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因素,在唐宋时期的夔州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杜甫《峡中览物》中所言“形胜有余风土恶”可以看作是他对夔州地理文化的总体评价。
杜甫初到夔州,就对该地进行了全方位的书写,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夔州歌十绝句》,这组诗主要写夔州的山川形胜、历史文化及风土人情。在这组诗中作者对夔州地理景观与文化景观的体验是初步的,个人感情色彩较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在某些方面有极为明显的体验。首先,与成都温和的气候相比,夔州明显不同。在夔州的气候体验中,杜甫感受最强烈的就是热和瘴。作者在《雷》《火》《热三首》《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等诗中不厌其烦地叙写自己的毒热难耐。这里的瘴气虽没有岭南的那么让人恐惧,但依然引起了杜甫的注意,他在《闷》中道:“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十月一日》:“有瘴非全歇,为冬亦不难。”《不离西阁》其一:“地偏应有瘴,腊尽已含春。”《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瘴余夔子国,霜薄楚王宫。”宋人李复《潏水集》说:“夔居重山之间,壅蔽多热。又地气噫泄而常雨,土人多病,瘴疟头痛脾泄,略与岭南相类。”[7]正是对杜甫诗歌中关于夔州气候的很好注脚。
其次,杜甫对“边”的感受比成都府更为强烈。与成都相比,这里不仅与中原相距更远,而且夷汉文化杂糅的程度更甚,这里的“边”比成都的“边”更边。这从他的诗歌中一些措辞即可看出,《江月》:“天边常作客,老去一沾巾。”《夜二首》其一:“蛮歌犯星起,空觉在天边。”诗人用“天边”表达渐行渐远的苦闷。“绝”与“塞”二字似乎更能体现杜甫对夔州僻远的认识。有时候杜甫以“绝”来描述夔州的偏远,如,《奉送十七舅下邵桂》:“绝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远游临绝境,佳句染华笺”;有时候以“塞”来描述,如,《晴》其二:“雨声冲塞尽,日气射江深。”《秋兴八首》其一:“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与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七:“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社日两篇》其一:“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将“绝”、“塞”连在一起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如,《返照》:“衰年病肺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奉送王信州崟北归》:“故人持雅论,绝塞豁穷愁。”《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绝塞乌蛮北,孤城白帝边。”《社日两篇》其二:“欢娱看绝塞,涕泪落秋风。”
再次,漂泊西南以来杜甫对夔州的蛮夷文化体验最为强烈。唐代的巴蜀,地处西南一隅,由于山川交通的阻塞与长期夷夏混杂的局面,文化上相对独立,与中原颇为不同。符载在《为西川幕府祭韦太尉文》称:“国之西南,实曰成都,夷夏混合。”[8](P7086)《大唐创业起居注》:“三蜀奥区,一都之会,夷民纷杂,蛮陬荒梗。”[9](P49)杜甫未到达夔州之前,对夷夏混杂的文化现实已经有了认识,如他在成都所作的《江涨》:“江发蛮夷涨,山添雨雪流。”在梓州所作的《野望》:“山连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在渝州所作的《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这几首诗从地理上感觉夷夏之间的联系。《扬旗》:“三州陷犬戎,但见西岭青。”《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野膳随行帐,华音发从伶。”《愁坐》:“葭萌氐种迥,左担犬戎屯。”《阁夜》:“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这几首诗则从军事、文化的角度来说明夷夏文化的不同。
然而,在西南的蛮夷文化体验中,夔州让杜甫印象最为深刻。寓居夔州,不同民族杂居错处的现实,常常让诗人感到大为不同。这里形势险要,部族众多,正如杜甫所描写的:“峡口大江间,西南控百蛮。”(《峡口二首》其一)从杜诗来看,此地的主要部族有五溪、巴、獠等,其中獠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称呼,包括苗、瑶、越等部族,所以杜甫“西南控百蛮”的描写正谓夔州部族的复杂性。我们知道,杜甫在夔州时有两个家僮,男为阿段,女为阿稽,皆为獠人,他还有《示獠奴阿段》一诗。夔州固然有形胜之势,然独特的风俗,使杜甫感觉极为不适。他在《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中详细写了夔州风俗的可怪:
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
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
旧识能为态,新知已暗疏。
治生且耕凿,只有不关渠。
西历青羌板,南留白帝城。
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
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声。
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
这两首诗不仅写了夔人喜食粔籹、烧畬耕种的耕作习惯,而且还写了极为独特的龟卜和瓦占习俗。在饮食方面杜甫也极为不适,他在诗中所写的“山田饭有沙”(《溪上》)“苦厌食鱼腥”(《奉赠薛十二判官见赠》)及“敕厨或一味,求饱或三鱣”(《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时不时流露出对夔州饮食的不满。《雷》《火》二诗则描绘了夔人放火烧山以祈雨的祀俗。“殊俗状巢居,层台俯风渚”(《雨二首》),“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颠”(《赠李十五丈别》),反映的是当地人巢居野处的居住习惯。在《负薪行》中,杜甫描写了夔州的两类妇女:一类是男丁入伍、无法觅到郎君、抱恨独处的妇女;一类是在外从事体力生产,养家糊口而丈夫安坐在家的妇女。这两类妇女生活极为悲惨,杜甫给予极大同情;《最能行》则描写了文化教育薄弱、趋利从商的水手。王嗣奭认为这两诗“俱因夔州风土恶薄而发”。[10](P244)杜甫对夔州的乡曲俚乐也是深有感触,如,“蛮歌犯星起,空觉在天边”,“夷音迷咫尺,鬼物倚朝昏”(《奉汉中王手札》),“渔艇息悠悠,夷歌负樵客”(《雨二首》其二),“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阁夜》),“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社日两篇》其一),都是作者对夔州民歌的感受。
夔州的风土人情确实给杜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以诗歌的方式描摹了一幅别有风味的民俗长卷。对一地风土人情这样大量的描写,在杜甫其他地方的诗作中并不多见。夔州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在杜诗中表现得细致入微,的确是真切反映夔州现实生活的“诗史”。杜甫对夔州的地理文化体验,归根到底是一个身染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以中原文化为本位对“边地”的观察。
三、杜甫对荆湘的感知
荆湘地处长江中游,西以大巴山与蜀为界,南界五岭,东下吴越,其文化常常被判读为“楚地文化”。荆湘地区河流众多,湖泊星罗棋布,常年温润多雨,生态良好,动植物资源丰富。此地为楚人的发源地,文化神秘,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唐代很多诗人曾到达这里,体会楚地山川文化之异。大历三年(768 年)初,杜甫离开夔州沿江东下,开始了近三年的荆湘漂泊。杜甫在荆湘创作一百五十余首诗,诗歌中也不断流露自己对荆湘的地理文化感知。
作为唐代亲旅荆湘的诗人之一,杜甫对荆湘的地理文化体验与暮年垂病、不断奔波的个人遭遇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了新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荆湘很多诗歌是作于水上旅行途中,在旅行中偏僻的地理与暮年的内心孤独糅合在一起,颇有凄清之感。在古城店泛江途中,他写道:“老年长道路,迟日复山川。白屋花开里,孤城麦秀边。”(《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诸公》)行到松滋江亭写道:“今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泊松滋江亭》)在峡州写道:“春日繁鱼鸟,江天足芰荷。郑庄宾客地,衰白远来过。”(《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监湖亭泛舟》)在长宁写道:“天地西江远,星辰北斗深。乌台府麟阁。场下白头吟。”(《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在江陵附近舟行中写道:“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舟月对驿近寺》)“风餐江柳下,雨卧驿楼边。……飘泊南庭老,只应学水仙。”(《舟中》)在公安写道:“是日霜风冻七泽,乌蛮落照衔赤壁。酒酣耳热忘头白,感君意气无所惜。”(《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白头供宴语,乌几伴棲迟。”(《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从公安往岳州途中写道:“挂帆早发刘郎浦,疾风飒飒昏亭午。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十日北风风未回,客行岁晚晚相催。白头厌伴渔人宿,黄帽青鞋归去来。”(《发刘郎浦》)在潭州写道:“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蘋愁杀白头翁。”(《清明二首》其二)纵观杜甫在荆湘的活动,诗人似乎总是行走在水路上感受楚天风云的变化。一方面他在行进中不断观察楚地景观的变化,另一方面他又将垂暮之年的凄凉与风物描写相结合,使楚地风光皆着作者之色彩。
荆湘的气候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多有描写。最让杜甫感慨的是春天湘潭北部的花石戍,他对这里的暖春现象感到惊异,便作《宿花石戍》云:“午辞空灵岑,夕得花石戍。岸流开辟水,木杂古今树。地蒸南风盛,春热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气候何回互?茫茫天地间,理乱岂恒数。”诗人以一个北方人的身份观察这里的春天,春夏秋冬四时本是平分的,但是这里的春天却有夏天的味道,简直就是在乱天常。荆湘的气候给杜甫最深的感受是湿热,他在诗歌中多次描写了这里的湿热,如,《水宿遣兴奉呈群公》:“泽国虽勤雨,炎天竟浅泥。”《遣闷》:“暑雨留蒸湿,江风借夕凉。”《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须气郁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峯硉兀火云升。”荆湘之地的酷热潮湿令来自北方的诗人极为不适,而更令杜甫感到不适的是这种酷热卑湿外加瘴气、雾霾,这种天气在杜甫的诗歌描写中只出现在荆湘,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淫。”《江陵节度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赋七字句同作》:“楼上炎天冰雪生,高飞燕雀贺新成。碧窗宿雾蒙蒙湿,朱栱浮云细细轻。”《北风》:“春生南国瘴,气待北风苏。向晚霾残日,初宵鼓大罏。爽携卑湿地,声拔洞庭湖。”瘴气、雾霾、湿热对于一个北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深刻独特的体验。秋冬之季的荆湘,往往雨雪交加,时冷时热。洞庭湖及其以南的雪倒是一道别有韵味的南国景象。诗人在《北风》中写道:“洞庭秋欲雪,鸿雁将安归。”《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泛》:“涨沙霾草树,舞雪渡江湖。”《对雪》:“北雪犯长沙,胡云冷万家。”《岁晏行》则写得更有风味:“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在潇湘洞庭湖边,渔夫罟鱼与莫徭射雁两个场景与北风白雪的自然景象融合在一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自然民族风情画。
杜甫对荆湘方位感觉是极南,他在诗歌创作中,极为频繁地表达着作为“南边”的荆湘。有时,诗人用“南纪”、“南极”等词表达荆湘的偏远,如,《泊松滋江亭》:“今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暮楚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北辰征事业,南纪赴恩私。”《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南纪风涛壮,阴晴屡不分。”《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南纪改波澜,西河共风味。”《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南纪连铜柱,西江接锦城。”《北风》:“北风破南极,朱凤日威垂。”有时候,作者以“南征”“南客”“南国”“南斗”“南溟”等词表达荆湘的南偏,如,《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南征为客久,西候别君初。”《移居公安山馆》:“南国昼多雾,北风天正寒。”《官亭夕坐戏简颜十少府》:“南国调寒杵,西江浸日车。”《陪裴使君登岳阳楼》:“敢违渔夫问,从此更南征。”《南征》:“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宿白沙驿》:“随波无限月,的的进南溟。”《水上遣怀》:“一纪出西蜀,于今向南斗。”《遣遇》:“春水满南国,朱崖云日高。”《发白马潭》“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回。”《冬晚送长孙渐舍人归州》:“南客潇湘外,西戎鄠杜旁。”作者在不断向南行进的过程中,总是迟疑不决,极为无奈,如,诗人在《入乔口》中写道:“漠漠旧京远,迟迟归路赊。残年傍水国,落日对春晖。”黄生这样评价这两句:“步步入南,心心怀北,写出此行万非得已。”[11](P1974)的确,这种愈走愈南的现实,使诗人处处感觉到边地的气氛,且多有无奈之感。他在《楼上》写道:“皇舆三极北,身事五湖南。”就是入南与怀北之间的矛盾,而且兵戎交加的现实与边地环境相结合,使这里也有了朔风塞垣的边塞感。他的两首诗把这种氛围烘托得更加凄清,《夜闻觱篥》:
夜闻觱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
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欻悲壮。
积雪飞霜此夜寒,孤灯急管复风湍。
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
《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
朔风吹桂水,朔雪夜纷纷。
暗度南楼月,寒深北渚云。
烛斜初近见,舟重竟无闻。
不识山阴道,听鸡更忆君。
朔风、朔雪、塞曲多是北方塞外之地的地理文化景观,作者将这种体验移植到了南地,显然与这里“云山兼五岭,风壤带三苗”(《野望》)的边界感与异质文化感是分不开的。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对边疆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是防御性的,以维持现状为主,并不主张积极经营。这种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有的疆域空间逐渐变小,唐代很多诗人都有这种感受。杜甫从秦州到荆湘的这段飘泊生活,就是不断感知疆土空间压缩所带来的“边地”地理文化的过程。这种感知使他的诗歌不仅在题材方面有了很大开拓,而且艺术的提炼也越来越自觉。明人江盈科《雪涛诗评》说:“少陵秦州之后诗,突兀宏肆,迥异昔作,非有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少陵能象镜传神,使人读之,山川历落,居然在眼。所谓春蚕结茧,随物肖形,乃谓真诗人,真手笔也。”①(明)江盈科《雪涛诗评》,见于《中国诗话珍本丛书》(第十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页743。“秦州”原作“夔州”有误,与下文明言“蜀中山水”有矛盾,而《杜诗详注》卷八引用此条亦作“秦州”。可谓部分道出了杜甫秦州以后诗歌艺术上提高的原因。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清)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清)钱谦益.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宋)李复.潏水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清)董诰等编.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3.
[9](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清)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转引(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 李剑波
I207.22
A
1006-2491(2016) 01-0011-07
本文是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 13YJC751051)“唐代文学中的西域感知及地理意象”阶段性成果。
田峰(1980-),男,甘肃会宁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与文化。
——以清代与民国“秦州志”编纂为例
——评《产品包装设计( 第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