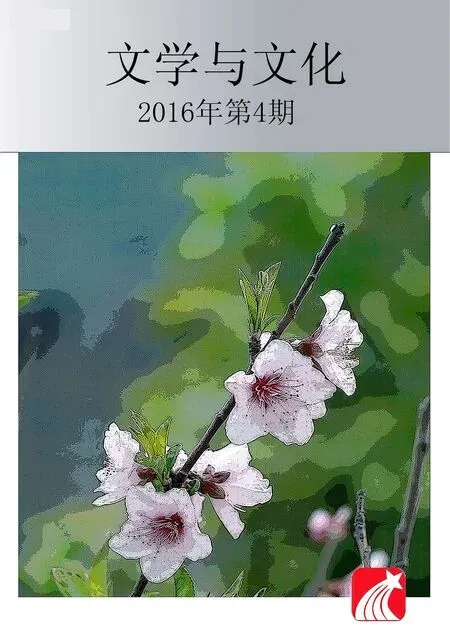当“新工人”①遭遇“梦想秀”
——一个文化研究的媒介分析实践
郭春林
当“新工人”①遭遇“梦想秀”
——一个文化研究的媒介分析实践
郭春林
当新工人遭遇日益资本化的电视产业,无论是新工人的生存境遇,还是新工人的情感诉求以及他们的文化理念,新工人面临的困境,都更加触目惊心地暴露出来。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是,除了无法拥有住房这一最大宗的生活资料外,其余生活资料的拥有状况也不可能有多好,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媒介生产及传播等方面的生产资料更几乎完全被资本和官僚集团以及技术精英集团所掌握。在这样的情势下,当电视节目将新工人及其文化生产作为再现对象的时候,新工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冲突更加显豁地呈现出来。本文通过对2014年5月北京皮村社区活动中心文艺小组成员参与浙江卫视节目“中国梦想秀”的遭遇的分析,揭示在主流媒介的生产和再现过程中被过度剥夺的新工人更加严酷的生存现实,同时,希望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视频在网络空间传播的反应,寻找新工人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可能性空间。
新工人中国梦想秀媒介分析文化生产电视
引言
新工人及其文化在当下媒体再现中的状况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学术自不能例外,文化研究就更不能例外。用文化研究方法,就某一个案进行媒介分析的实践似乎还不多见。
2014年5月23日,浙江卫视播出的第七季《中国梦想秀》②《中国梦想秀》是浙江卫视于2011年开播的一档综艺节目,至2015年已有9季。根据百度百科“快乐蓝天下·中国梦想秀”条目,“节目第一、二季的主持人为朱丹、华少主持,第三季两人相继退出,第四季以后由亚丽、陈欢、周立波黄金三角主持。第一、二季版权引自于英国BBCW频道的《就在今夜》,主打明星圆梦,主要关注普通人对舞台的渴望,对明星的崇拜与追求。节目第三季开始,放弃版权,由浙江卫视金牌团队重新设计,关注普通人更为平凡、更为贴近生活的的愿望,并加入梦想大使、梦想助力团概念,梦想大使一直由周立波第三季担当至今。节目中,普通人站上舞台,与梦想大使交流梦想,并通过梦想助力团投票,票数达到要求后,梦想则有可能实现。”2016年5月5日,该节目正式宣布停播。周立波除担任梦想大使外,还是该节目的创意总监。参看http://baike.baidu.com/link?url=nxixK5rtrXd-ZCgCnoCxywMRA2m1KIl1DVr1FqDIG Ov8nW5DDiPppgQlp8wuDWlpMDq_5-igHTU9fmAOr-Z9ceHfGFBfASjeR9LtIkpte7zAIHnEfge6HSfoQrHspARZp53pksh488E5e xyVvqXH9qwgvtbZVJ4n2BLLCz2zvSCSwifeQhzBC66_rfzwyNah。节目中,有一段节目是来自北京皮村社区活动中心文艺小组八位工友的表演。他们表演的是根据北京新工人艺术团核心成员之一许多①许多,浙江人,新工人艺术团(原打工青年艺术团)成员、发起人之一,2014年以来的三届“打工春晚”总导演。创作的《打工号子》改编的《打工者之歌》②原歌词是:“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我们热爱这生活,所以离开了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勤勤恳恳把活干;凭着良心来打工,堂堂正正地做人,谁也别想欺负咱,咱们有咱们的尊严。”改编的歌词是:“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我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毅然背上行李来城市闯荡,想学身技术,回家办个厂,带动俺们的家乡更加富强;我的工作是搞电焊,切割焊接努力把钱赚,一身的衣裳像张破渔网,裸露的皮肤像在上战场,咋的了,咋的了,过火了,哥们,打游击的电焊工就是这个样;我提着心,吊着胆,只为端好盘,稍息,立正,我就是小保安,风里去雨里来,说的是快递员,不停地穿梭在车水马龙间,临时工,不好干,没有合同,没保险,心中的梦想它何时能实现;我的家乡在湖北,常常梦里把家回,干的是电脑维修工,勤奋努力地向前冲;俺们两个是山东德州的,俺们两个在厂里头打工,俺们俩有个同样的梦想,娶个媳妇在城里安个家;我们是来自北方的姑娘,为了梦想和幸福在城市打拼,拥挤的车间有我们忙碌的身影,长长的流水线有我们挥洒的汗水,脱下了工装换上了春装,我们更是一道靓丽风景线。”,他们的“梦想”是为皮村社区活动中心添置一套能为两三百名工友演唱的音响设备。根据节目规则,表演者(就其“梦想”诉求而言,他们又被称为“追梦人”)表演结束后,全场投票,如果达到240票,则“梦想”立即兑现。如没有达到规定的票数,追梦行动一般即告失败,但也有柳暗花明的时候,梦想大使周立波可以使用反转权,一票否决第一次的投票结果,这时,第二次投票往往都能超过240票。在皮村工友的追梦行动中,第一次得票194,周立波使用了反转权,第二次289票,“梦想”实现。节目尾声,画面显示的是音响设备第二天就由梦想助力团成员之一的北京盈郎文化有限公司运送到了皮村。③视频字幕显示,本次梦想助力团共有三家单位,分别是金海岸(全称:杭州金海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盈朗文化(全称:北京盈朗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洋河股份,嘉宾方俊被誉为“中国电视舞蹈第一人”,做过多家电视台,包括央视舞蹈节目的艺术总监,并有方俊文艺创作中心及方昭舞蹈学校。
无论如何,就“结果”而言,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个底层民众借助电视的力量成功获得帮助的个案,它“再现”了主流媒体与资本集团合力参与慈善/公益④这个节目能否算公益节目,我无法确认,更多时候,它像慈善行为。我理解,慈善和公益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慈善是慈善家的行为,而慈善家都是成功人士,因而,慈善是捐赠、赏赐;但公益则是公共利益,普通民众均可参与,甚至有一些人毕生投身于公益事业。活动的行为,体现的是积极意义,是“正能量”。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未必。在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北京工友之家的吕途就发表了《仗势欺人的人肉大宴——评〈中国梦想秀〉第七季“打工文艺小组的梦想”》⑤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d0cea60101qzq2.html。的博文,对播出节目和节目录制过程中的一些“冲突”进行了批判和回应,博文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讨论。我将吕途博文的关键词归纳为两个:剥削和感恩。实际上,这两个语词正是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并造成冲突的关键词。仅就这两个关键词,我们也就大体能想象录制现场的冲突之紧张。无论如何,这是一档娱乐节目,“感恩”和“快乐”是它的关键词,从这一期节目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⑥参看http://vod.kankan.com/v/61/61825/403361.shtml?id=731015。下文凡引用节目中的台词等,均不另注。本期节目中的另外两组追梦人一再遭遇到周立波的追问,譬如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与其所救孩子的故事开始,周立波就问当事人:“这个梦想不难过吧?”第三个小节目中,“北京我的梦残疾人艺术团”的单腿舞者同样也被迫面对周立波这样的语言:“(我们)不会因同情给你掌声”。这样对待残疾人和幸存者是否合适是职业伦理和个人修养的问题,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娱乐节目所要求的“快乐至上”和“娱乐至死”。这其实也是我们时代最为普遍的精神特征,拒绝同情,拒绝沉重,给我快乐,给我轻松。但同时,很多人(包括中产和底层)以反对道德绑架的理由拒绝反思,拒绝媒体的这一种现实再现。需要说明的是,网址在互联网产业不断重组变化的商业化环境中,会不断变化,包括使用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在不同的网站搜索的结果也会不一样,一个电视节目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也必然与互联网的环境密切相关。。“剥削”这一政治色彩强烈的语词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娱乐节目的规范和氛围。有意味的是,节目经过后期“处理”还是如期播出了。虽然经过了“处理”,但节目仍然拥有较好的完整性。
在这个制作出来的“完整”节目中,哪些内容被“处理”了,编排的顺序是否有变化,依据什么原则?这些都值得通过这个看似完整的节目进行细致而深入的分析,而特别值得分析的是节目中的“反转”和“翻转”的关系。从剥削话题转换为感恩话题的翻转是如何完成的?反转权的使用与话题的翻转是什么关系?其中所表征的是怎样的冲突,是同一意义空间中的意义的争夺,还是两种不同意义系统之间的对抗?这两个不同的意义所属社会集团是怎样的?争夺或对抗的结果怎样?更重要的是,这一争夺或对抗仅仅发生在意义领域吗?如果不是,它与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存在怎样的关联?从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我们是否可能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生产及传播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角力进行归纳总结,进而进一步理论化?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将其作为文化研究媒介分析的有效实践对象。
上电视的权利
看起来,与越来越多的收费电视(包括视频网站收费)聚焦于中产阶层及以上家庭/个人的营销模式好像很不一样,但占有市场的根本目的其实并无实质性差别,这就是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打出“草根”、普通民众的旗号,选秀类、婚介类、综艺类,包括新闻类节目①收费电视的营销模式是现在流行的P2P模式,而电视以“草根”为号召,则是希望将一般民众一网打尽。而我所说的新闻类节目再现普通百姓,并非新闻内容关涉百姓,而是指在新闻节目的板块中,设置某一栏目,让老百姓自己说话。比如央视在节日里,通过公共空间中类似电话亭一样的设备,邀请路人进去,对着摄像头说话。还有一些类似街头调查一样的节目,颇为有名的是央视关于“您幸福吗”的调查节目。,更不必说近年发展迅猛的电视购物频道了。这一现象似乎标志着电视的普罗时代已经到来。然而,这一期“中国梦想秀”节目中的一个看似惹人发笑的细节却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在该段节目的后半部分,现场播放了五位工友的亲人对他们说话的视频。②节目中,八位工友中的五位有相应的视频,缺了杨诗婷、赵晨和王修财这三位的。但这些视频并非都是电视台提前录制,大多数是工友们请亲戚朋友帮忙用手机拍摄的。一位朴素的北方农村妇女,抱着一个孩子出现在画面中,工友苑伟被周立波叫出了队列。看着画面上的母亲和孩子,苑伟始终微笑着。母亲说:“大伟,你为家里打工不容易,你照顾好身体,家里爸爸妈妈很想念你,妈妈给你做不了鞋了,眼睛花了,老了,看不见了,(你)在外头买好鞋,买着穿吧。有空就来家来嘛,孩子挺想你。”这些朴实却饱含着深情的话打动了现场的观众,这是一个当代版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从播出的画面上可以看到不少观众在抹眼泪,他们被感动了。这当然是人之常情。但奇怪的是当事人苑伟却一直在微笑。主持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细节和机会,于是问苑伟。苑伟说,原来,他没有来节目之前,父母就给他打过电话,以为他被传销组织给骗了。此时,现场爆发出一阵笑声,周立波也笑了。苑伟接着说,“根本都不会让我上这儿来的,所以我就在想它是怎么拍的呢”。全场爆发出更大的笑声。而周立波的点评是,“你很有意思”。
这只是一个细节,但这个细节绝对不是一个“有意思”就可以了结。实际上,这八位工友能上电视,也确实经历了一番周折③参看刘知远:《虚伪的〈中国梦想秀〉惊醒工人一场梦》(http://opinion.m4.cn/2014-05/1232819.shtml)。,而这个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说原本是为了一种特定的效果,却在无意中将电视生产的一个秘密暴露了出来。这就是上电视的权利。
在苑伟父母这样的农民的理解中,显然并非什么人都能上电视;即使在一般城市市民的观念中,恐怕也并非人人都有上电视的权利。就一般意义而言,目前各级电视台和电视节目的门槛比二十年前已经低了很多。这既得益于电视产业的发展,各级电视台和电视频道的数量迅猛提高,电视节目虽然仍不够多样,但毕竟为更多的人进入电视提供了可能。这也得益于市场化的体制,市场既需要与众不同的看点/买点,也需要争夺收视率/观众,只要不触碰法律和国家政治以及公共道德底线,电视的生产空间看上去无比巨大。也正是在争夺更多观众的意义上,平民路线成为一个选择,毕竟占社会大多数的是普通民众,大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更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会坚持认为市场化生产了民主,但实际上其中隐藏的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这同样也得益于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理念,关注民生无疑是近年官方宣传颇多的主题。于是,一个被符号化/象征化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地成为电视的参与者,甚至主角。然而,苑伟的话和新工人这一次在梦想秀的遭遇就告诉我们,实际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上电视,“老百姓”这一概念在被抽象为一个集合名词的时候,也迅速被文化工业的媒体工业符号化/象征化,并进一步地被空洞化。因为像苑伟这样的新工人,就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约2.7亿,他们身上除了贫困和艰辛的生活经历外,既不具有意识形态的代表性/典型性,也没有多少媒体工业需要的故事。就电视娱乐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快乐和轻松,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的成功学案例,是与众不同并有看点的故事。而看点选择的主要参照是收视率,因为作为商品的收视率直接关系到广告收入。
这只是上电视的权利的一个方面。在理想的状态中,电视作为公共空间,对所有人而言,上电视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当代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商业化的电视媒介系统中,一方面,不可能因为群体数量的多寡而获得相应的分配比率,它有一系列明确或潜在的、必须符合的媒介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和规定;另一方面,成为电视节目的参加者,也有基本能力的要求,譬如表达能力就是其中一个颇为重要的方面。换言之,当电视作为文化工业的一种形式和一个部分的时候,必然对表达能力有要求,因为电视的时间在这个系统中早已被转换为金钱的数量,一个结巴的人,一个无法把自己的想法正常表达出来的人,无疑就是在浪费时间,而浪费时间也就是浪费金钱,除非节目特别需要这样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节目,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八位工友,包括他们的亲人,表达能力都不够好,甚至很差,除了来自黑龙江五常、身为网媒编辑的杨诗婷外。当年幼的姑娘有些冒失地一下子说出“剥削”这个敏感词,当他们面对周立波咄咄逼人的追问和霸道十足的抢话,在现场显然有些压抑的气氛中,紧张的他们就更无法将他们的想法很好地说出来,更何况要说清楚“剥削”,不仅仅需要经验和感受,还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而常识告诉我们,表达能力与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有关,虽然不能将其彻底普遍化,毕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表达能力差的大有人在,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因为教育体制及教育方法出了很大的问题。但就这八位工友而言,他们的表达能力普遍不够好,无疑与其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紧密相关。
我们当然要问他们为什么没能接受必要的教育,譬如即使不读大学,起码也应该读完高中。我们从画面的字幕中了解到,来自吉林的电焊工王修财年纪最大,40岁;杨诗婷31岁;来自甘肃白银的快递员李向阳29岁;组装工苑伟28岁;来自河南濮阳的木匠王宇27岁;来自德州的软包工李国富26岁;来自辽宁抚顺的服装店销售赵晨最年轻,只有18岁;而来自湖北公安县的电脑维修工林波则没有年龄介绍,看上去应该20出头。也就是说,八位工友中,一位70后,一位或两位是90后,余皆为80后。而从他们的出生地则可以看到,基本上属于老少边穷地区,从他们亲人说话的视频所呈现的环境也可以判断,他们的家境显然都不怎么好,甚至很糟糕,有些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且多是农村的场景。他们差不多在90年代开始读小学,倘使家境好,自己也愿意努力学习,应该能够在90年代末开始的大学扩招的市场化过程中,进入大学,哪怕是很普通的大学,甚至二本三本,即使不少二本三本院校毕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就随之失业,成为“蚁族”①“蚁族”是描述新世纪初主要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打工漂泊的大专院校毕业生生存状况的专有名词,他们在公司做的是最底层的工作,拿的是最低的工资,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根本买不起房价高得离奇的住房,甚至连市区月租千元以上的房子也住不起,只能租住在城中村、城边村,甚至城郊农村。参看廉思主编:《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但是他们未能走上这条路。
而且,这其中同样还存在9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一方面是城乡教育水平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却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锦上添花,再添花,却就是很少雪中送炭。农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产生了大量的失学儿童。这从一个相反的方向也可以看到其严重性,那就是希望工程的实施,此外还出现了不少类似“感动中国”中救助失学儿童的“当代武训”白芳礼老人②“当代武训”的提法究竟始于何时,一时无从查考,据百度搜索,最著名的无疑是天津老人白芳礼,此外有山东冠县(即武训故里堂邑县)的么富江、江苏镇江的邵仲义、陕西蓝田的李小棚、河北邢台的王彦西、山东招远的刘盛兰等。实际上被各级/各类媒体或行政机构命名为“当代武训”的人很多。,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颇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当然,他们之中,一定有不愿意读书的,就像城市中同样存在不愿意读书的孩子一样,但我相信他们多数应该跟李国富一样,因为经济困难,因为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父母没有能力供他们读书。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竟然还有这样的农村贫困现象存在?我相信一定有许多城里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但这是事实。而之所以有人不能理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与电视有关。电视作为公共媒体,并没有将这些贫困的乡村展现给观众,而是沿着文化工业的发展方向,为了收视率,在眼球经济的指导思想引导下,致力于当代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娱乐工厂的生产。甚至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乡村基本上就从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中逐渐淡出,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电视,更不必说戏剧等其他文艺形式,乡村都成为一个绝对边缘化的再现对象。换言之,90年代以来,文化工业化程度日渐加剧的电视产业,参与制造了整个社会一片繁荣祥和的幻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参与生产了一种社会视野的狭隘化,并由此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中产与底层的鲜明区隔。
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9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农村在实行了十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先因半私有制而被释放出来的生产力遭遇农产品价格过低及政府摊派增多等压力,特别是在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仅仅依靠粮食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普通农村家庭的日常生活。可是,越艰难,就越需要更多劳动力的投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落后地区的农村产生了大批失学儿童和青少年。更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地方政府的基层组织多处于涣散的无所作为的状态,甚至为害乡里,乱收费,硬摊派,更增加了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压力。于是,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大量外流。③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请参看温铁军等著《八次危机》(东方出版社,2013年)中的有关章节。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实际上存在内外两个动力,其一来自农村经济落后的内部压力,其二则是来自城市劳动力商品价格相对较高的外部吸引力。这其中主流媒体更是全面参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建构和生产。但就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内外在动因来说,媒体的作为不过是其手段而已。城市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要求。90年代以来,大陆工业化经过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为主的发展过程,而这一发展的开端正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资本的大规模转移同步,也正是在这一同步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大规模工业化必然与城市化如影随形。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正是中国农村危局的出现。这也就是“三农”问题在90年代末引起社会关注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90年代以来,大批农民进入城市,绝对不能简单地表述为农民要进城。这样的表述既是非历史的态度,更隐含着城市中心主义者对整个“三农”的歧视。正如上电视的权利一样,农民不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农民进入城市,是内外交困的结果,是迫不得已,并不意味着进城是其主动选择的、包涵主体性的行为。对此进行简单地辨析是为了阐明,新工人上电视的权利不能被孤立地仅仅视为一个新工人参与主流媒体及大众文化生产活动的权利的问题,而实在是一个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整体性问题在这一点上的反映。
作为权力场域的电视
然而,无论如何,他们进城了,他们甚至也上电视了,带着他们对电视的想象,带着他们第一次上电视的喜悦、自豪和忐忑、惶恐,带着他们的梦想,带着他们为工友争取一点利益的美好愿望。虽然他们行前也有一点点戒备之心,但他们多半没有想到会经历这么一场一言难尽的电视经验。几天后,他们回到了皮村,带回的只有第一次乘飞机的新奇感的满足,还有几百块钱的劳务费,此外就只剩下强烈的挫败感。
在视频中,本节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音响设备运送到皮村的画面,我们还听到了这样一段画外音:“八位来自皮村的年轻人,通过他们的努力,成功实现了共同的梦想。我们相信梦想的力量可以穿越生活的阴霾,抵达阳光灿烂的彼岸。在节目录制后的第二天,盈朗文化就将音响设备运送到了皮村。希望这些打工者们在劳累工作之余,可以享受片刻的娱乐和放松。今后只要皮村的文艺活动需要帮助,我们一定鼎力相助。”剪辑师不失时机,在这段视频和画外音结束后,特意插进了八位工友在录制现场的集体谢辞:“感谢中国梦想秀”,“爸妈你们辛苦了”。紧接着的是现场的热烈掌声。很明显,这是一个通过数码技术重新编辑而刻意制造的效果,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我们一诺千金,言出必行,而使用的手段则是非常现代的时空交错。糟糕的是,这不是艺术电影,更糟糕的是,粗糙的技术穿帮了,遗憾地留下了虚伪和欺瞒的证据。
据北京工友之家的朋友讲述,送去的音响是旧的,在经过交涉后,他们后来不得不再捐赠一套全新的音响设备。设备的新旧与否并不仅仅关系到承诺的落实与否,也不仅仅是旧的设备能否正常使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尊重。捐赠不应该是嗟来之食!而有意味的是,节目的播出使这一发生在电视外的行为及补赠都成为似乎没有多少意义的尾巴,实质上却很好地反映了新工人群体及其文化诉求在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中的位置。一般意义上,人在电视上和电视外都会存在明显的差别。上电视的人会自然有一个自我审查的心理和过程,因此,被观瞻的形象和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经过一次主动过滤,而在电视之外的日常生活甚至一般的社会生活中,这一主动过滤即使存在,其程度多半没有电视上那么严重,这就是媒体作为特殊的公共空间对人产生的作用。然而,问题是,梦想秀的节目性质对电视的内外理应作为一种约束力,换言之,电视外的行为不应该与电视内的承诺存在偏离。然而,偏离还是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偏离的发生也就意味着电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约束力量没有实现。而这也正是本文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即电视作为一个权力场域,就“中国梦想秀”这一娱乐节目来说,究竟存在哪些力量,这些力量之间有着怎样或隐或显的勾连,这一权力场域给进入其中的人们带来了什么?同时,这样一个各种权力角逐博弈的空间所生产出来的文化商品又给社会,更具体地说,给观众带来了什么?
这一电视内外的不同提醒我们,对当代中国此类已经完全成为商品的电视节目而言,其公共空间的功能是否因其商品属性而发生变化?同时,这类节目的生产和传播应该被视为两个既关联又存在差异的空间,既因其所关联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因而,所再现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也不完全一样;同时,因其方式的不同,特别是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传播过程不再仅仅局限于电视系统内部,因而给电视的受众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但有一点应该可以明确,权力在电视节目生产过程中的复杂性要远大于后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重心放在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上。
在当代中国的电视生产系统中,其秘密既属于商业情报,也与法规和政策有关,很多时候,局外人无从得知,也不允许外泄。然而,在通讯技术发达的今天,很多秘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借口。当我们依靠电视的生产和传播之外的渠道而知晓了现实中发生的一切,节目的结束部分给我们的印象就只有“虚假”和“虚伪”这样的词能够概括。原来,电视节目的制作竟然可以如此有效地利用录制和播出的时间差制造虚假的“善行”。但我们知道,所有非直播节目一般的生产方式都是如此,而当代中国电视产业近年普遍采取的制播分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给生产者提供了更大更自由的空间。制播分离的体制创新,目的是提高电视节目的水平和数量,但市场化的手段及其市场化完成后的实际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既不能保证节目的质量,也给监管带来了阻碍。虽然监管者其实对所要监管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楚,并因此造成简单粗暴的恶果,更使必要的监管无法实施。更重要的是,制播分离是资本摆脱行政控制、获取最大限度资本增殖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恐怕就不能简单地将这一节目中电视内外的言与行的脱节视为体制权力缺失的后果,也不能仅仅将其归结为电视产业的独特生产方式,毕竟这仍然是一个宏观层面上的权力再现。在我看来,对宏观层面的权力分析必须深入到内部和细部,进入微观层面,方能揭示权力的核心图式。
实际上,在社会生产领域,很少有完全封闭的关系/空间,即使看似封闭的空间,也多半存在外在的作用力,只是外在的力量一般会在内部寻找相应的代理人。权力在关系中生成,权力关系的生成也就意味着平等被打破(此处的“平等”只能在抽象的、理念的意义上成立,实际上,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真正“平等”的状态和关系在近三十年中越来越少,几至绝迹。而且,马克思早就阐明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平等应该建立在不平等之上,在对不平等的全面、完整的把握中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平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绝不是机会的平等和市场体制中的平等。)。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权力关系表述为支配与被支配,更强化的表述则是宰制与被宰制。权力关系的复杂程度因场域中关系层次的复杂程度而变动。
因此,就具体电视节目来说,其生产者无疑是一个支配性的存在。但生产者必须受制于市场和政策、法规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监管,这两者可能是对抗性关系,也可能是同谋关系,抑或对抗与同谋相纠缠的关系。而生产者与此二者的权力关系视其对两者的认同和接受的程度不同而不同。譬如,2011和2013年国家广电总局相继发布了加强上星电视节目管理的相关法规,被坊间称为“限娱令”。①2011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2013年10月,发布《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这一噱称反映了电视产业在市场化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双轨之间的冲突,但相当一部分人仅仅将后者视为一种权力,而将市场想象成一个自由的、可以自我调节并自我控制的空间,实际上,号称自由的市场最起码必须服从资本的权力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不自由,也就是俗话说的,得赚钱(这其中往往忽略了怎么赚、赚多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就目前中国大陆的各级电视台来说,对市场的认同明显高于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接受,对《中国梦想秀》这一类的娱乐节目而言,尤其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梦想秀》这一类娱乐节目的生产策略是,原则上不直接反对国家政策和法规,在节目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不触碰底线,但求最低限度地满足要求,或寻找替代性方案。但各种形式的资本的进入,使可能不那么复杂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了。换言之,在最低限度地满足政策法规的要求,与最大化地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之间存在着颇为激烈的冲突和斗争。于是,如何化解成为当前电视节目生产者的首要任务。而当这一首要任务落实到具体的节目生产环节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一个笼罩性的框架,一重权力关系,一个支配性、压迫性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这八位工友所代表的新工人群体的表达能力都不错,不仅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能够将剥削被剥削的道理说得清清楚楚,既形象又生动,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在如今的电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中拥有一席之地?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这并不意味着新工人不能讲述/再现底层的故事,关键是如何讲述/再现。在节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开始的欢乐气氛在“剥削”出场后陷入了尴尬。当然,这一点尴尬对早已熟稔于电视生产的从业人员来说,对在节目录制现场早就游刃有余的周立波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但技术的熟练程度在这里并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谁掌握生产资料。
也因此,正是因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属于新工人,他们才不能轻易地拥有上电视的权利。权利与权力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正相关的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而是这一权力场域中所有参与者进行生产的组织者,也是权力和权利的分配者。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很清楚地明了,为什么梦想大使周立波在尚未进行梦想投票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要向工友和观众们宣布,“如果没有超过,我也会给你们一个surprise(惊喜)”。这里的“我”不仅仅是周立波作为梦想大使和该节目创意总监的身份,也更清晰地指向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身份。而这个惊喜就是反转权,它是设计好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说,反转权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力,而反转权的使用就是权利分配的环节。于是,当工友们的表演结束,周立波迫不及待地说,要用“梦想表决来为你们的梦想做一次诊断”。当投票结束,果然未能达到规定票数的时候,当工友们为未能实现梦想而哭泣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的眼泪是被事先设计好的“阴谋”逼出来的),周立波以他惯用的鸡汤式语言①即心灵鸡汤。鸡汤是营养品,心灵鸡汤取其比喻意,意为对心灵有营养,通常是关于人生的哲理、关于感情的教导,关于成功的秘诀等温暖、励志类语言,也因此多出自名人。据说,2014年在网络上出现一股反心灵鸡汤的言论。一定程度上与网络语言“人艰不拆”(人生已经很艰难,就不要拆穿了)的流行相似。实际上,此类网络语言的流行是底层群体长期被压抑、失去上升可能性的征候,也是社会结构固化的曲折反映。,说道:“虽然你们没有通过梦想表决,但是,也许这是你们梦开始的地方。”很清楚,从这里开始,被蒙在鼓里的八位工友基本上被完全纳入预先设定好的轨道。
反转权当然不能在这时使用,因为预先编排好的内容必须按照既定的逻辑发展下去。这个既定的逻辑就是要使反转权显得合情合理,然而,怎样才能让说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一大禁忌的新工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呢?他们必须让新工人在这里实现梦想,得到恩赐,才能体现节目的正能量,博得主管部门的认可甚至表扬,赢得更多观众的支持,从而获得节目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是,真正隐藏在最深处的则是节目为资本集团服务的目的。更直接地说,这些馈赠给工友的东西恰恰来自资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当被剥削者揭穿了这个秘密,他们的恼羞成怒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为了攫取更大的剩余价值,不得不尽其所能地掩盖并转换话题。资本集团既然已经进入这一场域,既然要摆出公益和慈善的姿态,他们就必须,也只能“大度”地将游戏进行下去。既不愿意背负这一恶名,又必须以公益和慈善的高姿态心甘情愿、理所应当地方式体现正能量,于是,感恩出场了。
实际上,感恩的话语是与剥削的话语相继出场的。当毫无电视经验的赵晨一下子说出了资本增殖的秘密的时候,故作镇定的周立波不失时机地插科打诨了一下,还很高姿态地表扬了一下赵晨:“妹妹,这是个很好的话题。”但当赵晨进一步解释、描述新工人们遭遇的拖欠工资等境遇的时候,周立波忍不住打断了她,强行插话,以一种普遍人性的思路,说道:“我觉得人与人,无论是老板还是工人,彼此要有感恩的心,你们要感谢老板给了你们机会,老板要感谢你们付出辛勤的劳动,所以不要轻易用‘剥削’去描述大部分好的老板。”但有意味的是,后期制作的电视节目,在这一段添加了侧屏字幕:“八位不同行业的打工者,各自讲述心酸从业经历。”在这里,字幕所起的作用是提示,也应该被视为自我广告行为,希望观众不要摁遥控器,不要转台,继续收看本节目。但字幕的内容却恰恰呼应了赵晨所描述的现实,也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周立波所说的大多数老板是好的这一结论,这大概也是生产者所始料未及的。
然而,重要的是周立波的话应该如何理解。老板和工人要彼此感恩,老板要感谢工人付出的辛勤劳动,没有工人的辛勤劳动,也就没有老板财富的增长;工人要感谢老板给了你工作的机会,老板如果不给你工作,你就只能失业,只能更辛酸;老板给了你工作,你因此可以养家糊口,过上好日子。于是,一个诡异的逻辑形成了一个荒唐的结论:工人是老板养活的。即使我们不追问老板是如何成为老板的,而且,我们也承认工作是老板给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工人是老板养活的,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养活了自己。而老板则不然,没有工人和工人的劳动,老板则不能成为老板,老板更不可能有财富的增长。财富增殖的重要来源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剥削的存在。
我们无法在这里就剩余价值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剩余价值存在于所有商品的全部商品化的过程中,包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包括销售)等环节,绝不是如一些所谓经济学家讲的那样,根本不存在剩余价值。但糟糕的是此类经济学打着科学的幌子,欺世盗名,牟取资本,其言论假借正义之名广为传播,更兼9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双赢”理论的大行其道,政治经济学被日益边缘化,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这样的叙述中被颠倒。于是,老板与工人的关系被抽象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普遍人性论再次成为时代观念的主流,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和生活。而感恩的话语也只能放置在这样的语境中才能被普遍接受。
其实,生产者对此并非不了解,他们甚至深谙个中道理,因此他们要规定工友讲述的大致方向,即他们的辛酸经历,但他们并不知道新工人们会怎么讲述,他们恐怕也并不在意工友们究竟有怎样心酸的经历,他们希望的是,只要他们讲述出令人感动的、不一样的故事,反转权才能“合情合理”地使用,才能使原本属于娱乐性的节目也披上宣传正能量的外衣,才能使资本集团获得馈赠的机会,才能使作秀取得真实的效果,归根结底,这个理应包含两个面向(其一是新工人,其二是捐赠)的正能量必须来自资本集团。因此,感动必须被询唤出来,感恩必须被制作出来。可是,他们知道让工友们感激老板是不可能的,他们就只能设计出感恩父母的招数。怎么才能做得严丝合缝、不留痕迹呢?特别是在方俊自告奋勇、现身说法之后,朴实的王修财仍然坚定而勇敢地站出来申述的时候,已经恼羞成怒的周立波莫名其妙地教训起王修财来:“孩子,你有怨气。”并更加莫名其妙地要八位工友举手表决,他要看看究竟有几个人同意王修财的意见。但他的盛气凌人和工友们复杂的心理,使大多数工友没有举手。“怨气”一词值得分析。为什么周立波对王修财所言反应如此强烈,竟要摆出一副长者的高姿态来教训人?在我看来,这是周立波的一个近乎直觉的反应,他不仅不喜欢这样的表达,他还直觉到了这一表达意味着什么,但他不能直接说,你不可以这样,于是,急中生智,他以更隐蔽更严厉的方式堵住了工友的嘴。你现在的处境已经很好,你应该知足,应该感恩,而不是批评不公;因为你所批评的那个不公的体制,恰恰是“公平地”给予他们机会和成功的体制,为什么他们成功了,而你们没有成功?在他们看来,一定是你还不够努力,要不就是你命不好。你不能以你的不成功来批评那个给他们成功的体制,否则,就是你的心态不正常,心胸不够宽广,你的批评就是怨气,你的心态就是仇富。“怨气说”还站在了一个道德的高度谴责了对现实的批评,也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为现有秩序辩护的用心。而这也充分地证明了“道德”的阶级性,实际上,在阶级社会根本不存在抽象的、普遍的道德。周立波的不准有怨气的道德绝对不是新工人必须说出剥削的真相的道德。
工友们返回皮村后专门开了一场讨论会,从中我们知道,此时周立波是想取消这个节目的。在电视上,我们看不到录制现场紧张的冲突,但剪辑在这里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工友们说了什么,我们看不到,但我们看到了周立波强势的表达:“当我们用自己的辛勤的双手去劳动的时候,我们只知道我们的辛苦,为什么我们不去感恩别人给我们的机会呢!”此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由方俊引出的幸福的话题,经工友国富的表达,终于走上了感恩的轨道,但那并不是同一根轨道,而是不同的轨道。生产者事先准备的视频都是工友们亲人的问候和叮嘱,怎么样让他们的亲人出场?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在心酸经历的讲述之后,让亲人的问候抚慰、温暖他们,也让家庭的温情打动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但剥削的话题干扰了预先设定的进程,王修财们拒不接受感恩老板给予机会的“顽固”姿态更使这一进程难以继续。但是,录制最终还是完成了,而就作为文本的节目所呈现出来的结果看,国富的讲述无疑是打破僵局的重要因素,因为这正是那个既定的轨道。
但亲人们问候的视频不能在这时播放,因为现在仍然不是反转权使用的最佳时刻。必须在梦想表决失败后,才能“合情合理”地使用反转权。既然如此,也就必须保证表决的失败。但现场毕竟有近三百人,要控制,还要保密,显然并不那么容易。技术再一次出场了,通过控制投票表决的时间长短同样可以达到目的,于是,在一些观众尚在犹豫的时刻,周立波宣布投票结束。这才是真正的天衣无缝。但周立波再一次告诉我们,他要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巨大的漏洞既暴露了他的颟顸和自大,也将这一电视生产的秘密昭告世人。
请注意,周立波一再强调的是,他,要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就是反转权的使用。反转是权力的实施和结果。在现在的“中国梦想秀”节目中,只有“梦想大使”周立波一人拥有反转权。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并且可以使用反转权?依据什么原则?反转权的使用是事先安排的吗?为什么要设置这一特权?反转权使用的效果如何?反转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权力?是单一的权力主体,还是一个权力的集合体?如果是后者,它又包含了哪些主要的构成部分?如果我们看了这个节目,就知道反转权基本上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观众和节目的参与者都被蒙在鼓里。但就电视作为文化工业的一种,其生产者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甚至数个团队,内部也不能完全保持统一,因此,在“中国梦想秀”节目中,我们很难判断,究竟谁,或哪一个集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我们只能说,周立波作为梦想大使,作为该节目的艺术总监,一再强调他的特权,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是整个生产者权力在这一场域中的代理人。然而,他对自己所拥有的特权的强调,一方面是显示其公平、公正和权威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将这一权力据为己有,为个人的文化资本的积累而服务。也因此,我们在这里既可以看到,现实中的特权模式及权力垄断在电视生产和传播空间中的复制,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公共权力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化为个人权力,更进而转换为私有财产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当前大陆电视产业颇为普遍的现象。遗憾并且糟糕的是,这些被电视产业或相关文化工业包装、生产出来的电视明星,却在很多场合打着反特权、反专制的旗号(有意味的是他们不反市场经济中私营或跨国资本的垄断)。其中的讽刺意味深长,如果将其延伸到受众层面,正如该节目中被蒙蔽的观众和节目参与者一样,电视节目的受众也被这巧妙的转化和转换机制所蒙蔽,为他们对特权的抨击而喝彩,为他们点赞,殊不知,所有的喝彩和点赞除了强化其权力资本外,在其商品化的过程中已经悉数转化为资本积累,也就是明星们的身价。
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节目中周立波那些夸张的表情,他的恼怒,他的作秀,他的咄咄逼人、盛气凌人,还有他的伪装;我们才能理解节目最后呈现给电视观众的那些断点和裂痕。断点可以通过技术处理得天衣无缝,但裂痕却无法通过鸡汤式的语言走向和解和弥合,因为心灵鸡汤是为回避社会分化所造成的阶级鸿沟而采取的策略。也因此,可以说,周立波在这一场的反转权,与其说反转的是节目中八位工友梦想能否实现的过程,毋宁说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歪曲,以表演掩饰紧张,用设计制造幻想,以感恩掩盖剥削,用亲情遮蔽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
因为存在k不等于整数的情况,所以随机抽样时先对k取整.根据首次入侵发起时间点t1(0≤t1
在这个权力场域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新工人的命运,他们不仅仅是社会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更是权力关系中的弱项,处于当代中国文化工业电视产业生产线的末端,既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压抑,更受到资本权力主导的文化工业的压迫,他们即使不是被遗忘的,也是被实实在在边缘化的群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将生产资料划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类,既是在一般意义上重申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也更深入地表达了思想、文化、精神的生产,与其生产资料的占有之间同样存在直接的关系这一思想,进而言之,被压迫者不仅仅在物质生产领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在精神生产领域同样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但他们并不是待宰的羔羊,他们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他们之选择来“中国梦想秀”,就不单单是为了一套音响,他们也希望借助主流媒体,能够将他们创造的新文化传播出去,即使他们仅仅只为了一套音响,但客观效果已经超出了这个简单的目的。虽然是因为冒失而说出的“剥削”,却意外地有了与主流媒体和主流价值观面对面斗争的经验,其结果虽然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战斗,但正如道出了皇帝新衣的真相的孩子,天真而勇敢。
新工人、新文化的困境和未来
斯图亚特·霍尔从电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提炼出两个重要的环节:“编码”和“解码”。电视生产者将他们要表达的意义以一套专业化的知识和技术编织进一系列的符码中,而受众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但解码所产生的意义之和并不完全等于编码时放进去的全部意义。霍尔在对理论阐述后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编码—解码方式:主导—霸权式、协调式和对抗式。②参看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在这一期的梦想秀节目中,新工人的出场使这一原本被生产者完全操纵的生产过程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完全主导—霸权式的生产方式,而不得不采取协调,或协商的方式展开。这一点显然与其他各期不同,这个节目的绝大多数参与者在这一权力场域中,多半是配合的、认同的、服从的,既因为这一场域中权力集团的强势,也因为参与者多半已经被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所同化,甚至也可以说,因为认同才会去参加节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期节目中的八位工友有不那么一样的价值观。他们唱的是非主流的、他们自己创作的音乐,他们也并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他们有的“想学身技术,回家办个厂,带动俺们的家乡更加富强”,有的要“娶个媳妇在城里安个家”,这些梦想当然有与主流一致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其中蕴涵着的尊严和平等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人剥削人的现象,可他们并没有像周立波说的那样,有什么怨气,而是在自强自立之外,希望为被压迫的新工人群体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依靠团结的力量维护劳动和劳动者失去的、被剥夺的尊严,而并不是个人的成功。如果说,他们因为说出了剥削是这个时代成功的秘密就是有怨气,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最富怨气的不朽之作,出身资本家阶级的年轻的恩格斯所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为英国工人阶级发出的最真实也最强烈的怨气。这不是怨气,恰恰相反,成功者将对取之无道的批判视为仇富心态,这才是真正的怨气。他们不允许被剥削者揭穿真相,他们还要继续伪装下去,继续蒙蔽下去,继续他们的财富积累,继续维持这不平等的社会。
电视节目是意义的生产者,电视因而是一个意义生产的空间,娱乐节目也不例外。很多时候,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在电视的生产和传播中走在生产者设置的轨道上,然而,在这一期节目中,新工人及其亲人的出场虽然未能在其中创造一个足以与其对话的意义空间,但是他们还是依靠亲身的经历和朴素的认识,在这个既定的空间中展开了一场意义的争夺战。
感恩的环节如同反转权的使用一样,都是事先设计、安排好的。亲人的视频和新工人们的自述确实感动了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亲情牌是近年来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消费主义和治理策略所生产出来的一个有效手段,但其核心的价值观仍然是个人主义和成功学。有论者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懂得如何对穷人的眼泪进行有效的营销和包装,资本主义残酷行为的力量将从中获益……”①这是彼得·麦克拉伦为保罗·弗莱雷伟大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所写的“修订版前言”中的话。《被压迫者教育学》“修订版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页。在这个意义上,亲情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煽情”就正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手段,因此,这些真假难辩的眼泪,说到底,不过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温情。当节目嘉宾方俊现身说法,告诉工友,也告诉大家,他当年如何在卖水果之外坚持梦想——舞蹈练习,抓住很不容易得来的一次上台的机会,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方俊被他自己叙述的成功故事打动了。因为他自己的成功,不仅有自己的公司和学校,还可以经常作为嘉宾和裁判出现在电视上,他也因此就拥有了现身说法的资本,他忍不住不假思索地说,“你们太幸福了”。这时,他和台上所有的观众一样,也还没有看到工友们亲人的视频。然而,一方面,他忘记了自己成功的关键是伴随着全面市场化进程而展开的文化工业的兴起,他也忘记了时代不同了的老话。更重要的是,他忽视了工友们的梦想与他当年个人奋斗的梦想完全不搭界,对八位工友来说,他们并不是要通过这一次的上电视为自己积攒文化资本,并由此获得未来个人的成功。方俊的话中甚至还包涵着这样的意味,我努力了,我奋斗了,于是我成功了,你们没有成功,是因为你们还不够努力。也许王修财敏感地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问题,也许他仍然是为了回应关于剥削的讨论,总之,他试图以协商的方式进一步地强调剥削的存在。
虽然亲人们的视频不是由于工友们对剥削的认识而不愿对老板表示感恩才拍摄的,虽然这仍然是电视生产者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而预先设定的,但观众们确实被打动了,他们的眼泪是真诚的,一如工友们的眼泪一样。但不同的是,观众们多半应该是居住在杭州的城里人,即使是新城市人①这里所说的“新城市人”,譬如新上海人,新北京人等等,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人,也有一部分是依靠市场化的力量,比如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房地产市场吸纳小城镇和农村资本而获准进入大中城市的人,他们拥有该城市的居民户口,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也有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也就是说,新城市人不包括新工人,也不包括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知识劳工,他们未获得该城市户籍。,也与八位工友的生存状况不尽相同,视频中工友们家乡的经济落后和家中的贫困状况一定使他们震惊了。而对工友来说,那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亲人,就是他们原来的生活世界,他们就是从这里走进城市的,他们不会震惊于那简陋的居住条件和俭朴的生活环境。当电视将这些画面呈现在城市人眼前的时候,巨大的落差唤起了人性中最朴素的同情和怜悯,他们流泪了,他们为这些受苦的人而流泪。而这些受苦人的泪水则是感恩的泪水,是对他们亲人的感激。当前者在节目散场后,他们抹掉眼泪,又重新回到消费主义的时空中,继续他们中产或梦想中产的生活;但工友们却只能回到他们的工厂中,站到他们的工位上,继续挣扎在为生存而战的现实中。因此,他们感恩的对象绝非“赐予”他们工作的人,而他们对感恩的理解也显然不是电视生产者所希望的内涵。一位在网上看了视频的网友说的好:“难道你们就觉得农民就应该呆在山里吗?他们有权利选择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说要反哺?因为社会欠农民太多,要说到感恩,最应该感谢的是他们,时(是)他们的辛勤劳动给这个社会提供的(了)最基础的生活保障,没有他们就没有发展,现在发展起来了却忘了他们,当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有怨气时,你们却搬出所谓的‘感恩’,而最应该感恩的却是你们。”②参看优酷视频的评论页: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2MTgyMzc2.html?from=s1.8-1-1.1。上引文字为网名“含笑66167152”的评论,因仍然不断有网友追加评论,该网友评论的网页地址会有变化。引文中手误标示在括号中。在这个意义上,感恩环节的设计,既是为了推卸责任,你们的贫困与我无关,也是为了感动人,为了赚取眼泪,还是为了转移剥削的话题,摆脱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同样也包涵着缝合阶级裂隙甚至鸿沟,弥合阶级对立和冲突的技术诉求。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也源于他们对新工人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对家庭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之所以形成这一刻板印象,根本的原因既在于城乡和阶级之间的鸿沟,也因为时代严重的非历史化现象。即使我们不回溯更久远的历史,仅仅就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事实而言,网友所云基本不错。然而,这个事实恰恰被许多人遗忘,或不愿意正视。
虽然亲人们说的都是勉励、安慰的话,大多也都是好好干,不必挂念家里,可是向阳母亲的一番话,却说出了成功学绝对不会在意的内容,她说:“好好在城里头打工啊,不管做什么事儿都要诚实啊,人诚实才能干的(得)好事情,老实,诚实……”视频是向阳的姐姐几经周折,托人用手机拍下的。无论是国家和社会层面,还是家庭和个人层面,发展主义都算得上这个时代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但国家层面尚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压力,而个人的发展主义一旦内在化为全部生活的动力,则完全蜕变为丛林法则,老实、诚实这样的品德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势必被扫进垃圾堆。然而,恰恰是这些被抛弃的价值观才是一个好社会的必要条件。如果老板人人都诚实地将他们的利润,以及如何获得利润的方法都公布出来,如果老板人人都不以剩余价值的攫取为生产的目的,而能够主动地为工人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如果老板人人都能给工人以尊严,而不是只把他们当成抽象的劳动力,甚至劳动的机器,工人还会有怨气吗?我知道,这是痴人说梦,资本的天性绝不是这样,而是相反。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资本可憎的面目被资本主导的文化工业装点、打扮得一如我们每个人的梦中情人,它只让我们看到能够看到的,那些不能看到的早已被他们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并且生产出一套又一套动听的说辞,让我们相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网友们自发地为老板们辩护的行为。③参看优酷视频的评论页: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2MTgyMzc2.html?from=s1.8-1-1.1。
同时,亲人们的视频无疑是真实的,你看他们面对着镜头,无论是手机镜头,还是摄像机镜头,他们都以最朴实的面目示人,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夸张自怜,老人的慈祥,孩子的害羞,就像我们在农村见到的任何一个老人和孩子一样。工友们大多也是如此,如果说他们的演唱因经过主办方排练而显示出一种不熟练的舞台气,他们说话时身体的姿态和语言的表达,就多是自自然然、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面貌,是真正老百姓、普通人的形象。然而,他们是道具,就如亲人们的视频一样,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是为了完成他们即将得到的“施舍”而设计的道具,是为了体现节目的“正能量”,也为了以他们为对象继续建构这个“正能量”而编排的道具。但他们是活的“道具”,是醒着的生命。他们的拒绝,他们的眼泪,甚至他们的迎合,都是他们在这个作秀的舞台上自觉的自我意识。然而,他们也还是被当作了“道具”。
这就是困境,万物商品化的商品生产与保证商品生产继续扩大的消费行为之间构成了资本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一个结构,这一结构化的力量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权力、意义、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换言之,它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反对资本主义。
困境永远存在,但危机中隐伏着生机。这是困境与生机的辩证法。既然现实都不允许电视生产者制造出工人感恩老板的谎言,而八位工友的协商式参与虽然不能代表整个新工人阶级,但毕竟有了清晰的主体意识。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的表达还不是很好,但毕竟已经无需代言,他们已经具备了自我表达的意识,也已经基本掌握了自我表达的方法。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们所演唱的《打工者之歌》就完全出自十来年前和他们一样的新工人之手,而不是文化工业的制造。北京工友之家以及新工人艺术团近年来在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的诸多实践看,他们已经在探索反抗资本主义的方式,创造自己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上了电视的八位工友作为新工人的一部分,还是他们的父母作为传统的一部分,以及网络空间中支持工友的网友,都昭示着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所生产、打造的新主体存在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今天的电视观众也并非全无独立思想意识的“沙发上的土豆”,一种集体的、阶层的,甚至是阶级的意识正在逆向生长,如地火般在繁华的地表之下酝酿、生成。
虽然新工人创造的新文化与新工人一样,仍然处在被压抑的、边缘的位置,主流也并没有为它留下相应的空间,但新工人们早就看清了现实,他们要“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更何况,网络上的跟帖足以证明新的力量正在孕育中,戴维·哈维期待的“通过日常生活的共同关系产生的大众文化”①[美]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3页。已经被创造出来,并将有更多的创造。
但是,必须客观地说,新文化的未来较之新工人艰难的处境而言,必然更加艰难。当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几乎完全被利益的精英集团所占有的时候,哈维所说的共同关系的生产虽然并非不可能,但毫无疑问是困难的。一方面,必须与之展开有力的争夺战。葛兰西也许没有想到,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会有如此迅猛的发展,文化工业的商品,无论是音像制品,还是印刷电子产品,乃至其在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强劲渗透,包括建筑空间,几乎占领了我们全部的生活世界,共同文化的阵地是否存在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必须进行的就不可能是阵地战,而是阵地的争夺战。在争夺阵地的同时,利用已有的阵地,进行阻击同样也是必须的。就如上文引用网络上网友的文字所表明的那样,网络空间当然是资本和权力主导的世界,它制造了一个看似自由表达的空间,但不能不说,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表达的可能确实存在,然而整体上又是被掌控的。因而,在这个逼仄空间中的争夺会异常艰苦和困难。另一方面,必须创造新的空间,新的阵地,新的形式,重建共同世界。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工人阶级运动中,虽然那紧握的拳头是一个必要的象征符号,但握紧拳头并不意味着不能摊开双手,伸出十指,去发现并塑造一个全新的现实世界。”①[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345页。握紧拳头是在战斗的时刻,伸出十指是创造的时刻。必须重新通过讲述一个实际存在但被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工业肢解为原子化的“共同关系”,在共同关系中重建一个共同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探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动员和社会动员的可能和新的形式。
(郭春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When“New Workers”Come Across“Dream Show”——Analysis and Practice of a Cultural Research Media
Guo Chunlin
When they come across increasingly capitalized TV industry,the new workers are exposed to the helpless plight in many aspects:living circumstance,emotional appeals,cultural concepts,and so on.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cities,they are not entitled to own an apartment,which is important property in cities.They don't have much living materials,either.What is more,they are almost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of education,media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which are mostly controlled by capital groups and bureaucratic groups and technical elite groups.In this case,when television programs try to involve these new workers and their culturalproduction,emerg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new workers and the mainstream ideology.The members of community center at Beijing's Picun Village participated in Zhejiang Satellite TV program“China Dream Show”in May 2014.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participation,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operation of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bitter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deprived new workers.It hopes to better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 for the new workers via the spread of TV programs on the webs.
New Workers;Chinese Dream Show;Media;Analysis;Culture;Production;Television
①吕途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很清晰地辨析了“农民工”与“新工人”的异同,并特别强调话语/概念使用的政治意味,因为前者包含了一种不易察觉的歧视性。遗憾的是,虽然不少声音都在呼吁不再使用“农民工”,目前主流媒体和学术界仍然顽固地继续使用着这一被新工人群体所反对的称呼和概念。参看吕途著《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