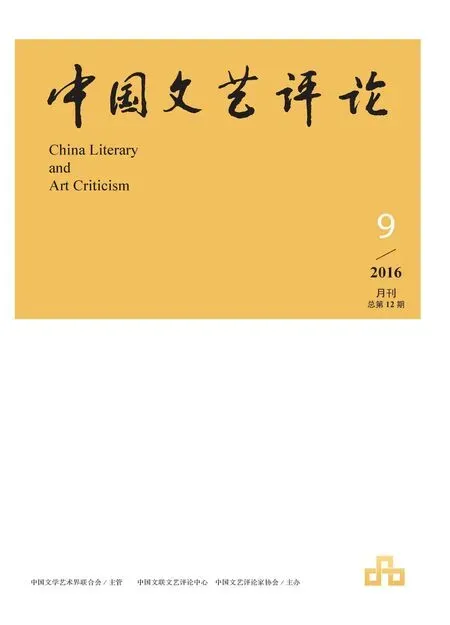屏幕艺术的“入侵”与剧场艺术的嬗变
臧娜
屏幕艺术的“入侵”与剧场艺术的嬗变
臧娜
屏幕艺术的兴起无疑是技术推动的产物。美国学者Erkki Huhtamo就曾以“屏幕学”为对象,专门探讨了屏幕艺术演进的历史脉络,从19世纪初期镶嵌着半透明图像的手持防火屏风(法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电视的诞生,他强调,“屏幕考古”作为媒介研究的一个分支,并不仅仅关注屏幕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它们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联,[1]Erkki,Huhtamo.Screen Tests: Why Do We Ne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Screen?.Cinema Journal,Winter2012,51(2):145也就是要在历时性的社会运动过程中审视“屏幕”。
屏幕艺术与剧场艺术之间发生的审美关联与文化碰撞,正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动态沿革展开的。在20世纪初叶的西方,一部名为《恐龙葛蒂》的动画电影就曾经被改编为剧场艺术形式,电影屏幕动画演绎与舞台真人表演相结合,揭开了“屏幕”与“剧场”媒介互动的序幕。同样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屏幕艺术逐渐摆脱了屏幕舞台置景的生硬模式,转而以更加灵活多变、虚拟交互的方式融入到现场表演之中。
从电影、电视这类传统影像媒介屏幕,到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现实的仿真媒介屏幕,影像介质的嬗变过程中,隐含着某种相似的价值诉求,就是西方哲学中业已存在的“being”观念,即在分析和思辨的过程中明辨真假,进而把握世界的真相。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推动了屏幕艺术媒介技术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价值观渗透到屏幕艺术与剧场艺术相互融合的审美空间当中,潜在地改变着剧场艺术形态的本体内涵。
屏幕艺术与剧场艺术的融合推动了多媒体舞台艺术的发展。当代中国多媒体舞台艺术虽然起步较晚,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升和国人文化视野的不断拓展,屏幕艺术也开始“侵入”剧场艺术空间,在丰富本土多媒体舞台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也改变着创作者和受众对于传统剧场艺术的理解。
一、影像的介入与艺术本体的图像化重构
如前所述,以传统影像媒介为主要物质形态的屏幕艺术,是多媒体舞台艺术发展初期较早进入剧场空间的屏幕艺术形态。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众多多媒体舞台艺术作品的“常客”,从舞剧、音乐剧乃至各类晚会,这种具有高度逼真性和较强视觉冲击力的舞台置景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舞台美术的缺憾,增强了舞台的视觉表现力,也逐步实现着对各类舞台艺术形态的图像化重构。
“多媒体钢琴音乐会”就是此类屏幕艺术与剧场音乐表演相结合的产物。2009年,旅法钢琴家宋思衡推出了他的首场多媒体钢琴独奏音乐会“交响情人梦”,引起广泛关注,宋思衡也由此成为中国多媒体独奏音乐会的创始人。时至今日,他创作搬演了多场不同主题的多媒体钢琴音乐会,这些作品有一些共同特点,即将大屏幕投影制造的视觉影像与现场钢琴演奏相结合,用影像辅助诠释钢琴音乐作品,以叙事性的故事文本串联音乐表演,甚至辅以话剧表演等等。
在“寻找村上春树——宋思衡‘挪威的森林’多媒体钢琴音乐会”中,村上春树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成为影像叙事的重要对象,牵引着音乐的走向。在演绎小说《遇见百分百女孩》这一主题时,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钢琴曲《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介入进来,屏幕上时隐时现的少女形象与古典音乐主题相交融,以视听结合的方式诠释了村上春树对于“女孩”“青春”“爱情”的想象,也为古典钢琴音乐的舞台呈现提供了文学脚本。在演绎肖邦第二钢琴奏鸣曲《葬礼》时,创作者同样将每个乐章所讲述的内容和所要表达的情感以屏幕艺术的方式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这种创作手法使这部严肃的古典音乐作品变得更加清晰、直观,将肖邦的传奇人生和他博大的情感世界呈现在当代大众面前。而“肖邦·爱”多媒体钢琴音乐剧(2010)的现场,更是将话剧、舞台动作融入到多媒体钢琴音乐剧场中来,青年作曲家田艺苗对宋思衡的一篇访谈文章随即以“多媒体钢琴音乐会是一部戏剧”为题,来界定这种钢琴、多媒体与话剧多元杂糅的音乐表演形态。
多元艺术形态的介入,打破了传统钢琴音乐会“一盏灯、一架钢琴、一名艺术家”[1]【现场】宋思衡的多媒体钢琴独奏http://www.infzm. com/content/48157的古老舞台样式,“多媒体钢琴音乐会”以当代年轻群体普遍接受的视觉化传播方式提升音乐表演的舞台表现力,尝试接通古典音乐与当代社会的艺术血脉。正如宋思衡所说,“现在的社会人群,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都对视觉的要求越来越多。古典钢琴音乐之所以没落,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近50年中钢琴无论从构造还是音乐会形式都处于历史上的停歇和僵化期,和我们的时代精神严重脱节。因此我想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演奏传播之同时,通过自己对古典音乐的认识和理解,改变一下古典音乐赏析方式,结合科技,让观众更能有立体化的体验。”[2]刘莉娜、宋思衡:《当黑白键遇上多媒体》,《上海采风》2013年第1期,第40-41页。古典音乐的大师们虽然早已作古,“古典”与“当代”之间虽然存在深远的时空沟壑,但大师们对于人生、自我的深沉思索却经由他们的作品留存下来,对于极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开启人的心智于无形。从这个角度讲,“多媒体钢琴音乐会”以视觉影像甚至戏剧动作辅助观众的听觉,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古典音乐,拉近大众与古典音乐的距离,这可以说是一个造福苍生的文化事件。
回首多媒体舞台艺术发展史,19世纪俄国作曲家斯克里亚宾也曾在交响乐《普罗米修斯》的演奏现场采用多媒体技术,制造视觉与听觉、色彩与声音之间的联想效应,希望把交响乐从听觉艺术变为一种多官能协同的感官体验。但斯克里亚宾的这种尝试在当时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力,世易时移,21世纪中国钢琴家宋思衡的“多媒体钢琴音乐会”却在听觉艺术领域掀起了视觉革命,并在票房上把历年钢琴音乐会远远甩在身后,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事件。
早在1938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指出“如果我们来沉思现代,我们就是在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1][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89页。。这位哲学家所说的“世界图像”并不是指今天眼光可及的视觉媒介那么简单,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在这里,‘图像’(Bild)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2][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6页。,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致力于凭借技术理性的无边法力将外在世界化为一种“表象”去把握,而“图像”被视为是这种“表象”的真实写照,世界由此被把握为图像。在对于“图像”的“观看”中,人类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宰,似乎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也能够更加有力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海德格尔在这里事实上是在慨叹人类的骄傲和理性的有限,面对庞杂的世间万物、复杂的群体社会和深邃的心灵世界,在人类目力所不及的地方,万事万物都在依循自己内在的规律运行,真实的世界和世间的真理可能并不是目力所能达到的。
但“世界图像时代”似乎一如它的技术规划那样日益清晰。有影像媒介介入的“多媒体钢琴音乐会”在票房上击败了晦涩难懂单调的古老音乐会样式,在影像以及戏剧动作的帮衬下,钢琴音乐似乎具备了更具理性线条的叙事功能,变成了需要“认知”而非“感受”的对象。
当然,创新是应该被鼓励的,“多媒体钢琴音乐会”为危机四伏的古典音乐搭建了一个与当代大众沟通的平台,为这门伟大的艺术找到了新的传播契机,这一点功不可没。但海德格尔的忧思依然挥之不去,经过影像乃至话剧的解读,自以为准确把握了古典音乐深邃内涵的现代观众,是否会在心中形成一种对于古典音乐的刻板印象,而忽视了这种艺术形态凭借听觉唤起人类自我意识和文化探究愿望的终极目的。
包括舞剧、音乐剧等舞台表演艺术,也都曾积极尝试与屏幕艺术相融合,提升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但这种植入与融合是否会潜在地改变多元舞台表演艺术的本体样貌,带来“影像殖民”的一体化后果;对多元艺术样态的图像化重构和视像性把握,是否会导致人们对艺术本体感知能力的降低,“技术”进步中这些潜藏的忧虑仍然是“艺术”无法绕开的终极命题。
二、拟像的仿真与艺术意蕴的数字化改写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推动屏幕艺术由影像呈现步入到了数字拟像的仿真境界。西方著名媒介哲学大师鲍德里亚就曾经在著作《拟像与仿真》中揭开了新媒体数字技术的真实面目。在鲍氏看来,数字化的终极目标就是构建比现实更加真实的“超真实”视界,数字仿真时代是“一个新的形而上学的时代”,“拟像”则是“人类建构的巨大的图像世界”[1]孔明安:《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数字拟像所构建的图像世界是对传统影像媒介技术哲学思想的观念性超越,传统影像媒介试图营造一个主客二元的对象性视界,人类以图像的方式把握世界,双方处于主体与客体的位置,主体以此来解释和把握客体。数字化的技术逻辑则是消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鸿沟,人类与外在世界、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被日益抹平,模拟现实世界建构的数字虚拟世界乃是一个比现实更加真实的拟像视界。与“影像”的主客二元逻辑不同,在仿真逻辑的驱动下,多元主体之间保持着交互、对话的关系,人类以“沉浸”而非“认知”的方式漂浮在拟像构筑的仿真空间之中,在“超真实”的数字视界中,人类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实现了历史性地跨越,而实在世界被遮蔽并隐退了。
数字技术推动屏幕艺术进一步发展,使得多媒体舞台艺术也向着交互、仿真和多元主体并存的方向发展。在当代中国多媒体舞台创作领域,数字投影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涉及到歌剧、舞剧、音乐剧等多元剧场艺术样式。数字屏幕艺术形态与剧场艺术的融合,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改写着传统剧场艺术的内在意蕴,由于东西方艺术思维方式业已存在的差异,这一嬗变在极具东方特色的戏曲艺术领域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
多媒体京剧《梅兰霓裳》(2013)正是这样一部东西合璧的多媒体舞台艺术作品。作品将数字虚拟景象与舞台实景相融合,同时伴以风声雨声等极具现场感的听觉效应,观众体验到的是与以往“一桌两椅”简约主义戏曲表演不同的“超真实”观剧感受。创作者在阐述运用数字技术初衷时曾指出:“舞台三维虚拟景象,与之相辅相成的高科技手段都是为台上‘唱、念、做、舞’,推动剧情发展服务的”[2]梅葆玖:《从〈梅兰霓裳〉谈梅派的“中和之美”》,《戏曲艺术》2013年第2期,第5页。,这种倡导数字技术为传统戏曲表演服务的创作理念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技术进步对剧场艺术创作带来的深远影响,以至于戏曲这样的传统艺术形态也希望能够借此实现创新发展,拉近与当代大众的审美距离。还有多媒体音乐戏剧作品《白娘子.爱情四季》(2009)、昆曲《怜香伴》(2010)等,都致力于将数字化屏幕艺术与舞台表演相互融合,营造出更具视觉感染力的剧场效果。
然而,源于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域中的数字技术,对东方传统戏曲艺术的剧场植入,其间必然存在着某种源于文化传统深处的悖谬。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在舞台置景方面所倡导的简约观念与戏曲艺术的虚拟性特质不无关联,虚拟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区别于西方戏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质,它倡导以相对写意、简约的舞台表演和舞台置景,承载更加丰厚的情感内涵,同时为观者留下更为宽广的艺术想象空间。早有戏剧研究者指出:“戏曲艺术要求把人物的内在形象,用形体动作表现出来……善于把感情形象化诉诸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1]房长勇:《焦菊隐戏剧导演艺术对戏曲的借鉴》,《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83页。,在戏曲艺术中,这种内心情感形象化的过程很多是通过虚拟化来实现的。在没有任何实景道具辅助的情况下,一次开门、一次拈花,这些在虚空中完成的程式动作,却蕴含着无尽的韵味,此即戏曲艺术特有的情感形象化。
与这种以含蓄取胜的虚拟性特质相比,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域中孕育的“数字虚拟”,崇尚的却是营造“超真实”的视像空间。正如鲍德里亚所说,“过去一切看不见的东西都不可思议地出现在眼前”[2][法]鲍德里亚:《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页。,“技术理性希求的乃是一个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被完全抹平的仿真世界”[3]臧娜、代晓蓉:《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8-229页。。当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孟菲斯对尼奥平静地道出,“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你一直生活在鲍德里亚的图景中,在地图里,而非大地上”[4]臧娜、代晓蓉:《当代文艺娱乐化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9页。,数字技术的理性图谋就愈加明晰,“仿真再也不是领土之类的东西,它不是所指的存在或实体。仿真产生于没有起源或实在性的实在模型:它是一个超真实。领土再也不会超前于地图,它也不会拯救地图。相反,地图先于领土(仿像的序列),即地图产生了领土……”[5]J.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1 转引自孔明安:《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可见,在《梅兰霓裳》的剧场空间中,两种精神旨趣完全不同的“虚拟”特质奇妙地并置在一处。然而,写意与写实两种审美观念的对话,数字屏幕对传统戏曲艺术的剧场植入,势必存在相互消解及何者为主体的问题,如何使两者相反相承地交融在一起,如何确保“数字化”之后的传统艺术仍然不失其应有的韵味,这是数字时代抛给创作者的一道艺术命题。老一辈艺术家已然参透了其中的真意:“如何用三维动画技术和虚拟景象设计表达梅兰芳艺术的‘写意传神’,做到‘移步而不换形’可能是今后一代人、两代人长期攻关的科研题目。如果让一些‘大场面、大制作’被人诟病太过写实反而使戏曲虚拟表演显得虚假,真的改变了梅派的‘形’了,那就直接破坏了我父亲一直强调的‘综合’与‘平衡’了”[1]梅葆玖:《从〈梅兰霓裳〉谈梅派的“中和之美”》,《戏曲艺术》2013年第2期,第5页。。这事实上也正是鲍德里亚所担忧的,他曾经以“高保真音乐”为例,表达了自己对超真实听觉空间的忧虑,“不仅有环境空间的三维,还有内脏的第四维,即内部的空间——还有完美地还原音乐的技术狂热(巴赫、蒙特威尔第、莫扎特!)”。[2][法]鲍德里亚:《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8页。鲍氏认为,这种技术性添加进来的听觉效果对听者的音乐想象空间是一种剥夺,“它剥夺了你任何细微的分析性感知,而这种感知本该是音乐的魅力所在”。[3][法]鲍德里亚:《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页。数字仿真对传统艺术的技术植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统”的当代新生,使以往蕴含在“传统”之中目力所不及的东西得到了清晰的显现,但这种数字化改写是否会消蚀传统戏剧场域特有的艺术意蕴,双方如何间性共融,这是思想家们留给后世的精神余韵。
三、屏幕的“入侵”与人性的反思
从以传统影像媒介为主要物质形态的屏幕艺术到数字化屏幕艺术,从影像发展到拟像,在技术进步的动力作用下,屏幕艺术的外在形态日益多样,屏幕艺术的内在观念也日趋成熟。事实上,在这种技术嬗变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恒定的价值观,那就是把握外在世界真相的恒久愿望,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推动了屏幕艺术媒介技术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价值观渗透到屏幕艺术与剧场艺术相互融合的审美空间当中,潜在地改变着剧场艺术形态的本体内涵。
影像的介入使多媒体钢琴音乐会变得极目可视,甚至具备了戏剧性特质;数字仿真使传统戏曲艺术的舞台空间更加唯美华丽,更具视觉感染力。屏幕艺术对剧场艺术的植入与融合,既体现了视像化时代的强势与霸气,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剧场艺术的本体特质。听觉艺术的视像化、戏曲写意的仿真化,这些形式的嬗变使屏幕艺术对剧场艺术的植入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入侵”。从海德格尔到鲍德里亚,从“世界图像时代”到“超真实”,西方思想界对技术理性形而上学的忧虑时刻警醒着后人,也引发了对于“多媒体舞台艺术”的忧思。注重分析、思辨的技术理性对于剧场艺术的大规模植入,是否会削弱人类自身对于剧场艺术的感受力,使传统剧场艺术的艺术想象空间受到挤压,这是“多媒体剧场艺术”嬗变过程中有待考量的问题。
倒是英国的新锐创作团体“1927剧团”为业界带来了些许启示,他们用动画投影与舞台表演相结合的方式创作了一系列多媒体戏剧作品,在屏幕艺术与戏剧形式相结合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上街的动物和孩子们》(2010)描述了伦敦贫民区底层市民的生活状况,诠释了有关理想、现实、冷漠、疏离等一系列人性主题,表达了对人类自身的关怀与反思。作品将多媒体动画作为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与三名真人演员的表演有机融合,多媒体设计天马行空,极具象征性和夸张的黑色幽默效果,使观众沉浸在一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阐释的意象世界中,而现场演员的戏剧表演则适时地彰显了剧场艺术特有的现场性,观众在影像与表演之间体味着阐释与思考的快慰。《机器人魔像》(2015)也以相似的多媒体创作手法探索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终极关联,黑色科幻故事讲述了作品对社会问题的前瞻性预言,令人联想起“阿尔法狗”[1]“阿尔法狗”(AlphaGo):一款围棋人工智能程序。2016年3月,“阿尔法狗”挑战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并以1∶4最终胜出。对于人类智慧的挑战。这些充满反思与批判色彩的多媒体戏剧作品,以视觉隐喻的形式引发人们的思考,屏幕艺术对剧场艺术的技术性植入却更加有力地阐释了人性主题,这恐怕正是对技术理性满怀忧虑的思想者们所乐于看到的。正如海德格尔始终倡导的“存在”,“存在的意义也因人之在变成精神的现实,在与人的际遇中呈现无比丰富的意义,并以无限多样化的形式向人洞开”[2]郭忠义、韩贵昌: 《“向死而在”何以可能——基于海德格尔死亡论的理解与领会》,《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8页。,人的现实存在本身才是意义所在。剧场艺术的魅力之一就是将观者召集在一个密闭的艺术场域之中,借艺术作品来开掘人类精神世界的巨大意义创生空间,延展人们对于人生在世的深沉思索。在屏幕艺术与剧场艺术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技术革新对艺术精神的改写不应该以消蚀人类自身的艺术感知能力与思考力为代价,那些在更大程度上拓展剧场艺术意义维度的多媒体舞台作品,才能够从根本上确证新技术在剧场艺术领域的存在价值。如何在屏幕艺术大举来袭的当代剧场空间实现两者在“意义”层面的有机交融,而非单纯的图像化改造,这是我们发展当代剧场艺术必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问题。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当代青年传统艺术审美接受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批准号L15AZW002)成果;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立项课题“提升艺术类本科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的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JG15DB391)成果。
臧娜: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陶璐)
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成果丰硕
8月21日,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第一次工作交流会在西安召开。全国22家首批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的代表作了交流发言。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庞井君作总结。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周由强主持会议。建设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强改进文艺评论工作而作出的重要举措。22家基地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和华南,覆盖了文学、电影、电视、戏剧、音乐、戏曲、美术、书法等多个文艺门类。基地成立近一年来,累计举办研究研讨等各类学术活动80余次,形成专著成果10余种,理论评论文章近百篇。
(供稿:胡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