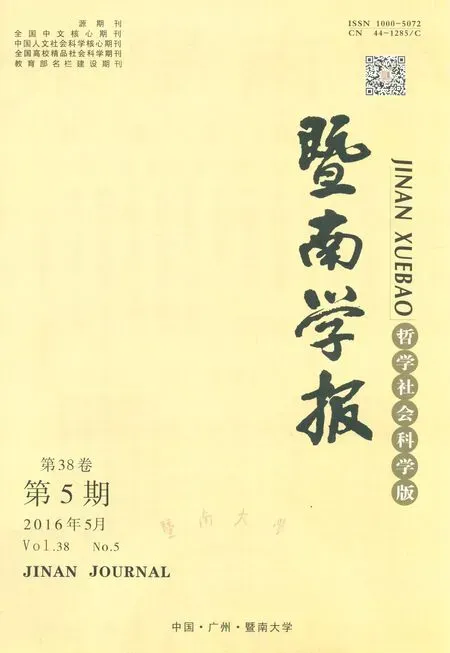辩护与诠释: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研究
肖清和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72)
辩护与诠释: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研究
肖清和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72)
明季天主教入华,既面临着如何与本土文化相处的难题,又时常遭遇到官方或民间的强烈反教行为。针对官方与民间的反教行为,天主教传教士与信徒撰写了大量的护教文献。然而广义的护教文献不仅仅包括因为教案而产生的辩护文本,还包括由传教士与士大夫所撰写的为天主教进行合法性论证的文献。通过对典型的护教文献的文本分析,文章尝试对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的论证模式进行总结与反思。从明末到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的论证模式主要有实用论证、适应论证、差异论证与先例论证。这些论证模式是天主教根据不同的社会处境,为天主教的合法性进行论证而形成的。
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
外来宗教进入中国之始,往往会与中国文化产生碰撞与冲突。作为“异质”的天主教在明末清初进入中国之后,也与中国社会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在面临着本土文化的强烈反弹之时,天主教的传教士以及信徒如何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文化进行辩护,不仅值得细致深入的研究,而且对于今天思考基督教中国化、构建汉语神学均有裨益。目前学术界对于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研究散见于一些对明清教案的研究成果之后。①目前学术界对护教文献研究的成果有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关于早期希腊罗马护教论与中国护教论的比较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Xiaochao Wang,Christianity and Imperial Culture:Chinese Christian Apologe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ir Latin Patristic Equivalent,Brill Academic Publisher,Leiden,The Netherlands,1998.王冰:《关于〈熙朝定案〉的研究》,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李向平:《明末天主教与中国佛教的冲突:以〈天主实义〉与〈圣朝破邪集〉的对应中心》,载《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420页;诸伟奇:《“不得已”、“不得已辨”、“历法不得已辨”之书名及版本》,载《古籍研究》,安徽古籍研究所编,2001年第3期;周杰:《“事天之学”如何“补益王化”:从〈辩学章疏〉透视徐光启的天主教信仰》,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第62-65页;董少新:《论徐光启的信仰与政治理想——以南京教案为中心》,载《史林》2012年第1期,第60-70页。本文首先概述明末清初护教思想的来源即由反教运动引发的护教行为,其次对明清天主教的护教文献进行分类,并就典型文献进行探讨,最后就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的论证模式进行总结与反思。
基督教进入罗马帝国时期,曾遇到如何处理与希腊、罗马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面对反教指控之时,希腊、拉丁教父使用不同的路径进行处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求同”(如查斯丁,St.Justin Martyr,c.100—c.165)与“辩异”(如德尔图良,Q.S.F.Tertullian,c.160—c.225)。②参见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关于早期希腊罗马护教论与中国护教论的比较研究》以及《剑桥基督教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Volume 1-2,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2007)的相关论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也采用了类似的辩护策略,但由于时代处境不同,传教士们护教思想的论证模式有所不同。除了要说明天主教在文化上的合理性之外,传教士迫切需要论证的是天主教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合法性,而外来宗教的合法性往往要建立在既有的传统政教关系以及夷夏关系的框架之内。因而,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思想不仅仅是传教士以及天主教徒对反教思想的回应,更是对自身发展以及如何在中国社会立足发展、如何与中国社会文化进行良性互动之基础。
一、教案与护教运动
而“三柱石”当中护教最为得力的当属徐光启。万历四十四年,徐光启获读了沈的奏疏后,七月便上疏竭力为天主教辩护,此奏疏被教中人称为《辩学章疏》。徐光启洋洋洒洒数千言,针对沈的控诉一一反驳。在奏疏中,他禀明自己是一名天主教徒,通过数年来与耶稣会士的交往,他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实皆圣贤之徒,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徐光启在分析完天主教的优胜之处后,请求朝廷像容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那样宽容地对待天主教,并提出了考验的办法让皇帝自行判定其辩解是否充分。万历皇帝阅完《辩学章疏》后御批“知道了”三字,而对于沈氏奏疏置若罔闻。当南京教难爆发至无可挽回的地步,驱逐传教士的圣旨颁布后,徐光启亦明白此事已经无法挽回,便劝说庞迪我、熊三拔自动南下,由礼部派遣专人护送,故而此两人没有收到押解之苦,而安全抵达澳门。此外,他还像杨廷筠一样,设法在家中藏匿被通缉的传教士,这一点可见于其多封家书之中。万历四十四年一封家书云:“郭先生(郭居静)何时来,何时去,仍在西园否?”⑤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89页。另一封家书又云:“南京诸处移文驱迫,一似不肯相容,杭州不妨。如南京先生有到海上者,可收拾西堂与住居也。”⑥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2页。万历四十五年又一封家书曰:“旧年先生到,住在西园,今年若旧先生来,可仍住在西园。若他新先生来,可请于蟠龙住。如无房屋,可收拾几间,得与东园内者住。如少,再造一二,不妨也。”①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页。可见徐光启对于传教士可谓关心备至。南京教案稍稍平息时,徐光启深知传教士在中国宣教,非筹划一永久坚固之基础,不得平安无事。为此,徐光启积极推荐西士治历,欲圣教在中国得以坚植其根。②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此举后,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等得以修历,得皇上盛宠,出入宫禁颇形便利。除此之外,南京教案中积极为天主教辩护的人还有叶向高等,南京教案的爆发,不至于扩大并一直延续下去,非徐光启等人的护教不可也。
南京教案稍稍平息不久,艾儒略等开始入各地宣教,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好景不长,明崇祯十二年,福建地区文人僧俗在自称“白衣弟子”黄贞的呼吁下,撰写并由徐昌治订立而成八卷本辟邪巨著《圣朝破邪集》,对天主教展开了全面而猛烈的攻击。为辩驳《破邪集》对天主教的攻讦,耶稣会士和中国天主教徒纷纷著书立说,为天主教辩护。此阶段的护教运动主要表现为著书立说,为天主教辩护。
清初借历法宣教的汤若望得以行走宫廷,从而大大促进了晚明受严重挫折的天主教宣教事业的发展。距离南京教案五十年后,明清天主教传教士遇到了其在中华大地宣教史上的第二次重大教案——1664年至1665年间由杨光先鼓起的“清初历狱”。③肖清和:《身份认同与历法之争——以〈不得已〉与〈不得已辩〉为中心》,《天主教研究论辑》(第5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220页。早在“历狱”爆发之前,杨光先就已经开始对天主教展开了攻击,然而耶稣会士始终都在针对其攻击一一为天主教辩护。1659年杨刊著《辟邪论》散布谣言,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神父便以“妄言繁兴,圣教日晦”,作《天学传概》④《天学传概》,利类思著,1662年成书,书前有许之渐、李祖白作序弁首。许之渐,字仪吉,号青屿,五进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江西道御史,性耿直,弹劾不避权贵。以辩之。⑤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杨光先见此更怒,著《不得已》诬圣教,利类思又做《不得已辩》以辩驳之。康熙三年,杨光先上疏弹劾汤若望等三大罪状,掀起了“历狱”的风波。无从反击的耶稣会士和诸多中国天主教徒皆受极刑,非因时太皇太后(顺治母后孝庄)以天谴可畏而不得减。“历狱”风波平息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以其卓越的治历之术,成功地再次取得皇帝信任,并于1669年8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此后他治历之余努力为“历狱”中蒙冤的教友平反,且著书为天主教辩护:1678年编辑《熙朝定案》,把康熙皇帝亲政之后有关处理“历法之争”的文书汇集起来,充分反映“历狱”平反昭雪的始末。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徒的行动让康熙得以判定天主教教理实与中国礼教相符,并于1692年3月22日发布敕令,准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并强调“留下诸教士实有益于国家”。⑥杨森富:《中国天主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2页。
在明清天主教的护教运动中,平民护教的方式与士大夫信徒有所不同。平民信徒如姚若望愿意为保卫天主教而摇旗呐喊“愿为主死”。士大夫信徒在教案发生之时,不仅通过为传教士提供保护,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来为天主教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士大夫信徒所撰写的大量著作,为他们所信仰的天主教进行解释与宣扬,并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会通、融合。这些护教文献不仅是在传达天主教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天主教在面对中国社会之时对自身的合法性而进行的论证与说明。因此,所谓护教文献是指天主教在面对中国社会对天主教的批评与攻击而形成的证明天主教为合法的文献,其中包括针对官方的反教行为而形成的护教奏疏、文集等,以及针对民间尤其是佛道教的反教行为而产生的护教文章、著作等,主要来源于一次次反教运动后的护教运动。在护教作品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天主教徒的作用尤为重要,大部分护教作品是由中国天主教徒完成的。当然,耶稣会士们在护教作品的大量问世过程中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而广义的护教文献远非仅仅来自于教案后的护教运动,奉行“刊书传教”传教策略的耶稣会士,一直都有著书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性辩护,如艾儒略在福安传教时著有《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三山论学记》和《口铎日抄》等向士人阐明天主教的教义及其与“合儒”的本质。换言之,护教文献是随着明清天主教的宣教事业而诞生的,并非完全出自护教运动。
二、明末清初的护教文献
在明末第一次大规模反教运动南京教案后,出现了一大批护教文献:徐光启《辩学章疏》、杨廷筠《鸮鸾不并鸣说》、庞迪我《具揭》等。《圣朝破邪集》问世后,面对文人僧俗的批判,中国天主教徒又撰有一批为天主教进行辩护的文献。这些护教文献大多是通过对反教言论的逐条辩驳而形成的。杨光先掀起“历狱”风波后形成了一系列试图从皇权对宗教的支持来获得天主教的合法性的护教文献:如南怀仁《熙朝定案》等,类似文献主要是收集前朝皇帝对天主教的褒奖之词或无形中承认天主教的存在与发展的敕令、诏书等为天主教辩护;在此后的乾隆朝大教案中,又出现了戴进贤的《睿鉴录》等护教奏疏集。
明末清初天主教护教文献繁多,按其来源可分为被动地针对反教者攻击而形成的护教文献和积极主动地为天主教辩护的护教文献。其中被动产生的护教文献又可划分为针对官方的反教行为而产生的护教文献和针对民间以及佛道的反教而形成的护教文献;主动为天主教辩护的文献主要是从文化、政治、义理等方面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性进行辩论的文献。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以及中国天主教徒的护教文献中体现了两大主旨,即:天主教合乎儒家正统,天主教信仰是“合儒”甚至能够“补儒”,并非邪教;佛道妄谬。护教者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并努力从这些文献中寻求与天主教信仰相合者,为天主教辩护。
(2)通过深部钻孔系统揭露破头青断裂、九曲蒋家208断裂深部行迹并通过切割深度、资源量规模对比,确定九曲蒋家208断裂为招平断裂北段深部找矿的主要目标。
(一)徐光启与《辩学章疏》
南京教案发生后,被誉称为教内“三柱石”之一、时任“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上疏为天主教进行辩护。该疏是最早由信徒为天主教进行辩护的公开文献,因而具有典型性。《辨学章疏》全文只有3 000多字,但其中所体现的护教思想却深刻影响到后来天主教的护教行为。
以上三点辩护,实际上表明徐光启想表达三个意图。首先是意欲说明传教士都是“圣贤之徒”,因而天主教与异端邪教不同;其次,徐光启将传教士主动向中国宣教说成是传教士“闻中国圣贤之教”而“来相印证”,从而将“归化”中国的传教目的有意隐藏,而突出天主教与儒家的“合辙”;再次,徐光启辩称天主教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教化功能,实际上是说明天主教可以存在的直接原因。接下来,徐光启以较多篇幅论述儒家、佛教因为自身原因而失去了道德教化功能。在这里,徐光启对儒家与佛教予以分别对待。徐光启认为儒家“空有愿治之心,恨无必治之术”,所以借助佛教,但“佛教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实际上,徐光启护教思想与传教士所采取的“补儒易佛”策略一致。但徐光启在《辩学章疏》里,并没有提出要让天主教代替佛教,而是“救正佛法者”,并希望让天主教“暂与僧徒道士,一体容留,使敷宣劝化”。换言之,在《辩学章疏》里,徐光启希望天主教能和佛道一起辅助儒家,“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徐光启认为:“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主,以容纳僧道者容纳诸陪臣,则兴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之上矣。”①徐光启:《辨学章疏》,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1册),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5-27页。
综观之,徐光启《辩学章疏》表明天主教的合法性来源如下:首先,天主教合乎儒家正统,即传教士是来与儒家“印证”,并且是在儒家正统之下,可以弥补儒家在道德教化方面的不足;其次,天主教合乎传统的政教关系,即天主教主动接受官府的控制与管理;再次,天主教具有儒释道所不具备的社会功能。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徐光启在论证天主教存在的合法性时,还使用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例子。释道二教,“道术未纯,教法未备”,但仍然被朝廷若容纳;而“回回一教,并无传译经典可为证据。累朝以来,包荒容纳;礼拜之寺,所在有之。”因此,在道术、教法、经典等层面上高于释道、伊斯兰教的天主教理应被接纳。
《辩学章疏》的护教思想影响深远,甚至被后世传教士以及信徒刻碑立石,以天主教对儒家社会的功能与作用来为天主教的合法性进行辩护。②《辩学章疏碑刻》,附于《明相国徐文定公墨迹》,阳湖汪洵书耑,光绪癸卯年鸿宝斋石印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航头书库。
(二)艾儒略与《熙朝崇正集》
艾儒略,字思及,明末来华的著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生于1582年,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来华,1649年卒于福建延平,其在中国传教长达十年,堪称天主教传华史上第二代耶稣会最为杰出的传教士之一。③[意]柯毅霖著,王志成等译:《晚明基督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2页。艾儒略一生致力于天主教在中国地区尤其是福建的传播,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使其传教事业一路辉煌,“福建宗徒”、“西来孔子”等美称便是其宣教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佐证。此外,艾儒略知识渊博,与中国知识分子广泛交游,诗集《熙朝崇正集》便收录了当时艾儒略所交游的闽中士大夫酬答其的诗作。
《熙朝崇正集》④《熙朝崇正集》,载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初编》,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633-691页。又名《闽中诸公赠泰西诸先生诗初集》抄本,原稿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古郎编目第7066号,后被收录于《天主教东传文献初编》。其书封面左题“是集以相赠先后为次,未能尽序齿爵也,尚有赠者容刻”,目录页题“崇正集卷□”,又题“闽中诸公赠诗”。据方豪考证,此书是福建文人赠与传教的诗作合刊。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另有一部《熙朝崇正集》,是为明崇祯十一年(1638)福建泉州天主教刊刻,内载有景教碑文、温岭发现十字架、上谕与奏疏以及徐光启和张赓等的撰文等等,此册亦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古郎编目1322号。⑤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此两本书籍虽名同,内容却迥异,方豪认为抄本之所以与课本采用同一题名,“盖同为表扬天主教性质”①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康熙以后陆续刊印问世的《熙朝定案》也属于同一类别。
《熙朝崇正集》是一本中国士大夫赠与耶稣会传教士的诗集。这本诗集中,赠诗作者多达71人,并且相当一部分还是当时非常有名望的人,如叶向高。诗集收录的诗作更是数量可观,共有84篇,受赠者是当时的天主教来华传教士。
(1)西方天主教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实乃“心同理同”,传教士是“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的西儒。《熙朝崇正集》所收录的诗篇中,最少有十二首直接提出了“圣学无二门”、“异地同心里”、“此心此理何分地,同轨同文自一时”之类的诗句。②《熙朝崇正集》,载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初编》,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653-666页。“心同理同”是士大夫们宽容、接受乃至弘扬天主教的基本依据。《熙朝崇正集》中的友教诗人宣称西方天主教、西学与儒学传统“心同理同”,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是仰慕中华文化的“西儒”,而并非异类。
(2)西学科技精良,传教士是“万国舆图收掌上、一元星历灿玑穿”的畸人。随耶稣会士而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是儒家士大夫友待甚至接受天主教的又一重要因素。《熙朝崇正集》中的诗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赞叹与仰慕主要集中在历法、地理科学、数学以及一些传教士进贡的精巧仪器等方面。首先,关于修改历法,按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法制,个人是不能从事天文历法研究的,它是被朝廷所垄断的,即使是个人修史这样的事情,一旦被官府发现也是灭门之灾,况且涉及关乎国运的“天学”。③此处“天学”,指天文学研究。然而这些入华的传教士却几乎个个精通历法事宜,且他们的测定结果比之钦天监的官员更加准确,这让人惊叹不已。其次,关于地理科学,《熙朝崇正集》第二十七首蔡国铤提及传教士所携带之地球仪:“地轴圆球自利君,年来西学又奇闻,周天日表图中见,二极星枢眼底分,宛转金声开八面,依微绿字起三坟。”此外,在地理方面传教士还开创了中国舆地学的研究先河,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也就是《熙朝崇正集》第八首庄际昌所言的“万国车书会”;再次关于数学方面,《熙朝崇正集》第三十首陈圳所书“自是西方一伟儒,载将文教入中区,发挥原本几何理,指示微茫万国图,大道繇来传竹简,迷川何处问金桴”提及并赞叹利玛窦的《几何原本》;最后关于一些精巧贡品的描述在《熙朝崇正集》的诗篇中也是处处可见。西方耶稣会士精湛的科学技术是友教士大夫的宽容乃至接纳天主教的重要因素。
(三)西学补儒、合儒。传教士是“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的良师益友。对于中国儒家传统士大夫而言,接纳天主教的重要因素即为西学可以补益王化。入教士大夫认为,耶稣会士所带来的西学合乎儒学传统,允许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能有起到“合儒”、“补儒”的功效。《熙朝崇正集》的赠诗者们也毫无例外地持此观点。《熙朝崇正集》所收录的赠诗中至少有十篇以上的诗句论述了天主教合儒、补儒的有益之处。
(4)西方传教士是“知天事天”的虔诚传教士而并非邪教徒。《熙朝崇正集》的友教赠诗者们还从宗教信仰方面为天主教传教士颂扬,为耶稣会士树立了一个“知天事天的虔诚传教士”的形象,并且在《熙朝崇正集》的赠诗中也能得到体现。
(三)利类思与《不得已辩》
康熙四年,杨光先所撰的《不得已》刊行后,利类思、南怀仁等撰有《不得已辩》,一方面为了论证西洋历法之合理,另一方面即消除杨光先反教的不良影响。
《不得已辩》原刻本为康熙四年北京刻本,单边,单黑尾,书口标有书名及页码。此刻本后分别于康熙九年、康熙二十年(前后)、道光二十七年和民国十五年重刻。纵观《不得已辩》全文可知,《不得已辩》是以“条驳”的形式对杨光先基于天主教的指控逐条反驳。根据内容,利类思的辩驳主要集中于天主论、耶稣神人二性、耶稣降生受难等问题上,而其中心主旨,即为证明天主教的合法性。利类思的辩驳以杨光先之攻讦为基,逐条辩驳。
首先,关于天与天主。《不得已辩》第一至第十四条、第二十至第二十四条以及第三十二条皆是利类思针对杨光先对天与天主的攻击所做之辩驳。利类思一方面采用利玛窦的辩教策略,使用精审的经院哲学作为主要的辩论材料,另一方面援引中国儒家经典,辩驳杨光先的错误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天主乃全知全能之造物主,他无始无终,并主宰着天地万物。其二关于天主降生及耶稣神人二性说。针对杨光先对天主降生的误解以及对耶稣的错误判定,利类思用了很大的篇幅解读何为天主降生的要旨。
其次,关于天堂地狱。《不得已辩》第十五至第十九条乃利类思针对杨光先在《不得已》中对天主教天堂地狱说的指责所作的辩论。杨光先对天堂地狱说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天堂地狱乃释氏传教借用之说并非真实存在、有罪哀求耶稣即可升天堂之说荒谬无度、耶教窃佛氏天堂地狱反辟释以自树等方面。利类思亦从这几点出发对杨光先的指摘进行深入的辩解。利类思首先举《诗》、《书》所载以证“天堂地狱之说,载之经史,见之事迹,班班可考”。紧接着举耶教天堂地狱说与释家天堂地狱说之区别。最后总结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说与佛教宣教史天堂地狱说“名同而实异”。利类思针对杨光先攻击耶教辟释之说,辩驳云天主教实“治世之大端,治人心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①《熙朝崇正集》,第274页。,传教士东来后辟佛道实因佛道荒诞无益于治世。
最后,关于天主教传教士之传教目的。《不得已》乃至其他众多反教文献对于天主教及其传教士的指责大多都极力批判其传教动机不纯:“西士在中国借传教之名,而谋不轨之事”;天主教之传教书籍,乃“窃中夏之语言文字,曲文其妖邪之说”。杨光先在《不得已》中即控诉利玛窦等图谋不轨,称其以贸易为名,“实踞澳伏戎谋中国”。利类思据此深入阐释了传教士入华并非谋为不轨。利类思在辩论中诠释了杨光先所指摘西士居于澳门是实际理由,并说明海寇攻击澳门时传教士有功于保卫澳门,并无谋不轨之嫌。至于世间所传传教士图谋不轨,利类思列举了数端予以反驳。
利类思《不得已辩》所依据的主要是天主教神哲学,所做的辩驳实际上是就某些难以理解的天主教教义进行详细解释,目的在于证明天主教并非如杨光先所言的邪教。当然,利类思主要是对古代儒家经典重新诠释,证明天主教与古儒相一致,并引用朝廷对天主教的许可,尤其是对汤若望等传教士的认可,证明天主教并非邪教;同时,亦表明天主教传教士只是来华传播教义,非有图谋不轨之意。
(四)戴进贤与《睿鉴录》②《睿鉴录》,载吴旻、韩琦:《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60页。
戴进贤(Ignatius Kgler,1680-1746),德国耶稣会传教士,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美丽小镇——兰茨贝格的一个平民家庭。十六岁时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并顺利成为一名修士,继而步入大学深造,主修哲学、数学、神学以及东方语言。后由于受到耶稣会士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1506-1552)的传奇故事的感召,他坚定了一个愿望:“前往中国,传播主的福音。”1715年戴进贤等到上级通知乘船东行来华。戴进贤东行的旅程比较顺利,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顺利抵达澳门。然而此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处境与康熙初年已经远不相同了。这主要是由于“礼仪之争”的爆发,一向宽容对待天主教的康熙皇帝,也于1706年改变了其刚刚发布不久的“容教政策”,禁止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同时又欢迎身怀技艺的传教士到宫廷为大清服务。他下令只有深谙天文历法,且遵“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方能进入中国。戴进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国的。据记载,他到达北京之前就已闻名遐迩,到京之后即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任职达29年之久。③[法]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版,第775页。戴进贤担任钦天监监正期间,在天文历算方面的工作是扎实而卓有成效的。同时,在传教期间的护教行为亦是功不可没,最具代表的成就即《睿鉴录》的编订。
戴进贤进入中国传教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然而他可称得上是十分尽职,虽然那时口头公开传教已不可能,但他试图以文字的方式宣传天主教。《睿鉴录》,系他与耶稣会士徐懋德(Andreas Pereira,1690-1743)①徐懋德,葡萄牙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关于其出生时间有1689年和1690年两说,澳门文化司署1990年版《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一书第134页注26载:“1741年的简历说他生于1690年,但是,其他人说他生于1689年。”故此处以简历上的1690年为准。合撰,1737年刻于北京。《睿鉴录》的撰写与刻印都是秘密进行的,后来河南省巡抚雅尔图在河南查禁天主教书籍时,才发现了这本书。雅尔图还曾上疏建议予以缴销:“是月,河南巡抚雅尔图走言:豫省民俗,崇尚邪教,近查获天主教书《睿鉴录》一本,镌刻龙纹,朱字黄面,系西洋人戴进贤奏折及他所奉谕旨”,雅尔图奏请缴销此书,然乾隆皇帝仅批示“著海望查奏”。②《清史编年第五卷·乾隆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另据乾隆五年四月的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5载“乾隆五年河南查获钦天监正戴进贤编纂的传教书籍《睿鉴录》,朝廷未置如何”。
《睿鉴录》的主要目的是戴进贤希望借此书上奏乾隆皇帝,以先已有之对待西人之例友待西人。③至于《睿鉴录》题名及其所含意义详见Jocelyn M.N.,Marinescu:Defend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The Jesuit Defense of Christanity in the Lettres Ediflantes Et Curieuses&Rulijianlu in Relation to the Yongzheng Prosciption of 1724,Kansan State University,Manhattan,Kansas,2008,p.237.《睿鉴录》共记录九份奏折的全文,其中第四条和第七条为“刑部尚书兼兵部事臣尹继善”与“内大臣兼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海望”为遵旨所奏,其他皆为戴进贤、徐懋德、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1697-1747)等耶稣会士所奏。④《睿鉴录》,第54-60页。内容大致是乾隆元年(1736年)至乾隆三年耶稣会士戴进贤等因教会事宜向乾隆皇帝奏请的奏折。按奏折具体内容可划分为三大类,其中第一、三、五为第一类,此三份奏折皆由耶稣会士所奏,旨在肯定乾隆“免禁”天主教;第四、七条为第二类,此两份为清廷官员所奏,旨在“为奉奏事”;其余的四条为第三类,旨在按例奏报相关教会事宜、谢恩。此三类奏折中,具体涉及戴进贤等为天主教辩护事宜的主要是第一类。
《睿鉴录》第一条为乾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西洋人戴进贤等奏,其标旨为“为沥愚诚、求恩怜悯事”⑤《睿鉴录》,第54页。。戴进贤等在奏折中首先阐明此次奏请缘于有官员上疏要求禁教:“顷闻通政司参议查思海以臣等系外国小人,请禁止军民入教”;然后,戴进贤从正面展现了耶稣会传教士自1593年至1736年间在清廷的突出贡献,其中重点提到利玛窦东来后“特疏容留,建堂传教”,以及汤若望因功高而得顺治皇帝所赐“通微教师”及立碑颂扬之事,并附语康熙三十一年内阁会同礼部议定之“容教赦令”全文,并得出结论:“故自利玛窦以来将二百年,各处西洋人皆安居乐业,得尽其传教劝人之志。”进而述及耶稣会传教士东来的目的“惟笃守敬主爱人之十诫,劝人趋善避恶”,他们表明奉教人亦非贪图利益而来华,这一点圣祖章皇帝及圣祖仁皇帝皆洞察,故而才会屡次颁旨声明天主教并非左道,无关异端,对传教事业“保护矜全”。戴进贤等在此番叙述后发出呼喊:“今之奉教军民皆在康熙三十一年准行之后,何曾违禁乱行?”控诉反教者“信口雌黄”诬天主教为邪教,居心不良;奏折最后指出,反教者控诉传教士要求禁教,对西人的污辱等都无关紧要,然“玷辱教名,且重伤列祖钦褒指点”关系匪浅,故而不得不列陈事件始末于乾隆钱,请求圣明裁判,并肯定乾隆以康熙三十一年同行之案例停止禁教。
《睿鉴录》第三条为乾隆元年十月十六日,西洋人戴进贤等奏请,旨为:“为诬陷实深、孤踪无倚、仰求睿鉴、俯赐救援事”。乾隆元年十一月初六,北京内外大小街道皆张贴告示禁止天主教,宣称严拿教中人送刑部治罪,戴进贤等访得此番风波缘自中国天主教徒刘二因“依教规与小孩洗额诵经”,刘二亦因此入狱并受重刑。戴进贤联合徐懋德等为护刘二,更重要的是为护天主教立即上疏请求乾隆皇帝救援。戴进贤等在奏折开篇即坦言事情原委,随后表明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缘由乃“慕义向风,委身阙下,无非劝人以当敬当爱之道”,戴进贤列举六大案例,力言耶稣会士入华后“褒嘉巨典,炳若日星,笔难恭纪”,戴进贤以先之案例上呈乾隆,并称在康熙雍正时期耶稣会士皆因功而备受保护包容,为何此时却遭到反教者的一再迫害,①此处迫害是指当时朝廷内反教官员引雍正年间满保案要求禁教。并表明自己可以忍受欺侮,但不可波及“教名”,故而上疏恳请乾隆“睿鉴”,以还天主教“清白”。
《睿鉴录》其他条目的奏折皆为饱含当年皇帝对天主教褒奖、包容之词,其中一些是传教士按例向皇帝上禀教会发生的与朝廷相关的事宜,一些是对皇帝赐予教会人士金银的感激之词。由此可见,《睿鉴录》在护教思想上继承了利玛窦的适应政策,戴进贤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乾隆初年的禁教中获得康年三十一年“容教赦令”的待遇,期待在附合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乾隆皇帝的承认和容许。
三、结 论
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清天主教在面临着中国社会尤其是官府的弹压之时,需要对自己的信仰与文化进行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对天主教的合法性进行必要的论证与说明。对比天主教之前的佛教、道教而言,天主教在论证合法性的方法与模式略有不同。与佛道相同的是天主教意识到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往往取决于该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天主教也积极寻求政治的许可,自觉接受传统的政教关系,从而为自己的发展提供保护。当然,针对不同的面向,天主教在论证合法性的时候有所侧重。
首先,实用论证。此模式常常针对官府的反教行为。类似于佛道常常使用的论证方式,天主教证明自己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社会治理。徐光启在南京教案之后所撰写的《辩学章疏》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此模式的问题是明季中国社会已有三教,天主教对社会的正功能可以由佛道提供。因此,徐光启又提出“补儒易佛”。“补儒易佛”正可以说明天主教在功能上独一无二,从而非常强有力地论证天主教之必要性。
其次,适应论证。此模式主要针对儒家士大夫群体。利玛窦成功运用“适应策略”,通过附会古儒经典、使用儒家词汇来解释天主教神学,同时与士大夫成为朋友,利用人际网络为天主教寻求庇护。利玛窦的做法后来被康熙皇帝总结为“利玛窦规矩”。其论证方法是“合儒”、“补儒”、“超儒”。从表面上看,“合儒”、“补儒”是论述天主教与儒家(古儒)相一致。类似于罗马帝国时期护教士查斯丁论述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相一致。但在“合儒”、“补儒”之背后则暗含着德尔图良的“信仰主义”内容,即“超儒”。当然,利玛窦的超儒色彩还不是很明显。艾儒略的《熙朝崇正集》也是适应论证的具体体现。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展示天主教与儒家的一致性,可以为天主教提供较为宏大但易被儒家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合法性基础。
再次,差异论证。此模式主要针对反教群体有关天主教以及西方科学的指控。适应论证虽然获得奉行“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士大夫的认同,但是反教群体则往往指出此模式的缺陷,即既然天主教与儒家相一致,那么持“孔子道无亏欠,本不须二氏帮补”观点的士大夫认为,儒家同样不需要天主教。因此,传教士以及信徒在论述其一致性之时,还常常论证天主教与儒家之不同。在针对杨光先有关天主教以及西方科学的指控之时,利类思撰《不得已辩》解释西方天主教,南怀仁撰《历法不得已辩》解释西方科学。由于西方天主教与西方科学与中国儒家迥异,二者的论证与解释差强人意。
最后,先例论证。此模式主要针对皇帝本人的反教行为。在清初,皇帝与传教士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关系。康熙晚年、雍正以及乾隆时期都发生了皇帝本人的反教行为(如康熙的禁教令、雍正时期的苏努案以及乾隆时期的禁教等),传教士则通过上疏诉诸既往天主教对朝廷的贡献、先帝对天主教的优容等来天主教进行辩护。戴进贤的《睿鉴录》就是此例,《睿鉴录》之前的《熙朝定案》以及之后出现的《正教奉褒》都是使用此种模式为天主教进行辩护。
从明末到清初,天主教护教的论证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当然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依然承继了适应论证,但是清初的局势不同于明末,实用、适应论证虽然依然有效,但天主教与儒家之间的张力日益明显。第三代天主教徒越来越多地诉诸差异论证,提出超儒(如张星曜)、复儒(如刘凝)等主张,或者诉诸先例论证。但很明显,这些模式的辩护效果越来越差。反思今天的基督教中国化以及构建汉语神学,我们更应重视处理基督教的合法性问题。最为迫切的是基督教在现有的政教关系框架之下,如何获得如佛教、道教等宗教同等的地位与空间;而最为重要的则是要处理在中国文化处境下,作为外来的、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正当性。窃以为,合法性问题是基督教中国化以及构建汉语神学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明清天主教所提供的四种辩护模式或可为解决此问题提供有益参考。①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讨论,可参见张志刚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2015年版;汉语神学的最新成果,参见赖品超:《广场上的汉语神学:从神学到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道风书社2014年版。
(上海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王丹丹在资料收集与论文撰写过程中提供了诸多协助,谨致谢意。)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B975
A
1000-5072(2016)05-0085-10
2016-03-01
肖清和(1980—),男,安徽潜山人,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基督教史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和研究》(批准号:12&ZD128);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儒家基督徒研究:历史、思想与文献》(批准号: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