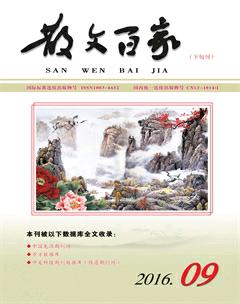光
江书怡
这是六月的一个下午,阳光还不带有灼烧的滚烫感,像是亮金色的缕衣随性地垂坠下来,挂在云端上,草尖上。在这种暖烘烘的热气中,抱着最心爱的民谣吉他,哼着旋律,拨出一两节Blues,坐在落地窗前看着地板上灰尘旋转舞蹈,放纵自己浮想联翩杜撰一颗砂砾的故事,是最最幸福惬意的事。
看了一眼时间,快三点了,我站起身,蹬上一双盛满阳光的帆布鞋,出门,坐上电梯,走上楼顶的天台。几张格子布的,条纹的橙色的床单被夹子固定在钢丝绳上,等风来把它们吹成一面面明艳光亮的旗帜。隐约看到了那唯一一面爬满了常青藤的墙壁,紧挨着一条漆皮已经剥落的长椅,我疾步往那个方向迈去,那个熟悉的背影再次映入眼中;只夹杂着一丝深色的短卷发用橡皮筋潦草束成一个结,褪了色的蓝色中袖布衫,驼着背但眼睛却始终平视正前方,像是盯着某处的虚无。脚步轻轻地慢下来,走到那人身边,坐下,用与她同样的角度直直的盯着正前方,空气仿佛都安静祥和地要静止。
与这位老人认识,是半年前的事了,那天是雪后的第一场放晴,我搓着手哈着气第一次走上天台,寻求冰封后午阳的温度。我第一次见到她,坐在还裹着冰碴的常青藤下,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我有些好奇地走到她身边坐下,迟疑一会,开口道:“奶奶好?”她缓缓地转过头,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久久才转过头去,阳光把她的几缕银丝映在脸颊上,看上去在微微发颤。过了许久,她终于开口:“姑娘多大了?”“15。”逐渐,我们开始慢慢说起话来。一天天下来,竟也渐渐熟络,慢慢地得知了她的故事。
老人已经七十春秋,本当是安享晚年的年纪,可上苍仿佛是决意不许她就这样度过最后一段幸福时光。两年前,她的儿子带着一家三口自驾游,出了车祸,无一幸免。得知这个噩耗前一秒时,她正坐在床边边织毛衣边嘟囔着孩子的归期。而下一秒就像陶瓷碗被重重摔碎在地上一样,她扶着床沿慢慢站起身,圆满的幸福被狠狠撕裂,与毛线一起散落在地。老人想哭嚎,又像是被抽空了全部力气,只能伴着胸腔颤抖起伏的频率从皱纹深处泻出一滴一滴的眼泪。她老伴走得早,本以为还有儿子可以依靠,而在那个无尽的阴雨天里,一瞬间竟就只剩了孤零零的她。花凋零了至少还有果实,而她就像是白忙了一辈子,到结局,却什么也没剩下。
她跟我讲这些时,阳光正温暖的超乎情理,软绵绵地把我们融在一块,常青藤又新添了不少叶子,新洗的被单散着肥皂的清香,空气澄清得温暖好闻,仿佛有苏格兰的bagpipe在回旋,奶奶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连着略窄的额头,抿成一条直线的皱巴巴的嘴,还有脖子上挂着的用蓝色绳子穿起的一串钥匙,都一齐注视着我,仿佛并无什么缘由,又好似有所寻觅。从她脸上我已看不出哀痛与绝望,只是深深的疲惫,深的仿佛要刻进皱纹里。每当此时,我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无以言状的心疼,心疼这位长我将近六十岁的老人,握住她的手,她也握紧我的,在阳光的见证下,两朵影子稳稳地叠在一块儿,分不出区别。
我问过:“奶奶你为什么喜欢来这天台呢?”她总是轻轻地说:“因为这上面有光啊。”
“有光?哪里没光啊奶奶?”
“你来了后啊,只有这里有光了。你看,这常青藤又长高了……”
想起《圣经》第一章的一段话: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
何其幸运,我竟也可以成为一道光。哪怕是在这珠灰的墙边,在这斑驳的长椅上。但这也不会妨碍光的婉妙与柔软,哪怕只能笼罩一个人,一株常青藤,半个下午。
后来,仿佛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只要有阳光普照的空闲下午,我就一定要去那盛满金色的天台上坐在老奶奶的身边,或与她说会话或陪她发发呆。
教科书说:光能是一切生物体的最终能源,那会不会,我们其实就是由光而构成的呢?
正如一切生物都不能背离光而独自生存,那么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那一捧光呢?简爱是罗切斯特的光,绿子是渡边君的光,露伊莎是威尔的光,尼克胡哲是所有残障人士的光。
你呢?是否还记得曾经温暖、照耀你的光呢?
还记得老师笑着说,地球的几十亿年历史,本质也只不过是是能量的周而复始。有人说,人类的存在还真是微茫得毫无意义,但这不是更要我们去传递我们所具有的那温度吗?与其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何不成为即将渴死之人嘴边的一滴泉水呢?
神说,要有光,那你呢,愿意做那道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