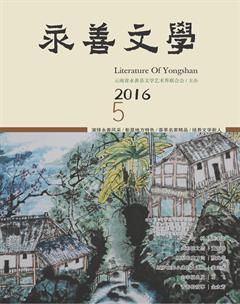古树
陈孝荣
1
张钊拿着斧子和锯子刚刚一打开堂屋门,他老婆邓晶恶声恶气的声音就从黑暗中横劈了过来:“你又到哪里去?”
张钊吓了一跳,似乎看见了声音爆炸背后的火花,刚刚准备迈出门的脚停下了。刚才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张钊发现邓晶已经坠入了梦乡的怀抱,打起了轻微的鼾声,没想开门的声音还是把她弄醒了,看来她对他的警惕并没有放松。在这个世界上,知道他白天是人晚上是鬼的只有他的老婆邓晶和他的儿子张龙。张龙正在外面读大学,自然不会监管他。邓晶自然成了他唯一的监管人。
“你别管我。”张钊没好气地说过,就轻轻地掩上房门,一头扎进了黑夜之中。
此刻,夜的脚步已经迈到了深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抬头朝前面望去,发现极少数农户的路灯正在闪烁,就像燃烧的鬼火,他脚下的步子也就迈得更快了。
张钊有非常特异的能力,善于走夜路,他可以不用任何光源就能够在石榴坪村那些小路上如进入无人之境一样,很顺利地行走。这种功夫是村里的其他人所不具备的,但张钊自己知道这个能力是他自己训练出来的。在漆黑的夜里,他也和别人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他内心深处却有一双明亮的眼晴指挥他很顺当地行走在那些乡村路上,哪里该转弯,哪里有石坎,哪里有土坑,他的心里都清清楚楚。其实唯一的诀窍,就是他白天把那些路一一记到了心里。
从屋里出来,张钊就朝西面走去。走过了一段公路,接着就从一个回头线上折下,踏上了一段小路。他的脚步异常轻,几乎没有弄出任何声响。那些小路弯弯曲曲的,要穿过许多庄稼地和一些树林。这样花了几十分钟时间,他就顺利地来到了一个农户家的门前。这个农户叫李波,离他家大约是三里半的路程。站在李波家的门前,发现他家里也是黑灯瞎火的,没有一丝灯光。顿时,一种让张钊无法抑制的喜悦就在他的心里左右激荡,便迈开步子走到了李波的稻场前。先是站在稻场坎上支起耳朵听了听周围的动静,发现这片区域就像一片死亡区域一样,根本听不到任何声响,哪怕李波圈里的猪、牛、羊、鸡都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张钊的胆子就大了起来,继续走到李波家窗前,站在窗下认真听了听,很快就听到了从屋里传出的一丝轻微的鼾声,而且那鼾声响过一声之后就再没有响了,所以张钊就更加放心了,脸上便呈现出了一种会心的微笑。因为他知道,李波老婆娘家里过喜事,李波和他的老婆都回娘家了,只有李波的母亲留在家里。他的母亲被张钊称之为吴二婶。
张钊放下心,从窗前退回来,然后拐上一条小路朝李波屋后走去。大约爬了半里的路程,终于来到了那片竹园里。张钊先把随身带着的锯子和斧头放下,然后就摸到竹林中间,伸出手去探那些杉树。他知道,这块竹园里一共有七颗杉树,而且这七棵杉树都快成古树了。在这之前,张钊也多次观察过这七棵杉树。这是李波专门蓄下来准备为他母亲做棺材的,其中随便一棵都够制一副棺材,几乎算是石榴坪的老古董了,村里再也找不到这种粗大的杉树。这些年,李波这几棵杉树之所以在偷盗成风的环境里还稳稳地长在这里,是因为这些杉树离他的家非常近,就在他屋后的一片竹园里,不管是哪个盗贼都不敢来偷他的这几根杉树。但是今天张钊决定要对它下手了。这之前,他就对这几个杉树垂延了许多年,也一直在寻找机会,这一次当他听说李波和他的老婆要回娘家,他这才觉得机会终于来了。
把杉树丈量完,他终于找到了最大的那一棵。他记得最大的那颗是在竹园正中的。找到了,他便拿来锯子开始锯杉树。那把锯子一直是他最忠实的老伙伴,好帮手,他已经弄不清这把锯子帮他偷过多少树木了。现在当这把锯子锯进这棵杉树的时候,它依旧非常卖力地扎进了木头中。但是张钊知道他不能用力过猛,不能弄出很大的声响,李波的母亲年纪并不是很大,今年65岁,耳不聋,眼不瞎,如果弄出响声让她听见,他今天就逃不脱了。所以张钊就这样既用力地锯着,又压着锯条防止弄出很大的声响,很快就累出了一身汗。但是当时间慢慢过去之后,那棵杉树就终于被他锯断了。他听见树的根部发出了一声轻微的脆响,似乎是压低嗓门的一声惊叫,紧接着一系列的响声就传来了。那是那棵杉树扑向竹林的时候发出的。不过还好,那些声音并不夸张,就在杉树刚刚接触到竹林的那一刹那发出了一声算为响亮的声音之后,那棵杉树就慢慢地靠到了那些茂密的竹林上,接下来的声音就算是轻言细语了。这个情况也是张钊在这之前就已经设计好的,他知道杉树倒下来并不会发出巨大声响,原因就在那些竹林是消声器,它们把它挡着,不会让倒下的杉树狂暴。当那些响声过后,张钊就像一棵长着的树,站在竹林里没有立刻进行下一步动作,而是打开所有的感官感知周围的一切。因为他要防止刚才发出的响声惊动睡在屋里的吴二婶。这样站了大约半个小时,没有听见异样的声音传来,他才放下心来把那棵杉树锯成了七段木料。因为这棵杉树实在太大了,即便是三五个张钊也不可能把一整棵杉树弄回家,所以他只得把它锯成一段一段。只是在锯的时候他留了一个心眼,就是这些杉树的长短不能搞坏了,那样就卖不出好价钱,他裁出的长短必须适合做棺木。
锯木料的时候,张钊显得非常平静,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里做着一件极为寻常的事情一样。这之前他也都是这样,并没有因为干着这种事情而感觉特别惊慌。当然这得益于他长时间做这种事情。他记得这种习惯是乡村里掀起打工潮之后养成的,那个时候张钊并没有像村里的其他人那样,携家带小出去打工,而是选择留在了家里,因为他的负担大,两个老人都老了,又有病,他无法走出去。但是当他看见那些打工的人赚回钱建起了漂亮的楼房之后,那些漂亮的楼房就深深地刺激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最开始做的时候,自然是惊慌失措。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老婆邓晶极力地反对他这样做。她警告他,说他这是犯法,如果他这样下去她就和他离婚。但后来张钊找到了一条很好的理由,说他这是做善事,救助更加不幸的人,邓晶便没再提离婚的事了。再加上张钊确实没有翻过船,家里的开销又大,偷盗的利益让邓晶尝到了占便宜的甜头,每一次她也只是抱怨一番就算是默认了,警告他下一次不要这样做。但后来送走了两个老人,儿子张龙又渐渐长大,张钊的这个习惯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也知道这是犯法,每一次做过之后心里总有一种巨大的犯罪感,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但每次做完之后也并不是最后一次。就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和纠结中,张钊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只是张钊告诫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必须要小心谨慎,不能翻船。第二、不能把事情做得太大,也不能做得太绝。因为他知道偷盗是不可能发家致富的,发家致富必须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所以他在当地,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勤劳善良、遵纪守法的人,并不知道夜晚的时候他就是鬼。
将木料锯成七段,张钊便就扛着其中一段朝家里走去。回到家,发现大门被从里面反锁上了,张钊用木料的一头撞击了一下大门,大门没有开,他内心的火气就上来了,便用那木料更用力地去撞门。他想大声吼叫,但是他知道在这个漆黑的深夜里,他是不能发出任何声响的,否则让别人听见不知道他们家里发生了什么,就会暴露。他就又更加用力地用木料的一端去撞大门,大门发出了轰响的声音。不一会儿,那个大门还是打开了,接着电灯也亮了。
打开大门,发现邓晶就站在灯光下,邓晶的脸色非常难看,张钊只望了她一眼就没再望了,扛着木料就大步朝后屋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你来给我帮忙。”说过就将那段木料扛进了后面的私檐屋里。
“要我帮什么忙?”邓晶在身后问。
“帮我想办法把木料搞到楼上去。”说过张钊就将木料的一端靠到墙上,将那段木料放了下来,也随手将手里的斧子扔到了地上,斧子显得非常愤怒,和地面碰撞时发出了砰的一声顿响,接着木柄又弹跳两下才安静下来。
张钊摸了一把汗,就对立在那里邓晶说:“帮我把它搞到楼上去。”
邓晶没有做声,但还是走到他身边给他帮忙。
这样两人就各自抬着木料的一端,张钊走在前,一步一步朝楼梯爬去,这样他们就吃力地将木料搞到了楼上,再打开楼上的灯,就将木料放倒楼上的一个旮旯里。那是一个堆杂物的地方,放了不少木料,有些木料也是他偷来的,因为舍不得卖就放在了这里。
从楼上下来,张钊又大步朝屋外走去,刚刚走出门的时候邓晶在身后问:“还有多少?”
“你把门不要关紧。”
“嗯。”
然后,张钊就一头栽进了漆黑的夜里,把剩下的六段木料一一地搬回来,又在邓晶的帮助下一一地抬上楼藏了起来。
当七段木料全部放好之后,邓晶的脸上也终于开出了喜悦之花。“你是搞的谁的?”
“李波的。”
“李波的?就是他竹园的那根杉树?”
“是。竹园里最大的那棵。”这样说的时候,张钊的脸上有一种自豪感在那里荡漾。
邓晶没再说话,便转身朝楼下走去。张钊也没有做声,跟着她朝楼下走,但此刻张钊内心里明白,他老婆心里的喜悦一定比这楼高多了。现在的杉树非常值钱,这七段杉树起码也可以卖到数千元,平白无故地搞到这么大一笔钱她内心里没有不高兴之理。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张钊像过去那样,所有的精神气一下子就不知从什么地方漏掉了,浑身变得软弱无力,心里充满了一种虚幻感和无力感。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当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快感,然而当这件事情做完,他却显得是那样的虚弱和无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如果说他想以这种方式表明他的巨大存在,然而这种方式却从来没有配合他,几乎每次都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他。
“赶紧洗个澡,浑身汗得水沱湿溜。”邓晶一边说着一边朝火垅屋里走去。
然而变得虚弱无力的张钊没有理她,直接就走进卧室躺下了。
第二天,派出所的警车就开进了石榴坪村。这个时候,张钊和邓晶已经在地里收拾乱草和庄稼的桔梗。听见警车呼啸的声音,张钊的心里就钉进了一枚钉子。
邓晶问:“不要紧吧?”
张钊没有看邓晶,但他知道邓晶的心里也钉进了一枚钉子。这是每次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所留下的后遗症,每次做完,他们总得提心吊胆一段日子,直到风平浪静了才处理脏物。“不要紧。”
两人没再说话,继续整理土地。季节已经把秋天请进了村子,收获的田野处在歇息之中,张钊和邓晶得赶紧收拾完那些乱草和庄稼的桔梗后准备播种小麦。
果然,警车在李波家的门前停了一天之后,于傍晚时分开走了。之后就风平浪静下来。再后来张钊从别人嘴里得知,说李波家的最大一棵杉树被盗了,派出所给出的答案是被外地人盗走了,加上事情又太小,就没有立案。听到这个消息,张钊心里的那枚钉子才被拔出。
2
“张钊、邓晶,你们来歇歇,喝口水。”
这天,张钊和邓晶两口子正在一块地里播种小麦,田头就走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大娘,她手里提着茶水,站在那里笑吟吟地叫着他们俩。这个老人就是石榴坪村的失独老人,她叫谢良敏。此时,石榴坪晴空万里,太阳忠实地照在石榴坪的山山岭岭上。谢良敏老人的脸上也挂着太阳般的笑容。
听见声音,张钊和邓晶抬起头来,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张钊抹了一把汗,将锄头放到地里就朝老人走去,邓晶则跟在他的身后一边走一边说:“大婶,你别忙,我们不渴。”
“怎么不渴?快来喝点水,歇歇再种。”
这个老人,就是张钊所找出的借口,说的那个善事。自从张钊送走了他的父母之后,他和邓晶就将失独老人谢良敏赡养起来,默默地帮她安排好一切。在整个石榴坪村,没有谁的命运比谢良敏老人更悲惨了,她四十多岁的时候男人就患绝症离开了她,后来她没有再嫁,一直一个人把儿子抚养长大。他们只有一个独子,独子也结婚成家,而且也有了孙子,可是有一年她的儿子、儿媳带着她的孙子在外面打工回家过年的时候,因为车祸,一家三口的性命就全被夺走了,最后只剩下谢良敏一个老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钊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谢良敏当成自己的母亲赡养。最初,谢良敏老人并不相信,说他有他的家庭,有他的负担,他的好心她心领了。但张钊说到做到,带着邓晶默默地帮谢良敏老人安排好一切。到了播种的季节他们就来帮谢良敏老人将庄稼种下地,到收割的季节他们就帮助老人把庄稼收回去。隔上几天,张钊总要来看看老人,帮她做做家务。邓晶也过来帮她收拾屋子,洗洗刷刷。每年还坚持给老人添置几套新衣服。就这样,不仅是感动了谢良敏老人,而且也感动了全村人。他的老婆邓晶也因为这件事情,被村里、镇里、县里、市里连年表彰为“三八红旗手”,多次到各级去领奖,受到领导的接待。他们的事迹也上了电视、报纸。然而只有张钊自己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做则带着一种赎罪的心理。他夜里去做鬼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作为了最大的借口。其实他知道,他的这个借口没有找到内心的平衡。至少他觉得他这样做对不起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张龙非常出息,现在在武汉读大学,已经快要大学毕业了。不过还好,儿子并没有染上这个坏习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盗过别人的东西。
张钊和邓晶来到谢良敏老人身旁,从她手里接过滚烫的热茶,就转身坐到一个峁头上,一边喝茶一边歇息。
张钊说:“我们最多大半天就可以将小麦种完了。”
“过去我就说要换一换田。”邓晶说,“这快地去年种的小麦今年又种小麦,是不是不太好?”
“不要紧。”谢良敏老人说,“小麦不需要换田,不会减产的。”
这样说的时候,老人的脸色仍旧挂着阳光般的笑容,因为这些安排都是谢良敏老人自己做的主。年过七十的她身体还非常硬朗,每年还喂一头猪,养两只羊,哪一块地里种什么都由她自己说了算,所以今天早晨来的时候,邓晶就对谢良敏老人说,要把这块地换掉,谢良敏老人则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种上了小麦。她一共有六亩多土地,她想拿出二亩地种小麦,剩下的四亩地种洋芋,张钊和邓晶就只好按照老人的安排执行了。
“大婶,你回去忙吧。”喝过茶,邓晶摸了一把汗说,“我们又继续干。”
谢良敏老人说:“还喝点水。”说过就又来给他们的杯子里续上了茶,然后就将开水瓶放到旁边的一个卯头上说,“你们渴了就自己在这里倒了喝。”
张钊说:“好的。”
“我现在就回去做饭,你们把这几行掩上了就回来吃饭,我就不来叫你们了。”
“好的。”
这样老人就笑着从地里走到那边的小路上,然后又扭过头来对他们夫妻说:“你们也别太累着。”
邓晶笑着说:“知道。”谢良敏老人这才离去。
其实他们每一次见面就像一家人一样,没有任何隔阂,只是他们没有改口叫她妈罢了,在内心深处他们早把谢良敏老人当成了自己的母亲。因为在这之前,谢良敏老人也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通过村干部立了一个遗嘱,说她离开人世以后,她所有的家产和山林土地全部由张钊继承。这个情况自然让石榴坪的老百姓嫉妒得眼睛充血,说张钊名义上是赡养谢良敏老人,实际上是想白得了人家的家产。这个消息后来传到张钊的耳朵里,张钊也从来不反驳和做任何解释。
张钊和邓晶喝了茶接着就继续种小麦。夫妻俩都是一把劳动的好手,他们种的地在当地被当做样板,年年都获得了丰收。尽管他的儿子张龙在大学里花费很大,但张钊并没有感觉吃力,地里的收入,喂猪的收入,再加上他偷盗所获得的收入,完全可以对付儿子上学。因此当别人都出去打工的时候,张钊则对他的老婆说,他不出去打工,就在屋里守着她,不然他这个家庭就散了。邓晶则狠狠地剐了他一眼,笑着说:“你就是怕吃苦。”
“屁,你嫁给我二十多年,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个能吃苦的人吗?”
这样一说,邓晶也就无话可说了,因为正如张钊所说,张钊确实是一个劳动模范,他每天从早上睁眼开始就不停地劳动,一直要等到天黑收工了才能歇下来,就像老黄牛一样。
将地里的小麦种了一大半,他们回家吃中饭,一进屋就发现老人弄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看了一眼,张钊说:“大婶,你弄这么多菜搞什么呢?”
“没有什么菜,都是一些平常的菜。”
这样说着,洗过手,就坐到桌前吃饭。三个人坐在一起也就像一家人一样,谢良敏老人问了张龙在学校里的学习情况,邓晶和张钊都一一地向她如实汇报了。张龙在学校里学习刻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问完了儿子的情况,又说了他们家里、地里和村里的一些事,一股看不见的暖流就涌遍了整个屋子。
吃过午饭,谢良敏老人也一起下地。三个人只用了大半天时间,当太阳将它那张红脸搁在西边山头的时候,两亩地的麦子就种完了。回到家,张钊就帮助老人锯柴、劈柴、打扫房间。邓晶则忙着给老人洗衣服、理头发、洗被窝。老人也是里里外外地忙碌。这样将整个屋子和老人都打整得清清爽爽了,又吃过了晚饭,张钊和邓晶才放心地离去。
走的时候,张钊说:“剩下的那几亩地就窖洋芋,最多两天都可以窖完。”
谢良敏老人说:“还是和历年一样,去高荒里搞点洋芋种来。”
“好。过几天我就去荒上买洋芋种。”
说过,便告别老人朝自己家里走去。
此时此刻,黄昏已经在村庄里徘徊,乡村也在快要关上黑暗大门之前显得非常热闹,各种呼喊的声音、牲畜的叫声充斥在整个村庄,张钊抬起头朝前方望去,一股巨大的激情就在他心里迸发出来,他便自觉不自觉地哼起了山歌:
郎在高山薅高梁,
姐在河下洗衣裳。
跟在他身后的邓晶则应和起来:
薅下高梁望下姐,
洗下衣裳望下郎。
两人接着合上最后一句:
下下捶在岩板上。
因为只有这个时刻,张钊才觉得他找到了自己,他还活着,活得非常踏实。
3
吃过早饭,张钊背着洋芋种朝地里走去,邓晶扛着锄头跟在他的身后。一边走张钊就一边问:“你说我们大约要几天才能把洋芋窖完?”
“最多一天多一点吧。”邓晶说。因为他们决定只种二亩洋芋,他们的责任田也并不多,只有六亩地,所以他们决定拿二亩出来窖洋芋。
“我希望今天一天把它窖完。”
“把它窖完了干什么?又没有其他紧要的事情。”
“还要给谢大婶窖哩。”
“她的洋芋最多二三天也就窖完了,窖完洋芋就到了农闲季节,再又没有别的事做,慌什么呢?”
夫妻俩就这样有一句话没一句话的说着朝地里走去,其实在生活中,他们就是靠着这些废话维持他们最基本的夫妻感情的,感情的光束只集中在眼前的事情上。这样说着来到地里,刚刚将洋芋种在一个砍边放下,就突然听见上面传来了话,“我来帮你们种。”
抬起头一看,发现说这话的是冯柏林,他扛着一个挖锄就站在上面的小路上,这样说的时候他脸上也挂着微笑。一看见冯柏林,张钊的心里就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因为他非常讨厌这个家伙,而且他一直也对他和他老婆之间那种说不清的关系怀恨在心,只是那种怀疑没有抓到证据而已。倒是这个时候邓晶热情地说:“那好,你今天帮我们种了,我们再去给你还工。”
冯柏林就啪叽啪叽地从上面的路口来到了地里。张钊就只好和他打招呼:“你的事情搞消缓了?”
“消缓说不上,反正今天有时间,可以帮你种一天。”
“那好吧。”
说着,张钊就从背篓上将洋芋种提下来放到了田的正中央,邓晶和冯柏林则走到田边开始掏洋芋行子。站在田中央,张钊望了一眼冯柏林和邓晶,发现他们离得非常近,而且他们脸上也都一律挂着开心的笑容,正在说着什么话,但是那些话张钊并没有听进心里去,因为这个时候他意识的深处被愤怒的情绪撕开了。冯柏林是石榴坪村一个最贫困的户,他的年龄和张钊差不多,今年也是42岁,只是冯柏林的家里常年打滥仗,他们的儿子也是在外面读大学,而且学习成绩比张钊的儿子张龙还要好,他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而张钊的儿子只考到了武汉。冯柏林家里的滥仗主要是他的老婆常年生病,已经不能下地了。他的老婆有多种疾病,心血管、胃、肺、肝都有问题,血脂、血压都不正常,所以她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过她在家里能够帮助做一些轻松的家务劳动,还能够做饭,因此冯柏林在石榴坪是一个每年吃低保的贫困户。他的学生上学也是靠的国家贷款和别人的资助,不过常常让张钊感觉眼红的则是冯柏林的儿子非常出息,他在外面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几乎不要冯柏林给他寄生活费,所以别人家都羡慕冯柏林有一个出息的儿子,今后的前途不可限量。也正是因为家庭的滥仗,冯柏林在石榴坪村并不受人尊敬,至少在张钊的眼里他觉得他们不是处在一个层面上的人。尽管张钊自己知道他白天是人晚上是鬼,心里被犯罪感、虚幻感、无力感、空落感等众多的情绪填充,但他至少获得了人们的尊重。然而冯柏林却恰恰相反,因为人穷志短,他常常到别人家去吃闲饭,也就是当别人在地里劳动的时候他就主动扛着锄头去给别人家干活,吃上几顿别人做的现成饭。但是冯柏林的这种热情也不好拒绝,所以他每一次扛着锄头走到别人田头的时候,那些人家也只好答应。过去张钊家每到农忙时节,冯柏林的身影也总是适时出现,就好像他长着一双眼睛随盯着他家一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张钊觉得他和他的老婆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关系。而当冯柏林和邓晶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显得非常亲热,那种亲热深深地刺激了他,他也多次在邓晶的面前酸溜溜地说:“我发现你对冯柏林比对我要好。”但是每一次邓晶却遮遮掩掩的。“你说的什么话?人家是来给我们帮忙,我能对人家不热情吗?”这样张钊也就无话可说了。
看见他们在那里热情地说话,张钊也只好拿着锄头去挨着他们掏洋芋行子。三个人一起劳动,很快就将行子掏出了三分之一。为了把冯柏林支开,张钊对冯柏林说:“柏林,你帮忙放洋芋种吧。”
“要得。”冯柏林说过,就去田中间提起洋芋种开始往行子里放种。张钊和邓晶则继续掏行子。但是当冯柏林离开他们之后,张钊和邓晶却没有话说了,沉默横亘在他们之间,就好像它们是两个陌生人一样。掏了一会,张钊才首先打破沉默:“这个冯柏林好像总是知道我们家里该做什么。”
“哦,昨天我看见了他,他问起我,我说过我们今天窖洋芋。”
“我们家的事无论大小你总是都告诉冯柏林。”
“你怎么这样说话?”
“我怎么说话了?”
眼看要吵起来,邓晶就没再说话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离冯柏林很近,一旦提高声音,冯柏林应该是可以听见的。邓晶一闭口,张钊也就没再说话了,但是张钊心里的怒火正在轰轰燃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们等着,什么时候我一定会把你们抓住的。”
这样想过之后,张钊就极力压着心中的怒火,故意对冯柏林很热情,问他家里的情况,老婆治疗的情况,儿子在大学里读书的情况。冯柏林也一一回答了他。见张钊已经放掉了怒火,邓晶也常常插上一两句话。
这样,因为有冯柏林的帮助,二亩多地的洋芋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就窖得差不多了,抬头看了一眼偏西的太阳,一个新的主意立刻在张钊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他便对邓晶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昨天我给儿子打电话,他说他想要点钱,我去镇上给他汇点钱吧。”
邓晶抬起头来问:“你怎么这个时候想起来给他汇钱?”
“事情一忙,我忘记了,现在突然想起来了。”
“给他汇多少钱呢?”
“汇500元钱吧。”
“要汇你也等到我们把最后的刹尾搞完了再去吧。”
“那不行,等把这里搞完再赶到镇上,镇上也就下班了。”
听了这话,邓晶找不出理由拒绝:“那你去吧。钱在床头的柜子里,你自己去拿。”
“好的。”张钊说完就转身朝家里走去,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们等着。
这样想着回到家,在邓晶说的床头柜里拿出500元钱,然后就骑着摩托朝镇上赶去。其实他现在想的就是把这个单独的时间留给他们,然后再搞个突然袭击,等他再返回来的时候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来到镇上,在邮局里给儿子汇了1500元,除了刚才在柜子里拿的500元之外,他又从身上掏出1000元一起汇给了儿子。汇完款出来,他就拨通了张龙的电话:“儿子。”
“爸。”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下课了。”
“我给你汇了1500块钱。”
“爸,我不差钱。”
“不,你在外面读书,钱要多一点,你别给我节约了,当花的要花,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了。”
“我知道,谢谢爸。”
“谈了女朋友没有?”
“没有。”
“我给你说了多少次?在学校里读书,一定要往这方面想。”
“爸,机会合适的时候我会自己安排好的。”
“不,爸给你说过,早点恋爱对你也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让你懂事早一些。”
“我知道了。”
“我给你多汇的这些钱不是让你随便乱花的,是给你预支谈女朋友的,所以我现在命令你,必须给我处一个女朋友。”
那边的张龙没有说话。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挂了电话,张钊抬头朝街上望去,街上自然还是车水马龙的样子,这个时候一丝甜蜜的感觉就从他心里生长了出来,因为他对儿子的爱是最无私的,他常常瞒着他的老婆给张龙多汇钱。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张龙不要走他的老路,他因为家庭贫穷没有读过大学,高中没毕业就回了家,偷盗的恶习又总是改不了,所以他就期待他的下一代能够真正翻身,不像他那样过浑浑噩噩的日子。之所以催他尽快处女朋友,他真实的想法是希望张龙能够尽早地尝到女人的滋味。因为在他的意识深处,他认为能尽早地尝到女人味,一个男人才充满激情和活力,才不枉活一世。
骑上摩托朝家里赶的时候,张钊将速度调到了最高档。按照时间来算,留在家里的冯柏林和邓晶应该将剩下的洋芋窖完了,而且现在他们应该回了家,正是他来一个突然袭击的最佳时间。然而等张钊回到家的时候,却发现家里只有邓晶。张钊劈头就问:“冯柏林呢?”
“回去了。”
“回去了?他不吃晚饭吗?”
“他说他不吃了。你走了之后我们很快就将剩下的洋芋窖完了,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他说他要回去做他自己的事情,就走了。”
听了这话,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又再次在他心里升起。
4
给谢良敏老人窖完洋芋,又给冯柏林还了工,农闲的季节就终于迈着蹒跚的脚步来到了石榴坪。而在这段时间里,张钊也有很长时间没到郭英那里去了,原因不是他不想去,而是他口袋里剩下的钱不多了,所以这天早晨起来,他抬头望了一眼对面的山峰,心里的渴望又再次爬出来:那就还做一次吧。因为这一刻他想到了高山到了敞放牛羊的季节,他想趁现在这个时间去一个叫长阴坡的地方去偷一次牛。这样吃过早饭,他就对邓晶说:“我有事出去了。”
“到哪里去?”
“荒里。”
“荒里?”
“你不要多问了,反正我有事。”
“你能不能不做了?”
“还做最后一次。”
“每次你都是这样说,你说你什么时候停过手?”
张钊便望着邓晶说:“我给你说过了,我这是在做善事,我搞的那些钱最终都到谢二婶那里去了,所以我心里也搞得坦然。”
“你什么时候一定会翻船的。”
“翻就翻吧,我认了。”说完他就骑着摩托走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张钊就想过,至少眼前他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收手,收手的时间得看儿子张龙什么时候大学毕业,什么时候能够搞到一碗饭吃。只要张龙有一碗饭吃,他的脚步就一定会停下,所以当摩托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他望着远处的山峰对自己说:我发誓,只要张龙有饭吃,我就坚决洗手不干了。
长阴坡离他家很远,有三、四十里多地,属于海拔一千五百多米的高山,过去他也曾经在那个地方数次得手。因为那个高山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场,当地农民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到了九月重阳一定会敞放牛羊。因为到了这个时期,地里的庄稼都收割了,农民们就把过去绳养的牛羊解掉绳索,把它们赶上山,让它们自己去寻草吃,晚上那些牲畜也就自觉地回到家里来。也正是这种传统给了张钊一个可乘之机。
经过半天的颠簸他终于来到了长阴坡高高的山上,摩托车拐下乡村公路就驶上了森林的防火道。长阴坡是个巨大的山坡,无数的山峰连成一片,在山顶和下面的农户之间就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场,森林和草场中间有一条长长的防火带,那条防火带改成了公路,所以现在他只需要在那条公路上行驶就可以了。一驶上防火带,他就放慢了速度,因为这条防火带平常车辆很少,只是到了蔬菜的收获季节外面的车辆才会进山,才有车辆在那里奔跑,因此这条路的路况很差。张钊一边小心翼翼地骑着,一边四处观察,看哪里有耕牛出现。这样当他往前骑了一段,果然就有牛铃的声音传了过来。牛铃的声音非常清脆,从声音上判断,他知道这里应该不只一头牛,而是有一群牛。听见这个声音就好像是听见了号角,他把摩托车停在一个山弯里,然后又走过几个回头线站到一个山包前,借着几颗巨大杂树的掩护朝那些草场中望去。眼前的草场是由各种杂树和野草共同铺成的,牛羊钻在里面很难被发现,只能通过声音来辨别。站在那里观察了一下,他很快就发现在距他不远的一个树丛中有三头牛。那三头牛在吃草,尾巴正在不停地甩动,轰赶蚊子,而他发现其中有一头牛的角上缠着绳索,很显然那是农户不想把牛绳解开而缠在它的角上的,那样便于要使用绳索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解开使用。看到那条绳索,张钊就自然看到了希望,因为牛的鼻子上没有绳索他就无法把牛偷走,那就把目标就对准那头牛吧。但是仔细观察之后,他发现这头牛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牛铃,这就要命了,不将这个牛铃解下来他也无法盗走。想了想,张钊便就从他隐藏的树丛后面出来,朝那三头牛走近。然而那三头牛非常怕生,当他的身影刚刚在牛前出现的时候,那三头牛突然停止了吃草,都不解地望着他。张钊与牲口打交道惯了,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不能擅自行动,就在那些牛的面前站了下来。那些牛和他对视了一会,见张钊并没有向它们走来,就又低下头继续吃草。
见牛放松了警惕,张钊又慢慢地向牛靠近,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经验。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莽壮,必须是让牛保持一种放松的状态,所以他走到离牛还剩下一段距离的时候,就停下来解开裤子,掏出他的弟弟在那些草上撒了一泡尿。这一下果真应验了,其中那头角上绑着绳索的牛向他这边靠了过来。当牛来到他的身边,望了他一眼,发现张钊并没有敌意,牛便继续靠近。只是在走到离他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它停下来望着他,不再往前走了。张钊知道它是在试探,所以他就又向后退了几步,那头牛终于放松警惕,来到他刚刚撒尿的那块草地吃草。当牛低下头吃草的时候,张钊慢慢地靠上去,一下子就抓住了牛的缰绳。牛遭到突然袭击,头向上一扬,还好,他已经抓住了它的牛鼻圈,张钊喝问一声:“哇。”那头牛就乖乖地停下了。
将牛逮在手里,他没有半点犹豫,赶紧散掉牛角上的绳索,那头牛就再也没有反抗了。因为牛长期和人打交道,即便是陌生的人,只要将牛绳抓在手里,那头牛就只有乖乖听话。牵住牛绳,又顺手捏了一把草塞进牛铃之中,那个牛铃就终于哑巴了。当这一切弄好,张钊便就拉着牛朝停放摩托车的那边走去。
“站住。”可是刚刚走出几十米远,他的身后突然爆发出来一声断喝。
听见这个声音,张钊吓了一跳,一转过身就发现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站住。”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又大声喝斥。
但是此刻的张钊却并没有惊慌,他正在观察那个青年人和他周围的情况。
“抓强盗,抓强盗,有人偷牛,有人偷牛。”青年人扯开嗓子大声呼喊起来。
喊声一出来,接着那边山头上也突然跑出了几个人大声问:“在哪里?在哪里?”
“在这里,在这里。”
那些人就疯狂地朝这边奔跑了过来。刚才的那个青年人也开始朝这里奔跑。张钊一见,只好扔掉牛绳不要命地朝前奔去。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边跑一边叫着一些人的名字:“你们在上面的防火道上拦住他。”
一听这话,张钊吓出了一身冷汗,知道这次可能真要翻船了。这种情况他过去从来都没遇见过。其实在这之前,长阴坡的老百姓就已经形成了联盟,因为高山每到这个季节总是丢牛,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到敞放牛羊的季节,各家各户商量之后决定各户派出一个人,采取轮流的办法在山上放哨,监视那些牛羊。今天正好轮到那个青年名下,他之所以发现张钊偷牛,就是刚才张钊喝住牛时所发出的那声声响。当时他正在那里割草,他便循着声音走过来就发现了张钊。
张钊快速地扫了一眼,发现至少有五六个人已经朝他奔跑过来了,而且那些人一边奔跑还在一边不停地呼喊。可以想象,全村的老百姓很快都会涌到这里来,那样他就死定了,即便不被打死,也会送进牢房。所以他便不要命地奔跑起来。好在张钊年轻,奔跑的速度并不比那些人慢,再加上那些人离他隔了很远的距离,这样当他用尽全力奔跑到那个山弯里,发现他的摩托并没有被人发现,便飞快地跨上摩托疯狂地朝前奔去。
当他转过一个山弯再回过头来时,就发现那些人已被他远远地甩掉了。
摩托车仍在疯狂地跑着。直到奔过了无数山头,确定那些人不会再追上来了,惊魂未定的张钊这才慢慢地踏实下来:“他妈的。”他望着远处的山峦骂了一句,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收手吧,该收手了。
5
傍晚时分,张钊在距离郭英家还剩下一段路程的时候,就将摩托车熄火推着走。来到郭英的门前,他抬头望了一下房门,发现那里的大门洞开着,似乎正在向他发出邀请。他便推着摩托朝公路下走去。当他费力地把摩托车推到郭英稻场里时,郭英听见声音也从屋里出来了。但因为她瘫痪的婆婆在家里,郭英和张钊也只是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此时郭英的眼里露出了既诧异又期待的眼神。而刚刚经历了一场惊险的张钊,非常期待郭英的安慰,所以见到郭英,一种安全感也在他心里塞满了,他冲着郭英笑了一下,将摩托锁好,走到郭英面前伏在她的耳边说:“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里了。”
郭英也没有说话,则笑着推了他一把。
张钊笑了一下,心里的期待和一种幸福感就充盈在他的心间。因为郭英的这个动作恰好是告诉他,她答应了,看得出这也是郭英所期待的。接着郭英就转身朝屋里走,张钊就紧紧地跟了上去。
“郭英。”刚一进门,屋里就传来了她婆婆的声音,“刚才好像外面有什么响动?”
“什么响动?是我在抱柴火。”
屋里的婆婆就没有再做声了。郭英则转过身冲着张钊笑了一下。看着她那张漂亮而又生动的脸,张钊的心里更加享受,这样他就随她走进了那边的灶屋。
张钊说:“我还没有吃晚饭。”
郭英小声对他说:“你帮我架火。”
张钊点点头,就坐在灶门口帮她架火。郭英则转身走到那边火垅屋,给他端来了一杯茶。接茶的时候,他一把抓住了郭英的手。郭英停顿了一下,还是轻轻地从他手里将手抽了出来。而这个时候,张钊内心深处有非常想和她说话的渴望,刚才经历了那惊险的一幕,让他觉得这个世界更是不稳定了,到处都在摇摆。此时此刻,他非常渴望他孤独的心灵能够得到安慰。尽管他知道,她的安慰什么用处都没有,或许会给他增加更多的虚幻感、无力感和失落感,但他还是渴望这样的安慰。然而他知道,这样的安慰是没有的,他们不能大声说话。因此他喝了一口茶便就接着继续架火。郭英也就开始在灶台上忙碌。做好了饭,郭英将饭端进她婆婆的房间,服侍她的婆婆吃过了才过来和张钊一起吃晚饭。吃饭的时候她小声问:“怎么今天舍得来住上一晚?”
“我一直都想来,就是找不到机会。”
“今天怎么找到了?”
“我对邓晶撒了谎,说要出趟门,这样就找到机会了。”
“你骗我。”
“没有。”
郭英便没再说话,两人默默地吃完饭,又迫不及待地洗过澡,就进了郭英的卧室。两人又像先前那样,一番雷电交加之后才睡在被窝里小声地说话。这一次他们说了许许多多,各自的家庭、内心的孤独、难处、渴望、期待等等。也就在这样的交流中,两颗心挨得更紧。因为这一刻,他们都知道两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不过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孤儿,渴望交流,渴望心灵得到安抚。接着,他们又来了一次。这一次他们和风细雨,非常缠绵。完事后,待两人把气息喘均匀了,郭英突然说:“高桥铁路快要动工了。”
“高桥铁路快要动工了?你听谁说的?”一听这话,张钊心里就被激活了。因为张钊一直期待着高桥铁路的开工,去年测量专班就在石榴坪一带进行了长时间的测量,按照当时测量的线路,正好张钊、郭英、冯柏林、李波等人都在征收的范围之内。高桥铁路是打通西部的大动脉,这是国家的重点项目,所以这些要被征收的人家得到这样的消息之后都非常期待,希望征收的时候能向国家要上一大笔搬迁费,从此咸鱼翻身,彻底告别过去的贫困时代,过上衣食丰足的生活。
郭英说:“我听村长说的。”
“村长说的?”张钊说,“为什么每一次这些重大的消息村长都告诉你?”
“那你就别管了。”
“你是不是和村长也搞到了一起?”
这话一说,郭英火了:“你管得着吗?”
郭英这话就像从天而降的一盆冷水,一下子把张钊浇清醒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对呀,郭英并不是我私人的,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确实管不着她。所以张钊没再说话,心里则翻起了无边的厌恶,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是那样的肮脏。郭英也没再说话。沉默和寂静塞满了天地之间。直到过了很大一会,郭英才碰了碰张钊:“你睡着了吗?”
“没有。”
“是不是生气了?”
“我哪敢呀。”说过,张钊就从床上坐起来,打开电灯说,“我现在想起一件事,得马上赶回去。”
“什么事?”
“那你就别管了。”
这话一说,也把郭英冷在了那里。张钊便速度穿好衣服,就打开门朝外走。这个时候,郭英一把拉住了他:“你什么时候再来?”
“我也不知道。”说过就开门出去了。然后,又将摩托推到了下面的公路上,便启动摩托朝家里奔去。
当摩托车在公路上奔驰的时候,张钊望着前面的公路,脑子里被一系列的念头塞得满满的,那里有恶心、后悔、懊恼、愤怒等等负面的情绪。他既觉得郭英是那样的恶心,他自己也是那样恶心。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和郭英这样的女人搞到了一起。既然她能够和他这样的人搞到一起,那么她身边肯定远不止他和村长这两个男人,或许有其他更多的男人。
他也想到了报复村长。村长叫谭力铁,年龄和他差不多。这个家伙在村里耀武扬威,那些人家的男人出去打工之后,他究竟和多少女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谁也说不清楚。人们谈起他都是咬牙切齿的,背后都咒他要遭雷劈的。但张钊没想到自己倾心的女人竟然和村长也有一腿。不过张钊很快就放弃了报复村长的想法,因为他知道他和村长不在一个等次上,他斗不过村长。而让他更加明白的是,郭英并不是他原来想像的郭英,所以他望着前方的道路对自己说:放手吧,我们的事情也就到此终止了。
当这个声音在心里响起的时候,他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加快了摩托的速度。可是当他刚快要接近自己家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车灯前闪过了一个人影。那个人影只是轻轻地一闪就突然钻进了一片树林之中。
“谁?”张钊大喊一声。
但那里并没有传出回音,只有树林被触动时发出的响声。张钊没有半点犹豫,停了摩托跳下来,借着摩托车的前灯在那个林间搜索。“谁?”
但是那里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影,也没有传出任何响声,就好像刚才那个身影是个鬼魂似的,突然间消失了。张钊便将摩托熄掉火,站在那里继续听着。但是听下来,天地间一片宁静,听不见任何声音。现在的夜已经很深了,所有的生灵都已经休息。随即,一股无名的怒火立刻就充盈在心间,因为他想到了冯柏林。而且这块树林离他的家很近,这片区域只有他一户人家,再也没有第二户,所以他可以肯定,刚才那个人就是从他家里出来的。而能够频繁出入他家的没有别人,只有冯柏林。想了想,张钊只好启动摩托,继续将摩托开到了家门口。在门口熄掉火,再朝自己的家望了一眼,发现自己的家也停泊在沉默之中,大门紧闭,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将摩托推到大门口,然后就用力地擂门,大声喊:“邓晶、邓晶。”
喊了好几声,邓晶的声音才从屋里传出来:“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听见这个声音,张钊的火气更大:“你快点把门打开。”
不一会,邓晶就披着衣服出来打开了门,灯光也打开了。张钊用不解的眼神望着灯光下的邓晶,想从她的脸上找出一些蜘蛛马迹。但是现在的邓晶看上去却是那样的坦然。她接着问:“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你帮我把摩托推进屋来。”
邓晶没再说话,出屋和张钊一起把摩托推进了堂屋,然后关上大门。张钊问:“邓晶,你和我说实话,刚才冯柏林是不是来过这里?”
“放你妈的屁。”
“我刚才就看见冯柏林了,他钻进了一片树林之中。”
“张钊,你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就随你去说吧。”说过,邓晶屁股一甩就进了里面的屋子。
看着她消失的背影,张钊也不好继续发火,因为他没有抓到任何真凭实据,所以只好强压住自己的怒火进火垅屋,咕噜咕噜猛灌了一通冷茶,让心里的火气渐渐地回落了,才转身朝卧室里走去。卧室里的灯光开着,邓晶也睡了,但是她的背朝着这一边,张钊看了她一眼,也就无声地在她的旁边睡下了。
6
醒来的时候,张钊发现他是被他老婆弄醒的。邓晶正坐在床头穿鞋子,背对着他。张钊望了她一眼,也就从床上爬了起来。邓晶穿好衣服,也没有和他说话,就大步走出了屋子。张钊一边穿衣服一边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的火气又大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冯柏林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你难堪的。因为昨天晚上在邓晶的身旁躺下之后,他拿定了报复冯柏林的主意,而报复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的那一坡杉树全部搞掉。冯柏林屋后有很大一块杉树,那是他们家的一笔巨大财富,尽管那些杉树没有李波竹园里的杉树大,但是他的那坡杉树却是成片的,现在成熟的杉树大约有三十多棵。张钊在心里对自己说,冯柏林呀冯柏林,你敢动我的女人,那我就动你的杉树。尽管我已经决定金盆洗手不干了,但我还必须做最后一次。
起床洗过脸,再走到堂屋里就听见邓晶已经在那边灶屋里做饭了。那里传出了碗筷碰撞时发出的声响,但张钊不准备在家里吃早饭了,就从堂屋里推出摩托,直接朝镇上奔去。来到镇上,他先在一个早餐点前停好摩托,然后找老板娘买了四个包子,一碗稀饭,吃完,付过钱,再出来就直接朝棺材铺奔去。当摩托车在棺材铺门前停下的时候,就听见屋里传出了锯子、刨子的声响,很显然,木匠石秋林已经在干活了,锁好摩托再走进屋,他就大声叫着:“石师傅、石师傅。”
“唉。”那边传过来了石秋林的声音。
一走进去,果真见石秋林带着他的徒弟正在屋子里干活,整个屋子里被刨花散发出来的木香塞得满满的,石秋林答应一声之后也大步朝他走了过来,脸上也挂着微笑:“今天又有生意了?”
“有大生意。”张钊一边说着一边朝石秋林走去。“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说。”
石秋林指了一下旁边的一个房间,两人就走进去坐了下来。这个房间是石秋林师徒们在这里休息吃饭的地方。屋子里放着一个煤炭炉。坐下后石秋林先给他泡了茶,然后在他对面坐下,问什么大生意?
“这一次的生意够你忙活一年了。”
“够忙活一年?”听了这话,石秋林的脸上也充满期待,“这么大的生意?”
“石师傅,我们打交道也是这么多年了,你信任我,我也信任你,这一次我之所以专程来找你,就是想和你合作。”
“和我合作?”
“是这样,我们那里有户人家山上有三十多棵杉树,凭我一个人无法搞走,再说我离得近,也容易被察觉,我的想法是我们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你开着车,一下子去把那三十多棵杉树搞走。”
“这是一件大事。”
“当然是一件大事。而且你请一辆车还不够,至少要请两辆车才行。人手也要多,至少得请七八个小伙子才做得了。”
“我得想想。”
“还要想什么呢?这么好的生意你不做,机会过了你再想做就没有机会了。你说你在这里开个棺材铺,所用的木料哪一棵是从林业部门批来的?不都是山上的农民乱砍滥伐或者是偷来的吗。”
“这个我自然知道。”
“所以你就不要犹豫了。”
“那这样,为了稳妥起见,我还得跟你去看一看,我觉得可以做我们就做。”
“说看就去看。”
“现在?”
“当然现在。”
“好吧,那走吧。”
两人从屋里出来,坐上张钊的摩托车就回到了石榴坪。当他们在张钊门前停下车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房门已经上了锁。张钊掏出钥匙打开门,对石秋林说:“到屋里坐。”
“那就不坐了吧。我们还是先去看看。”
张钊便就站在稻场里,指着那边的一片树林说:“你看见没有?就是那里。”
石秋林抬头望去,发现那边的山坡上果真有一片杉树,冯柏林的房屋就在杉树旁边靠下一点的位置。那些杉树之所以还牢牢地长在那里,就是因为离他家近。看了一眼,石秋林说:“不靠近看不清楚。”
“行,我带你去。”说过,张钊就关上门带着石秋林朝冯柏林家里走去。
来到冯柏林屋房的时候,张钊一眼就看见邓晶和冯柏林正在前面的地里窖洋芋,他们两人就好像是两口子似的,冯柏林正弓着背挥动锄头挖洋芋行子,邓晶则在放洋芋种。冯柏林的大门开着。很显然他的老婆现在在家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张钊心里更是怒火熊熊,他在心里再次对自己说,必须把它做掉。
“你跟我来。”张钊说过,就避开他们的视线选择另一条小路接近了那坡杉树。
当他们站在那坡杉树跟前时,石秋林的心里一下子就热了,这坡杉树大约有数百棵,其中大些的大约是三十多棵,而那些小的杉树其实也是可以用的,至少现在已经成材的大约是一百多棵,这确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看了看,石秋林又转过身朝那边的公路望了一眼,发现冯柏林的这片杉树离那边的公路大约不到一里地的路程,所以杉树砍下来也很容易搞上公路。
“我没骗你吧。”张钊小声对石秋林说。
“这个风险也太大了。”石秋林说,“离他的家太近了,动斧子锯子绝对不行。”
“那是当然,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走吧,我们不能卯站在这里,不然被别人怀疑了。”说过,张钊便就带着石秋林朝自己家里走去。
回到家打开门再次在家里坐下来,两人心里也就坦荡了,石秋林说:“那就做。你觉得什么时候最合适?”
“最合适的时间是下了一场大雪之后,所以我们还要等。当一场大雪下下来,他们在家里睡死了,我们再动手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正月里冯柏林带着他的老婆回娘家的话,那就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所以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观察冯柏林,你在那里随时做好准备,一旦得到我的电话,你就必须迅速来。”
“好的,就这么说定了。”
“就这么说定了。”说过,张钊就把石秋林又送回到了镇上。
当石秋林再次从摩托上下来,张钊说:“石师傅,你可千万不能再变卦,我这次是出于帮你,才给你出的这个点子。”
“知道,谢谢你。”
“到时候我们两个平半分。”
“行。”
“走了。”
“慢点。”
“嗯。”
张钊便骑着摩托到镇子的中心,然后将摩托锁在商场前的一个棚子下,就走进了商场。他在商场的货物前不停地转着,脑子里也在思考着给谢良敏老人买点什么。当电热毯闯进他的眼帘,他的心里突然亮了。因为马上要进入冬天,他得让谢良敏老人热热乎乎地过一个冬天,所以他就买了电热毯、护手炉、暖脚宝、一双棉鞋、一件羽绒服、一条棉裤,整整花去了1200多元,然后将这些东西包好出来,就直接骑摩托送给了谢良敏老人。
当摩托在谢良敏老人门口停下的时候,谢良敏老人正好从地里回来。“谢大婶,今天在忙什么呢?”
“也没忙什么,我把羊子拉到地里放一下。你来啦,快到屋里坐。”
张钊便提着那些东西随谢良敏老人走进屋,然后将那些东西打开说:“谢大婶,我给你买了一些过冬天的东西。”
谢良敏老人说:“给我买什么东西啊?花那么多钱没必要。”
“大婶你就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你先来试一试,看这件羽绒服、还有棉裤、棉鞋合不合身?如果不合身的话,我得赶紧去换。”
听到这话,谢良敏老人高兴得似乎要跌倒了,大步走过来,惊喜万分地从张钊手里接过羽绒服、棉裤和棉鞋试过,都非常合身。
“太合身了。”谢良敏老人说,“就好像你知道我的大小似的。你说我这个人,怎么老了还能享这样的福?这是老天爷对我的关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