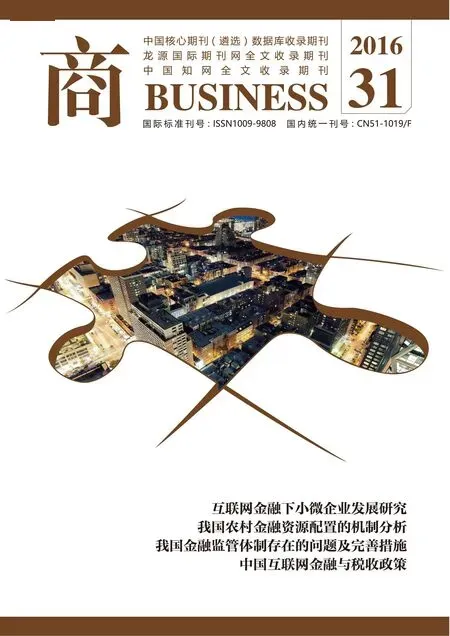论盗窃罪中的秘密性
王苗苗
论盗窃罪中的秘密性
王苗苗
盗窃罪是我国最为古老且犯罪率最高的侵犯财产类犯罪之一,从财产有了你我的区别时开始,盗窃罪便有了其形成的前提条件。而对于盗窃罪的认定是惩罚犯罪人的基础,通说观点认为盗窃罪的秘密性是区分盗窃罪与其他财产类犯罪的重要要件,本文简述秘密性如何一步步演化成通说观点。
秘密性;秘密窃取;公开盗窃
一、我国盗窃罪中秘密性的发展
(一)我国古代盗窃罪中的秘密性规定
“盗窃”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常见,是秦汉以往侵犯财产罪的概称。”①先秦文献中“盗”、“窃”一般单独使用。“盗”的概念,首次在《晋律注》中得到明确区分。《注律表》曰:“取非其物谓之盗。”指盗窃所侵犯的客体为非己之所有的他人的物,但并没有规定以什么样的方式取之。
对于“窃”,《说文解字》曰:“竊,盗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由此可见,“窃”为“盗”的一种特殊形式,包含在“盗”的含义之中。据《说文通训定声》表示虫私食米,虫私食米不易为人所察觉,引申为乘人不知而取得非份食物。从字义上看,盗,着重于因“贪而取”;窃,则强调‘乘人不知’。盗窃连成一词,便有“贪利”、“乘人不知”、“取食”三层意思。可见,“窃”从一开始就有不让人发觉的意思。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关于“盗”和“窃”的说明包括强盗和窃盗两种形式,相当于今日的抢夺、抢劫和盗窃的综合。然而,《唐律疏议》对“盗”的各种形态有严格区分,并奠定了“秘密窃取”意义上的“盗窃”的概念。
(二)我国旧刑法关于秘密性的规定
在我国立法过程之中,对盗窃罪的称谓也在不断地变化:1、窃盗,如1950年7月2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其中称“抢劫”为“强盗”。2、偷窃,如1954年9月30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和刑法草案22稿、33稿;3、盗窃。如1952年4月21日《惩治贪污条例》。1979年的第一部刑法典称“盗窃”,1997年的修订刑法继续使用“盗窃”一词。从名称可见对盗窃的认定有强烈的秘密性要求。
(三)我国现行刑法对秘密性的规定
1997年我国对刑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一直沿用至今。其中一改79刑法将盗窃、抢夺和抢劫规定在同一条文中的做法,将三者清楚地划分开来。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其中也未对客观行为进行秘密性的限定。
二、盗窃罪中秘密性的理论分歧
(一)通说的观点
前文已经说明了通说观点的演变过程,概括而言“盗窃罪的行为只能表现为秘密窃取(不包括公然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取财的‘秘密性’是盗窃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犯罪的本质特征之一。”,何为“秘密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特征:
1、“秘密”的主观性:简单说就是秘密性的成立与否关键在于行为人自己主观上的判断,即行为人自认为财产的控制人不知道或者没有发现其窃取财物的行为,至于客观上财产的控制人是否发现,与成立盗窃罪没有关系。按照通说的这一观点,以下四种实践就会出现下列情况行为人取走财物时自认为被害人没有发现,事实上被害人确实没有发现,此类完全符合秘密性,因此是绝对的秘密窃取,成立盗窃罪毫无异议。
2、“秘密”的相对性:仅仅是针对财产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来说的,行为人在盗窃财物的行为过程中如果被财产所有人、占有人以外的第三人所发现,只要认为财产的所有人、控制人没有发现这种盗窃的行为,那么就可以认定是秘密窃取。其实这里关于秘密性的主要判断还是主观性,就是行为人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只要自认为被害人不知情,就成立了秘密性。
3、“秘密”的时间性:秘密窃取行为主要是针对实行行为时而言。秘密窃取并不是必须贯穿盗窃犯罪的全过程,而只针对取财的过程。即并不要求从盗窃预备行为起就是秘密的,或者不让财物的所有人、占有人知觉的行为。如果在实施秘密窃取行为的过程中,行为人的行窃行为被财物的所有人、占有人发现,行为人马上公开夺取或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这种行为已不再是秘密窃取行为所能包含的,已转化为抢夺行为或抢劫行为。
以上三个特征即是通说所认为的盗窃罪中秘密窃取行为的判断标准。其中有合情合理的部分,然而其中也有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否定说便对其提出了质疑。
(二)否定说的观点
张明楷教授认为:“窃取行为虽然通常具有秘密性,其原本含义也是秘密窃取,但如果将盗窃限定为秘密窃取,则必然存在处罚上的空隙,造成不公正现象。”他认为,盗窃行为并不限于秘密窃取。张向阳法官认为,不仅理论上而且实践中,存在大量公然盗窃罪的情形。盗窃行为的本质是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即一方面盗窃行为破坏或者排除了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另一方面建立了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新的占有。建立新的占有与秘密窃取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三)本文观点
分析以上两种学说,本文认为否定说的观点更符合现今司法实践的要求,并且是从行为这一客观方面进行阐释说明和区分,更有利于对定罪的把握,不会造成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但通说则不然,一方面其认为,客观的盗窃行为既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秘密的,另一方面,又要求行为人必须“自认为以不使被害人发觉的方法占有他人的财物”,换言之,即使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公开盗窃时,行为人主观上也必须认识到秘密窃取,这简直不可思议。因此,我认为以秘密性这一特征来确定盗窃罪,范围过于狭隘,会出现处罚上的空隙,或者造成司法过程中的难题。
因此,本文观点认为,否定说更为客观现实地解决了实践中出现的难题,更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更有利于打击犯罪,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总结
通说要求的一些观点还是值得肯定的,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通说不能完全应对。由此很有可能会导致不能公平地定罪处刑。
以行为人的主观性认识来判断是否具有秘密性并且再以秘密性来区分犯罪类型,这样会导致形成的结果也是主观的,因为起初的认定就是通过主观认识得来的。而一个正确的决定是要主客观相统一作出,这样才会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所以,通说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国立法没有对通说观点进行肯定,但司法解释却完全支持了该看法。对于公开平和的行为,通说的解决方法是“平和抢夺”,而否定说的解决方法则是“公开盗窃”,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的困扰,而实践中更多地承认公开盗窃,且立法对于扒窃进行了规定,扒窃带有很强的公开性,说明立法已经慢慢承认盗窃的公开性而并不局限于秘密窃取。
综上所述,司法实践越来越多地承认公开盗窃的行为,所以司法解释对于秘密性的规定便形同虚设,因此,为了避免造成司法实践的困扰,有一个统一的学说更好地定罪科刑,去掉对秘密性的规定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①刘柱彬.中国古代盗窃罪概念的演进及形态.法学评论,1993,6:46.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
[2]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赵秉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4]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通史(第三卷).法律出版社,1998.
王苗苗(1993.4-),女,河南郑州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