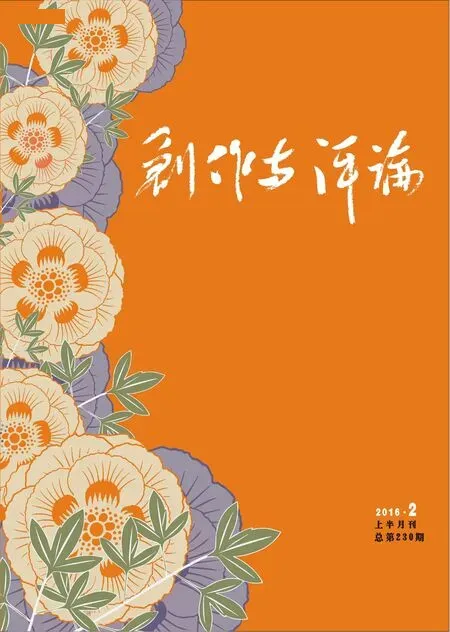老司城散记
○薛媛媛
老司城散记
○薛媛媛
1
2015年11月10日,天飘着细雨,我随湖南艺术家采风团走进永顺——老司城。
我们进入老司城的第一个参观点——博物馆。这是一座用圆石、圆竹和圆木建筑的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就像穿越八百年前的土司领域,打开了一部活生生的土司历史。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群雄鏖战,辰州剌史彭咸向五溪最强的土著首领开战,大获全胜。从此,中国西南武陵山的五溪之地尽归战功彪炳、威望煊赫的彭氏。从此,开启了彭氏土家这部历史。开启了彭氏土司的文化、彭氏土司的璀璨建筑、彭氏土司的生活、彭氏土司行政、彭氏土司祭祀、彭氏土司手工业……中国土司制度始于元朝,结束于清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
嗵!嗵!嗵!
呜——!呜——!呜。
咚咚哐!咚咚哐。
穿越时空的电子屏幕向我们展现:三眼铜响起来,牛角号吹起来,咚咚哐奏起来,土家的器乐发出激越的声波,冲击着夕阳下的寨子。挂满彩色绣球的白果树,松明火把树围成一圈,火焰熊熊,映红天地。戴着凤冠帽子,穿着红法衣的梯玛(又称土老司)手持着法器(套着铁环的宝剑),一步一摇地走来,几面龙凤大旗从竹林掩映的吊脚楼里飘过来,旗后簇拥着盛装的男女,在白果树下,围成一个大圆圈。圈子中间立放着一面牛皮大鼓,一个男人腰扎红绸带,手持鼓槌,起落地擂鼓,槌柄上的红绸带上下翻飞,舞成一片红霞,急雨般的鼓点震撼着人心,男女老少手脚不由自主地摆起来。
土家人告诉我,这是他们在庆祝社巴日。
社巴日是土家人的头等庆祝活动,商周之际,土家族先民——巴人,以军乐歌舞的形式出现在沙场上,到唐朝逐渐形成了跳摆手舞的习俗,凡有土家聚居的地方,差不多都建有摆手堂,正月新春,或者阳春三月,由寨子里有名望的梯玛主持。先用十全的供品敬土家祖先,八部大王。然后,大家围成一个圈子唱起来,跳起来,少则一个晚上,多则七天七晚。
咚咚锵!锵咚锵!屏幕上锣鼓更欢了。姑娘们一个旋转,绮裙飞起来,随着哦嗬声,姑娘们的舞姿像孔雀开屏,男人仿佛注进一股强力剂,把劲头都凝到了鼓槌上。擂鼓的姿势更加矫健,时而背身反击,时而腾空摆手击鼓,嘴里有节奏地喊着,嗬——!嗬!白果树下变成了狂欢的海洋。
我发现跳摆手舞是存心走同边线。而且还要弯腰膝,矮着身子,嘴里还不停地唱,每唱完一段,身子突然直立,像从重负中挣脱出来一样,并伴着吆喝声“嗬也嗬”。那声音,从宽厚的胸膛发出,有一种撼人心魂的壮阔气势,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两个范畴:阴柔和阳刚,在这里找到最好的解释,二者又结合得和谐,女的舞步轻盈柔和,男的动作粗犷健美。那一套套夸张的充满原始野性的动作,展示出一幅土家人模仿狩猎和耕种的画面。
土家人告诉我,跳摆手舞不能笑!如果笑是对这个欢乐而又带着庄严场面的亵渎。
我看到那些载歌载舞的人们,虽然都沉浸在狂欢之中,但每个人脸上都凝聚着虔诚,凝聚着一种自然而又神圣的表情。
我问土家人,你们唱了些什么?
我们唱的歌里有好多故事,有张果老制天,李果老治地,八兄弟捉雷公,兄妹成亲续人种……
洪荒时代,世间只剩下一母所生的布所和雍妮两兄妹,天上飞的,地下走的动物都关心人类的命运,都来劝兄妹俩人成亲,兄妹因一母所生,不肯答应,经过滚磨岩、烧火堆、破竹子、种葫芦等过程,结果两扇磨岩合在一起了,两股烟子绞在一起了,两头竹子破到一起了,两根葫芦藤子缠在一起了。经乌龟公公指点,两兄妹成亲了。百日后,生下一个肉坨坨,天上掉下了一把金刀,地下抛起一块砧板,把肉坨坨剁成一百二十块,合上三斗三升砂子洒出去世界上有了客家。再合上三斗三升泥巴洒出去,于是世界上有了土家。最后合上三斗三升树苗洒出去,世界上就有了苗家。
我觉得土家人对人类起源的解释更富有人情味。于是,土家人给我唱了段由土老司领唱的人出世:
……
左边一看咧
毕兹卡在唱歌了
白卡在跳了
叭卡在笑了
右边一看咧
毕兹卡惹惹惹了
白卡卵卵卵了
叭卡伙伙伙了
这里烟光隆隆
那里歌声绕绕
毕兹卡的子孙哩
白卡,叭卡的子孙哩
像笋子一样发出来了
……
听着歌再看大屏幕,我突然想起两句古诗:红灯幕照人千迭,一片缠绵摆手歌。银屏上披着稻草的毛古斯和摆手舞,都是世界上最古野、最张扬、最粗犷、最雄性的舞蹈,它们通过八百年时光,已溶入血液里,是土司城血脉相传,最具有生命的力量。
2
从博物馆出来我们像是从上千年穿越到现在。我看到土家人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美。男青年大多穿着镶边的对襟衣,腰系绣花板带,挂着阿妹赠送的绣花荷包,姑娘们穿着镶有梅花条的满襟衣,胸前挂的银枷,银冠,银项圈,银手镯,我数了数有二十八件之多。随着姑娘的脚步移动,绣花鞋上绣的蝴蝶像要飞起来。他们背着花花绿绿的背篓,头上的青丝帕不光是一种服饰,还像个聚宝盆,头帕卷起老高,可以装东西。女人的头帕里放一面小圆镜,一把梳子,一方手帕或者刚买来的丝线;男人头帕里放着香烟,火柴。有个中年汉子的帕子里还放着一瓶酒呢。
我们来到河边,土家人告诉我,这条河叫灵溪河。
清澈澈的河水,鳞鳞的波纹闪着银光逶迤向前,水面飘着几只木船,撑篙的人站在船头,伸长脖子喊:啊嘿嘿!呃嘿嘿。
河滩上,有几个妇女在洗衣服,这里人有个习惯,在河滩上的洗衣如果天气好就摊在卵石上晒,到傍晚收回。我走近她们,她们洗的衣不是我常见到布料和颜色,她们五彩缤纷布料上绣有着万字花边。万字花边绣的是一只飞舞凤凰,几朵带露的牡丹迎风摇曳,像一缕阳光透过,流进布面,增添了布料的绚丽。
土家人告诉我,这是西兰卡普。这是土家妇女最爱编织的一种手工艺品。关于西兰卡普,有一个哀婉的传说,西兰是一个俊俏聪慧的姑娘,卡普,是土语中的花。相传西兰姑娘为把最美丽的白果花织上土锦,在白果树下等到半夜三更等白果花开,结果被诬为品行不端迫害致死,而西兰卡普则成了土家族最美的织品,成了土家人追求美好事物的象征。土家族男人的职责是保护女人,女人的职责是忠于男人。这个保持原始状况的地方,崇尚患难之交和坚贞不二的爱情。
我们坐到一条船上,眼神里出现了画家喜欢的调子——绿。墨绿、黛绿、翠绿。河两岸密集的古树像墨一样破下来是墨绿,墨绿映在水里呈现的倒影成了黛绿,黛绿映出的天空成了翠绿。你眯着眼看,眼前一片绿雾。这时,山上响起了歌声:
这山画眉儿叫一声啊,
那边画眉儿就接罗音罗,
两边画眉儿一齐叫罗啊,
口对口来心对罗心罗。
土家人告诉我,在很久以前,月亮寨有个聪明美丽的女子叫银姑。银姑不仅是个绣花织布的能手,还是个远近闻名的歌手,在一次对歌中,她把心中的歌献给了寨子里最勇敢的猎手,两颗心就像山中的鸳鸯藤连在一起。正当两人高高兴兴准备婚礼时,土司王送来一道命令:把银姑送到土王宫里去,按当时的规矩,凡要结婚的女子,须让享有初夜权的土司王睡三晚,银姑不甘受辱,在新婚之夜和猎手逃离寨子,土司王派兵追到这个洞前,银姑和猎手跑进洞里,土司王的兵见洞里阴森可怕,不敢进去,只好把洞口团团围住,一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银姑和猎手始终没出来,却从洞里沁出两股清泉,在洞口合二为一,滴落在岩下,岩下的石头上滴出一个椭圆形水池。若干年后,情窦初开的男女饮了这里的泉水,就变得格外多情很会唱歌。
山歌甜美而没有人接音,只有山谷里的回声。一股山风从山谷里冲上来,在我身后迅速合拢,汇入一片自然之中。
3
从船上下来,踏上了老土司城遗址,也就是踏上了当年彭氏政权的司治所在地。卵石铺就的图案遗留在时空的隧道,每块石头和每个建筑都见证着彭氏土司的形成,彭氏土司的文化和建筑。彭氏土司的生活、行政、祭祀、文教、手工业都在这里聚落构成。也是这里,它以残垣断壁所呈现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唯一性,在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湖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
走在当年土司威风的土地上,庞大的遗址仍然透出王者之气。山路蜿蜒,一忽钻进树林深处,一忽又延伸到峭壁边缘。哟,前面是山,还是人?是人又是山!山的灵秀和山的曲线在好像附在人的胴体上熘熘发光。
土家人说,这是土家人的英雄彭咸呢。你看,巅峰岩缝里长的巴山松是他的头发,突出的巨石是他高耸的额角,凹进的两块石头是他的眼睛,那一绺岩缝里长出的青藤是他的胡须,他一手插腰,一手按膝,是在检阅兵马,是预备跨上马鞍。据说几百年前,当时明朝皇帝收复天南弯,土家出了个英雄,树起竿子,打着“天子国”的旗号和朱家皇帝对着干。后来,明朝皇帝派大军征讨,他就在这里点齐兵马。
我看到了彭氏土司以一种睿智和忠诚恪守平反的职责。
我们走过一道山,再转过一个山口,突然像舞台上拉开大银幕。连绵不断,连绵起伏山峰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像跻身在一个新的世界:质朴和凝重,古朴和原始。画家的六种取景:高远、深远、平远、阔远、迷远、幽远,在这里都能运用。记得达芬奇讲过,凡抛开自然界这个一切大画家的最高向导而另找标准或典范的人们,都是白费心机。可以这样说凡只研究现存的画而不研究自然的人们,你们不配作自然之子,只配作自然之孙。我们闯进一个美的部落,感到一种沉积于心底的情绪不可遏止的奔涌,抓住心中最美的印象。
土家人告诉我,这连绵起伏的山峰是“万马归朝”,你看那山峰像马头,山脊像马背,匍匐在苍宇之下。
透射八百年沧桑怆美,我不但看到了王者的尊荣与威严,还见证了世界独有的中国土司制度的兴衰存亡,铸造了一个家庭历经九朝司治时间长达八百多年的世界奇迹。
废墟和遗址虽然代表昨天,没有昨天也就无所谓今天。没有昨天的历史也就没有今天的辉煌。
薛媛媛,湖南桃江人,一级作家。曾任《新创作》杂志社副主编,现为长沙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作协副主席,湖南省作协理事。小说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收入各种年度版本。出版长篇小说《湘绣女》《我是你老师》《六三班的成长报告》《我开始烦恼了》《城域外的喊叫》、中短篇小说集《湘绣旗袍》、散文集《那个女人那个雪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