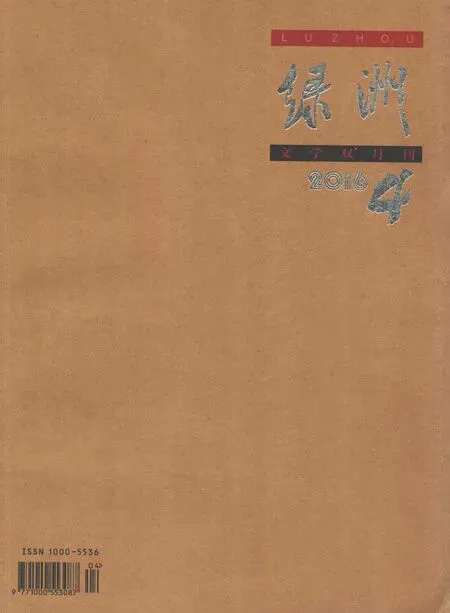山峁杂记
朝 歌
山峁杂记
朝歌
三棵杨
仅就三棵杨而已,确切地说,在白杨系列,这种杨树叫钻天杨,这是当地人给它起的一个俗名,据说它会嗖嗖地一直向上蹿,直至云霄。也没有什么怪异的,因为这种白杨太普通了,在陇东地区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房前屋后,乡村道路间,它那挺拔的身子,往往成了高塬上标志性的蓝旗。就是这么一种杨树,而且是三棵,却害得我痴痴地瞅了半天。脑海里甚至缠满了网络,思绪万千。
这是陇东庆阳特有的地形地貌——塬峁沟壑的一种:峁。峁,据辞海释义为黄土堆积起来的土丘。而我个人认为,这个定义下得还是比较准的,而这里正好是一个群峁的世界,黄茫茫的土峁像一层层刚出笼的馒头,就参差不齐地罗列在这片黄土中,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天边。而这三棵杨恰好站在这些众多土峁中间其中一个土峁的峁头上,并且在阴面。
这是一个极干旱的地区,每年的降雨量超不过70毫米,而这些有限的水分,则大多顺着峁头流到了峁的脚下,进入沟渠,汇成小溪,小溪奔向另一条沟,就成了小河,小河里的水则成了当地人畜赖以存活的生命源泉。
我目测了一下,附近的峁头均光秃秃的,像剃掉了头发的爷儿们的头,平淡无奇,只有忽喇喇打着唿哨的过山风,扬起土尘,嗖地一下掠过去又一下掠过来,让这些光秃秃的峁头心惊肉跳,狼狈不堪。在这般单调的背景下,这三棵杨就特别惹眼,让人过目不忘。
我仔细观察了三棵杨一阵,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每棵杨都不甚高大,高者约有3米,低者2米5左右,东西向依次排列,每棵之间约有5至6寸的落差,他们的腰身也不甚粗壮,杯口粗细;叶子也不甚阔大,呈小叶型。从低处向高处瞭望,高低错落有致、一字排列的三棵杨,不管怎么看,都像一母所生的三个亲兄弟。这三个亲兄弟却让人有种侏儒的感觉。
其实,十多年前,我就见到这三棵杨了。我的一个舅舅住在这片山区里,我那时还是个学生,利用暑假骑一辆自行车,去看自己的舅舅。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满眼都是一垛一垛的黄土峁,没一点色彩,我感到异常的孤独落寞,就是在那一刻,我一抬头的当儿,看见了那三棵杨。
三棵杨长在这座不太大的峁头上的背洼处,山道从这座山峁的腰部绕过。因此,我在山道上抬眼看三棵杨,三棵杨就很显眼,那挺挺的枝干,浓绿的叶子,独一无二的站位,在空旷单调的群峁世界里,突然多了一种别样的意象,一种亦真亦幻的色彩,仿佛一面绿色的旗帜,在我的头顶撑起了一片绿荫,本来我已口干舌燥,疲惫不堪,甚至想折回,放弃这艰难的苦旅,但因了这三棵杨,我还是骑上自行车,两脚一蹬,向前途奔去。我想,有绿色的地方,就有希望,就有生命,仅管那三棵杨还很小,仅鞭杆口粗细。
仅就三棵杨而已,而这三棵杨又实在不怎么出色。算起来,他们的树龄也该十多年了,放在平原上,早长成了参天大树,抑或用做了檩条木椽;而生在这个地方,却怎么也长不大,正像他们脚下的那一墩一墩芨芨草一样,终生贴在地皮上,没有出头的日子。
光秃秃的峁头上缺少树,却不乏像芨芨草一样的草本植物,譬如梭草、蒿草、冰草之类。这些草本植物抗旱耐碱,生命力极强,有时你连根铲掉,第二年还能长出来。记得张贤亮给颇丑陋的芨芨草起了个挺诗意的名字:绿化树,就使这种植物一下了温暖了许多,美丽了许多。但草毕竟还是草,怎么能变成树?山里人还是习惯叫这些草的俗名,正像他们平时叫自己孩子的小名:狗剩、来福、改改、招招从不叫大名似的,倒显得亲切、自然。
那么,这峁头上的三棵杨还有没有人唤他们的俗名:钻天扬?我不得而知。
这地方是抵达山区村落间最荒凉的一段过站,根本没有庄户人家、鸡鸣狗叫之声。只有站在三棵杨所处峁头上的高处,才能瞧见远处山缝间袅袅升起的炊烟,目光尽处山洼上隐隐约约白棉花般移动的羊群及牧羊老汉挣破嗓子才飘传过来的信天游:荞麦结籽三十三道楞,唱上一簸箕酸曲儿解心焦。更多的时日,三棵杨定是寂寞的,在这无人烟的地域,他们要幻想听到那一声亲切的呼唤,也许就成了一种奢侈。
实际上,三棵场也清楚,自己早已不是钻天杨了,如果哪一天,山民们兴趣来了,唤他们一声钻天杨,他们还会脸红心跳,觉得是一种羞辱呢。
是的,都十多年了,这三棵杨怎么也长不高长不壮,三棵杨自己也纳闷:曾经多么优秀的树种,放到这地方,就成了矮化植物?记得十多年前,一名拓荒者把他们从平原带到这里,栽到了这座峁头的背阴处,也许这人为了给这苦焦的地方种一片荫凉,抑或是为后来者竖一面蓝旗,使其树立信心,不断前行,总之,那人栽下三棵杨后,就继续踏上了拓荒的旅程。
那人当初并没有把他们栽到向阳处,因为这地方实在干旱,缺乏水分,那人害怕自己一走,三棵杨就被毒毒的艳阳晒死。最终,还是把他们的扎根地选在了背阴处。从此,三棵杨就与峁头做伴,与山风呼吸,没有人为其浇水培土,没有人为其修理枝杈,没有人呼唤他们的名字,在孤寂中生长,在荒野中守望,在冷落中期盼。缺少养分的三棵杨,还时时被严霜杀戮,被寒风袭击,被烈日暴虐……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生长慢得惊人。
从我最初见到的鞭杆样到现在的杯口粗细,三棵杨的成长史真叫人唏嘘嗟叹。想必这三棵杨也是非常焦虑的,想想自己的同类,那些长在平原上的白杨,早已做了檩条或木椽,成了栋梁之材,自己却迟迟成不了材,作为白杨系列,三棵杨肯定是很悲伤的。
此刻,三棵杨也许还在埋怨那位拓荒者,是他把他们从肥沃的平原带到了这贫瘠荒凉的山旮旯,叫他们怎么也长不大。水草丰美的平原,本该是他们的乐园呀!如今,固守在这穷乡僻壤、荒峁野岭之间,再瞧自己这侏儒般的身材,三棵杨对那拓荒人该是充满了怨恨。
但怨恨归怨恨,事实是,三棵杨依旧这般在峁头伫立着,而且这一立就是十余年。看起来他们并不伟岸、英俊,甚至有些丑陋、卑微,但毕竟他们顽强地活着,活着就是胜利。十多年前,那拓荒人也许没指望这三棵杨就能活下来,因为他是清醒的,这地方根本不利于树种生存,满目就没发现一棵树,只有遍地的茅草棵,他是带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这三棵杨安置在这里的。但没想到这三棵杨竟存活了下来,而且在这荒芜之地、光秃秃的群峁之间,再怎么看,三棵杨也像沙漠中的一片绿荫,绝望之时的一面蓝旗。如果拓荒人有知,他也该是欣慰的。
三棵杨像三个亲兄弟,手挽手站在此处,我下车端详了很久,像十多年前一样,他们周围多的是草,少的是树,多的是旱魃,少的是雨露。过山风打着唿哨掠来掠去,寒霜在阴面处尤为猖獗……对于三棵杨的境遇,病态发育,我理解了。
只是,在这个荒凉的境界里,我还是祈求多一些三棵杨,尽管他们丑陋、病态;但丑陋、病态,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像这阵儿,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三棵杨就很惹眼——在没有了绿色的地方。
三棵杨,我两次看到的三棵杨。
桐川之北
站在桐川的高处,向北眺望,总有一种苍茫沉重的感觉。黄茫茫的山峁,像一屉一屉刚出笼的巨大馒头,一个挤一个,数也数不清,就参差不齐地罗列在这片黄土中,俄顷,你的眼中便会蓄满了黄黄的馒头,让馒头刺激得眼花缭乱,世界整个是一个馒头的世界了。有阵儿,你会觉得这些馒头似乎旋转起来了,一直旋转着奔向远方,远方是缥缈的蓝天、白云。馒头便掩映在云蒸霞蔚之中了,给人一些五彩斑斓的印象。多半的光景,黄颜色是这些山峁的主色调,无变奏;要变奏,也是黄色主题下的简单变奏。千百万年以来,黄黄的山峁就恒久地伫立在这片黄土中,像俑坑里出土的兵俑,裹挟着醇酽的泥土香气,凝视着远方,显得古拙、冷峻,但更多的是悲情、壮烈。
这些山峁(严格的讲应称土丘或土峁,意即黄土堆积起来的丘陵),他占据的地域,包括甘肃庆城县太白梁、土桥、蔡口集、蔡家庙、翟河五乡及环县天池乡的一角。
一过北塬头,你就真实地进入山峁的世界了。这时,你才有机会细细品读这些山峁,但也会被山峁挤得喘不过气来。“蒸馍馍山,溜溜天”是当地民谚。当地人在两峁之间的沟底看天,天就是窄溜溜的,再看山峁却是异常的伟岸,山峁就是他们心中真正的山了。其实,若平视,这些“山”再怎么看,也只能称作土丘或土峁。但当地居民还是习惯上把峁称作山,把自己称作山里人。这倒多了一份峁的高大、山里人的朴实与憨厚。
如果你是个外乡人,突兀地处在两峁之间的沟底看天,天就很窄小,你犹如井底之蛙。此刻,你会被两峁挤压得近乎绝望,仿佛再也走不出这群峁的世界了。当你爬上峁顶重又看到塬时,你的心才会舒展一些,宽活一些。
山里人把大一点山峁的顶部叫做塬。塬一般不大,大则几百亩,小则几十亩。地势较平坦,多是乡政府或集贸之地,像南庄塬、高塬等。峁顶上的塬虽不像峨嵋山上的金顶,让信徒膜拜,但却是山里人向往的地方。每逢农闲或有集之日,他们会暂且搁下繁重的农事活动,带上自家的土特产,沿四通八达的小路向塬爬去。从塬上换回必需的日用品,如布料、食盐、农肥等,顺便听一听外乡人的胡谝冒聊,捕捉一些山外的新鲜事,回去后给村坊邻里海吹一番。
公路缠绕在山峁的腰部,一直蜿蜒着通向远处的天池,是山里人进出的要道。也经常能看到些特殊的山道,当地人叫崾岘或土桥。这种路两面是沟,中间横一条天然形成的土梁,就连接起了此峁与彼峁,走起来便利多了,省得翻沟。
翻沟也是山里人的一种行走方式。有时隔沟相望另一个村子,看似近在咫尺,却难以逾越,若转塬少算也得十几里路程。这时,山里人就选择了翻沟,翻沟只需四五里路程就到了。
过去山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毛驴,下沟驮水运柴,上洼运肥驮庄稼,跟集驮货娶亲都是毛驴的差事。现在,却能看见,在险要狭窄的山道上,一种像蚂蚱似的叫做“蹦蹦车”的机械,穿梭于群峁之间,这给山里人的行走运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给寂静的山乡增添了热闹。
山峁的脚下就是沟了,沟像无数的蚯蚓盘绕在山峁的屁股下面。沟永远是峁的脉络,也是峁的血液。多少年了,沟默默地滋润着峁,使峁在黄土高原上就这般伫立着。
沟常常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是牛羊的眷顾之地。沟里有山泉,冰凉的泉水渗出汇成小溪,潺潺的溪水奔向另一条沟,就成了小河。也有一些干涩的沟,连泥石也是焦黄的,没有一点水分,就叫干沟。干沟是山里人遗忘的角落,人畜极少到达。沟的尽头叫掌,若走到沟掌,就无路了,你得回头。也有许多沟,没有掌,能延伸至峁外的世界,像野狐沟。
梁是峁的脊,洼是峁的背。长久以来,洼是山里人主要的劳作和栖息之地。坡度小的洼开垦后成了耕地,坡度大的洼难以垦植就留作了草场。向阳的背洼处,劈开黄土,则修成了庄子,有半明半暗庄,罗圈庄。出门是沟,出水极顺畅,不害怕淹水。
洼上的耕地蓄不住雨水,缺少养分,粮食产量很低,常常几十亩的产量不抵董志塬上几亩的收成。有些山水冲积成的塌洼就比较平缓,耕种收割省力,产量也较高,但这只占洼地的极小部分。
山里人除了种植五谷杂粮外,主要种植的是油料和豆类。现今陇东城里人常食用的清油和豆浆,原料多来自这一地区。陡斜的山洼,留作牧场。放羊老汉把羊往山洼上一赶,向背荫处一“箭”,就任由羊自由地啃咬去了,煞是逍遥。有时,瞧见了沟对面洼上的牧者,兴趣来了,会吼上几嗓道情,算是交流。
从山峁的高处瞭望远处洼上的羊群,这羊群就很遥淼,像朵朵飘动的白棉花,在山洼上缓缓移动,不久,就消失在山洼的背面了,让人怅然若失。山里人却没有这种感觉,这是他们司空见惯的现象。
梁也是山里人出行的便道。当土梁上走来了身背毡弓的毡匠或邻村的熟人时,洼底庄头干活的山里人瞅见了,就会仰嗓用信天游腔搭话:“山丹丹开花背洼里红,娃他舅你从那搭来?”梁上的人就觉得很中听,知道到了该歇脚的地方了。赶快回应:“白葫芦开花头对头,我从娃他干大家里来。”一切的交流便在三腔两调的逗趣中完成了,显得亲近、诙谐。
山中的农活是非常辛苦的。往往每户要种七八、十亩甚至上百亩的山地,还要养五六条牛驴骡马、四五十只羊,天未明就得下沟挑水饮牲口,早饭一过即下地干活上洼牧羊,天黑才牛羊收圈,晚上还要铡草准备夜草,半夜起来喂牲口。常年累月的辛劳使山里人肤色黝黑粗糙,身板精瘦弯曲,但也使他们的体格特别硬郎、坚韧,翻山越岭脸不红,心不跳。
山里人平常食用的是自产的五谷杂粮,譬如荞面、苞谷面、糜谷、白豆、豌豆等。就连招待客人或过事主食也是荞剁面。这倒使他们极少有城里人惧怕的富贵病“富态”及矫情的“三高”。
山里的牛驴骡马也不像平原上的牲口那般高大威武,膘肥体壮,都较低矮、瘦小,但却很矫健、灵活,在洼地上耕作如履平地,行走自如,是山民们最重要的拓荒搭档。
山里的羊分绵羊、山羊两种,是山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据说山里人相亲,女方先要看男方家羊只的存栏率高低,作为选择的重要条件。绵羊用来产羊毛、羊绒,山羊用作食肉。山里的羊奔山道、走崖洼、食百草、产毛量高,肉食香嫩,其味独特。羊是山里人的吉祥物,像狗一样,他们一时半刻都不能缺少。
狗是山民们用来看家护院和牧羊的。山里时有狼狐野物出没,伤及人畜。山狗异常灵敏,一嗅到响动,便吠叫来,一犬吠叫,百犬呼应,场面非常壮观,群峁便满是狗叫的回声,狼狐野物便被吓跑了,山乡回归平静。
而在平时,山里是寂静空旷的,寂静空旷得令人落寞。一家一户要隔数里地,转两三个峁头才能到达。很少遇见人,大约到了秋季,收山货的外乡人来了,才使山乡热闹一番。大部分的时日,山里人与山峁做伴,看到的都是光秃秃的峁头。峁头是瘠黄的、单调的,只有春天的到来,淡黄的油菜花、蓝蓝的胡麻花、粉红的荞麦花,及一些不知名的闲花野草,才能给山峁带来一些变化,使孤寂的山峁多了一份色彩。
很多的时候,面对这些黄土堆积起来的奇景,造物主的神奇造化,我禁不住都要唏嘘感叹;我在感叹它们神奇与博大的同时,也为它们黄黄的面孔忧思:什么时候,这些黄土高原上的兵俑,永恒的守望者,能披上绿色的铠甲?
桐川之北,确实是一块叫人震撼而牵挂的地方。
责任编辑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