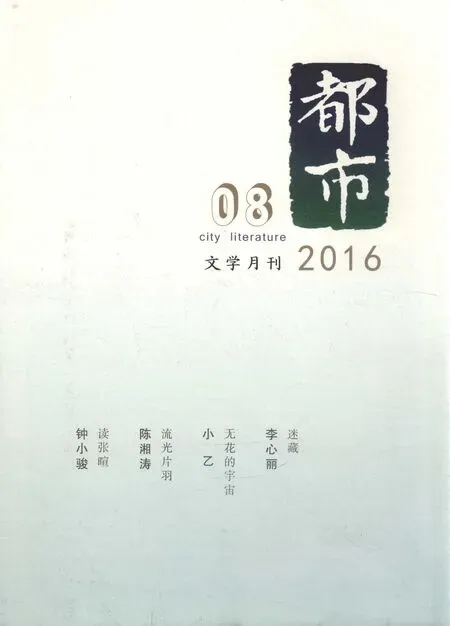读张暄
钟小骏
读张暄
钟小骏
霍金在那本让他声名鹊起的《时间简史》的开头,提到了一个定律:任何一本书,即使是数学或者物理学的专著,每引用一个公式,就会流失掉一半的读者。为了让自己的理论能够最大化传播,也就是能够让最少的读者离开自己的作品,他在整部书中只使用了一条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定理的数学形式,就是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质能方程——E=MC^2。于是,《时间简史》成为史上最畅销的科学著作。
无独有偶,后人在评价被誉为“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国富论》时,除了对亚当·斯密天才般的见解大加赞赏之外,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并且他的著作是以常识为基础的,让读者能够用他们自己的常识思考经济学问题。”
所以,我尝试着在这篇文章中尽量少地使用“理论”、“风格”、“派”之类的理论性字眼和词语,让自己的意见尽量地清晰而被大家读懂。
我呢,认识张暄本人,早于读他的文字。精确点说,我对他作为一个“人”的形象,建立早于他的“作家”的形象。所以,我来评价张暄,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自己主观印象的影响,这在评论来说,毫无疑问是大缺点——任何评论、比较,一旦不客观,必然失去权威性。不过,这个缺点有时也不是毫无用处。我对张暄作品的第一个印象,恰恰来自于对他文字的感觉与对他个人印象的背离。
听张暄说话,真是让我头疼,好像他生活过的地方一直都拒绝执行国家关于推广普通话教育的方针似的,他能够做到让自己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完美而固执地走到晋城味上。我的语言天赋很弱,即使与他聊天时内容范围已经被限制得相对较窄,哪怕仅集中在文学方面,也时常需要靠猜测才能让话题进行下去。尽管如此,我仍然十分愿意与他交流,那是因为他即使需要费力地放慢语速,并辅以大量的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他所说的内容,仍然会迸发出强烈的戏剧感。而他对话题的选择以及提供的意见,也总是因为精辟而显得精彩。只从这个角度观察张暄,你会自然地得出印象,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的迫近生活的家伙,他身上那种说不上来的热情劲,简直就要溢出来了。
直到我看到他的小说。
先不说张暄对小说题材的选择和想要表达的意见,只说作品里他的文字的感觉(是的,一个人的文字是有感觉的,这不是故作“文艺青年”的淡淡的装),就是一个字:忍。这里的忍,不取“忍受”意,而是“把感情按住不让表现”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冷酷、狠心”。这种感觉,猛一看上去,很像是“冷静”,有人也许会形容成“客观”,稍微偏感性一点的,会称之为“疏离”或者“旁观”。但我觉得,那些词语的程度,都不够猛烈,不足以形容这种对比给我带来的感觉的强悍程度。只有“忍”,接近“残忍”的“忍”,才能形容这样一个不同的张暄带给我的震撼——一种没有温度的文字。一个,与我之前所认识的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张暄。
从打社会学成为一门显学,对一个作家看法的建立就不再只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全部。所以,很多人一旦知道了张暄的社会身份——他那众所周知的警察职务,就作出一副果不其然的样子,觉得自己掌握了张暄的写作密码:警察嘛,就是这个样子喽!
曾几何时,所有与国家公职有关的形容词竟然都带上了贬义,比较直接的面对群众的几个职业也都有了约定俗成的固定特色。那些这么评价张暄的人之所以沾沾自喜地认为张暄的文字就是警察的文字,实际上是基于“警察”这个所谓的社会印象——麻木。于是他们说文字没有温度是正常的,描述没有感情是正常,故事没有倾向是正常的,简言之,一个麻木的人,写出这样的文字,是正常的。
不过我刚刚已经说过,张暄不是那样的人。
那么我就要解释,这巨大的背离,究竟是怎么造成的。一个像我说的那样热爱生活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文字?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所谓“文品如人品”一直都是一句被过度高估的夸大之词,反面的例子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应该就是严嵩了,其诗气度高然,飘然欲仙,深得一心修道的嘉靖帝欢心,甚至被称为“青词宰相”,可见其词多么淡薄而缥缈。但要是说到人品,“和之前最大贪官”的名号可实在是对“文品如人品”这句话的打脸啊!
不过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证否”,并不是说找到一个理由证明那些人说的不对就可以了,而是要“证明”,要找到一个道理说清楚张暄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写法,要说服人相信这么写作的张暄不是因为他的职业,不是因为他只能这么写,而是他要这么写,他是故意的!可是,这究竟是故的什么意?
现在比较主流的对小说的看法,都认同小说在中国的源流始于“说书”,于是理所当然地,描述唯恐不细密,情节唯恐不动人,语言唯恐不生活,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前提:让听众身临其境。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传说中的“小姐出门”——话说曾经有一位说书人带着小徒弟在一处说书,徒弟天资不错,但从来没有独自表演过。一日师傅突然有事要离开几日,便叮嘱徒弟,我这书说到了小姐要出门,正在梳妆,你且慢些讲,我不日便归。于是出门,可没成想事有耽搁,接近半个月才办完事回来,路上十分担心,后半部书还没教过徒弟,这小徒弟可千万不要砸了自家的牌子。一到家,徒弟如释重负地迎了上来:师傅啊,小姐今日已经熏香沐浴、装扮齐整,终于要出门了,您再不回来,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师傅大松一口气,小姐出门能讲半个月,这个徒弟,可以出师了!
于是大家可以明白,传统的小说创作,或者叫做曾经主流的对小说的判断,实际上就在于让读者能够通过不断的想象,在脑海中构建一个由作者提供的世界,并让作品的主人公在这个世界中行动起来,在其中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悲欢离合。
然后大家也可以明白,这条路,现在已经不好走了。
为什么呢?技术进步。
曾经的人们,即使是三十年代生活在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欧洲的人,也不可能想象我们现在的人每天竟然会接受如此丰富的资讯和影像,他们也不可能想象到我们,一个正常长大的普通人,在成年后,甚至可能还不到成年时,就已经把他们一辈子,甚至是很多人的一辈子所能看到、听到、接触到的故事听完了。收音机、电视、电影、电脑到现在的手机,信息的极大丰富不是一句空话。当Twitter140个字符的输入限制出现的时候,小姐出门,那就一定要快。
所以,小说的描述方法就有了变化,纯粹客观(当然这不可能,只能尽量接近)的叙述方式实际上有一阵颇为流行,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效果:让事件的意义呈现在事件本身。其中最近的也是最有名的,电影方面是贾樟柯的《天注定》,小说方面是余华的《第七天》。
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并没有向张暄求证过,换句话说,张暄的这种写法也很有可能是一种自发的对事件的看法的表达,或许他并不一定精确地实践这个理念,但我相信他一定是对自己的创作有过设计。理由,就在于他的风格的变化。
我得出这几个观点所基于的材料,是张暄最近出版的小说集《病症》。这部集子是山西省作家协会和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组织的“晋军新方阵”活动的成果之一,是张暄个人比较满意的作品的一个合集。里面几部小说并没有严格按照什么线索分列,时间或者题材什么的,所以我还专门询问了他一番,确定了让我有惊艳之感的第一部作品《刺青》就是他个人创作的处子作。由此,引发我的下一个判断:
力量。
任何作家,我是说任何一个作家,他的第一部作品,都离不开对自己经历的重现,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很容易就变成半自传性质的人生解读。其中比较优秀一些的,会变换一个形式,尽量避免自身的情感被过度代入。但是即使受过很好的文字训练,作家在没有取得成功之前,也无法真正的领会到“虚构”的精髓。换句话说,即使他已经虚构了,可是它体现出来的东西,绝大多数还是自身。于是,我们看到张暄在《刺青》当中,在看似冷静的笔调下,有几乎隐藏不住的涌动。这种涌动,不是单纯的感情,也不是单纯的欲望,可能只是一点点的气息,但是十分有力量。这种气息,在我看来,就是作者那种最原始的想要倾述点什么,想要展现点什么,想要让大家对他认同点什么的东西。这种东西很宝贵,却又很玄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找不到了,想保留都保留不住。当然,也有一些作者不愿意展现这一部分,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太原始太粗糙,没有那种经过打磨的质感。我认为这两种看法没有高下之分,只不过从纯粹阅读的角度上讲,我还是更愿意看到原始的那一种。同时,我也明白后一部分作者的感受——那么原始的东西,一定很稀少——所谓的元故事,怎么可能丰富?即使经典物理学的世界结构模型粒子,也不过区区64种,这还是前两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被确定之后的样子,不然还要更少。世界尚且如此,更何况故事?更何况只是一个人的故事?换句话说,一个人,就是他把作为人类所能经历过的事情都经历一遍,又能产生多少感想?何况你还未必能经历多少。说句题外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一代小说家目前看来大部分成就比这一代小说家要高一点的原因,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是时代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可重现了!
那么,那些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作家们总会找到一种方法,来维持自己对于世界的敏感,来寻找一个合适的讲故事的切入点。功利点说,来维持自己的创作生涯。那么,他们会怎么办呢?于是得出结论:一要多读书,从别人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角度,二要有技巧,如何讲述一个故事,或者说,讲述一个故事的方法,就变得重要起来。
于是我看到在张暄的这部《病症》当中,赫然出现了一系列貌似“官场小说”的小说。我说它貌似,是因为我能看出张暄实际上并不是想展现“官场”,之所以这些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地方(县城或者小城市)的中层(甚至基层)官员身上,是因为作者觉得这样安排会更具有小说性。作者实际上并无意于展现官场当中那种所谓的“微妙”和“玄机”,或者是人事之间那种错位和揪扯。他想要的,实际上是在大家都熟悉(无论承认与否,官场实际上就是普通中国人最熟悉也最能理解的环境生态)的环境下展现自己想展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荒谬感,当这种荒谬感在一种尽量符合生活逻辑的状态下被展现出来,其中的故事感,也就是小说味,也就变得鲜明起来。
可是,这就涉及到我刚才说的那个感觉,在对小说形式的安排上花了大功夫之后,有时候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因为不能伤及到结构,有的时候甚至因为不愿意损害讲述的节奏,于是,我们对这个故事讲述的冲动被人为地减小了。说得明白点,因为对形式的看重,没有精力,或者叫没有动力再去讲故事了。也就是说,力量小了。
这实际上很好理解:一个故事,即使再精彩,你要是讲上十遍,也就寡然无味了,要是一百遍呢?不夸张地讲,一个作者,对自己的故事,想过何止一百遍。再加上,如果已经尽量仔细地考虑过结构,那么在讲述(创作)过程当中,想再重新寻找到讲述的激情进而能够在结构范围内保持情绪从而达到一泻千里的状态,那除了天赋之外,一定还需要千锤百炼的磨砺,以我有限的经验来看能做到者也实在寥寥无几,王朔算一个,毕飞宇算一个,咱们山西的作家中,手指的某些作品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认为张暄将来一定达不到这个水准:首先,这本来就是我的一点个人意见,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达到达不到什么的本就没什么意义;其次,谁也不敢说自己的眼光就牛到可以评价一个人写作生涯高度的水平;最后,文艺创作本就是唯心的东西,所谓文无第一,就算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待早期的屠格涅夫的作品时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回到张暄创作本身,我对张暄这个时期的作品的看法,就是太像小说了。这一论断,尤其体现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的结尾部分。有句话叫做灯不点不亮,那个时期的张暄也一定要在作品的最后点这么一下。虽然他点得巧妙,巧妙到我在阅读时候甚至都听不到那熟极而流同时也完全不懂的晋城话,但这对作品来说仍然是不成熟的表现,是伤害。以至于我从朋友角度出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总是难免要叹息一下。
好在他进步了。
这种进步,不是说类似扔飞镖,新手乱扔有时也会正中靶心,而是创作者在经过无数次痛苦的自我解剖之后,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判断,然后寻找到创作方向并按照该方向尝试着迈了一步。这一步要是走的结实,就意味着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前途一定不平坦,但肯定向着光明。
于是,我看到了《洗脚女关婷》。这个故事中的女人,这个“小姐”,已经有了她自己的温度,甚至,有了自己的人生。我们看到的,除了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故事,还有她身边的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虽然也只是在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中的庸常事件的集中再现,但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味道。而终于在故事最后,我担心的那个刻意做出来的“结局”没有出现——这个被小姐妹背叛,受过家庭伤害,忍受背离家乡,并最终再次受到情伤的女人,在故事的最后,只是打开门,“迎着呼呼的北风,往夜色深处走去”。由此,我认为,张暄踏上了那条注定不平坦但向着光明的道路。并且,踏的很稳!
刚刚引用的那句话,并不是我认为那句话是张暄的小说创作中最出色的句子(也确实没有那么出色),也并不是因为这句话提供的意向有多么高明,只是因为这句话回归了本心,也就是我认为这句话的文字本身和它提供的意象做到了统一,并在结尾的时候出现给整部作品带来了一丝韵味,这丝韵味终于因为没有被明确说出来而被读者一直咂摸,由此就完成了小说在读者心中的再创作。于是整部小说的完成度也就再次提升了一点。当然,不可否认,我私心地认为,作为一篇评论,倘若没有对原始文本的引用,似乎在“文学评论”这个领域是被看做很业余的事情,但是我最喜欢的张暄的文字,却实在是太大段了,只好把这句我个人认为对张暄意义很大的话单独拿出来放在这里,以示专业,再把我最喜欢的那段文字单独做成一个题目,放在文章的最后。
细心的朋友已经看出来,我一直不说我最喜欢的是张暄的哪一部小说而说是一段文字,那是因为,我最喜欢的那一部分确实不是一部小说,甚至我认为这部小说因为强行地在这段文字之前和之后安排了段落而让我有很强烈的割裂感。如果你们也都看过张暄的《病症》,那么,你们一定知道,我说的,是《还有一滴泪》。
《还有一滴泪》是乡情小说,这是一种带着乡土气息,但又不是典型农村题材的一种小说类型。这种题材要写好并不容易,近来很多作家试图“接地气”时大多数会选择在这种类型上下功夫,我们山西的作者就更是如此,但做得好的真的不多。小说的开头是张暄擅长的那种夫妻间似有若无彼此纠缠虽然无力却又无解的描写,所以当我看到那个习以为常的失眠的夜晚时,心中并无多少期待。直到第二段开始。或者说,竟然从第二段开始,整个作品,就已经完全脱离了那种氛围,那种“张暄”的氛围,开始了流淌。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是苏轼对好文章的评价,也是我的一贯价值判断标准,所以在我来说,对好文章的最高赞誉,就是“流淌”。
这篇文章,从第二段的爷爷出现开始,就进入了自己的河道,然后是“奶奶”,然后是“支地枪”——第一道洪峰;然后是“三旦”——这里是急弯,然后“爷爷死”——河水平静期;“小秋学枪”,“打狼”——二次高峰起;“父病”,“占卜”,“狼灭”,“狼崽”——波峰波谷,高潮不断;“小秋死”,“收枪”——悬崖湍瀑,飞流直下。行文至此,顺畅而有波折,其下深潭,幽深而有遗韵。
可他非要加上最后一段参军的故事,我第一次读到时,咬牙切齿。
这篇小说,张暄用数字在每段之前做了标示,一共13段。如果除掉第一段和第十三段,是很显格调的一篇小说,反而加上之后颇有蛇足之嫌,文气割裂,意象凌乱,甚至主题都显得模糊了。最让我不可忍受的,他竟然把这篇文字去掉头尾放到了以前出版的一部散文集中。我询问原因,他说在这整部《病症》收入的13篇小说中,只有这一篇没有发表过,言外之意,别人并不像我这样看好这篇文字。我听后默然,“不识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翻译过来就是:这帮编辑眼瞎了吗?然后我找他要了那部叫做《卷帘天自高》的散文集,翻到了被取名为《最后的狼》的散文,读过之后,很想骂张暄两句——我一直以为他所谓的去掉头尾,就是去掉了1和13,结果,他实际上是从5开始写到11。贾岛“推敲”的典故上过学的人都知道,而在一部小说中这样涉及结构的调整几乎就相当于重新创作了,他竟然说“只是”加上了头尾云云。在这里我想对那些我在心里骂过的编辑们道歉。
可看着张暄的眼睛,我也实在说不出骂他的话,对小说一直很虔诚的他应该是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这多出来的几段话,几个字,几个人物,几个意象,就是一个小说家的进步啊!
在11的结尾,他写:“从此,我们村里再也没有狼。”
在12的结尾,他写:“从此,我们村里再也没有猎人。”
你们说,这力度怎么会一样?
他还写:
“最让人惊讶的,那只公狼虽然已经冻成了一块冰坨子,可那只母狼居然还没死。从它灰中泛黄的毛上沾染的雪渣和四蹄被铁丝勒出的血口子,可以想象昨晚它进行了如何的挣扎……”
“……就有几个大孩子把那几只狼崽子抱出来。看到它的孩子们,那只虽然未死但虚弱到极点的母狼把眼睛睁了一下。”
“有几个淘气小孩子用木棍戳击、敲打狼崽子,小狼疼得嗷嗷叫。母狼又看了一眼它的孩子们,身体轻微的震颤了一下子。”
“然后,我真切的看到,一滴眼泪缓缓地从它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它的眼睛外围有一块发白的毛发,那滴眼泪淌过那块白色区域,深入它通体的毛发之中。随后,它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
我爱这样的文字,我爱这样的流淌。
(责任编辑梁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