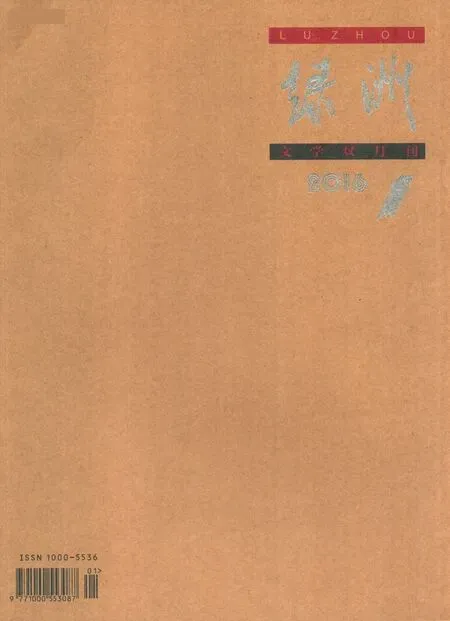我落入记忆的陷阱
高维生
我落入记忆的陷阱
高维生
我被月光弄醒
突然间,如同泼上一身水,我被月光弄醒。昨夜睡觉前,由于天热,我未拉上窗帘。此时天空的月亮,仿佛喷壶的喷嘴,撒落细密的光。
我躺在床上,完全暴露在月光下,月光涂在身上,我无一点隐私可言。我下意识地用手想挡住涌进的光,这只是一种想象。我让月光控制在编制的笼子里,变成它的奴隶,任何反抗都逃不出去。我不动弹,目光和月光在空中碰撞,瞬间被湮没掉。我感到自己的目光软弱,经不起一番的冲击,就溃败下来。我很想报仇,因为它将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的睡姿,身体隐秘的私处,录下放肆的呼吸声,甚至偶尔的咬牙声,呼噜声,将我的另一面收入它的档案中。
坐在床上,改变一下姿势,月光以最快的速度,构画出我新的形象。我看到月光,竟然爬进胸毛中,顺着毛孔进入身体中。月光太强大,在水泥铸造的城市中,很少看到这么亮的圆月。卧室中堆满月光,我不知该如何面对眼前的局面,我拿芭蕉扇挡住私处,还是用毛巾被裹起身子,蜷缩在其中。要么干脆拉上窗帘,让滑轮在槽里敲响,发出严重的警报,然后合拢帘子,割断月光通往卧室的路。我的思想斗争,两只手搭在床边上,等待发出的命令,然后按照指示,采取一种措施,三下五除二,把事情做得漂亮。
我毕竟不是年轻人,身体发生老化,皮肤松弛,肚子前堆积的脂肪,不仅难看,而且损害身体的健康。我订制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按照每一条去做,绝对不应付。清晨5:30起床,6:30吃早饭,然后是散步的时间。7:30回来,坐在案前读书,8:40左右,清洗茶具,开始每天的第一次喝茶。9:30再次写作、读书至11:00。中午小憩,前后大约半小时。然后是读书,2:30沏茶,喝40分钟茶,同时静心不想杂事,将自己从世俗的烦躁中挣脱出来。随后是一天的第二次散步。我通过一系列的条款,保持旺盛的精力,在和时间进行搏斗。我不想对月光讲,让它把我所有的秘密发现。在现代社会,有一个私人的空间,是十分重要。
我光着脚,踩踏月光在地板上行走,这是重磅地回击。我回头一看,走过的地方,月光未被破坏,不留下一点踪迹。我的行动只是心理安慰,不见任何效果。我站在窗前,瘦弱的风,从纱窗钻进,吹在皮肤上略有凉意。一轮圆月挂在天空,犹如盛满丰富想象的银盘,吸引人的思绪。
我变得安静,臣服于月亮的面前,柔美的月光,不似火焰那般激情飞溅,但也能融化坚硬的情感。
我在场,看到夏日的午夜,月光淹没这座城市。
挣扎的美妙
你是谁?每天走到坡形台阶时,我就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问。我不用回头看就知道,这是一种幻觉,声音真实得吓人。这个时候,我手中的自行车钥匙,不知不觉地放到包中,我像有阴谋的人,怕别人发现这个计划。我竖起衣服的领子,往下压了棒球帽,一双不大的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关注进出办公楼的人。
我不想遇到同事们,早晨总要问候一声,我更怕开车来的同事,拿的钥匙似一把小手枪,在手中玩弄。感应门有意和我做对,有几次前边的人刚进去,到我这却不开门了,我隔玻璃看着站立的保安,大盖帽下的脸笑得灿烂。我急速地穿过大厅,如果电梯出入口有人说话,我就在墙角等一会儿,不拐那个弯,听他们进了电梯,再等下一趟。我害怕电梯窄小的空间,人们肚子贴着后背,后背贴着肚子,感受对方的喘息声。一天中,在电梯是一次聚会,都是同事,在一起工作多年,见面免不了逗嘴。瞧我这副行头打扮,有人说:“风尘仆仆的,怎么来的?”我帽檐下的脸,肉不笑,皮也不笑,不自然地说:“穷人,骑自行车来的。”他的问话,我觉得是挑战,犹同拳击台上的拳击手,还没开打,就向对方展开心理攻势,做出各种鬼脸激怒对方。我感到包中的钥匙这时变成一把锋利的刀,刀尖游走着强烈的欲望,想做点什么。对方身上残存的酒味扑鼻,夜里他一定喝了不少酒,喝得很得意,那种得意延续到今天。我对酒味特别敏感,它和身体味掺合一起,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冬日的一天,我清晨上班顶着西北风,风如同我使用的“飞利浦”剃须刀,把脸刮得干净,不留一点空白,钻进每一个毛孔中。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奋力蹬车子,风一堵无形的墙向我倾倒。远远地看到单位的大楼,我身上出透汗,却没一点的力量了。我一只脚撑地,调整一下体力,戴手套的手,抹了一抹挂霜的嘴。汽车一辆辆从我身边疾驶而过,我是马路上的一道小坎,汽车从我的后背爬过,再从前胸下去,我甚至听到轮胎落地的咯噔声。这时一辆车停在我的身上,摇落的车窗露出熟悉的脸,就是他,开着小车认出我,他关心地问道:“怎么不走了?”我慌忙地说:“我接个电话,没事,你先走吧。”我慌乱地把手伸进背包,做出要掏电话的样子。同事招招手,排气管喷出的尾气,如同一串流行歌曲的音符在空中飘荡,我目送汽车的背影,重新开始蹬自行车了。
我盯住显示屏上,红色的箭头,快速地上蹿,我盼着跳出16这个数字。电梯是一只老鼠,在水泥的缝隙中窜动,顶棚的射灯光,仿佛老鼠竖立的根须,有一股阴森的不安全感。出了电梯,松了一口气,有一种逃脱的感觉。包中的自行车钥匙给了我很多的勇气,像一棵我能依靠的树。
在办公室里,我的自行车钥匙都是在包中从不外露,不像自己有汽车的同事,钥匙随便地丢在办公台上,金属的气息,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时飘散的气味。这朵金属花,能启动一辆凶猛得像钢铁狮子一样的汽车,在城市的街道上,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它碾死一个人,要比动物残忍。它像妖魔发出的音声,引诱人们不肯离去,抚摩它,坐在它的身上,不惜重金相许。
站在16楼上,透过大玻璃窗子,俯望楼前的一排排汽车,恰似冬眠的甲壳虫,在动物界我最不喜爱甲壳类的虫子。多年前,父亲在我儿子小的时候,给他买了一本《绘图儿童动物辞典》,教他识图,读介绍动物的文字,父亲对这件事很看重。如今儿子上大学了,书脊破损,贴上了透明的胶带,他早不看这本书,我却经常翻看。我喜欢把无脊椎类动物叫甲壳虫,像金龟子,名字叫上去很美丽,却是农作物的害虫。蝗虫能飞善跳,大面积地扫荡,是绿色植物的天敌。它们不像狮子和老虎,长得英俊、洒脱,跑起来美丽迷人。
有一天,还未到下班的时间,我溜出了办公室,电梯理解我的心事,没等几秒钟,我就走进电梯。空空的电梯里,竖起衣服的领子,压低帽子,我手伸进包中摸到自行车的钥匙。我知道它的位置,因为我不会随便放它,我离不开它,没有它我回不了家。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沙尘暴刚过去,天空小说中描写的那么蔚蓝,那么高远。天气好,一天的工作顺利,人的心情如歌声一样欢快。我走在大厅中,一个人没有碰上,只看到落地大钟的钟摆,表情严肃地晃来晃去,显示自己权力的威严。考勤机就在它的旁边,每天打卡以它的时间为准,打早了是旷工,晚打了是迟到。保安对我的经过,头都没抬,在簿子上登记什么。
出了大楼,我快步向停车棚走去。停车棚前是一条不宽的甬路,一辆白色的轿车没有熄火,停在门口,骄傲地耸立。我必须横着从车头前走过,进入车棚,走到最里面,在一排自行车中找我的车。停车棚不能乱放车子,按等级排列。摩托车摆在外,靠在门口出入方便,其次是电动车,最里边是自行车。门口的小车头朝阳光,没有看清开车人的脸,我对机械一点不感兴趣,很少辨清车型和车名,对车漠不关心。我在包中拿出钥匙,弯腰去开车锁,我的脸正好看到小车的侧面,摇落的玻璃,去掉了视野的障碍。驾驶座位上,坐的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的手不听使唤,钥匙不听话地掉落在地上,我弯下腰,向车和女孩鞠了一大躬,才捡起钥匙。那女孩始终带笑地注视我的举动,我这个年过四十的中年人,手忙乱地不听话,钥匙竟然插不进锁孔中。我的黑包也耷拉下来了,不敢抬头和女孩对视。我无处躲藏,钥匙在锁孔中转了几圈,终于打开锁,我的目光像被一阵狂风刮断的树枝,一折两截,无力地搭落。
单位迁到西区,很多人买上了汽车了,我还是骑破旧的自行车,我觉得无所谓,骑自行车锻炼身体,不花一分钱减肥,这一次,却被女孩看得有些动摇了。环保主义大旗的旗杆,让她的目光拦腰砍断。
那几天我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女孩子的目光,像夜晚汽车的大灯,一束强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看不清前方的路。我慌忙地用胳膊挡住,不断后退。灯光像一条流淌的河水,波纹状地跳跃,我后退的时候,借着光束,却能辨清路的方向。我什么事不想做,昏头胀脑,像旋动的陀螺,工作累了的时候,就爬在窗前向楼下观望。一排排甲壳虫似的小骄车,像街头醒目的广告牌,压迫我去读每一句广告词。
我在的报纸是一张娱乐报,生活周刊是针对老百姓的版块。编辑部多次开会,为了适应读者需求,面对广大的消费者,开辟一块汽车版。自打被女孩的目光折磨一次,我对汽车的感受,如同赛道上高速奔跑的F1车赛,在弯道一个大急转弯。我平时从来不看汽车版,每期报纸一出来,印刷还没干透,看完一张报纸手沾满油墨。现在我却不管自己负责的版面质量如何,有没有错误出现,却急忙地翻到汽车版,汽车信息对于我变得重要了。我认识了“雅绅特”“东风雪铁龙”“自由舰”“千里马”一些汽车的品牌和车标,我顺口溜达出这么多的车牌,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记者部接到一家汽车销售公司的邀清,参加本市最大的一次车展,我找到了领导要求参加这次采访。请柬印刷得精美,一辆小轿车前,站着漂亮的“汽车宝贝”,我看着彩印的美女,小心地放到我的背包中,和我的自行车钥匙待在一起。
小梳子
汽车的轰鸣声,将我从睡梦中拽出。夜里未睡好,凌晨三点多钟,睁开眼睛,看到窗外的亮色爬上窗子。
“朋鹏酒店”处在哈尔滨南岗区马家街与建设街交叉处,也是我此行落脚的地方。今天我将结束东北的田野调查,8点15乘南方航空公司的CZ6285班机,飞回济南的遥墙机场。
时间尚早,我赖在被窝中不愿起来。拉杆箱立在床边,相机包放在桌子上,它们准备好了,只等和我一起行走。躺在床上睁着两眼,向这座北方冰城,作告别的仪式。我不是马上穿好衣服,来到卫生间的洗漱台前,洗净脸上残留的夜迹,用一次性的牙刷刷牙。我看到盘中装的小梳子,躲在纸盒子中。
我有收藏小梳子的习惯,每到一处住过的酒店,都将小梳子装进包中。这不是怪癖,特殊的爱好,而是存下一种心情。时常翻出这些小梳子,看到形状、色泽不一。伸出食指尖,沿着梳齿滑动,发出清脆的响声。齿子粗细不同,长短也不一样,发出的齿声,不会相似。皮肤的温度,触摸塑料的齿子上,如同拉开时间的门,找出记忆中的日子,翻到那一天中。每一根梳齿,是一段难以忘记的日志。2014年6月27日,星期五,夜里下起雨,夹有电雷鸣,清晨雨停。我来到双阳,住进“星苑大酒店”,它的前身是军人招待所,现在重新装修,改名叫“星苑大酒店”。它们的梳子,有过去的影子,憨厚粗壮,拿起来有安全感。7月3日,我是坐一辆越野车,从牡丹江来到绥芬河,被朋友安排住进新华街41号“澳普尔国际大酒店”。我一进入酒店,到卫生间洗脸,看到长条形的黑纸盒,上面印有一枚烫金的钻石标志。里面躺着纤瘦的梳子。它的造型时尚,给人温馨的感觉。
我的藏梳中有很多的记忆,2009年6月,我第一次到重庆,住在西南大学的学校的“桂园宾馆”。在北碚的几天,我去了梁实秋的“雅舍”,来到嘉陵江边,徒步穿过大桥,看复旦大学旧址,寻找萧红的影子。“北苑宾馆”位于长春人民大街125号,2013年6月,去长白山开笔会,途经长春时。在这里很多老朋友相见,我和蒋蓝在金华分手后,又一次在北方相会,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中。
我收藏有几十把小梳子,没有值钱的,都是酒店一次性的小物品。我看重小梳子,它记载我的旅行,不起眼的小梳子,深藏一段故事,可以编写一本踪迹史录。
今后的旅程,还在前方等待,我不会放弃每一次机会,收藏小梳子,它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和怀念。
我的目光变成一条鱼
清晨拉开窗帘,窗外下着细雨,楼前的甬路,被雨淋得湿漉漉的,泛出一片亮色。灰蒙蒙的天空,阴湿的雨天,让人的心浮出忧伤。
这样的天气,使我很快地进入角色。早饭后我去阳台上,角落里竖着三把伞,我要选择其中的一把,和它一起在雨中散步。绿白相间的伞,适合在细雨中,那把蓝布伞,适应在大雨中使用。时间越久,蓝色渗出的美更有味道。在伞下听雨敲打,将人的思绪带到多少年前的事情。我选择这把伞,具有浪漫色彩,在轻缓的雨中,走在街头,一个人犹如走上舞台,变成剧中的角色。
走出楼道口,撑开伞,我向上望去,一条绿色,一条白色,它们间隔有致,给人不仅有躲雨的功能,多了一份温情。雨不大落在伞顶,我们一起开始,融入早晨的街头。出了小区的大门,摆小吃摊的店主,早支开移动布篷,下面几张白色的桌椅前,已经有客人在吃早餐。渤海九路我走了二十多年,清楚地记得每一处地方。来到路口交叉处,马路对面的售货车,专门售“绿洲”面包,还有一系列糕点。店主是一个稍胖的女人,挡窗板关闭,可能是雨天的关系,每天这个时候,她早就开门营业。不远处是一个短工点,二十几个人,或坐在马路牙子上,在人行道上铺一张废报纸,几个人围在一起打扑克。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乱摆在路边。这伙人中,其中有一个人,引起我的注意,矮墩墩的个子,敞开衣服,袒露结实的腹肌。我每天要小心穿越这伙人中,彼此不说一句话,但都熟悉对方的样子。今天早上下雨,变成他们的休息日,我经过这里,人行道显得空荡,只有我举伞走过。
雨不大不小,吹来的小风,卷来湿润的凉意。故事不能总是平缓,一个调子往前,要有节外生枝的情结发生。雨中我的邻居,他什么雨具没有用,牵着他家的小黄狗,从远处走来。雨将他们淋湿,我们打招呼,匆匆地擦肩而过。
我要避开地上积的雨水,目光被打湿,心中长出苔藓一般的感伤,寻常的日子中,只有这位天上来客带着纯净,无一点杂念,送来贴近的关照。
我将手伸出伞外,感受细碎的雨,积落掌心的感觉,雨清除杂念。我的目光落在掌中的水洼中,如同一只自由的鱼儿,享受雨的单纯带给的快乐。
夏日雨中的清晨,我在一把伞下,看到自己的目光变成游动的鱼儿。
责任编辑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