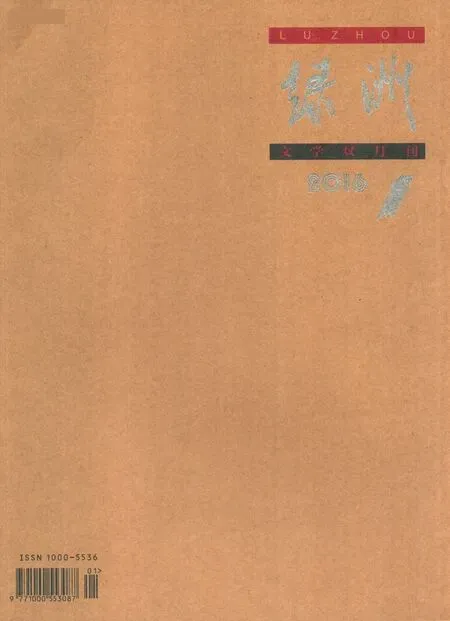秋天的村庄
王新军
秋天的村庄
王新军
秋日清晨,鸟鸣声在果园里左冲右突,响成一片,阳光从柴墙中腰处穿过树枝的缝隙射进来,瞬间将浓雾般的空气戳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窟窿,它们像一根根粗细均匀的柱子,排列整齐地旋转着,在他眼前轻浮地飘动。最近一些日子,这种相同的景况曾在他眼前出现过好多次,不过它显得不那么令人厌恶,反而给他迷蒙而深刻的印象,有时候照亮整个院子的,也只是一支从远处投来的狭长的光柱,就像高处有一个洞,五颜六色的光亮从那里泻下来,把他开着两株大丽花的院子妆扮得像个花园。每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都像小鸡看到一条胖虫子一样感到惊奇,他想把这个奇迹告诉远在北京城里的孙子,他想告诉他出现在爷爷眼前的这个花园他是熟悉的,但他脑子里有那么一块却迟滞着一点也辨不出它的来龙去脉。可当他透过光柱中若隐若现的五色花影向它们深处看去的时候,目光在一片迷蒙掠过之后,脑海里便会出现一大片闪烁的微光,他似乎熟悉那个地方,却不知道它确切是哪里,那个无边的花园会很快变成一个深渊的底部,继而由模糊而黑暗。每当从这种虚幻的情景中挣扎出来的时候,他都要在心里默默念叨,好让自己安静一会儿,他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老了,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否则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传说中应该是在另一个世界的真景花园哩。
果园里靠东的一行杏树被完全照亮了,翠绿的叶子上晃动着明亮的反光。立在杏树底下,园子里湿漉漉的空气带着沁心的湿意进入胸腔,使他的身体蓦地生出一些着凉的感觉,他赶紧把披在身上的外套褂子裹了裹,这时候他才发现,两只立在杂草丛中的大脚已经被露水打了个半湿。入秋之后,天气的变化立刻就加快了,首先是露水厚了,几乎到了拌脚即湿的程度。他有早起的习惯,几十年了,他一直用这种勤劳的习惯打理着一家人的日月。现在的他生计无忧,不缺衣不少食,是村子里公认的最幸福的人。
杏子已经熟完了,树梢上仅剩的几颗也在这几天悄然落了地,最靠近地面枝条上晚熟的也已经撑持不住,在鸟儿上窜下跳的嬉闹中无奈何地跌离枝头,地上到处是腐烂的杏子。那一排李子树上的李子也已经着色发红,梢头上早熟的已经开始有了将要跌落的迹象。那几棵苹果树上枝条被果子压弯了,他不得不用木棍一根根支撑着。那一树桃子把枝条都挂累了,中秋节前后是它们成熟的最佳时间。园子里的梨树有两种,一种鲜吃特别甜,一种耐储存的能放到第二年春天。他在一片空地上停下来,听着鸟鸣,嗅着果园里丰富的味道,心里突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恍惚中她又来到了他的身边,老婆子,你看看,这一树一树的果子……你看一看它们……李子多红呵,桃子快赶上苹果大小了……杏子嘛,都已经熟光了……他的这番自言自语,分明是说给老伴儿听的,她已经去世五年了,但他却觉得她从来不曾离开自己半步。他自然知道老伴早已过世,但他依然要不经意地这么说,仿佛老伴就在他旁边。他伸手摸了摸腰里,手机就在那里,似乎已经被他的身体焐热了,他从皮套里取出它的时候,竟然有点怕它着凉似的舍不得拿出来。他在心里把自己嘲笑了一下,这么个塑料疙瘩,又不是细皮嫩肉的娃娃。他拿着手机眼睛盯着屏幕摆弄了一阵,又重新把它放进了拴在腰上的皮套里。
时间还早——刚刚七点,这时候打电话过去,那边能不能接到还是个问题,接到了,十有八九也只能是匆匆忙忙说上两句,然后就是——没事我挂了呵——他把目光从脚下移开,又在果树上依次扫了一番,那些光鲜的果子全部张嘴向他笑着。他在园子里慢慢绕了一圈,这时候园子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鸟儿的啁啾听上去也是水汪汪的,一切与昨天并无什么区别,但与昨天又仿佛完全两样,每一只果子分明都长大了一圈。他在一棵杏树下站住了,这是一棵李广杏,在树腰的地方,一根没被剪掉的偏条上还有一只杏子,好像是被有意遗忘在那里了。绿叶掩映下的它居然顽强地撑到了现在。这让他感到无比惊奇,他下意识地伸手拿出了手机,儿子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挂在树上自己长熟之后又被露水一激,摘下来丢进嘴里一咬,嘻——那味道真是透进骨头的美,他的这个习惯未必就不会完全地传给他的孙子。
他把手机拿在手上,忽然又僵在了那里,现在是孙子吃完早点要去上补习班的时间,孙子马上要进高中了,据说又到了什么关键期。因为这一个一个的关键期,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对孙子说,爷爷想你了。孙子在电话里说他马上自拍一张发过来让他看。但是他始终没有收到,孙子在电话那头一个劲数落他说,爷爷你怎么这么笨呀,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的这种手机根本收不到彩信。当他把接收不到彩信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手机的无能时,孙子在那边埋怨他说,爷爷,这年代了你还用那种手机呀,你也太噢特了吧。他心里美不滋滋地说,我这个噢特手机,听电话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很好使唤哩。孙子在那边说,爷爷——什么噢特手机,我说的是英文,真悲催。孙子这么说,他就完全听不懂了。听不懂他依然觉得十分开心,只要能听到孙子的声音,他觉得他的日子就是有滋有味的。
他拿着手机翻了一阵,儿子的号,大女儿的号,小女儿的号,两个女婿的号,孙子的号,两个外孙女的号……一组组数字依次在眼前闪烁,他手机上的电话号码并不多,联系人一栏也一满是用数字标的,加上村医张大夫,乡卫生院胡院长,总共也不到二十个,村里左邻右舍的电话,他大多记在了脑子里,要找谁,默默想一会就能准确无误地拨过去。阳光渐渐亮起来了,他踌躇着一时拿不定主意应该停在哪个号码上,然后按下绿键。多年来他一直遵从着没事不给孩子们打电话这个他给自己和老伴儿立下的规矩。放手让娃娃们自己闯去——这是他在儿女们还小的时候就一直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老伴几乎从来没有反对过他。他们夫妇打理着自己的十三亩地和三亩果园,儿女们也个个靠着父母的撑持,闯出了自己不同的人生。大女儿师范上出来留在酒泉城里一所小学当了老师,两年后嫁给了一个戴眼镜的同事,在酒泉城里安了家。小女儿上的是省城兰州的工业学校,学的是财会专业,人还没毕业,就被一家银行招走了,现在听说已经是个什么部门经理了。儿子年龄最小,却考了个远在南方的一所大学,专业是计算机工程啥的,他始终没搞懂。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儿子,儿子嫌解释起来太麻烦,就直接了当地对他说,爹,我这个专业,说白了就是整天玩电脑的。儿子的这句话让他暗暗思忖了好些时日,整天玩电脑,听起来这好像不是个什么正经的好营生。上一趟大学,四年时间学个玩电脑……他心里总觉得不是个事。他怕儿子走了歪道,就分别在电话中向两个听话的女儿求证,结果当然是被她们好一顿数落。尤其是大女儿,仿佛他就是她班上一个脑子不大够用的小学生,那口气已经近似呵斥了。后来碰到村小学的大鼻子刘校长,他才确认儿子这个整天玩电脑的专业,不是什么歪门邪道。那都是十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乡里还没多少人用手机,更没有人用电脑。现在想起来,他都觉得当时的自己很落后。为这事,老伴也曾暗暗取笑他,说他是瞎子摸象,还说他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但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儿女们的事,做父母的始终不能装糊涂,哪怕是不懂,这个淡心也还是要操的。放开手脚让孩子们干自己的事业,不等于放任不管。
儿子在大学里摆弄了几年电脑,毕业后闯到了北京。说是在北京一个叫中关村的村子里和几个年轻人合伙开发什么软件项目。儿子还是一如既往地怕给文盲父亲作解释,临完了这样对他说,总之还是整天整天一伙人凑在一起玩电脑。他放下电话想,儿子这会出息了,独个玩着不过瘾,拉一伙人凑在一起玩上了。
这么着,三个孩子都陆续在外面成家立业了,当然,他老两口也是一天一天见老了。老伴去世的那一年还不满六十五,这在村里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岁数,说病就病了,病了三个月,说走就走了。儿女们哀伤地聚集在躺着母亲遗体灵床四周的那一刻,好像他们的母亲是独自一个人离开了,把幼小的他们丢在了家里——那一刻,他感觉自己也已经离开他们了。老伴去世之前和之后,他在三个儿女跟前都住过些日子,看着孩子们的日子又开心又忙碌地过着,他就放心了。但他始终认为这样的日子只属于儿女们,所以当他们执意挽留父母的时候,他们老两口总是会在计划离开之前提前离开。老伴过世这几年,他甚至再也不愿离开村子半步了。儿子的电脑玩出了名堂,在北京买了大房子,一定要接他去享福,但他没有答应。儿子转而让两个姐姐做父亲的工作,他却向她们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劝他离开村子,就不要再来电话——他将把手机扔到村庄南面的疏勒河里去。这对儿女们的确是一种震慑,他们果然退缩了。儿子又借口孙子想爷爷,让孩子与他通话,他看出了儿子的伎俩,就大声对儿子的儿子诉苦说,北京那么高的楼,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路,那么多的车,爷爷脸盆大的字不认识一斗,去北京吓都吓死了,你爸说是让我去享福,其实分明是想要我这条老命哩么。此言一出,儿女们再也不提接他进城享福的事了,他的日子这才算消闲下来。
他在园子里转悠着,太阳升高了,偶尔有熟透的果子从枝头上嗵——地跌下来,跌到半树腰里,又砸下了另外的几个,于是草地上有时候会嗵——嗵——嗵——一连响上三五声,这种景况他已经见怪不怪了,果子熟了总是要从枝头上掉下来的。
从杏子开始熟的时候起,他就开始收集起来晾杏干。杏子熟的时候正是学校放假的时候,看着一树树黄灿灿的杏子,他就开始坐在树下给儿子女儿打电话,先是问他们最近工作忙不忙,然后就是一阵家长里短,最后的落脚点,基本是不变的:有没有时间……带孩子回来……杏子熟了……
但得到的回答全是否定的,为吃几个杏子大老远的回一趟老家?孩子的英语班上不上了?钢琴课上不上了?还有奥数呢……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不敢说自己想孙子想孙女了,只要他这话一出口,儿女们马上就会说:想你就到城里来住呀,城里房子早就给你备好着呢。
唉,咋说哩,不是他不喜欢城市,是他习惯不了它呀。在城里住上几天,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好像生病了一样。可一旦回到了他的这座庄户院里,他的身体立刻就恢复了那种清爽的感觉。他把这种奇怪的现象归结为接地气,他像一棵老树一样,离开了这块土临近河水的坷垃地就要干枯。他不住城里,儿女们也不便强行留他,只是一再交代,让他但凡有个头疼脑热,必须马上去村卫生室找张大夫。而张大夫那里,儿女们也有许诺——他们的父亲一旦有了村卫生室看不准的病,马上送乡里送县里,所有费用由他们承担,包括张大夫本人的劳务费。后来儿女们怕他有病暗暗扛着,就规定即使没有什么毛病,他也必须一月找一次张大夫,做一次常规检查。有时候他到了时间没有去,子女们不论哪一个就会马上把电话打过来,他们会像教育他们的孩子一样用电话把他打发过去。如果这样实在不行,他们还有办法——他们会用电话把张大夫请过来。他知道张大夫出珍一次要收三十块钱的出珍费,虽然这一切都由子女们大包大揽了,用不着他去操心,但他还是觉得这个钱掏得有些冤枉。所以这样一来,他只能是乖乖地按时去找胖乎乎的村医张大夫。每次为他量血压测体温的时候,生着一脸短小胡茬的张大夫嘴里都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敬德叔唉,老人能活成你这个样子,也算把世上的福给享尽喽。时间久了,这话就在村邻中间传开了——他的日子,自然是幸福的了。
晒好的杏干他已经用三个纸箱子装好了,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被邮到城里,邮到孙子孙女手里。当他们吃着那金黄的带着太阳和老家味道的杏干的时候,也会看到他们的爷爷苍老然而甜蜜的笑容吧。
他把那只杏子摘下来,他突然觉得还没长大的儿子就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他下意识地将那只金黄色的李广杏回身递过去,他的身后除了果树和地上的杂草什么也没有,甚至鸟叫声也在刹那间消失了,他有些失望地将杏子装进褂子口袋,又小心翼翼地捋了捋,生怕把它弄坏了。
阳光渐渐升高的时候,他来到了村街上,这个曾经鸡鸣狗叫娃娃闹的大村子现在已经完全变了,安静得很,村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影。一些人外出了,一些人上地了,娃娃们上学去了——小学全集中到了乡里,初中高中集中到了县城。虽然上大学的娃儿寥寥无几,但只要初中高中上出来,基本也都不回村里来了。村里四十岁以下的人没有几个,年轻人不愿意回来,甚至中年人,只要手上稍稍有点儿能耐,譬如能垒个砖头,能抹个墙面,能刷个房子修个围墙打个地坪,会开汽车能修摩托,都到城里谋日月去了。他们说种地只能养活个人,挖光阴不行——不能叫人富。要想过上好日子,光守着一点土地哪里能行哩。他却并不这样认为,一个农民不守着土地,不侍候土地,干那些乱七八糟的活路,咋能算是正道哩。但时势并不因为他的这种认识而改变,村庄的寂寥和冷清确乎在一日一日加剧着。现在的人对土地没有感情了,他也只能这样感叹。
几天前的一个早上,年轻的大学生村官——支书毛成带着一班人又来找他,当然还是谈他那十三亩地的事,人家已经谈妥村里好多户了,村上成立的合作社要把村西所有的耕地转租下来,要搞规模种植。他们甚至鼓动他说,像他这样的,完全可以把庄子连同耕地一次性出售或者出租,只管住在城里按时收银子就是了,村上的合作社会把租金按时打到他卡上的。这在毛成他们青年人看来十分清爽的事,在他这里却十分纠结十分苦闷。他名下的十三亩地,这些年一直由他地连地的邻居黄海种着。当然这也是孩子们的主意,按他的想法他是不会这么办的,自己虽然种不动了,但他完全可以雇人来照看。再者说了,他可以种些容易经管的作物呀。但孩子们自有孩子们的一套办法,最终他只能妥协。结果自然是他可以继续按自己的意愿住在村里养老,但地必须全部出租。好在三亩果园的日常打理也够他一个老汉消遣的了。
黄海一直有将他的十三亩地一次性买断的打算,找他说过几次,都被他断然拒绝了。去年清明的时候,黄海暗中和回乡上坟的大女儿联系上了,之后就一直在电话中商量着这件事。子女们商量好后试探他的口风,他愤然放出了一句狠话——要卖地,除非我死了。一个农民,好容易有了自己的土地,刚刚搂在怀里焐热乎,又要卖掉……他如割肉剜心一般难忍,却又有种实实在在的无奈。他愤怒着自己渐渐逼近的衰老,忍受着内心渐渐因为不舍而酿造着的不幸。做一个没有了土地的农民,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全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呵。
他很想在村街上碰到黄海,他想和他唠扯唠扯,他还是愿意自己的地继续由黄海种着的,毕竟黄海是本村知根知底的人,也是一把种地的好手。虽然是近五十的人了,但作为一个农民,这才是刚刚过了毛躁之年、刚刚摸透了地的脾性、刚刚懂得了如何务作庄稼的好时候,把地交到这样的人手里他才放心。他已经想好了,万一要是黄海打起退堂鼓,他宁可把一亩地五百元的租金降一降。
黄海家带门楼的街门紧闭着,门口的皮卡车也不在,看样子是上地了。长着玉米和食葵的地上也没有见到黄海的身影,这不免让来到地上的他有些失望。他抄几条小路,用一个上午的时间绕着圈子,用目光把村里所有长着庄稼的土地都抚摸了一遍。偶尔看见村人在绿色的作物间劳作,他也远远避开,不与之搭话。面对蓬勃的田野,他像一个无力挥刀冲杀的老军人面对旌旗猎猎的战场,除了黯然神伤什么都没有了。他觉得他脚下的每一块地上都有一些丝状的东西,它们潜伏在被青绿覆盖的地面上,只要他经过,它们就会像聚集了魔力精灵,伸出看不见的手绊住他的身体,那情状又仿佛他身上刹那间生出了无数根须,要扑过去扎进那一片片香酥的泥土。
午睡之后,他离开一堂两厢两挂角的院落,从前院的角屋旁门来到后院里。后院的鸡舍和羊圈都是空的,事实上这里有十几只鸡,再有八九只羊才是对的,但是没有了,整个前院后院加起来,出气的只有他一个年过七十的孤身老汉。他来到农具库房里,与鸡舍羊圈相比,这间库房是不算大的,也就五步见方。老犁头、新式犁、耙子、木锨、镢头、榔头、锯子、棕绳……一样样摆放在靠墙的矮木架上,在渺茫中满含希望地等待着,他看着它们,像注视着一排解甲归田的老兵。房梁上是一个独木吊架,五六把镰刀挂在那里,除了一把他在打理园子的时候用过之外,另外的几把刃口上已经有了一层锈迹,但拂去灰尘之后,镰柄依然是光滑油亮的。这些都是他的伙伴,他的孩子,他的作品,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曾经在他的手里被赋予了高贵的功用。但是他和它们,现在被时间搁置起来了。还有无数的它们,被忽略在了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他把一只小木凳放到屋子中央,用赞许的目光欣赏了一阵自己的作品之后,默默地摸出腰里的手机,拨弄起按键来。手机草稿箱里储存着的一行字,不,是几个字,是他早就琢磨好了的一句话里的几个字——孩子们,我走了,祝你们一切安好!这句话是他从一个外国电视剧中学来的,这个电视剧临近午夜才开播,他感觉好像几个月才播完。后来又在另一个台重播,他又看了一遍。看完了,他便记住了垂暮之年的主人公在决定离开这个世界时,留给后人的这句短短的遗言。他觉得这样的遗言才是最完美的遗言,多一个字就嫌多了,少一个字又欠那么一点。从入夏他就琢磨着这句话了,现在“孩子们,我走了,祝你们”这几个字已经牢牢地嵌在了手机屏幕中,只要再嵌入“一切安好”这四个字,就一切完满了。他知道他们会在某个时刻完整地看到这句话,并从中得知一场准备已久的离别。
几天之后,支书毛成动员拿土地加入合作社的事他顺从地接受了,在村委会毛成那间挂满各种规划图的办公室里,他很快就完成了签字确认的所有手续,之后他便因为不用做更多的解释感到如释重负。毛成这样的年轻人已经不像他一样抱着土地去死下力气了,他们对土地也是深爱着的,但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他常到田间地头对大伙说:要让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是另一种解放。这话把好多人说动了,连一向十分固执的黄海也转过弯来了,同意拿出自己的土地加入合作社,并承担合作社的一部分工作。据说要不了一两年工夫,像四轮车这样简单的农用机械,几乎就要被淘汰了,现在有更加先进的农用机械和生产设备。从种到收,你只管开动机器就行了,黄海兴奋地说。前些日子黄海他们一批种地能手,跟毛成去酒泉参加了一个大型农机订货会,黄海订下了一台大型综合耕平整地一体机,只要更换附属配件,可以完成从播种收获到翻地平整的所有田间作业,全村的地也支不住它干。黄海说,现在种地一家一户的小打小闹已经噢特了,没有规模形不成气候,就等于把好端端的土地给日蹋了。他知道黄海已经接受了大学生支书毛成的那一套思想,他们甚至筹划在乡集镇的一块空地上盖几栋农民公寓,让村人们把生产和生活区分开,这样既可以让农民照看到自己的土地,做到就近务工,又可以让他们下班之后能过上城里人一样舒适的生活。这些新道道都是毛成提出来的,据说已经有不少人家响应了。中秋还没过哩,他们已经在为新一年盘算着了。他蓦然觉得有了毛成们的脑袋瓜,有了黄海们的干劲,土地算是找对自己的主人了,跟着他们,前景似乎要更加光明一些。他的身体已经走进了不被别人理解、连他自己也不大理解的困境,他被自己的衰老悄悄折磨着,这种无形的烦恼像潮水一般在他身体里涌动,似乎要淹没他眼前的世界了。他时刻感到眩惑,这是一种比衰老更深的病,是身体上的,却在向身体最深处郁结。
人老觉少,失眠让他更加经常地去光顾张大夫的卫生室。那种可以让人安然入睡的白色药片,每一次张大夫都不会多给他——不超过六片,而且一再地叮嘱他不能多吃,一天一片,最多不能超过两片,吃多了一觉睡过去就再也醒不来了。每一次,他都会呵呵笑着说,我咋会不知道哩。
一连好些日子,他都沉溺在一种平静的恍惚中,有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竟然发现自己是在老房里睡了一夜。老房是早在老伴过世之前一个有闫月的夏天打好的,三个匠人叮叮咣咣忙了九天,两口散发着松木浓香的老房就摆在了院子里。两年后他又请了匠人把它们画好了……
今年入夏的时候,他亲自为留给自己的那口老房糊好了里衬,又在里衬上裱了一层吉祥的黄绫。一切收拾停当之后,他躺在里面试了又试,直到自己认为妥帖了为止。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曾经俯视着老房新鲜的黄绫里衬,想像着在这个浅浅的深渊里他将度过怎样漫长的岁月。他把它始终同那个在他脑海里兀自出现的花园联系在一起,可是每一次它的出现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新内容。他暗中惊叹自己竟能这样随心所欲地看到眼前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高秋热地,土地绵软丰腴,这样的日子里,他的两眼时常会无端地噙满泪水,嘴里也会发出类似身处寒风而不能自禁的啵——啵——声。他沉溺在一种恬静的恐惧当中了,他在准备着自己的死亡。
一口气派的棺木、一瓶积攒下来的白色药片、一身老伴去世前两年便为他置办好的青缎面老衣、一座寂静但并不破败的老屋、一屋解甲的农具……给孙子孙女备好的今年的新鲜的杏干已经寄出……他身边的一切使得模糊的离别被清晰地具体化了,他感到眼前晃动着他将要拥抱的冰冷的幸福。
责任编辑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