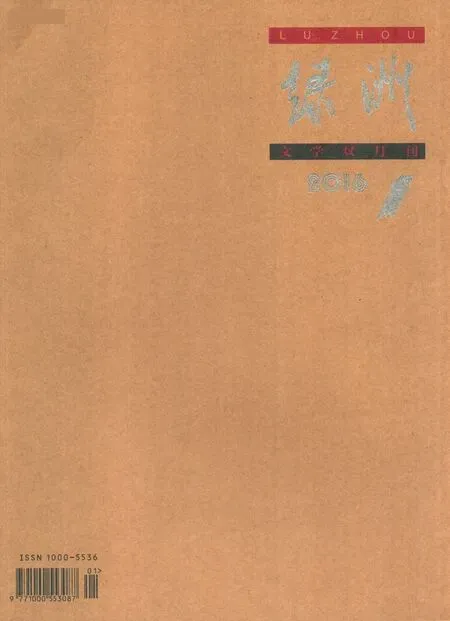与电影有关
尉然
与电影有关
尉然
以我当年的年龄,好多事我还搞不太明白。
当年我六岁。
比方说,我搞不明白三叔每逢看电影为什么总要拉上我。我们家刚吃完晚饭,三叔就兴冲冲地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高声喊道:嫂子,小胖在家吗?我领他看电影去!征得我父母同意后,三叔就亲热地拉起我的手走出了院门。不过,一走出院门,三叔就把我的手撇开了。他的脚底下好像安装了弹簧,在我面前一跳一跳的,有时能够到头上的树叶。如果他够到的是泡桐树叶,他就手执肥大的泡桐叶,屁股扭来扭去地跳起一种奇怪的摇摆舞;如果他够到的是柳树叶,他就把柳叶嵌进两片嘴唇之间,吹出欢快的曲子。
这样的夜晚,三叔总是穿得很好。那是他最新的衣裳,平时舍不得穿,而且一定是刚刚洗过的。他在我面前跳来扭去,清新的肥皂味飘荡开来,在我的鼻孔里若隐若现。三叔的白球鞋用粉笔擦过,白得耀眼;三叔的头发拿梳子蘸水抿过,看上去油光水滑。那个年代,被视为正常的头发都是乱糟糟的,像三叔这种梳理得油光水滑的头发经常被讥讽为“牛舔头”。
在村街上拐了几个弯,三叔领我来到林美玉家门前。
小胖,过来。三叔回头喊我。
似乎直到这时三叔才想起他身后还有一个小尾巴。他蹲在我面前,叮嘱我,一会儿见了美玉,你一定要笑。我点点头。三叔说,你笑一个让我瞧瞧。我咧了咧嘴。三叔说不行,嘴咧得不够宽,要这样才对。三叔说着,两只手揪住我的腮帮子把我的嘴角往两边扯了扯。三叔又叮嘱我,她要是不跟咱们一块去看电影,你就哭。我又点了点头。三叔说,你哭一个让我瞧瞧。我又咧了咧嘴。这一回三叔更不满意了,他板起面孔教训我,笨蛋!你这算是笑还是哭啊?要真哭,最好要哭出蛤蟆尿来。蛤蟆尿是啥,知道吗?我说知道,蛤蟆尿就是眼泪。可是,我哭不出来。三叔说哭不出来那是你没有切身感受,说着在我屁股上拧了一把,疼得我哇哇哭出了声。三叔这才露出了笑容,说这就对了嘛。记住喽,美玉要是不答应跟咱们一块去看电影,你就这样哭。三叔拿巴掌在我脸上抹了一把,替我擦掉眼泪,然后往我手心里塞了一颗水果糖。
得到水果糖以后,我立马就不哭了。
三叔抱起我,站在林美玉家门前高声喊叫起来。
美玉!
林美玉!
林美玉同志!
三叔的喊声一声高过一声,一声尖厉过一声,兴奋得就好像他妈的一只刚下过蛋的母鸡。我想,他是故意让四邻都听见,这样一来林美玉就不好在家里装聋作哑了。
但林美玉仍旧没有被三叔喊出来,被喊出来的是刘翠兰。刘翠兰是林美玉的娘。刘翠兰蓬乱的头发让夕阳照耀得似乎透亮,跳动着虚假的金色光芒,她用手在头上抹拉了一把,那些金色的光芒立即就消失了。她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了。笑容是她从屋里带出来的,见了三叔以后她的笑容呱嗒就掉到了地上,脸色变得很难看。
刘翠兰警惕地问,王建国,你找美玉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到黄泛区农场看电影呗。三叔嘻嘻笑着说,是一部新片,《于无声处》。
美玉不在家。刘翠兰没好气地说。
不过,随后出现的情景立即证明刘翠兰是在撒谎。刘翠兰的话音还没落,林美玉就从屋里袅袅婷婷地走了出来。与其说她是走出来的,不如说她是扭出来的,按现在的话说,她走路的姿势特别性感。林美玉大概正在梳头,一把小巧精致的木梳子卡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又黑又长,又直又顺溜,闪烁着青春的光泽。和林美玉的头发比起来,她娘刘翠兰的头发简直只能称为一团秋后枯萎的干草。
谁找我啊?林美玉边往门前走边问。
是我。三叔讨好地对林美玉说。还有小胖。小胖最喜欢美玉姑姑了,对不对小胖?
三叔这么说着,笑得两边的腮帮子上绽出了一个大大的括号。同时,三叔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瞥向我。我记起了三叔之前的叮嘱,赶紧朝林美玉使劲傻笑。
美玉姑姑,跟我一块看电影去吧。我无耻地说。
林美玉伸出两个指头,轻轻捏了捏我的脸,说,对不起小胖,姑姑今天有事,不能去看电影哟。
林美玉的手指头凉丝丝的,就好像夏夜里涂抹的清凉油;林美玉的话音软绵绵的,犹如唱歌般好听。我心里十分舒坦,本来应该冲她笑笑的,但按照三叔事先设计好的程序,我必须哭。我酝酿了一会儿情绪,突然放声哭起来。
林美玉立即就手足无措起来了。
王建国,你赶紧劝劝小胖呀。林美玉边说边搓着两只手,看起来像是也要哭出来的样子。
三叔幸灾乐祸地说,这个我可劝不住。这孩子啊,脾气倔着哩。美玉,你瞅瞅这孩子多喜欢你呀,你就答应跟他去看电影吧。
林美玉蹙起眉头想了想,哄我说,好了好了小胖,咱不哭了,姑姑答应陪你去看电影,啊?
如今看来,这些当然都是三叔玩弄的鬼把戏。如此简单的鬼把戏,一眼就能识破,但用在林美玉身上却屡试不爽。我不知道当年林美玉的心思,她是故意装糊涂,还是半推半就?反正林美玉乖乖地跟着我们去看电影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黄泛区农场看的电影不是《于无声处》,而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由于三叔和林美玉走路磨磨蹭蹭的,还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说话,当我们走到农场的老电影院时,好位置已经被人家占完了。所谓的老电影院,是相对于后来新建的电影院而言的,其实老电影院根本算不上一个正经电影院,只是一个被踩实的方方正正的场地,场地的一边竖着两根水泥电线杆子,银幕就挂在两根电线杆子之间。好位置占完了,我们只好站在银幕的背后观看。在银幕背后看有些别扭,上面的人的左右手和左右脚都是反着的,似乎电影里的人都是左撇子。我们刚站定,电影就开始放映了。当银幕上出现电影名称时,我听见林美玉轻轻地呀了一声。
呀,王建国,你不是说《于无声处》吗?怎么成了《落角的忘遗情爱被》?咦,这电影名字咋这么拗口啊?
三叔说,你念颠倒了。
林美玉不服地说,不是像书上一样从左往右念吗?
因为咱们站在银幕的背面,所以要从右往左念。你再颠倒过来念一遍试试。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好你个王建国!你是不是故意的?
林美玉一边埋怨着,一边拿手捅了一下三叔的腰。三叔好像被捅到了痒处,弓了一下腰,乐呵呵地笑起来。
三叔说,嘿嘿嘿,这个爱情比那个什么破声处好看。往下看吧,保证你喜欢。
林美玉似乎害羞了。黑暗里,我没看见她的脸红,只看见她把双手捂在了脸上,一扭身背对着三叔,嘴里还咕哝了一句。我没听见她咕哝的是什么,但我猜,不是“讨厌”就是“你真坏”,好像漂亮姑娘都喜欢这么说。我站在他们两个前面,心里感到非常失落,不管是他妈的《于无声处》,还是他妈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都不感兴趣。我对一切彩色故事片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彩色战斗片,比如《渡江侦察记》什么的。我感到百无聊赖,一会儿挠头皮,一会儿拧耳朵,眼睛有一搭无一搭地瞄着银幕。在我眼里,银幕上的故事絮絮叨叨,无聊透顶,画面忽儿清晰,忽儿模糊。我靠在三叔的大腿上,打着一连串的哈欠,眼皮涩得要命。正要入睡时,突然感到三叔浑身哆嗦起来,就像拖拉机被发动起来一样。我仰起脸,发现三叔神色悲戚,银幕上的反光在他的脸上跳跃着,两只眼睛里噙满亮晶晶的泪花。再看林美玉,她已经是满脸明晃晃的泪痕了,甚至有一颗泪珠从她的下巴上掉下来,落进了我的嘴里。她的眼泪是咸的。要搁平时我早呸的一声吐掉了,但那天晚上我悄悄把那颗泪咽了下去,我怕吐掉会惊到他们。我看了一眼银幕,发现电影里的人也在哭。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哭。
反正我不喜欢哭的电影。我嫌哭的电影太磨叽。
我叹了一口气,蹲了下去,捡起一根小棍儿在地上乱画。哭就让他们哭吧,我才懒得搭理他们呢。蹲了一会儿,腿麻了,我想起来活动活动,不料刚起身脑袋就碰到什么东西。定眼一看,原来是三叔和林美玉握在一起的手。这两个没出息的,他们一边哭还一边偷偷地把手握在了一起。见我发现,他们迅速把手撒开了。
后来我就没有心思再看电影,也没有心思蹲在地上乱画了,我拿眼睛的余光暗中观察着他们的手,我料到它们还会有什么举动。果然,过了一会儿,三叔的手悄悄向林美玉的手靠拢过去,试探地碰了一下。林美玉的手似乎没有动弹。大约三叔以为没动弹就等于默许,他的手胆子大起来,想重新握住林美玉的手。但当三叔的手犹豫着要抓林美玉的手时,林美玉的手正巧抬起来,把垂在眼前的一绺头发拢到了耳后。三叔的手没有抓到林美玉的手,有些泄气了,无力地耷拉下来。不过,积蓄了一阵勇气后,三叔的手不再犹豫了,这一回它简直是直接扑了上去的。但最终它还是扑空了,林美玉顺势把手抬了起来,把两条胳膊抱在了胸前。三叔吃惊地侧过脸看着林美玉。不过看也没用了,她的手现在正好处于银幕的反光里,位于明处,三叔也不好在众目睽睽之下下手了。连我这个小孩子也能看出来,他们两个的手一个捉一个躲的,其实是在玩一种类似于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我发现林美玉瞟了一眼三叔,用一只手掩住嘴,偷笑。
黄泛区农场距离我们王皮溜村只有三公里。但因为黄泛区是国营农场,所以新电影片子总是他们那儿先放映,等一个月后轮到我们农村放映时,那些所谓的新片已经变成老掉牙的老片子了。先睹为快,因此我们情愿经常跑上三公里去农场看,也不愿在家等着,尤其是年轻人和孩子们。
三叔是其中积极者之一。
当然了,三叔看电影不仅仅是为了看电影。看电影只是一个幌子。另外一个幌子,就是我。三叔以这两个幌子邀请林美玉,说实话,林美玉是难以招架和拒绝的。因为林美玉不但喜欢村里的小孩子,而且更喜欢看电影。
因此三叔屡屡得逞。
和林美玉一起看过电影的第二天,三叔的心情总是无比愉快,脸色红润,印堂发亮,小分头更是梳理得井井有条。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三叔不但送给我水果糖,还从庄稼地里捉蛐蛐送给我,并且用高粱篾子给我编织了一个蛐蛐笼子。我知道,他这是在奖赏我哩。
三叔之所以奖赏我,不仅是因为我帮他邀请到了林美玉,更主要是因为我知道怎么配合他们。只要是战斗片,我就会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银幕,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甚至人物的细微表情和动作。三叔和林美玉知道,这种时候我就像插在田野里的稻草人一样,根本就不会挪窝,不用担心我会走丢了。他们放心地趁机溜掉,然后再在电影结束以前溜回来,以造成他们始终在我身边的假象。虽然我没有跟踪过他们,但凭嗅觉我也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小时候我的嗅觉特别灵敏,我娘经常说我的“鼻子比狗鼻子还尖”。他们去的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三八河边,一个是园艺场的苹果园。因为我能闻到他们身上带回来的水腥味和苹果花的芳香。我没有揭穿他们,装作浑然不知,是想给他们留点面子。让我搞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宁愿看磨磨叽叽的故事片,而不喜欢看激烈的战斗片呢?
后来我就此问过我三叔。
三叔的回答让我非常失望。他首先指出我的问题是一个操蛋的问题,然后,他弓起食指在我的脑门上弹了一下。
小屁孩儿,长大以后你就明白了。三叔弹了我一下脑门以后,来了这么一句。
大约有半年左右,每逢黄泛区农场放电影,三叔总能邀请到林美玉。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说说笑笑,亲密无比,但白天在村子里两个人相遇时,只要有外人在场,他们基本上是不说话的,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他们只是心照不宣地交流一下眼神。那段时间,三叔无论是走路还是干活儿,都唱着歌。三叔五音不全,而且老是跑调儿,他一唱歌村里人就无比愤怒,就连狗都绕着他走。但三叔依然我行我素。什么叫得意忘形?这就叫得意忘形。
不过,得意忘形了一段时间以后,三叔就开始吃闭门羹了。
美玉!
林美玉!
林美玉同志!
林美玉的娘刘翠兰走出来。
美玉不在家!刘翠兰没好气地说。
开始三叔并不在意,他依旧呵呵笑着,踮起脚尖往里瞅。可是,瞅来瞅去的,林美玉却始终没有走出来。刘翠兰剜了三叔一眼,哐当就把院门关上了,门板差点儿撞到三叔的鼻尖。三叔脸上的笑容噼哩啪啦地剥落了一地,露出难堪的表情,双眼失神地盯着门板瞅了一会儿,挺直的腰身渐渐萎缩下去了。
三叔呆了一会儿,横起一根食指在他自己的鼻子底下像拉锯似的搓了搓,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说走吧,然后独自离开。三叔走得飞快,我跑步才能追上他。
等等我,三叔。我在他身后喊。
三叔没有停步。
还给你糖。我又喊道。
这一回三叔的脚步顿了一下,但接着他走得就更快了。我追不上他,只好放慢了脚步。我之所以要把糖还给三叔,是因为我没有帮他邀请到林美玉,觉得受之有愧。那颗水果糖在我的手心里已经被焐热,汗津津的。望着那颗水果糖,我的眼泪咕咕噜噜掉下来。他妈的,我也搞不明白我掉的是哪门子眼泪。我说过,当时我对许多事情都搞不太明白,比方说,当年许多男孩子的口头禅是,他妈的,他妈的并不是骂人的脏话,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鬼意思,我们只是觉得经常把他妈的挂在嘴边很帅。
开始我还以为林美玉不再接受我和三叔的邀请,是因为她不再喜欢看电影了,后来才知道,她是把和她一块看电影的人换掉了,换成了一个名字叫李军的人。
这些是三叔告诉我的。
那小子是邻村李埠口的。三叔咬牙切齿地说。
李埠口和我们王皮溜紧挨着,两个村子之间只隔了一条细长的土路,就像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
当时三叔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哼,等着瞧吧,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半个月后的一天,三叔来我们家借铁锨。他一只眼圈青了,两个鼻孔里都塞着揉皱的麻叶,上嘴唇留有残存的血迹。其时我们家正在吃午饭,我和父母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三叔站在门外,冲我爹闷闷地说了一声用用铁锨,拿了铁锨转身就走。我喊了一声三叔,他也没理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娘压低声音说,听说那个李军也伤得不轻哩,一条胳膊都折了。爹叹一口气,说,这个倔种老三呀,看来他这是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啊。然后不耐烦地扬了扬手里的筷子,算了算了,不说他了,吃饭!
这期间,我有时和家里人一块去黄泛区看电影,有时和小伙伴鼻涕儿一块去。我的父母酷爱戏曲,尤其是豫剧和黄梅戏。有一回,听说黄泛区要放映戏剧电影《卷席筒》,天不黑,父亲就用架子车拉着我和娘,兴致勃勃地上路了。六岁的我对《卷席筒》的剧情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其中一个名叫“苍娃”的小丑十分搞笑,他为了贿赂狱卒,竟然拿砖头瓦片当银两,差点笑破了我的肚皮。
在黄泛区农场,我还看了一部叫《画皮》的电影。电影里的那个女鬼太他妈的吓人了。不过,说实话她的心肠并不坏,因为她怕吓到人,所以整天裹着一副人皮。另外,你得承认那个女鬼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她自己身上的那副人皮其实不是真正的人皮,而是她自己亲手创作出来的作品,不仅逼真,而且漂亮得如同天仙,恐怕连林美玉都比不上。大概是由于当时的颜料质量不过关,容易褪色,没事的时候她总是偷偷脱下人皮,重新描画一番。脱下人皮后的女鬼着实令人恐惧,看得我头皮发麻,后背发凉。回家的路上,我走在人群中间,不敢太靠后,也不敢太靠前,生怕电影里的那个女鬼从路边黑糊糊的庄稼地里窜出来。那天夜里,我吓得连茅房也不敢去了,结果尿了一炕。
看了《画皮》以后,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是不是所有漂亮姑娘都在衣箱里备着一副人皮,出门的时候才穿上?包括林美玉在内。为此,我还偷偷观察过林美玉。
那时候农村的居住条件非常差,大多数人家的房屋都是木格窗户,夏天窗户是透的,只有秋冬季节才在木格上糊一层报纸,或者钉一层塑料布。报纸和塑料布只能防风,防不了人的眼目的。只消从家里的神位前偷一根香点着,在那塑料布上一戳,那上面就出现一个小孔。报纸更好办,舔湿手指头,在报纸上一抠就能抠出一个窟窿。我伏在林美玉家的后窗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着窟窿往里瞄。不对呀,怎么一片漆黑呢?想了想,原来是我自己搞错了,把闭着的那只眼睛对准了那个窟窿。调整了眼睛以后,我终于看清林美玉卧室里的摆设了。正好这时候林美玉吃完午饭回到了卧室,她一边走一边解衣服上的扣子。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因为她只要脱掉衣服,就有可能把那层皮脱下来。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别动不动就脱!林美玉的娘严厉地说。
林美玉有些撒娇地说,人家要睡一会儿觉嘛。
这是秋天,不冷,睡觉也用不着脱衣盖被的。一个姑娘家,脱习惯了就麻烦了。
林美玉嘴一噘,和衣倒了在床上。
还有一回是在晚上,我透过报纸上的那个窟窿,看到林美玉在煤油灯下往一个木盆里倒热水,然后把一条毛巾搭在了盆沿上。她显然是在准备洗澡!哈哈,这一回看你怎么办,洗澡总不能不脱衣服了吧?
噗——!林美玉吹灭了煤油灯。
我一下子傻眼了。
听了一阵黑暗里传出的他妈的无聊水声,我只好怏怏地离开了。就这样,我到底也没观察出来林美玉是不是女鬼。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从此以后不怎么害怕女鬼了,并且渴望着能够再看一次电影《画皮》。遗憾的是,《画皮》再也没有在黄泛区上映过。
每次去黄泛区看电影,放映前或放映后我总是在人群里寻找三叔的影子,但始终都没有找到。
也许三叔已经发誓不再看电影。
有一天,为了捕捉一只蝴蝶,我追踪着蝴蝶钻进了一片高粱地。在高粱地里,我没有找到那只蝴蝶,却意外地发现了三叔和林美玉。他们并排坐在一道田埂上,不过称不上并肩,更称不上依偎。我目测了一下,他们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十个拳头那么远。他们低垂着脑袋沉默着,就像在为他们早夭的爱情默哀。
我没敢惊动他们,屏住呼吸蹲在了一丛茂密的高粱后面。
还是林美玉先打破了沉默,她说,建国,你别再闹了好不好?就算我求你了。三叔说我没有闹,我可是认真的。林美玉说可是,可是,可是……我替林美玉数着,她一连说了八个可是,可是她最终也没说出来可是后面的话。三叔着急了,说可是什么,你倒是说呀。林美玉突然说话就流畅起来了,她说可是我心里装的是李军,不是你王建国呀。三叔一愣,接着就轮到他结巴了,说,难道,难道,难道……我也替三叔数了数,不过,三叔只说了六个难道就把话说流畅了。三叔说难道我们俩的过去就这样一笔勾销了?林美玉说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过去。三叔说怎么没有?我拉过你的手,还……还亲过你的嘴。这些都不算数吗?林美玉说那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发生的,是因为看了那部电影一时冲动。一时冲动你懂吗?三叔冷笑了一声,说吆嗬,好家伙,你看电影就能看冲动喽?这真是一个稀罕事儿,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林美玉反唇相讥,说,哼,你看电影是不会冲动,这一点我相信。我真不知道你瞪着俩大眼珠子看的是什么,看了也等于白看。三叔说,我看的是……三叔语塞了,他抓耳挠腮了一阵,突然在林美玉面前跪了下来,美玉,你就答应跟我好吧。林美玉吓了一跳,她几乎是像皮球一样从地上弹跳起来的。大概三叔认为林美玉跳起来是打算跑掉,他一下子扑过去抱住了林美玉。林美玉大概也领会错了三叔的这一举动,以为三叔要非礼她,于是奋力挣脱开,一个耳光打在了三叔的脸上。然后,她就真的逃跑了,冲撞得高粱秆噼噼啪啪一阵乱响。
三叔在高粱地里坐了好久。
究竟三叔在高粱地里坐了多久,我也不知道。高粱地里太闷热了,我出了一脑门子大汗珠子,实在遭不了那份罪,就提前蹑手蹑脚地撤离了。
有一段时间,我把三叔忘在了脑后,因为电影《少林寺》开始在黄泛区上映了。武打片在当时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直惊得张嘴瞠目,血脉贲张,不能自抑。《少林寺》一连放映了三天,每天放映三场,方圆十里八村的人们潮水般涌向黄泛区,黑鸦鸦乱哄哄的,场面十分壮观。我随着人流来来回回穿梭于黄泛区和我们王皮溜之间,《少林寺》连映九场,我连看九场,看得我昏天黑地,晕头转向。
我不得不承认,除了战斗片,就数武打片最好看了。
记得有一回去黄泛区看电影的路上,我见到了在路边田野里锄草的三叔。那时候已经夕阳西下,三叔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他的身影在宽阔的田野里显得十分孤独。路上看电影的人群像游行的队伍一样浩浩荡荡,三叔却不闻不问,埋头干活。一顶草帽低低地扣在三叔的脑袋上,那顶草帽又破又脏,一边的帽檐已经烂掉,往下耷拉着,将他的脸完全遮住了。我跑进田野里,跳起脚一把将三叔的草帽摘下来,扔到了地上。
三叔,黄泛区在演《少林寺》啊!我说。
我的话音尖细而飘忽,听上去都变调了,那是因为我太兴奋了。我觉得三叔放着让人热血沸腾的《少林寺》不看,却还有心思在地里锄他妈的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三叔把草帽从地上捡起来,重新扣在了脑袋上。
臭小子!三叔在草帽底下慢条斯理地说,电影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它有毒啊。你小子当心中了它的毒。
我没听懂三叔的话。
电影是用来看的,又不是用来吃的,怎么会中毒?
我又问他,三叔,林美玉要是《画皮》里的那个女鬼,你还喜欢她吗?
三叔一怔,一脸茫然地望着我。这时我才想起来,三叔根本就没看过《画皮》,所以他还不知道有那么一个漂亮的女鬼。我真替三叔感到惋惜。
这孩子,果然中毒了。三叔咕哝了一句。
三叔说完便不再理我了,仍旧埋头锄草。我觉得三叔这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也有些生气了,转身跑开。
从八岁开始,我成了一个彻底的影迷。那时候我不仅喜欢战斗片和武打片,也开始喜欢故事片了。那么磨磨叽叽的故事片,我竟然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只要黄泛区放电影,我都和村里的伙伴鼻涕儿一起去看,几乎场场不落。只是那时候黄泛区在三八河西边建起了一座新的影剧院,开始出售电影票,票价两毛。新建的影剧院依旧是露天的,一道砖墙围起了一片场地,场地的一头多了固定的舞台和放映室,一排排弧形的水泥座位前后依次排开。我的父母偶尔也去看一场电影,他们当然要花四毛钱买票,但他们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毛孩子再多花两毛钱,就有些冤枉。
于是爹对我说,去,钻你娘衣裳底下。
当时我娘穿的是粗布长衫,下摆差不多垂到膝盖。我钻进娘的布衫下面,脑袋和上半身是遮住了,但屁股和腿却还像狐狸尾巴似的露在外面。通过狭窄的铁栅栏检票通道时,我心跳如鼓,胆揪成了一个疙瘩。这他妈的也太惊险了。
惊险归惊险,但我仍然愿意跟着父母去看电影,因为跟着他们我就不用担心买票的事了。不过,父母只是偶尔看一次电影。
我娘说,电影又不能当饭吃。
我爹的比喻更形象,他说电影就像小磨芝麻油,放几滴在饭里,是香,可是不放它,饭还照样吃。
因此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和鼻涕儿一起去看电影。没有电影票,进不了电影院,我们就在电影院外面等。在看门人面前,我和鼻涕儿装作若无其事地散步,其实我们心里像猫抓似的着急。那个看门的爱板着面孔,仰起下巴看天上的云彩,我和鼻涕儿就跟着他看天上的云彩。偶尔,看门人也把目光从云彩上收回来,瞟我们一眼。趁他瞟我们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回应他一个讨好的笑。
别等了,回家吧。看门人说。
鼻涕还嘴硬,说,我们不是来看电影的。
看门人问,那你们在这儿瞎转悠啥?
鼻涕儿说,跟你一样,看云彩呗。
我赶紧讨好地说,我们是来看电影的,大叔,你就行行好,放我俩进去呗。
有票吗?
没有。
没有一边凉快去!
电影放映到一半的时候,看门人打着长长的哈欠走进了电影院,就好像电影院里不是在放电影,而是摆着一张大床。我和鼻涕儿相互使了个眼色,跟在看门人屁股后面,猫着腰溜进了电影院。
有一段时间,我们看的都是电影的下半截。这让我们非常恼火,因为没有看到前半截的铺垫,我们老是把后半截的人物关系搞混。比方说,两个岁数看起来差不多的男人,我们以为他们是兄弟俩,谁料他们一开口说话,我们才知道弄错了他们的辈分,一个竟然是另一个的爸爸。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语重心长地开导一个姑娘说,大妹子,别犯傻了,听姐姐的准没错。原来她们不是祖孙俩,而是姐妹俩。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为了不再只看电影的后半截,我们决定不在门口等了。我和鼻涕儿沿着电影院的围墙转悠,盲目却认真,结果呢,还真让我们找到了既能看上电影,又不用花钱买票的好办法。围墙的外面长着一排高大的白杨树,我们爬到树上,骑在树杈上就能看到里面的银幕了,虽然角度有些偏,银幕上的画面有些变形,人脸都是扁的,身子就像电线杆子似的又细又长,但终于可以看到完整的故事了。
当电影结束,我和鼻涕儿从白杨树上滑溜下来时,我们都有些飘飘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自己还长了这么一颗聪明的脑袋。但是,还没得意多久,我们就从对方的身上闻到了一股异味。回头一看,哎呀坏了,原来人家早有防备,在树身上涂了一层他妈的牛屎。
说到底,还是花两毛钱买一张电影票,坐在那些水泥台子上看电影比较安稳舒服。
两毛钱的电影票对我和鼻涕儿来说,成了一个大难题。为了这两毛钱,我们开动脑筋,挖空心思。最后,鼻涕儿盯上了他娘头上的银簪子,我则瞄准在了我们家养的一只老母鸡的屁股上。
那是一只勤奋的芦花母鸡,几乎每天都涨红了脸“咯哒”“咯哒”叫唤,报告我娘它下了一颗蛋。母鸡下蛋的地方,在我们家院角的一个柴草垛下面。母鸡刚踱进那里卧下,我就搬来一条小板凳,坐在它的旁边,等。母鸡的脸渐渐涨红,我知道那是它在使劲。我替它着急,也在旁边替它吭吭哧哧使劲。不过,母鸡下蛋的过程太漫长了,我都使劲使得想上茅房去大便了,它的蛋还没下出来。再不下,我的父母就要干活回来了。我坐不住了,一会儿跑到院门口去望风,一会儿又跑回来观察母鸡下蛋的进程。
这时我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响起来。
美玉!
林美玉!
林美玉同志!
难道是三叔在喊林美玉?我重新跑到院门口,踮起脚尖朝发出声音的方向张望着。林美玉的家在另一条村街上,房屋和院墙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回头望了一眼还在使劲的母鸡,撒腿便往林美玉家的方向跑过去。刚拐过一个街口,我就发现原来喊林美玉的不是三叔,而是另外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我不认识,但我猜想,他可能就是李埠口的那个跟三叔打架的李军。
李军的头发比当初三叔的“牛舔头”梳理得还光滑,恐怕蚂蚁拄着双拐也爬不上去。李军的脚上穿着一双真正的白球鞋,而不是像当初三叔那样是拿白粉笔擦过的。李军的两腮潮红,印堂发亮。
林美玉袅袅婷婷地从家里走出来。
老天爷啊,林美玉她……她竟然穿了一条裙子。
我惊讶得下巴颏差点儿掉下来。要知道,当年农村女孩子穿裙子,就跟他妈的光屁股差不多。吓得我双手捂在了脸上,不过,我从手指缝里还是看到了林美玉裙摆下面露出的小腿,她的小腿圆润修长,像刚从烂泥里挖出的莲藕一样洁白。还想接着看下去,这时芦花母鸡的叫声传过来,我怕母鸡把它自己下的蛋弄丢了,急忙像来时一样撒腿跑回了家。
用带着母鸡体温的鸡蛋,从代销店里换回两毛钱。手心里攥着这两毛钱,我和鼻涕儿兴冲冲地去黄泛区看电影。那天晚上放映的电影叫《从奴隶到将军》。这部电影的上半截我看得津津有味,我的旁边空着两个座位,看累了我还可以在水泥座位上躺一会儿,一只手支着脑袋看,非常惬意。看到一半的时候,那两个空位的姗姗来迟的主人终于来了,我只好重新坐直了身子。这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像连体人一样摽着膀子走过来,又摽着膀子坐下来,从头到尾他们就一直没有分开过。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心猿意马起来,银幕上的画面在我眼里变得花花搭搭的,人物的对白也被我听得少鼻子掉毛的,不知所云。
让我心猿意马的首先是一种气味。那是苹果花的香味,丝丝缕缕,若有若无,就好像一根柔软的鸡毛在我的鼻孔里轻轻撩拨着,弄得我直想打喷嚏。这香味显然是从这对男女身上散发出来的,而他们又是从园艺场里带回来的。这香味在我面前飘来荡去,使我神思恍惚,如在梦里。另外,那对男女的举动和窃窃私语也让我不能集中精力于电影之上,女的半依半靠在男的怀里,她的身体像造桥虫一样不停地蠕动着。男的说话用的是气声,含混中带有一点神秘色彩;女的呢,根本就不是他妈的在说话,而是在哼唧,或者是在呻吟,听上去就像她患上了牙痛。
坐在我另一边的鼻涕儿,眼睛一直紧盯着银幕,他一会儿抬起袖子抹眼泪,一会儿又嘻嘻笑出声来。
我也强迫自己把目光放到银幕上。
可是,旁边那对男女好像具有强烈的引力似的,硬生生地把我的目光拽得歪歪斜斜,仿佛他们在上映着另一幕小电影。
也就在这时候,一股狂风毫无预兆地刮起来。电影银幕被狂风吹得先是愣怔了一下,然后使劲向后弯曲着,银幕上的所有人都吸着肚子,仿佛他们顷刻间都变成了罗锅腰。几顶帽子和几条围巾从观众席里猝然飞起来,随着狂风从我的头顶上掠过,有一顶帽子叭的一声扣在了银幕上。观众席上开始骚动起来,有人在跳动着追赶自己的帽子或围巾,女人的长头发像水草一样漂浮起来。混乱中,我身边的女子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她的叫声成为了这场骚乱的高潮。
啊——!
随着尖叫声,她的裙子被狂风掀起,两条腿完全裸露出来。
直到第二天,我的脑袋还晕乎乎的,眼前老是晃动着那两条腿。在黑暗的衬托下,那两条腿显得异常的白,异常的艳,异常的怪异,并且散发着鬼魅的气息。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画皮》里那个可爱的女鬼。
第二天我和鼻涕儿谈论昨晚的电影时提起了那股狂风。
什么风?根本就没有他妈的风!鼻涕儿肯定地说。
没有?我感到纳闷。
没有!骗人是王八。哈哈哈哈,小胖,你是在做梦吧?
难道是幻觉?或者真的是我坐在电影院里做了一场梦?我又问了昨晚村里看过电影的许多人,他们一致告诉我,昨晚确实没有刮风,连一丝风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所有人证实风根本不存在的那一刻,我突然之间就理解了三叔的痛苦,尽管那时候我才八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八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大了。我也不知道那晚坐在我旁边的那对男女是不是李军和林美玉,因为天太黑了,他们的面容模糊成一团,而且我压根儿没敢正眼看过他们。
我想把风和裙子的事告诉三叔。
但最终我也没有告诉他。那时候我已经对三叔不感冒了,他的头发不再光滑,也再没有穿过白球鞋。他的头发乱糟糟的,和当时正常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经常赤脚穿着布鞋,随意把布鞋的鞋帮踩在脚下。更主要的是,风和裙子已经与三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三叔再也没看过电影。或许,三叔根本就没有真正喜欢过电影。
跟不喜欢电影的人谈论风和裙子,是没用的,就像他妈的对牛弹琴。
责任编辑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