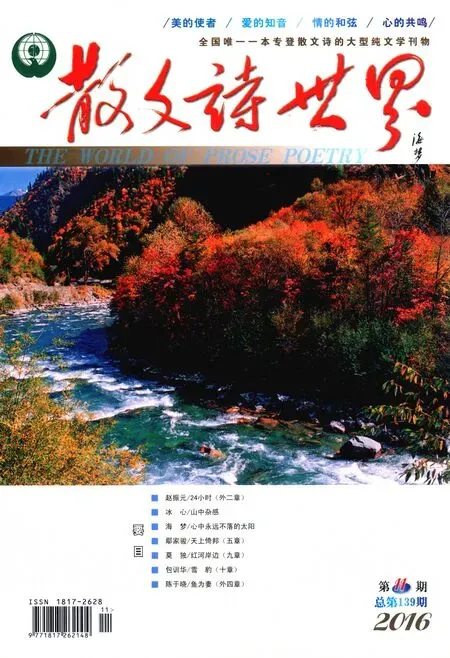曾经的烟火(六章)
北京 鲁橹
曾经的烟火(六章)
北京 鲁橹
车前草
工地给它的灰尘,白色的粉末要多一些,它的茎秆上,蚂蚁三只,是来躲避的。
轰鸣的搅拌机的声音,像天空巨大的咳嗽。
它越发的瑟缩起来,叶子开始卷边,本来准备结籽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
长长的吊车,长长的手,那么生硬,它索要的东西在凝固时更沉重。
它已失去水分,本就单薄的身体,只有三片叶子护卫着,虽然小心翼翼。
它尽可能承接露水,只是,露水粘了泥浆,
它尽可能记住星空,只是,星空那么厚,
像被遮蔽的一张脸,睁不开眼睛。
它驱赶着那三只蚂蚁,你们,走远一点,走远就有生机!
它慢慢失去呼吸。
它慢慢放弃生命。
工地上的狗
有三五只。是流浪的,抑或曾经家养?它们聚集在一起,像一个散漫的团队。
白色的、黑的、土灰的,它们大小不一,唯一的共同点是:皮毛凌乱,眼神凌乱。
每一只的特征都很暴露:像被抛弃的孤儿,嶙峋的脊背上,结壳的伤疤显眼。
它们不属于正规大院,那些皮毛顺溜的狗儿都一副养尊处优的神情。
它们不走到大院这边来,它们只是偶尔瞭望,偶尔狂吠几声。
清晨,它们也奔跑,是集体游戏或者打闹,仿佛捉迷藏的孩子,刚刚钻完沙堆。
黄昏,它们无精打采的扎堆着,趴着、立着、半蹲着,有的,耳朵上还挂着一根草,
它们,总体看来是忧郁的,该是清楚自己的处境,当一栋栋楼房挺立起,它们的立身之所将被占领——
哪怕只是钢筋水泥的空隙,
哪怕只是仓库阴影的深处,
甚至,有一天,不见了它们,连一点血也不见!
而,城市那么高,那么多的宠物狗在楼群里欢跑!
看工地的老人
生铁皮搭建的工棚,塑料袋挂着,一顶破旧的矿工帽,积满了尘土。
门半开,风大的时候,看得见生锈的铁丝绞着门把。
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时常唱的是河南豫剧,抑或,也有京腔京韵,
猛地还能听见老人几声大叫,像嗓子里搁了石头,词句模糊,应该是吼家乡戏。
清早,似乎废弃的工地,狗群在猛跑,像被谁驱赶,又像是玩闹,麻雀立在水泥栏杆上。不多,也就那么几只,翅膀扇动,空气中寂静的旋涡似乎被关闭了,
他的门半开着;
黄昏,似乎废弃的工地,狗群在猛跑,像被谁驱赶,又像是玩闹,麻雀立在水泥栏杆上。不多,也就那么几只,翅膀扇动,空气中寂静的旋涡似乎被关闭了,
他的门半开着;
什么时辰,空气中寂静的旋涡被打开?
什么时辰,老人的门完全敞开,或者,完全关上?
什么时辰,老人能听一出完整的戏,在家乡,而不是,在这生硬而干燥的他乡?
卖羊肉串的小夫妻
楼群拔起。那片还未拔起的,是一个小区的重建,灰色的云悬在每一个窗口,星光暗淡。
花坛里,花儿还没归位,水管子冲起的水柱,把泥浆溅撒得老远;
壮实的山东小伙,高个,大眼,长睫毛,纯粹的武男形象,他说他是窦建德的后裔。
妻子来自河北张家口,脸圆圆的,像个瓷娃娃。大专毕业,找工作,先找着了爱情;
收拾了少年的豪情,他们在街道边支起摊子,快八年了,我见证他们慢慢成为中年。
小伙的肚子开始高于他妻子的,长睫毛也短了,他大手张开,一会是一把肉串,一会是烤熟的馒头片;
妻子抱着孩子,妻子放开孩子,妻子去接送孩子,一个小男孩,生下来就胖嘟嘟的,到现在,更加胖嘟嘟了;
生意总是很好。羊肉串总比别处的烤的有味,是实诚的,也是谈笑风生的,他总能发挥他纯粹的山东人的特性:豪气,大方,陪客人喝酒时,他一罐到底;
妻子笑笑,也有小声的责怪。她偶尔跟桌子上的人说说话,但轻言细语,很像个南方人。
客人走时,她送去很远,像每个人都是亲人;
的确是跟别处不一样的,这对小夫妻。
只是,小区立起的时候,他们就该另寻地方,在某一处,继续他们的生活。
烟火升起。他们的人生有着肉串一样的香味,是正宗的,也是扎实的。
仓库里的钢筋
当它被浇铸,被裁断,被掩埋,抑或,被高高举起,它是活着的,仿佛从历史的断层来,
携带着钢铁的烈火和品性;
我所看到的火焰,是它的,我说看到的冷硬,是它的,我所看到的强大,是它的;
它的倒卧、竖立、斜躺,糅合或者化零为整化整为零,都那么义无反顾,义不容辞;
它要侵淫到庞大的建筑群中去,成为踏板,成为跳台,成为顶天立地的脊梁;
只是,莫要让它停下,让它废弃,让它孤独地发出低低的吼声;
莫要让它在堆积的仓库里守护漆黑的夜,仿佛黎明迟迟不来;
它宁愿在光芒中醉倒,看见忽远忽近的人群。
曾经的烟火
目睹又一片田地变换身份,有一阵阵战栗,仿佛从胸腔辐射开来,
又要进驻一批人类了,又要圈养起来,又要缩小本来就小得不能再小的地面;
绿色越刮越少,最后成为荒芜,开始堆放垃圾、砖头、水泥、钢筋,成为一大片新的垃圾场,
风中都是刺鼻的灰尘的味道,老鼠集合,爬行的昆虫迅疾的逃跑;
大地上已经没有泥土了,更别说栽种,那些遥远的地方,面临开发的危险,
消失不见的农作物,是不是也会慢慢从书本上消失,是不是真的会分不清韭菜和小麦,稻谷和青草?是不是饭碗里的米粒从空气中抓来?
农民工已经不能发言,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开垦另外一片土地,让这片土地成为坚硬的城市,
工人早就没有流水线了,他们涌向另外的流水线,用汗水和泪水喂养自己的尊严;
城市越发地繁华了,交流沟通的渠道越发地多了,但,你看见人们越发地亲密和谐了么?
别墅区越发地成群了,高档小区越发地扎堆了,但,你看见人们越发地尊礼重教了么?
一块土地的消失, 一栋新楼群的耸立,不是喜悦,是又一道人间烟火,冒着白色的浓雾,像镣铐,像鞭子。
曾经的烟火,曾经的人间,我们都喊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