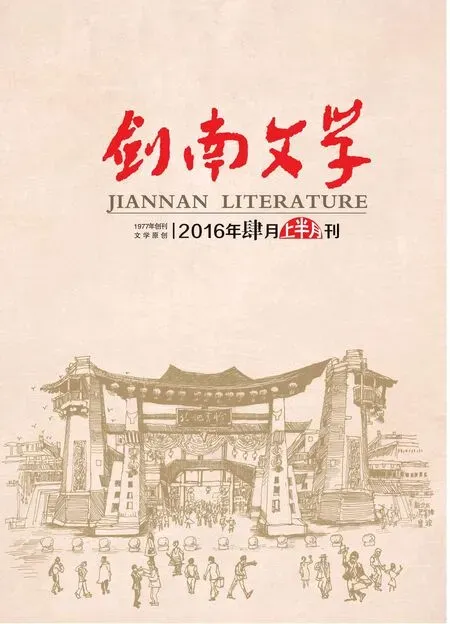父亲(外四首)
□甫跃成
父亲(外四首)
□甫跃成
村庄
隐约在变,又似乎从来没变。
一些人走了,一些人
继之而来,使用相同的姓
和类似的名,在同样的
山水之间,续写一个寨子
漫长的家谱。
多少故事发生了?
多少脚印不可磨灭?
一只乌鸦“啊”的一声
飞过村口,有人抬头——
这乌鸦似曾相识,难说是不是
两百年前的那一只。
父亲
我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他,
越来越像一个固执的老头,
会独自一人,躲在晦暗的屋里
看电视,或读一本破旧的小说。
会突然之间,莫名地生气,
与朝夕相伴的妻子争吵,又在
抽完两支烟之后,感到后悔,
努力想去弥补些什么。
我忽然感到,某种强大的基因
在我体内决绝地复活,使我确信
我跟这个长我二十四岁的男人
有切割不断的关联。
这些年来,想到他,我就依稀
看见了二十四年之后的自己。
他的手指被凿子戳穿,眉骨上有
木屑打出的疤痕。昨天我不慎
割伤了手指,就仿佛看到
这一刀,也曾割在他的身上。
二十四年过去了,我却依然
有些心疼。
过路站
向一个站靠近,看它在路的尽头
艰难诞生。一个点从无到有,
由浅入深,渐渐地露出
细微的轮廓。列车太长,铁轨太短。
速度稳中有升,拒绝下降。我看清了
小站的围墙、脱了漆的黄色屋顶。
说话之间,它迎面奔来。
“陈家沟站”——破旧的站牌上
四个黑字被雨淋湿,旁边一棵枇杷树
还在滴水。两个女人穿着制服
正在说些什么,一个坐着,
一个倚门而立。她们长得
多像我老家的两个亲人啊!
她们是否也有着
相似的故事,一个像我一样的
穷亲戚?那个站着的女人
往车窗上扫了一眼,视线跟我一碰,
随即转过脸去,接着聊天。
列车轰隆轰隆驶了过去,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招呼一声。
失眠之夜
他总是睡不好觉。房间太窄,就在公路旁边,
邻居的鼾声和汽车的喇叭轮流向他进攻。
他时常加班,下了班去接孩子,
定期陪父母到医院做健康检查。
他查看电表的读数是否准确,
持有的股票是否上涨。他想买车,
所以关心奖金的额度,柴米油盐的价格。
他和妻子偶尔吵架,作为薪水的两个来源,
他们合作默契,但交谈不多。
看完肥皂剧,他们辅导女儿的功课,
有时他也一个人呆在屋里上网。
夜里他会抱抱妻子,但更多的时候,
他独自醒着,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一言不发。
多少年前,他暗恋美丽的校花,
无数个夜晚为她失眠;如今他再次失眠,
只是已没有精力,去恋些什么。
生活面前,所谓爱情也不过屁大点儿事儿。
他翻一个身,闭紧双眼开始数羊。
通话记录
拨通电话,你就开始向我抱怨。
你急需意义、成就感,
讨厌没日没夜的操劳
都只为了挣钱。那些忙碌的工蚁
曾让你不齿,可你料想不到
终有一天,你会加入它们的行列。
这两年来,养活自己
就已耗去你这么多精力。
你总是腾不出手来,理一理思绪,
让自己活得更像一个人。
有一阵子,你迷上了买彩票,
期待着突然中个五百万,然后辞职,
爱干什么干什么,从一头物质的兽
变成一只精神的鸽子,飞上天去
就再不下来。可是熬了十个月,
不曾中过一枚硬币。过完星期天,
你仍得挤进地铁,钻进办公室,
放下高材生的架子,见到主任
就堆出满脸的笑容。
这样的日子令你痛恨。你甚至想
摇身一变,就已六十出头,呆在家里
领退休金。可是生活抓住了你,
死活不肯替你减掉
这受苦受难的三十多年。
多少个夜晚你睡不着觉,大喊一声,
坐起来,发誓要换个工作。
辞呈都已写好,却不知道
除了眼下正在做的这些,你到底还能
做些什么。所以你退缩了,反而更加
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一句话
得罪了谁,就被突然开除。
说到这里,你长久地沉默。
几分钟后,你挂断电话,
夹着公文包一个人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