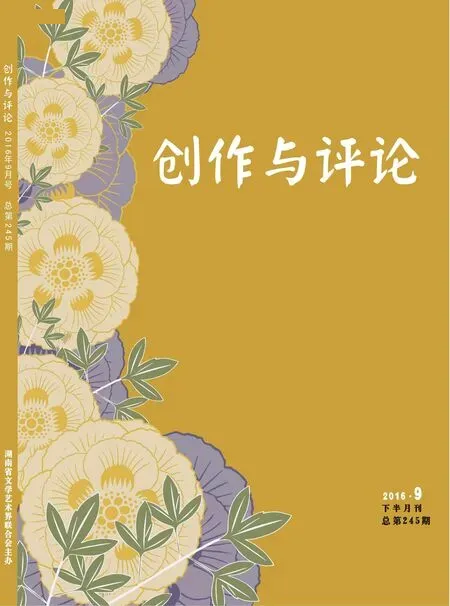“尖兵”与“后卫”
——2015年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之考察
○傅书华
“尖兵”与“后卫”
——2015年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之考察
○傅书华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山西作家在全国各个刊物上刊发中短篇小说197篇,其中中篇小说50篇,短篇小说147篇。有25篇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国内重要选刊及各种重要的年度选本所转载。在这一年,继续以“晋军新方阵”丛书的名义,山西新锐小说家出版了5部中短篇小说集:陈年《小烟妆》,李来兵《梅问题》,张暄《病症》,曹向荣《打街》,刘宁《光线笔直地照射》。无论从刊发、转载的数量,还是从作品的质量及作品的社会影响力考察,本年度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与2014年甚至前几年相比,都相差无几。
孙犁在谈到赵树理时曾说过:“创作的真正通俗化”所应具备的要素,在赵树理成名之前的文学创作中,均已具备。“在当时有见识,有修养的人才多得很,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他还说,“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细流,大江推动细流,汹涌前去”①。确实,文学的兴盛起伏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非文学自身所能左右,在我们考察一个时段的文学发展时,有两点是应该给以强调的:一是不能脱离时代而仅仅从文学自身来考察、评价文学的发展态势,譬如文学社会效用的变化,譬如某些文学形态优势的丧失等等。二是要避免沿用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许多人习惯了的“激进变革”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总是希望突变、巨变,希望一浪更比一浪高。常态才是正常的形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将文学的发展变化简单地归结于对时代的被动,并不是说简单地认可必然而放弃了对应然的追求。卢卡契认为:一般说来,短篇小说是长篇小说等宏大形式的尖兵和后卫……作为尖兵,它表现新的生活方式的预兆、萌芽、序幕;作为后卫,它表现业已逝去的历史时期中最具光彩的碎片、插曲、尾声②。如果说,短篇小说是时代大书中的片断与碎片,那么,别林斯基曾说过,中篇小说是在时代的大书中撕下的几页。如是,中篇小说也具备着如同短篇小说那样的体现时代变化的尖兵与后卫的功用。文学创作对时代变化的敏感度,这或许是我们可以用来考察2015年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得失的一个视角,而作为用以体现尖兵与后卫的艺术形式诸要素,也自然是我们应该予以考察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作这样的考察时,“典型现象”及“细读”的方法,不失为一个既有效又可行的方法。所谓“典型现象”的方法,就是“从某个‘具体’(如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年度等等)看一个世界”的方法。“对于某个‘具体’可以有两种考察方式,如果只把它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具体’的贡献和成就,如果把这个‘具体’看作是在它的身上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某些特征的‘具体’与一个‘时代’的统一体,那么,这个‘具体’就成为一个‘典型现象’”③。最为典型的成功范例,就是在海外倍受推崇的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典型现象”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在对2015年度山西的中短篇小说进行考察时,避免对作品的一般性罗列与描述,而深入到该年度小说创作的“肌理”中去。所谓“细读”,是西方新批评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原本是指斩断了作品与社会、作者、读者关系后,围绕着文本自身构成而进行详尽分析的批评方法,本文的“细读”则主要取其宽泛之义,是指立论从对文本自身的分析出发,这对于我们匡正多年以来形成的从一个既定观念、流行观点出发,再套取实例给以认证的积弊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尖兵”
中国社会在时代性转型中社会构成、人生形态、价值观念的动荡,是全体国民亲历其中且有着切肤之痛的,诸如经济领域的重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或隐或显的冲突,官场的反腐,国民日常生活形态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异、伦理道德的失序等等。相对说来,在时代性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中,新一代人的浮出历史地表,对传统人际关系的改变,男女情爱生活的丰富,在2015年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有着比较充分而又深入的反映与揭示,这或许呈现了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潮流的新的兆头。
中国社会时代性转型中出现的新的特点,在新的一代人的人生形态中,有着相当充分而又鲜明的体现。这是因为这一代人,其生命形态、生命经验、价值构成的形成过程,恰与中国新出现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生活形态、价值观念的动荡与形成同步。在2015年山西中短篇小说中,对新一代人的人生形态的揭示,大多是由青年作家来完成的,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对此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与倾诉的欲望。
浦歌的《孤独是条狂叫的狗》《合影留念》《狗皮》可以视为这伴随着市场经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的三部曲,只是这三部曲,我们是沿着从现实回溯历史的线索安排的。《孤独》写从校门出来走向社会的新一代人的生存困境、面对社会现实的茫然失措、精神上的躁动不安,这或许是在社会转型中,面对新的社会形态的典型“症候”。在《孤独》中,作者写步入社会不久的小说主人公“我”为了短暂地逃离逼仄而又卑琐的生活困境,与女朋友茫然地漫游于喧闹的现代街市:举目而来的现代街市的五光十色,拉二胡的乞丐,珠宝、时装的诱惑,基本的食欲需求,对男女情爱的渴望,金钱缺乏的困窘等等,在无奈地对此的感受与经历中,更映衬出主人公在面对现代街市的渺小、茫然与被排斥及外的异在性,而在无奈地感受与经历了这些后,主人公就好像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曾经试图逃离的逼仄而又卑琐的生活困境,只是这困境因为主人公的试图逃脱,显示出了对主人公的更大的敌对性外在性——周围的邻居,正在以敌视的态度窥视着他。读这篇小说,让人想到了鲁迅先生的《在酒楼上》,都是现代都市的漂泊者与畸形人,都是画了一个圆圈似的绝望地出走与无奈的回归,都是那种小小的希望被淹没在了巨大的灰色之中。这样一代青年的命运,倒溯回去,就是浦歌的《合影留念》。在《合影留念》中,两位步入社会遭遇困境的年轻的主人公,其逃离之地不是茫然于现代街市,而是试图在重忆校园生活中寻求解脱,却发现那重忆中的校园生活,却正是他们今天遭遇困境的出发地、逻辑起点,变化的只是岁月给他们带来的身体形态的变形与丑陋。这一代青年的命运,如果再从校园倒溯上去,那就是《狗皮》。《狗皮》的主人公就是从乡下那绝望、荒诞、穷困的生活中走向校园的,只是主人公父亲那奋争与失败同在的“脚臭味和汗腥味”“猥琐的嘘嘘声”和“狗嚎声”,只是那曾经的生活阴影,如影随形地潜藏于主人公的校园生活中,让他既对新的生活内心充满了渴望却在实践中又是那么无力,所以,主人公只能在学校的操场上,与自己心爱的女性站立拥抱一晚,其后却又形同陌路,最终知道这女性身溺于现代都市的欲望之河。要而言之,从传统的乡下,到大学的校园,再到现代的都市,其间血肉粘连,因果相互,让我们看到了新的一代青年与中国社会行进的同步及这同步之中的命运,而当我们用站在现实回溯过去的方法,让我们看到的也是现实困境视野下的过去的图景,犹如《合影留念》中主人公的校园生活是其在现实困境中忆念中的校园生活。
如果说,浦歌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写新的一代青年的人生过程,那么,陈克海的《土豹子》《没想到园子这么大》则是从共时性的角度试图全方位地写出这新的一代青年的生存状况。这其中,有这一代新的青年从个人欲望出发而对生活的追求,有在这追求中,因为被金钱、社会格局、自身位置所制约的困惑与无奈,有在这困惑与无奈中人生内容的扭曲与变味,有在这扭曲与变味中价值指向的迷茫。在《土豹子》中,我们看到,宋明凯身体的健壮与这健壮中所四溢的青春期的欲望激情,演绎了他与两位女性的人生故事。身体,在以伦理道德为价值本位的传统中国的价值谱系中,一向是缺失的,是不在场的,虽然老中国社会一向有风月场所的存在,文学世界中也一向不乏肉欲描写,但那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文学世界里,都是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都是不能赋予价值的所在。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身体,浮出了历史地表,成了个人性存在的直接载体。与身体一同浮出历史地表的,是新的一代青年。但这身体的置放与青春期欲望激情的实现,却又不能不受到金钱、社会地位的制约及在这制约后的变味,在变味之后映衬下原初本色的混沌。于是,我们看到了宋明凯与富家女马伊丽的亲热与分手,看到了分手后宋明凯对马伊丽的不时怀念。也看到了因为小企业家孟爱民的作用而促成了宋明凯与李佳青的结合,看到了在这结合之后身体与青春期欲望激情的渐入庸常,即使试图有所创造,譬如放弃闹市中的生活,搬入城郊田园“别墅”,但这创造也最终远离生命自身而徒具生命外形,譬如作者写那小狗亿花花的喻意所在。在《没想到园子这么大》中,主人公薛珊一直在试图追求新的人生新的生活,但能够让她经历的,全然没有任何新意,甚至离开丈夫去过新的独身生活,甚至以新的期待及追求与比自己年轻的王刚同居在一起——依旧是站在个体日常利益上的庸常与欺骗,算计与冷漠,且不论是从西德回来的闺蜜杨芹还是于国学在表面上风生水起的卫方正,亦或是作为上一代人的母亲,无不如此。小说结尾说薛珊的整个追求,无论中间有过多少血肉撕裂痛断肝肠,但“好像中间错过的东西对现在毫无影响”,于是这整个追求,这追求过程中的血肉撕裂痛断肝肠,也就成了无价值无意义的所在。
李心丽的《疼痛感》,张暄的《上下左右》以一种相对比较单一的人生形态写新的一代青年的生存困境,虽然不及浦歌与陈克海对新的一代青年生存困境描写的丰富与厚重,但却也因此给读者以更清晰鲜明的印象,可算是书写新的一代青年的另一种写法。《疼痛感》写主人公迟小立因了小家庭的生存境况,不得不极为看重个人职务的提升,为此,他在机关人事调整时,绞尽脑汁想给上司送礼,却又不谙此道而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折磨,却又因与好朋友形成竞争瞒着好朋友从而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内疚之情,但最后职务提升还是失败了。心理的压力,精神的折磨,现实的打击,凡此种种,共同给了初入社会的新的青年一代以难以言说的生命的疼痛感。《上下左右》写年轻的乡镇副书记乔桑在工作中应对上级、同事、下级、家人中的尴尬、不易、痛苦、无奈。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得以立足的重中之重,虽然市场经济必然会对原有的人际关系构成冲击,但在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完成改革之前,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观念,仍然是新的一代青年人在工作中所感到的最为不适最为痛苦之事,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也是新的一代青年人的人生特点,《上下左右》对此作了形象而又生动的描写。
与1950年代青年书写的浪漫、进取相比,与1980年代青年书写的理想(即使写失落,愤懑,也是因为有着理想的前提存在)、奋争相比,今天这一时代的青年书写,更多地驻足于个体性日常生存的苦恼、迷茫,即使写新的青年一代的奋争,写新的青年一代对美的追寻,也被融入于这苦恼与迷茫之中,有着“恶”的阴影笼罩其间。譬如杨遥的《弟弟带刀出门》,弟弟的奋争与打破生存现状的努力,与地方的黑势力有着血肉相连;弟弟心底的善良与一尘不染的纯净的“洁白”血脉相通,但这“洁白”却与风尘女子一体。再如陈克海的《马熊》作为新的青年一代的王勇、王强、苏银平等人,其对自身生存现状及因此而来的对原有社会形态的改变的努力,无不与原有道德形态相冲突,从而给其的努力,打上了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色彩。用原有时代的标准衡量,以原有文学观念来评判,似乎今天对新的一代青年的书写,过于灰暗,“亮度”不够,悲悯情怀不足,人性温度欠缺,但这或许是我们原来的价值标准与文学观念需要调整,或许是文学在去顽固的“伪理想”而走向直面现实必然的过渡,也或许是这新的一代青年的时代局限所致。
传统的老中国,是一个特别看重建立在血缘关系群体伦理标准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的社会,且这一人际关系,有着悠久而又稳固的历史。但是,当市场经济从经济基础这一社会结构的根本处动摇了这人际关系时,整个社会对此的恐慌感以及对新旧时代转型的不适感由此而生,且成为今天这一时代的主要的时代性“症候”。文学对此的揭示也因此成为文学的时代性主题之一。2015年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如王祥夫的《窗户人》写现代都市人之间对人际关系的恐惧与交流的渴望;《金属哨》写原有兄弟之情在现代社会的变异;杨凤喜的《火星》写新的代际关系下老年人的寂寞;《屋顶掌纹》写荒芜了的乡村之下人的孤独;杨遥的《黑色伞》写现代个体存在及其在沟通错位中的处境等等。在这些方面,特别优秀与突出而需要给以提出的,是杨凤喜的《玄关》、邓学义的《收心》和孙频的《柳僧》等。
杨凤喜的《玄关》写患了绝症的父亲,以“碰瓷”付出生命骗保骗民事赔偿的方式帮助儿子摆脱经济困境购得了急需存身之屋,作者又极写主人公对父亲的怀念及失去父亲的痛苦之情,父子情深令人唏嘘不已,与之相对比的,则是儿媳对装修住房的高度热情与在此热情衬托下的对为这住房而失去了生命的公公之死的情感上的淡漠。但作为赔付一方的老父亲,为了帮助儿子赔付所付出的辛劳、儿子被收押给父亲带来的痛苦及在其中所体现的充满着痛苦的父亲对儿子的慈爱之情,同样令人唏嘘不已且唏嘘不已的程度与前者不相上下,而被“碰瓷”的儿子之所以被“碰瓷”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自己急于去接自己的女友。然更令读者心灵震撼的,是这一切均是由于金钱而发生,金钱对亲情关系至深至强的影响力于此被揭示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其深刻之处有二:一是通过前述主人公妻子对住房对公公之死在态度上的强烈对比,写出了当今重金钱轻亲情的时风,但更深刻之处则在于,它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巴尔扎克式的或者在今天中国小说中,如我们前述的小说主人公妻子对住房对公公之死态度对比上,不是我们所常常看到的,金钱对原有人际关系亲情关系的疏离、破坏、摧毁,而是更为深入地写出了,这金钱对亲情关系至深至强的影响力是通过传统的爱的方式来体现的,且由此构成了更为惨痛的于己于人的悲剧。
邓学义的《收心》应该是中国2015年短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收获之一,是这一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的上乘之作。小说写一位腰缠万贯的老板老时欲包养一位人性极为纯净的十九岁的年轻女工小叶的故事,其对金钱与人性冲突的揭示与描写读来令人瞠目结舌回味再三而仍然不能尽其意而只能品味不已。其最为精彩处要而言之有四:第一,中国文化最具力量之处是攻心为上,是征服心灵为上,是让你的心灵、精神内化于其中为上。老时对小叶的包养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任何勉强的成份,也不存在着让小叶改变自身人性纯净的成份——甚至正是因为小叶的人性纯净,才让老时有了包养的意愿,而是完完全全地服从于小叶的自觉自愿,但这种无处、无法可逃的对心灵、精神的征服才最为根本,最为可怕。第二,小说写了对小叶至为关心的廖姐、让小叶从小就仰视的威严而有力量的大伯、沉默豁达的父亲与憔悴勤劳的母亲、与小叶一起青梅竹马长大对小叶爱到至极为了在小叶身边呵护小叶而不惜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从事最原始最苦累的建筑工的小叶的学法律的男友志飞,他们都先后从不同程度地反抗老时到被老时收心而心甘情愿地帮助老时,从而一步步地让人看到了金钱对心灵、精神的征服、内化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多么可怕。第三,小说没有把老时写成一个借助金钱力量来征服女性甚或玩弄女性的老板,他精神深处的最大危机是因为在积累金钱的过程中,对纯净人性丧失的恐惧,所以,是“每次吹得时候,她都能流进小叶心里,让里边的天空一片空明”的小叶用树叶吹的山曲,让他能够暂时从这精神危机与恐惧中挣脱出来:“小叶看见他的目光终于慢慢柔和了起来,全身也都松了下来,呼出了一口气,然后看了小叶这里一会儿,又安安静静读起了那本书”。如是,他用各种手段考验小叶对金钱诱惑的拒绝力量,对弱小生命的珍惜之情。当二十几个表面与小叶相似的女孩子在这些考验面前都败下阵后,小叶却因人性纯净的本色力量轻松从容地通过了这些考验。正是小叶的这一人性纯净的本色,才因了老时为了挣脱其纯净人性丧失的精神危机与恐惧而为老时所渴望拥有渴望征服,并在这种拥有与征服中,让自己确证自身金钱的力量而安妥自己的精神与心灵。这样的对抗与冲突,无疑给金钱与人性的冲突以更为丰富与深刻的“张力”空间。第四,小说的结尾极为精彩,当所有的人都被时老板收心之后,小说的结尾写时老板很真诚很庄重地问小叶“你愿意(被金钱收心)吗?”这可以视为是对所有国人的时代之问。
在写现代人际关系的动荡方面,孙频在2015年有四部中篇值得重视,这就是《柳僧》《我们的盐》《圣婴》《色身》。
《柳僧》写年轻时远离北方故乡乡村一辈子漂泊在南方工厂艰难生存的倪慧的母亲,在晚年时,满怀着对故乡亲人及对初恋情人的思念之情,回到故乡的遭遇:亲人早已亲情淡漠而是视其对自己经济物质的支持力度而随时变换着脸色;初恋情人不仅对当时的初恋毫无记忆,最后竟然为了劫夺她的财产而在其母女归途路上将其杀害。主人公思恋之情的真切浓冽与其最后结局的悲凉惨痛构成的鲜明对比,给读者以惊心动魄之感,并打破了幻化传统、乡村的现代迷梦。《我们的盐》写身陷冤案失去妻子的张利生,怎样从一个懦弱善良之人,最终一步步地把自己心中的恶之力激发到了极限并对仇人进行复仇的故事。小说的精彩之处有二:一是这心中恶之力的逐步激发的过程,一是这复仇过程中,对对方精神的致命摧毁,这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写出了对人精神、心灵的改变与伤害,才是最为可怕的致命的改变与伤害。《圣婴》写老女人宋怀秀为了自己弱智永远也长不大的女儿,用金钱挟制来城里打工的经济贫困的男主人公娶了自己的女儿并将自己女儿的终身托付给了他,但这对男主人公的精神、情感、心理都构成了极大的伤害,男主人公在被伤害的同时,又反过来伤害、报复宋怀秀母女,用残缺的方式拥抱残缺的人生,其结果可想而知。《色身》写女主人公杨红蓉从乡下到城里辛酸的打拼过程,其后迫不得已地嫁给了曾贪图其虚名的白志彬,而白志彬很快就始乱终弃让杨红蓉痛不欲生。白志彬出车祸成为植物人后,在陪护刘亚丽对白志彬耐心护理中所体现的对生命的珍爱的启悟下,杨红蓉有了对生命的新的发现与感受。孙频的小说,总是习惯于用超乎常态的情节,将善恶两极冲突特别是将恶的一极推向极端,并因此构成对常态中善恶两极的鲜明观照。在当今中国人际关系伦理道德急剧动荡之际,她的小说因此而为时人为文坛所特别瞩目。
在揭示现代人际关系方面,2015年山西的中短篇小说中,还有两篇小说值得一提。一篇是杨遥的《铁砧子》,一篇是曹向荣的《店铺》。前者写竞争给人带来的人生活力及对人生存状态的良性改变,后者写商业经济生态下,温暖的平常之心的可贵。说其值得一提,是因为写金钱、商业经济对原有人际关系的破坏的小说很多,写新的商业文明下,新的人际关系构建的小说很少,这两篇小说正因为涉及到了后者,所以,不应忽视。只是这两篇小说都写得偏于单薄了。
男女情爱形态历来是时代变化的最为敏感的风向标,当今时代也不例外。2015年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这方面,成就不大突出,但也不宜忽略。张暄的《孩子生病时我们都做些什么》写面对夫妻之爱结晶的孩子生病时,夫妻却纠缠于庸常的情感矛盾、冲突之中,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当今时代普通百姓家庭的生存境况和情爱境况。张乐朋的《红了樱桃》写多角男女情恋性爱给当事人带来的情感创伤,这创伤却是由美、丑、庸俗、鲜活生命等多重元素混合而成,从而写出了男女情恋性爱的复杂性。手指的《李丽正在离开》写身份差异、经济困境生存压力之与年轻一代的情恋性爱。李心丽的《两次错过》探讨了是什么导致着当今时代普遍存在的婚姻危机。王祥夫的《噗的一声细响》则写了对当前用钱、权实现邪欲的惨烈拒绝。张乐朋的《安蓓的空间》、陈春澜的《喧夜舞马》、小岸的《暗》则因其在某一方面的特色鲜明而需要稍稍多加论述。
婚外恋是当今国人的时代话题,张乐朋的《安蓓的空间》写婚外恋给当事人带来的惨痛结局。女教师安蓓本是一个洁身自好珍重男女之情的女子,但家庭夫妻情感的逐渐淡漠,丈夫不能为其分担的实际生活中无法逃避的生存压力,婚外男性冯前卫对她情感的诱惑,对她缓解生存压力的帮助,使她一步步地滑入了婚外恋的泥潭。婚外恋确曾对其精神、情感以短暂激活,给其身体以短暂快感,但这激活与快感,很快就因时间延续给婚外恋男性带来的审美疲劳而渐次消退,又因了时间延续必然带来的为外界所不容,最终让男女双方自蹈死路。小说以此让人看到了当今时代情爱性爱的有限空间,对此过程揭示的精确则殊堪称赞。
陈春澜的《喧夜舞马》写夫妻之间因为性事的隔膜最终造成妻子死于丈夫失手的惨剧。小说的女主人公因为在少儿时代为父母离异所刺激,所以,在婚后要求在夫妻性事上必需男方主动。其后,因为女主人公的社会身份日益高于丈夫,造成了丈夫心理上的压力,导致在夫妻性事上,虽然夫妻仍然恩爱,彼此都有身心需求,但丈夫不再主动,从而夫妻虽然同床而卧但却在从无性事中彼此忍受身心的折磨,最终在积累的怨气中,妻子死于丈夫的失手。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视情为纯洁,视性为肮脏。所以中国传统文学中,男女情爱绝少沾染性爱,似乎一与性沾边即与纯洁无涉。此种有情无性文化的长期浸染,身体性话语的长期缺失,使国人在今天面对身体及性的时代性开放,因缺乏价值资源的支持,不是把昔日的禁锢、无知幻化成美德,就是纵欲泛滥,然却是一体两极。《喧夜舞马》深入于此一领域,赋予性事以人生价值性,是其现实意义所在。
小岸的《暗》表面上是一个曲折离奇的女性的婚姻故事:尹雪青在年幼时,因父亲外遇导致母亲自尽,自己则在青年时,被人贩子卖于大山深处为妻生子,后终于逃出且依靠努力读了大学在高校任教,有了有身份的丈夫及体面的大家庭,但在大家庭于大酒店聚会时,却认出了那在大酒店当服务生的却正是被自己在大山里遗弃的孩子,这孩子仅仅凭着模糊不清的传说,来这个城市寻找自己的生母。这小说写得故事十分感人,其力量则在于让读者看到了,在当下那些表面光鲜的家庭中,或许有着只有当事人知道而不为我们所知的各种强大暗疾的存在,只是小说是以超常态的曲折离奇对这暗疾以突出的呈现。
虽然2015年度的山西中短篇小说在“尖兵”方面取得了如上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甚至是重大的不足。山西在近几年,官场的反腐,政治与经济关系动荡所带来的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在国内特别突出。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亦一向有着近距离关注并直接反映时代性的重大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传统,如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山药蛋派”的“新、短、通”、“晋军”的农村题材及“高知”题材写作、张平的社会问题小说等等。但在2015年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对如此尖锐的时代矛盾及其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动荡,却没有作出全面深刻的反映与揭示。究其原因,或许与老一代作者相对疏离现实生活有关;与新一代作者相对更多地是从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进行创作有关——新一代作者自身的生命经验,毕竟与时代性的重大的社会矛盾有着相当的距离;也或许与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文学创作正在从侧重于对社会的再现,转入对自身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在这方面创作的缺失,总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二、“后卫”
在新旧社会形态的时代性转型中,作为“后卫”,表现业已逝去的历史时期中最具光彩的碎片、插曲、尾声,既是对过去时代的忆念与回望,更是在这忆念与回望中,应对着新的时代因缺失而产生的情感需求及价值危机。在2015年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这种“后卫”形态,主要是通过对过去时代的人生形态、对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书写来完成的。
在山西2015年中短篇小说对过去时代人生形态的忆写中,葛水平的《望穿秋水》、曹乃谦的《初中九题》《高中九题》、杨红的《山谣》成就显著。在社会转型后商业文明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冲击所形成的人生价值的动荡中,如何看取建国后十七年的人生形态对于今天人生形态人生意义的作用,成为当今时代的热议话题。《望穿秋水》以一个主要发生在1960年代的动人的人生故事,令读者在感动之余不由会联想、深想许多。这部小说写在李氏家族为主的李坊村,闫家倍受歧视,十六岁的女孩子闫二变虽心仪会计的儿子李要发,但李家却压根看不起她。但在1961年那样的革命年代里,闫二变依靠自己在集体劳动中的突出贡献,走出了她母亲“一辈子也就是灶膛前的一个黑影”的人生轨迹,作为劳动模范,收获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社会对她的尊重。在城里积肥时,她相遇了崇尚劳动并送她小人书《山乡巨变》的城里“瘦高个男学生”并因之对社会、人生有了更高更广阔的追求。所以,虽然李氏村支书主动为她说合李要发,但却因为闫二变心中向往着“瘦高个男学生”这新的形象而为闫二变所拒绝。世事沧桑,一晃闫二变从十六岁到了六十岁,“瘦高个男学生”再未出现,闫二变独身一人却向往依然,只是这向往终成虚幻。在这个动人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在过去倍受重视而于今天被轻视的劳动的主题,看到了在一个时代里,集体劳动如何改变了人的命运,作为革命文化载体的集体劳动如何变革了家族性的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与价值结构,看到了混合着革命文化的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召唤及这召唤最终落入了虚幻之中,看到了在时代变革中觉醒了的个人及个人在觉醒之后与时代交错而带来的甜蜜与苦涩、正剧与悲剧,并由此联想、深想到了建国后十七年与今天时代的逻辑关联及在这关联中个人命运与时代变革的错位关系。单纯而又清晰的故事中,蕴含着如此丰富而又混沌的社会意蕴与人生意蕴,这正是大作品的气象。
近年来,曹乃谦一直在创作他的“九题系列”。在2015年他的《初中九题》《高中九题》中,我们看到了1960年代的时代风貌与人生风貌。真实性与素朴性是这作品最为主要的表现特征,你甚至可以说,这些小说是长篇散文、纪实文学、非虚构写作等等。中国传统文学是意象性文学,构成这意象之“意”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中,以退回内心世界求平衡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构”,所以,中国传统文学少有直面社会与人生的真实而更多的是满足自己心理意愿的意象性真实。这一传统,在建国后的共和国文学中,其意象之“意”又常常与某种观念形态如革命观念、文化观念“同构”,构成一种观念性真实。在这样的传统与背景下,曹乃谦小说的真实性、素朴性追求,就显得特别可贵且其特别可贵之处还不仅仅如此。新世纪以来,甚至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界的思想性标高,更多地体现在史学界而非文学界,是通过史实的真实还原,“敞亮”被“遮蔽”的“存在”并构建新的观念形态。相应地,非虚构写作,在这一时段的文学创作中,也因之而有了丰硕的收获,在纯文学日益边缘化之时,却有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但无论是史学界对史实的真实还原,还是非虚构写作,均偏重于用针对“大历史”的带有观念性的“小历史”来解构“大历史”,曹乃谦的《初中九题》《高中九题》却着意于呈现针对性指向性并不鲜明的民间的“小历史”,并因了这“小历史”种种具象、细节的鲜活,给读者以回望过去、回望人生以多种意义与回味的可能,这正是其超越史学的文学魅力之所在。
如果说曹乃谦的小说以民间“小历史”的真实性、素朴性著称,那么,杨红的《山谣》则以山乡民间纯净情感的抒情性而令读者难忘。小说以从城里到山村武城头下乡工作的杨干部在山村的经历为主线,写了在历经战争与政治运动风云中,山村乡民那顽强的生存能力与纯净的人性与情感世界。受尽日寇奸污的喜鸾,身上带着日寇刀劈的长长的伤痕,流落武城头,从此长期装哑,但却保有顽强的生命力——从容迎对山间狂暴的“黑旋风”即是形象一例,且在多灾多难的生活中,丝毫不失善良多情本性,那就是她对杨干部的女性情怀。看重自己情感世界的张兰花,在现代世风未开的封闭乡村勇于抗婚,却又为着自己多情爱着的杨干部,在杨干部的婚爱场上主动抽身而退,宁愿默默地长期关爱。还有身世、历史复杂的乡村教师张文彩,历经动荡,心静如水;还有积宽,虽然曾一度情迷神乱,但最终仍人性不失。小说中所写那凶险的“黑旋风”、山乡自然美景、孩童嘴里的民谣与山村乡民本然的生存形态、纯净情感,构成了不容雕凿的自然,是一曲温暖人身心的山谣,倒是城里符合国际规定的科学、符合社会规范的人伦,让主人公杨干部命丧黄泉。两相对比,引发了身处现代都市文明之中的读者,对那远逝了的山谣的无尽怀念,并在这怀念中,构成了对现实的精神性情感性的批判力量。
还应该一提的是,王保忠的《寻找父亲杨树林》作品写身在安徽的杨树林,青年时代去内蒙购买菜籽患重病时,与一位女性相爱,答应即使到八十岁时,也会来娶她。为了这句承诺,这位女性一直死等了几十年,甚至被家人视为患了疯病。而杨树林也在七十多岁时,为了履行诺言,从安徽赶往内蒙,最后死于去内蒙的路上。作品用在男女情爱关系上相对少了约束的杨树林的儿子的视角叙述这一故事,更加凸显了过去了的一个时代中那对男女情爱诺言信守品格的可贵,并在这一回望中,让人反思当今时代男女情爱中承诺品格的消退。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年纪念年节,所以,对抗日战争的回望构成了山西2015年中短篇小说“后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作品有小岸的《连翘》、杨晋林的《逃兵》、王保忠的《一路相伴》、郭永东的《搬仓鼠》和李迎兵的《复仇》等。一瞥近两年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大抵不脱对教科书的形象化反映。按说,中短篇小说在这方面应该有长足的进步,但纵观2015年山西表现抗日战争的中短篇小说,亦无更多的令人称道之处。除杨晋林的《逃兵》通过“逃兵”农穗最后被作为真正的逃兵处决、镇长猴脸错把农穗当日本兵杀反被农穗杀死而写了战争中个体生命命运的无常外,值得一说的,大多是集中于写战争中人性的复杂。《连翘》写当日本人索要“花姑娘”时,作为村长的郭秋山,担心村里人遭殃,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已经变傻的国军女战士顶替“花姑娘”上交,并为她起名“连翘”。连翘被关进日军据点轮番糟蹋后,彻底成了女疯子。日军投降后,郭秋山对连翘不离不弃。解放后,郭秋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入狱病亡,村民们继续照顾连翘。《一路相伴》写因倒卖一车军粮而被边区政府处决的抗日村长赵明之鬼魂,与作为继任村长的“父亲”一路相伴,无论怎样饥饿至极,无论怎样千回百转,最终将一担军粮丝毫无损的交付完好。《逃兵》中的晋绥军士兵彭大笨,溃散路上,抢劫民财民女,甚至想枪击同乡战友农穗,但最后是在与日军的战斗中死于日军刺刀之下。晋绥军士兵武秀在溃散路上,强奸民女,打死民商,最后陷害战友农穗是逃兵而置农穗于死地,但他在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也是一个血人。吴老栓父女为农穗所救,但吴老栓却贪财而将农穗捆绑于麻袋之中几置农穗于死地。在《搬仓鼠》中,作者也试图通过写日军少佐对妻子的怀念,写出日军军官人性的一面来。《复仇》在写日军的残暴时,也试图写出抗日一方的暴行,譬如孩子们将汉奸血糊淋淋的断腿像玩具一样抛来玩去;譬如将无辜的汉奸的妻子像物品一样分给穷人作妻子。但相比较作为“历史大事件”的中日战争来,相比较德俄反映二战的文学作品来,这些对中日战争的描写都显得分外肤浅。这一重大局限重大缺失,不独山西作家有,乃是中国文坛一大弱项,其中原因,有待反思。
相较2015年山西中短篇小说的“尖兵”任务,其“后卫”任务显然有所不及,这或许是因为“尖兵”更多地需要对今天时代的敏感,“后卫”则不仅需要对今天时代的“敏感”以确立回望的视角,还需要回望过去时的文化、情感的积淀,相较之下,其“后卫”难度远大于“尖兵”。
对于2015年山西中短篇小说的考察,因为与2015年山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近于同步完成,所以,时间距离的过近,也许影响着我们对其“肌理”清晰的透视,希望我们今后仍然给以进一步的审视与剖析,有着更新的发现,更到位的论析,也希望已经呈现给我们的2015年山西中短篇小说的经验与教训,能够给山西乃至中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以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孙犁:《谈赵树理》,《赵树理研究文集》(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4-25页。
②王晓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82页。
③钱理群:《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责任编辑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