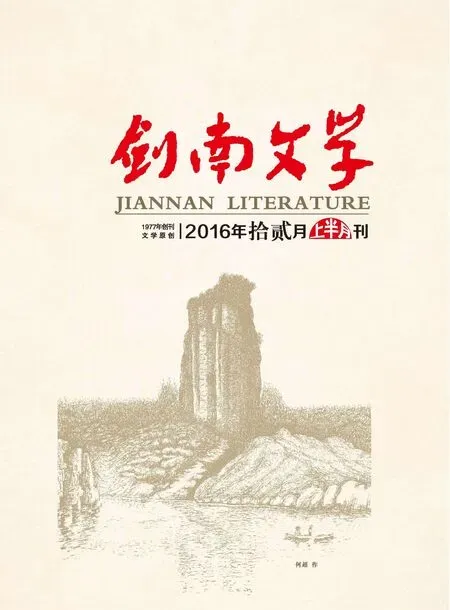枫树林
□石吉庆
枫树林
□石吉庆
枫树的叶子红了,就意味着又一个深秋来临。
刘桂兰从枫树林走了出来,头发有些凌乱,前面的刘海上还挂着一些干枯的草叶儿,她一边走一边用双手扣着衣服前边的两排纽扣,神色有些慌张,面上却带着红润,与枫叶形成了一个色调。她胸前的两个乳房还鼓鼓的,不知是胸罩弄得有些不舒服,还是没扣好后带,她又把手伸进了外套内去打理了一阵肩带,就向这边走了过来。五分钟以后,枫树林又一阵响动,接下来就有了“沙,沙,沙”的声音,接着又走出来一个男的,头发有些蓬乱,脚有点跛,走路一踮一踮的,一看便知道是丁三娃,他一边走还一边捆着裤带。
我站在楼上看着这一切,眼睛里充满了愤怒,恨不得拿把刀将这对男女砍死在枫树林。但我并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
刘桂兰是我母亲,四十二岁,父亲在两年前去世,我一直认为,父亲的死与她有关,但我不能说,一旦说出来,这个家就完了。至于这一切,我认为不是我母亲的母亲刘桂兰内心一定也有她的苦衷。
李峰,你站在这干吗?刘桂兰上了楼,见我站在阳台上开口问道。
没干吗?只是站在这,站在这看看父亲栽的枫树林。
刘桂兰听了我的回答没说什么,只是站在那动了动嘴角,马上又翕上了。
其实,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但我不希望她说出来。
父亲死了两年,留下我一个傻子,刘桂兰这两年里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一直照顾着我,她的事我看着,又恨又不想挑明。
我转过身,用眼睛看了一眼刘桂兰,说:我饿了,想吃饭。刘桂兰连忙说:“饿了,我去做饭。”对于一个傻子来说不思考什么,除了吃就是睡,刘桂兰早就适应了我的生活,也知道我要干什么。
接着,厨房里“咚,咚,咚”传来了剁土豆丝的声音。
我站在阳台上没动,享受着这深秋的阳光,晒在身上有一种舒服的感觉,那感觉我说不出来,但是心中总有一种光亮,这光亮还伴随着某种力量。
傻子,接着,丁三娃就站在房前,向我抛来一只红桔,我“嘿嘿”一笑,接住了那只红桔。
你不傻嘛,这都能接住。李峰,你站在阳台上看见什么了?
他这么一叫我的名字,而不叫我“傻子”的确有些诧异,这么多年来,除了父亲和刘桂兰,没谁叫过我的名字。他见我望着他笑,只好一边叹息一边摇着头,一跛一拐的走了。
吃饭了,刘桂兰今天将一张折叠桌放在了阳台上,端上土豆丝,打上饭菜,和我面对面地坐着,我放下手中的红桔吃起了饭来,当我爬头扒饭时,我眼光瞥了一眼刘桂兰,她衣服上面的两颗纽扣没扣上,透过缝隙,我看到了她的一对饱满而洁白的乳房,而乳头也被我发现了。我马上扒了一大口饭,让自己尽量稳定下来,我要让她明白,我永远是个傻子,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傻子。
吃了饭,刘桂兰收拾碗筷去了,我手里又握着了红桔,不知怎么,当我握住红桔,就想起那乳头。我知道,这一切将成为我抹不去的影子。
丁三娃下午闲着没事,来和我说话,他问我:李峰,上午你看见上什么了?我再一次诧异他为什么不叫我傻子。我喜欢别人叫我傻子,我觉得越傻越好,我的心里不勉有些难受,只是“嘿嘿”地笑。
他是站着的,见我不答,就干脆一屁股坐下来说:我看你不傻,你的聪明埋在心里。我还是什么也不说,我越不说,就越要让别人证明我傻。
刘桂兰吃过午饭,收拾好锅灶就到地里挖红苕去了,她忙了一个下午,挖了两大箩筐红苕,天渐渐暗了下来,丁三也站了起来,向红苕地里走去,不一会儿,他一瘸一拐的把两大筐红苕担了回来,我还有些纳闷,一个瘸子,怎么能把这么重的担子担起走。刘桂兰背着苕藤紧跟在丁三的后面,肩上还扛着一把锄头。
丁三娃这天晚上在刘桂兰的挽留下,在我家吃晚饭,本身上午我还恨这对男女,晚上突然间改变了看法。
晚饭时,刘桂兰坐下来,给丁三倒酒,这酒是“丰谷二曲”,五元钱一瓶。今天还宰了只鸡,刘桂兰用青辣子、花椒把它红烧着,味道非常不错,一向不喝酒的刘桂兰也酌了满满的一杯,就和丁三对饮起来。
这傻子的爹如果还在,家里就不缺男人了。刘妹子,对不起,李大哥的死,我有责任。丁三说着就开始流起泪水来了。
两年前的春天,父亲把门前的包产地全栽了枫树,叫刘桂兰在家管理,自己和村里的一帮人去山西挖煤,其中就有丁三,可是刚入秋时,刘桂兰就接到通知,父亲所在的煤窑由于渗水,塌了,井下四十多人全部被埋,经过全力抢救,救上来三十八人,死了五人,其中五人就有我的父亲。丁三娃被救出来,脚踝伤了,医了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每当想到父亲,我就会发生幻觉,我觉得父亲的死一定与丁三有直接或潜在的某种关系,我常在梦中梦到。
煤窑里人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着,丁三和父亲就在一起,机器的轰鸣声正在“哇,哇”地嘶吼着,父亲大叫一声不好,只见一股巨大的洪水涌了进来,父亲急忙向后面跑去,可刚跑几步,见丁三一下子被水冲扑在地上,父亲大叫“丁三,快跑!”接着转身又去扶丁三,刚扶起来,轰的一声,煤洞蹋了,父亲一把把丁三推了过去,父亲却被蹋方埋了。
我不知道这梦是不是现实的,但我相信它,就像我三岁时,亲生母亲因为吃不饱而得水肿病死时一样,我坚信父亲几年后会给我找个后妈,果然在我十岁那年,刘桂兰就被父亲娶进了门,也在那一年刚读小学四年级的我也犯傻了,上课不知道老师讲什么,整天坐在凳子上“咯,咯”的傻笑,老师没办法,就叫父亲把我带回了家,父亲和刘桂兰没少给我求医,就是没有好转。一天深夜,刘桂兰带回一个相貌极丑的女人回来,目光鼓得很高,手持木剑,把纸钱挑在剑端,舀来一碗水,嘴里念着“哞哩,哞哩轰!”左手一扬,一把白色粉末一闪,一道火光就在剑端亮了起来,然后喝一口水,从口中喷出来,火就熄了,那女人就坐下来休息,说我中了邪,现在被她驱了。经过这以后,我傻笑时少了许多,不过我一直在思考那被燃料的粉末是什么?我前几天才知道,那粉末叫磷。
后来,父亲说:“那神仙,灵。”
刘桂兰也说:“灵。”
刘桂兰和丁三喝酒,都有些醉了,就说起了父亲的死,说话的时候还不时地看着我,他所说的就是我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说到激动处他就双手搭在我的两个肩上摇晃,刘桂兰就会说:“别摇他,他一个傻子,懂什么?”
丁三不再摇我,放下酒杯说,刘妹子,我走了,说完就迈步出了门,刘桂兰没有留他,就坐着,又倒了一杯酒,把一瓶“丰谷二曲”给弄了个底朝天。然后一口喝了。
我看到刘桂兰从脸到脖子都红了,然后关上了门,走过来用眼睛盯着我说:你爸死后赔了五十万,我给你存着,我不会动你一分,别人也别想,我会给你娶个媳妇,娶不到,买也要给你买一个。我没说话,还是有傻笑。
刘桂兰和父亲结婚早,但就是没生育,她刚来我家的时候,父亲房间里总是发出一些异样的声音,要么是床响,要么是女人的叫声。隔壁的我看着屋顶的梁,好几夜没睡着。后来,父亲带她去检查,才知道,她没生育。回来时,父亲摸着我的头说:“看来,这就是我的命哟。”父亲说这话时,语中透着一股悲凉。
关于父亲的死,我没有悲哀过,我站在阳台上望着日渐成长的枫树,我一直坚信父亲活着,活得比我还好,我不会表达,父亲一直藏在枫树林里不愿意被我们看见而已,要不,不是父亲的浇灌,这枫树林长势怎么这么快,而且茂盛。
那夜,我没睡,我睡不着,我知道今晚上我整整十八岁了,刘桂兰宰鸡的时候我都意识到了。十八岁,对于一个男孩来说,应该有担当,有责任,但我怕,我宁可继续当个傻子。
我躺在床上,手一伸,触到了丁三上午给我的红桔,上午我没吃,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这时,我握在手里,就想起中午吃午饭时看到刘桂兰的乳头,和这桔子是一个色泽,想到这,我觉得我下身就有一股冲动,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我这一刻才感觉到,我是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了。
丁三来了,敲开了我家的门,带来了一脸的微笑。
开门的是我,他见我很诧异,就说:李峰,我要做你的父亲,行么?我摸着头,还是一脸的傻笑。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要娶刘桂兰,他又没房,他想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丁三一直是单身,父母死得早,给他留下了两间土坯瓦房,檩子是竹子做的,年代久了,快要倒了,更别说娶老婆,自从父亲去世后,我们家干农活需要男人,他常来帮忙,就私下和刘桂兰在枫树林有了风韵轶事。
他们第一次在枫树林干那事我都知道,我的内心就有一种预感,当时,我睡在床上,感觉床动了一下,就翻身起床,看见刘桂兰与丁三一起走进了枫树林,接着是一阵狂风吹来,把枫树林吹得“咯咯”地响,似乎树杆要被风折断。那一次他们很快就出来了,我知道,那是父亲在发怒,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干那种事,所以,从那次起,我坚信,父亲一定活着。
虽然我是个傻子,我只上过三年级,上四年级不到一个月就被送回了家。我偷偷的学习,七八年下来,我认了不少字,为了证明自己是傻子才傻笑。背地里我开始写小说,趁着发疯的表情到镇子上寄过几次稿件,可是寄后没抱发表的希望。
丁三没经过我的同意,在一个黄昏,搬进了我家,和刘桂兰住在了一起。我知道他们无须我同意,我是一个傻子,几乎与这两个人之间根本就没一点关系。但唯一有关系的是这两个没关系的人住进了原本属于我的房子。我又不好去争论,我想继续做个傻子。
没有争论,我只好让他住到一起,一起干活,吃饭,睡觉做爱,一切自然地从天亮到天黑,又从天黑到天亮。
这段时间,除了吃饭,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无论外面是吹风,下雨,似乎与我没有关系,只是偶尔站在窗口向外张望,看一下枫树林,它们落了叶子又长出了新芽。
这段时间,我开始做梦,梦里总有一个女孩走来,和我牵着手走进枫树林,然后拥抱,然后躺下……
这个冬天,我坐在床上,白天关上门悄悄地写我自己的故事,故事里写我对女孩的思念。
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是个男人,无法让自己再傻下去的男人。
吃早饭了,刘桂兰一个人在家,丁三去外地打工,去了三四天没回来。
“妈”,我叫道,声音极小,这是我第一次把刘桂兰叫妈,也是第一次以一个正常人的方式叫她。“妈”,她没听见,我又叫了一声。这下,她听见了,她抬起了头,两只眼睛盯着我,慢慢地,我看到了她的眼里饱含了泪水,越积越多,从眼眶里争先恐后地奔涌出来,她一把拼命地抱着我,嘴里叫唤道:“孩子,我的孩子。”好像我真的是她亲生的孩子一样。
“妈,给我点钱吧,我想去镇上。”
“要多少?妈都给。”
“一百行吗?”
“行。”然后,她一个劲的点头。
去镇上前,她给我找来了一些刚买来的衣服,皮鞋,将我打扮一番,还把我从前看到后,从左看到右,不断地说:“像,太像了,像你的父亲。”
那年,枫叶又红了。当我站在阳台上望着那片红了叶子的枫树林,我还坚信,我的父亲活着,就在枫树林里。
入秋以来,下了一场不小不大的雨,把红了的枫叶吹掉了,站在楼顶,我望见了一棵棵树干,它们相互依衬,又保持着距离,就如我与刘桂兰、丁三之间的关系。
刘桂兰并没把我叫她妈的事告诉丁三,不知她认为没必要,还是我这个人根本与丁三没一点关系。无论怎样,她的心中荡起了一层涟漪。我回来时她的面上还带着喜悦。晚上她坐在我对面看我吃饭,还为我夹菜,我的心里有一种不安,我知道,这种不安意味着将会有不幸的事发生。
吃完饭,我洗了个澡,就进了卧室,躺在床上睡觉,可是,外面的雨又下了起来,滴答,滴答的声音从窗外传进来,弄得我心绪很乱。偶然间,我听到屋内有来回踱步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刘桂兰,她今夜无从入眠,自从和父亲结婚到父亲死,又从父亲死后她无怨无悔的照顾我,我都没叫过她一声,然而今天叫了,叫的还是“妈。”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第二天,我还躺在床上,刘桂兰就在门外大声叫唤:李峰,李峰呀,快起来呀!房子淋跨了。那声音很响,如一阵雷声。我不得不起床,打开门,看到了她一脸惊惶的神色。我揉了一下眼,四处望了望,问:房屋没倒吧?“倒了,真倒了,丁三的房子倒了。”我一听笑了:他那几间破房子,早就该倒了,你惊慌什么?说完我又“嘿、嘿”地笑。刘桂兰这时很惊异,用手在我眼前晃了晃道:李峰,你不会又变傻吧。
刘桂兰到隔壁邻居家打电话去了,给丁三打,告诉他房子倒了。电话那头,丁三笑了:倒就倒吧,从今以后我就住你家了。刘桂兰听了脸上也略显微红,在电话里骂了一句“死鬼。”
我说桂兰呀!你和丁三把结婚的事办了吧,你们挺合适的。邻居瞅准时机向刘桂兰说。
我坐在屋里,望着窗外的雨,看着枫树上稀疏的枫叶,如一个秃顶的老人,耷拉着脑袋,我看清了自已昨天的一切,这让我开始后悔起来了,我此时此刻还希望过着傻子一样的生活。
我不能再傻下去了,我十八岁了,我认为,十八岁前都可以傻,何况我是个没娘的孩子。到后来还有个后娘,可那时我并不喜欢她,我只能傻,而且装傻,装傻没什么不好,如今,再傻下去对得起自己是个男人吗,难道这个家要让两个与我不相干的人来担当,特别是刘桂兰,她够苦够累了,我总不能老是装疯卖傻地让她继续苦下去。尽管我一直认为她对父亲的死有一定的责任。
刘桂兰与父亲的关系不错,前几年,家乡经济有些活跃,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出门打工了,夜里,刘桂兰对父亲说:我看呀,你也出去打工吧,家里我照顾李峰,没事的。其实父亲,早就有出去打工的念头,只是觉得我一个傻子没人照顾,又不好托刘桂兰,刘桂兰主动提出来,父亲当然就放心了。
父亲要走的哪个夜晚,刘桂兰早早地就进了房间,父亲也进去了,我还坐在灯下发呆,他们谁也不管我,我知道他们认为,我一个傻子,不用他们管,至少知道自己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夜特别的静,连我自己喘气的声音都听得见,突然,我听到一阵呻吟,一个女人的呻吟,我仔细屏息聆听,那是刘桂兰的声音,接着又听到父亲的喘息声。但我不想打挠他们,进屋仰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似乎有一种悲哀的心境,接着又仿佛看见刘桂兰的脸上挂着泪痕。第二天,父亲走了,留下了他去年开春栽下的枫树林。
雨停了,刘桂兰去了丁三跨蹋的房屋处,看有没有值得捡回来的东西。除了一堆烂泥,就是一些生了虫的竹子,的确没什么值得捡的东西,刘桂兰回来时两手空着。
我十八岁了,我得找事情做,为这个家分担点责任。不过在走之前,我得走进父亲栽的枫树林看看,自从父亲栽过枫林之后,我一直没走进去看过。
清晨,阳光刚升起来,我今天自己换了套衣服,很是庄重,来到枫树林前,先向枫树林叩了三个响头,站起来抖去身上的尘埃,才往里走,我认为这样才是对父亲的尊重,才能进入父亲的领地。
我走了进去,里面除了一些落叶,还有一些光秃秃的树干,什么也没有,我四处张望,看到林子深处,有一座坟茔,前面有一块碑,我走近一看,碑文上刻着,丈夫李大力之墓,妻子刘桂兰敬立,旁边还有我的名字。我知道,父亲被埋在井下,没找到尸体,刘桂兰是空手回来的,回来时带了一笔钱。
刘桂兰回到家里,找了一些父亲的衣物,和一些人去了枫树林,而我却坐在屋内发呆,我知道我失去了父亲,我很伤心,世界上没有谁体验过在失去母亲后又失去父亲这样的悲伤,这种悲伤还不能表达,因为一个傻子不会表达悲伤的。
原来,我一直坚信活着的父亲是一座坟墓,那坟墓是父亲的影子。我双膝跪下,不敢抬头,只是一个劲的磕头。
起来吧,孩子。刘桂兰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身后,她走过来扶我,我没要她扶,站了起来,转身走向了林子外。
后来,我到了镇子上,四处找工作,在一家私人的租书店帮人守书摊,书摊老板对人不错,除去住宿和生活,每月给我一百四十元工资,闲暇时可以看书,晚上写小说。
一场春雨过后,我的小说在本市的副刊上用了,我便成了当地的名人,丁三也回来了,他和刘桂兰结婚了,结婚哪天,我回去了,婚礼很喜庆。丁三一直笑着,刘桂兰也笑着,而我的心里有一种无名的难受。我站在窗前,木讷地望着窗外正在发芽的枫树。
李峰,刘桂兰和丁三走了进来,刘桂兰手中拿着一张存折:来,这是五十万,你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我没敢动,现在该给你了。
我拿着存折,心情很难受,我感到有无数只虫子在叮咬着我的心脏。我哭了:妈,你替我管着吧,我信任你。
没风的枫树林,突然间摇动起来了,而且树冠朝一个方向倾斜,像人在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