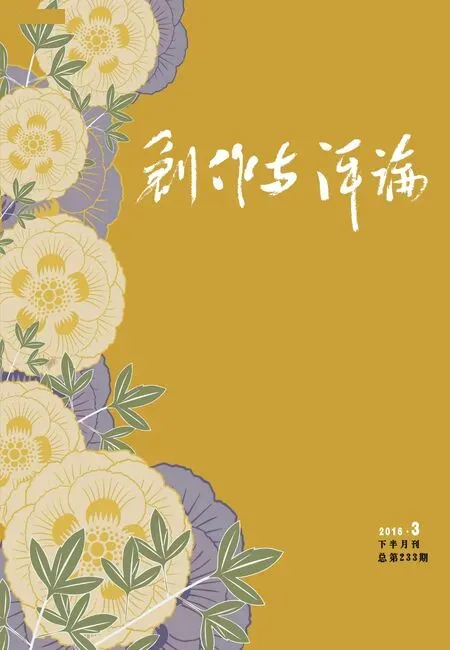一个人的散文世界
——评刘明霞散文集《临水而居》
○伍世昭
一个人的散文世界
——评刘明霞散文集《临水而居》
○伍世昭
我用“世界”来指称刘明霞的散文,乃就其散文整体而言的。当其多样的散文体式统一于完足的思想艺术整体时,其散文世界便自然形成了。而多幅笔墨、多种艺术手段及其所传达的日常叙事、人文关怀、诗意栖居与怀旧情结,便是构筑其散文世界的基本元素。
一、多幅笔墨
就《邻水而居》这个集子来看,刘明霞的作品涉猎到了多种不同的散文体式:既有传统意义上的以写景、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散文”,以说理为主的杂文;也有以人物塑造为主的特写,以文化事件为表现对象的文化散文;甚至还有文艺评论。尽管作者本人在分类上并没有更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在具体作品体式的把握上却是十分到位的,而且每一种样式中都有诸多佳作。
《邻水而居》是一篇以写景为主的作品,写了一个城市与水的不解之缘。作品对西湖的描写细腻、真切,饱含作者的深情。文题富有诗意,结尾的抒情余音袅袅、言有尽而意无穷,强化了标题所蕴含的诗意。《另类报人》是一篇人物特写,篇幅不长,但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其脱俗的打扮和不与流俗相类的举止相得益彰,让人印象深刻。《读书如吃饭喝水》是以说理为主的杂文,其“读书如吃饭喝水”的比喻大俗而又大雅,其理甚明。文章没有犀利的言辞,却很有说服力。其对伪读书的批评与对读书方式的看法,相信亦为多数读者所认同。《带着墨香的白鸽》是一篇文艺评论,重点写“我”与香港儒商“李老师”的文学交往,以潇散的笔触集中突出了对方为人的“诚挚”和人文情怀。《用时尚解开水东街的情结》是一篇文化散文力作,其对水东街的描述大气深沉,历史与现实交融,文化景深与情感律动共振,获致了非同一般的审美效果。刘明霞五彩斑斓的散文世界即由上述多种笔墨、多种样式构筑而成。
刘明霞驾驭多幅散文笔墨的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散文本身体制宽松、体式多样(除作者涉及到的几种体式外,甚至日记、报告文学、通讯等亦属散文文类),作者选择的空间较大而较少文体方面的担忧。二与作者的作家与报人两种身份、双重视野有关,《邻水而居》集子中的人物特写、文艺批评和一些出自采访视角的作品如《客家山村踏歌行》《龙门有两幅面孔》等,就与其报人的身份不无关系。三是作者感性与理性平衡的秉性使然,感性激发灵感,理性带来哲思,这就是作者一方面有写景、抒情、叙事之作,一方面又有文艺批评、杂文、文化散文的原因(这个特点在具体作品中也有体现:少纯粹抒情、写景或说理,而多有机兼容)。四是得益于作者个人的美术、音乐等多种艺术素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艺术散文、人物特写与文艺评论的写作。
二、人文底蕴
刘明霞的多幅散文笔墨所传达的人文底蕴可以用几个词组来概括,那就是日常叙事、文化关怀与诗意栖居。
刘明霞散文中有诸多指涉日常叙事的篇章,触及的生活范围较广,如吃(《在土桥村拼贴味觉》)、玩(《与音乐和美酒相约》《在新葡京赢了350元港币》)、购物(《这周有没人去香港啊》《走在高雄的大街上》)、开车(《我开车的“威水”史》)、探病(《病房里的市井》)等等。散文集《邻水而居》整体上自然平实的特点在这类散文中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作者以絮叨的笔触、平视的态度讲述了种种私密而又普遍的生活经历,引人共鸣。但作者绝不仅仅停留于对生活作表象的描摹,而善于发现隐藏在表象中的独特人文“意味”。《在土桥村拼贴味觉》将自然清新的土味与视觉时代的恶俗相比照,让人感悟什么才是最需要的和有价值的。《我开车的“威水”史》等几篇写独自驾车的忧与乐、险与趣,虽没有太高远的立意,但仍然具有普遍的人生意蕴。《这周有没人去香港啊》《走在高雄的大街上》则都由购物升华开去,或与港惠两地的文化交流相勾连,或由此去思考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问题。《与音乐和美酒相约》写的是酒吧及其音乐与美酒,但文化的思考却始终“在场”。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出自居高临下的教训,而大都是自然流露、点到为止的。《病房里的市井》是一篇值得重视的佳作。该文写人们习以为常的探病经历,却别开生面地将笔墨转向对“病友”之间的“较劲”——“显摆”的描述上,其以小见大的立意(小病房是大社会的“浓缩”)与独特的构思让人刮目相看。此外,该文对人情世故的描写也有着很强的表现力,朴质逼真、真切传神。
《邻水而居》体现了作者较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审美文化、民俗文化、市井文化、城市文化,甚至是遗址文化,都得到了其深度关切。
在上述诸种文化类型中,审美文化得到了作者更多关注,给读者的印象也较为深刻。《小众电影》是对日渐式微的电影艺术的聚焦,文章饰之以“小众”,体现了作者对江河日下的电影艺术的叹惋和不甘。《一嗓子把人吼到山西》是对山西原生态民歌的感悟,作者陶醉于其质朴自然的艺术魅力,又情不自禁地思考着原生态艺术的未来。《客家山村踏歌行》《龙门有两幅面孔》则分别是对客家山歌、龙门农民画的考察。作者关注审美文化的关键词应该是“传承”二字:无论是对拥有1500年历史的原生态山西民歌艺术发展的思考,对客家山歌的收集整理与艺术提升的描述,还是对龙门农民画创作盛况的由衷赞叹,都说明了这一点。文化遗址散文篇章不多,但质量上乘,《用时尚解开水东街的情结》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沉雄大气,富有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其关于水东街“时尚与艺术新地标”的定位,寄托了作者的深厚的人文情怀,因而作为一家之言,理当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如果仅仅是时尚与艺术的联袂,似还不足以打造城市文化的“特色与个性”。就水东街而言,如果能考虑到作者常说的怀旧元素,也许对达成这一目标有所增益。此外,《我与下角》所涉及的市井文化、《既然叫大王》中的民俗文化,都值得读者去感知。
文化的传承与葆有事关感情的慰藉与精神境界的提升。在作者眼中,“一条老街、一座老桥、一栋骑楼、一首老歌”,不仅“镌刻着先人走来的痕迹”,而且隐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源头”(《用时尚解开水东街的情结》);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很容易在客家歌曲中找到乡音乡情的共鸣”和“族性认同感”(《客家山村踏歌行》);而一场音乐会、一首经典圆舞曲则会使人“一瞬间远离了那纷繁喧嚣的现实”而经受灵魂的洗涤。这后一点已涉及到诗意栖居的问题了,因为诗意的栖居正是以跳脱功利的牵扯为前提的。
对诗意栖居的肯定、向往,是散文集《邻水而居》的一道重要人文亮色。这里的“诗意栖居”,即指跳脱功利欲望的束缚而获得精神自由的本真存在状态。我们看到,无论是对木棉花“摆脱世俗”“守住生命质量”的礼赞(《天幕上的舞蹈》),还是对拉琴者烂漫情怀的共鸣(《西湖边,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拉琴》),抑或是对自然纯真人性的期盼(《三人在芒果树下傻笑》),都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有关生命存在的价值取向。
在作者那里,诗意栖居首先与亲近自然相关。在作者笔下,“乡土那种阳光、树林、河流及纯净空气荟萃的气味”乃是“美丽、安然、宁静、和谐等一切人类最美好理想的归宿。”因而亲近自然,达成与自然的和谐,就成了实现诗意栖居的必然选择。作者在《石河》中说道:“客居山中的妙处就是,你可以将自己彻底地敞开,弃绝所有的装潢与伪饰……”所谓弃绝“装潢与伪饰”,其实就是本真自我的复归。作者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明确看法,我们可以在《邻水而居》中见到:“……水是人的衬景,人是水的释意,因了水的滋润,日子才生动,人与人才亲密。”这种和谐关系乃源于人与自然的“齐一”,作者游石河时的感悟很能体现这一形上思考:“石河果真是一个奇妙的背景,其实,人又何尝不是风景的背景呢?以生命的形式存在的人,不就是一棵树、一块石、或是一株行走着的草?”既然人是整体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人与万物的和谐原本就不是问题,只是由于文明的进步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才需要“重返自然”,以复归本真人性。刘明霞的意义也在于此。
其次与审美相连。《情调》篇这样写《蓝色的多瑙河》带来的感动:“那纯洁的蓝啊,使人自由如风,一瞬间远离了纷繁喧嚣的现实。陡然一阵感动,几乎要掉泪。”审美的特点就在于其超越性,既超越功利性,也超越逻辑性。当人们与美的艺术相遇或置身于美的氛围中时,往往会忘却现实关系中的诸多烦恼,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而当人们再次返回到现实关系中时,烦恼又将会蜂拥而至,而此前的自由亦随之消失于无形。那么如何持久地葆有这种精神的自由状态呢?那就是将艺术审美精神向日常生活迁移,实现日常生活方式的审美化。《我与下角》不止一次地对这种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作过描述,其中一处云:“湖畔生活,有山有水、有歌有舞、有琴有画、有书有酒,还有老火靓汤、烧烤、咖啡,这让我想起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更让我有理由去完整的歌泣生活。”这段话提到了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梭罗远离尘嚣、亲近自然,同样关乎本真生存状态的寻找与精神自由的追求问题。《我与下角》所描述和体现的,确与《瓦尔登湖》相类。
三、艺术魅力
刘明霞散文的艺术魅力来自诸多方面,如语言,构思,写景(叙事)、抒情、议论有机融合等。但若从第一印象所领受的审美冲击力来看,则意象的捕捉与运用,人物形象的把握与塑造,音乐元素的介入与渗透,似更值得讨论。
意象很长时间以来被视为诗的专利,这里用于散文的分析,是说其散文因了意象而有着诗的意味,平常所说散文的诗意即指此。“水”是《邻水而居》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意象(可见于近10篇散文),这既有作者所居城市水资源丰富的原因,也与作者本人的审美情趣有关。在作者笔下,“水”既创造自然美(《又不是绝代佳人》),又是“艺术的极致”(《石河》);既“滋润美人”和人们的“心田”(《惠州女人》《邻水而居》),又“藏着智者的哲思”(《我与下角》)。“水”创造美又滋润万物的特性与创作主体的情感投射取得了完美的契合。“木棉花”的意象尽管只出现一次,但很能见出作者的艺术匠心。作者准确捕捉到了木棉花“肥厚丰腴”“红彤彤的艳丽”“开于高处”“违背花与叶的辩证关系”“有的是一树红叶”的特点,又赋予其“舞者”的人格和“摆脱世俗”“守住生命的质量”的高贵气质,贴切而又富有象征意味。“盐酸菜”的意象见于《在土桥村拼贴味觉》一文。盐咸菜是乡间常见的家常食物,经济实惠,十分普通,几乎人人享用过。但当它作为一个意象进入刘明霞的散文时,立刻就获得了崭新的意蕴。它“口感脆嫩”“味道鲜美”“色泽鲜亮”;既平朴,又高贵;让人怀念“平和”“缓慢”的“庸常日子”。——附着在这一意象中的人生意蕴,得到了准确而温暖的抉发,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对乡土文明的深情眷恋。
值得注意的还有涉及文化遗址的系列意象,如“骑楼”“小巷”“石板路”等。“骑楼”意象主要见于《用时尚解开水东街的情结》,作品的描述颇为祥尽,不妨引用其中两段:“独具特色的骑楼有中西合璧的女儿墙,配以细腻精雕的窗拱……临街窗户上都是砖砌的圆心拱,窗拱顶部用太阳纹等图案装饰。窗拱外沿有雕饰线,支持墙体的是方形的柱子,柱子的顶部也有雕饰线。这些雕饰线工艺精美,线条流畅。”“建筑是凝固的历史,骑楼,像一根根柱子,支起了水东街的繁华,装饰各异的骑楼表现出的是水东街的性格……残旧的骑楼柱子布满墨绿的苔藓,栏下石缝里,不时盘根曲虬长出一两棵细叶榕和蕨类植物,给骑楼增添了一种古朴、浑厚的美。”这里不仅对“骑楼”作了细腻真切的描写,突出了其“古朴”“浑厚”之美,而且在此基础上将“骑楼”和一条老街的“繁华”与“性格”相关联,强化了其历史文化意义。作品对“石板路”(《路上的浪漫》)、“小巷”(《我与下角》)意象的描述所花笔墨尽管不多,但同样达成了创作主体怀旧情怀与对象“历史感”的高度拥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刘明霞散文写人的感觉和功力俱佳,所塑造的几个人物如“风”、老穆、向东、“我爸”“女儿”、韩石山均鲜活丰满,能给读者以深刻印象。其中的奥秘在于作者在细节描写、抓取特征、把握性格的丰富性等方面达到一定的高度和自觉。
好的细节描写能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刘明霞善于择取繁富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风”(《老街阁楼上的少年》)的形象主要就是借助细节描写塑造而成的。如“风”挂在租住阁楼墙上的霓裳羽衣、青铜长剑,牛仔裤大腿部位的“割口”,穿尖头皮鞋、德国品牌男装HlERS,扎马尾发,手臂上纹京剧脸谱,养一只名叫“秦颂”的小狗等等,就都是来自生活中的细节,逼真传神地传达出了“风”时尚、另类、自由不羁、“诗意地活着”等性格特征。“我爸”(《我爸》)的形象塑造也离不开细节的运用。如“老爸”教育小孩时要求孩子们“按年龄大小排成一排”,并“像军人一样立正站好”;耄耋之年仍穿着价值昂贵的皮衣、笔挺的西裤、铮亮的皮鞋;晚年切土豆“细若粉丝”等细节,就凸出了“我爸”的正统、军人作风、威严、注重形象、细心的性格特点。
抓取特征类似美术中的速写或漫画,寥寥几笔就惟妙惟肖。《另类报人》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文中的“老穆”最大的特点如标题告诉我们的就是“另类”,不仅穿着另类——花衬衫、半截裤、带卷边的礼帽、“一身唐装”;而且行事撰文另类,如评报“一针见血”,唱歌喜好“加花”,专栏文章“热辣”“扎眼”“才思喷溅”,让人忍俊不禁而又肃然起敬。作品文笔简练,多用白描,人物性格呼之欲出,让人经久难忘。虽不知“老穆”具体相貌(文章似有意略去外貌描写),见到也会一眼认出的吧。
把握性格的丰富性基于作者对人性的深刻体认。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性格丰富性的把握不仅符合人性,而且反过来还会帮助人们深入认识人性。《一个山西男人的责任与担当》写的是文坛名家韩石山。文章不说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与担当,而说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因为其责任担当是“全方位”的:作为一个作家,有“文坛刀客”之称;作为一个批评家,敢于“指名道姓真刀真枪”地批评;作为一名学者,治学严谨;作为一个市民,敢于批评政府;作为一个男人,正大光明地宣称喜欢美女;作为一个家庭的丈夫和父亲,情愿“拼命写稿”;而作为姥爷,会为了外孙而从台湾的宾馆里偷一个芭乐。文章写出了韩石山的超常与平常,富有人情味,从而还原出真实的韩石山。此种性格的丰富性在其他人物形象“风”、向东、“我爸”身上也能见到,这都绝非偶然。
音乐元素的介入与渗透在刘明霞散文中有突出表现。这并非出于作者有意识地创新,而源于一种审美情趣的自然流露。因为很显然,刘明霞不仅喜爱音乐,而且深谙音乐。
音乐元素的介入在刘明霞的散文中有多种不同表现形式,首先是直接以音乐为表现对象,如《一嗓子把人吼到山西》写山西原生态民歌,《情调》写新年音乐会,《与音乐和美酒相约》写酒吧音乐,《客家山村踏歌行》写客家山歌等等。其中《一嗓子把人吼到山西》《客家山村踏歌行》两篇大量引入歌词,《情调》则不仅对一些乐曲旋律作了精细描绘,甚至记入了《贼鹊》一曲的节拍调式。于这类散文而言,若说“满眼(耳)是音乐”,是丝毫不过分的。
其次是作品所具有的音乐色彩。《天幕上的舞蹈》可以说是一首散文诗,段落文字少则一行,多则四行,抒情性强,节奏明快,充满音乐的张力。《邻水而居》则以歌谣做结:“桥对桥,里对坊,烂地对马房;湖对岭,山对江,公廨对府堂……草把沽清出城直去河南岸,薯藤卖尺过艇回归水北乡……”余音袅袅,情韵悠长。《东江红都》亦以歌谣做结,收到了同样的艺术效果。
最后是与音乐相关的比喻、通感修辞手法的运用。关于比喻有两种情况,一是比音乐为他物。《西湖边,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拉琴》把小提琴的琴音必做“小鸟”:“音符跌落在湖水中,再通过湖水传出来”,“微弱的、稍纵即逝的音乐,想西湖中的小鸟一样,唯恐一不小心,惊动了它。”十分贴切传神,写尽了琴音的清幽之美。二是比他物为音乐。《石河》将幽谷中的水声比做“音符”:“踏着石阶往下行,真的是'隔黄竹,闻水声'了,哗哗的流水调频般把声音诠释得清晰而响脆,如一颗颗音符在两岸的树枝间跳跃、在树叶上穿行,那天籁之音从脚底漫上来,将我那颗跌落尘埃的心沐浴在这深山幽谷中。”这里的比喻将所写之景衬托得更加优美引人。通感手法见于《徽州女人》《天幕上的舞蹈》《石河》。前者说站在古老豪宅屋檐下“想起某一首老歌”;后者在描写木棉花时则说“该有一首曲调轻柔舒缓、歌词婉约优美的歌来伴随她舞蹈的”,都将视觉转换成了听觉——音乐,韵味完足。《石河》写音符“在两岸的树枝间跳跃、在树叶上穿行”则是听觉转换成视觉的例子,可谓诗意盎然。
不能遗漏的还有刘明霞散文所体现的怀旧情结。《爱情图解》对“老派典雅男人”严重稀缺的慨叹,《小众电影》对昔日电影艺术难以割舍的情怀,《大上海的老派细节》对上海老派细节的痴迷与沉醉,《寻找徽州女人》对“美到极致”的徽州女人的由衷赞叹,说明了:“怀旧”不仅是《邻水而居》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而且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在作者那里,怀旧总是与美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埋藏着对美的渴望和追求,不管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还是我们不未曾经历的,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种渴望和追求的执迷和疯狂。我们对美的体验,不是出自于理性的沉思,而是一种先天的反应。老派是一种古典的美,一种融入了文化和风情的美啊。”由于怀旧的对象已失却实用的功能,人们对它的怀想只关涉某种情感记忆而无理性的考量,因而某种程度上即可以说怀旧就是对美的沉醉。刘明霞的怀旧有一个不易让人觉察的特点,那就是常常与时尚如影相随、纠缠难分。《用时尚解开水东街的情结》一方面沉湎于对“一条老街”“一座骑楼”的“历史记忆”中,另一方面又期盼“让弃旧迎新的水东街披上时尚外衣”;《另类报人》从“老穆”时尚的打扮和“时尚画报上的潮流表情”中联想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格里高里·派克那类的老男人”等,就是适切的例子。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所怀之“旧”就是曾经的时尚,因而怀旧某种范围内即可以说就是对曾经的时尚的眷恋。《大上海的老派细节》中所列举的诸多“老派细节”,无一不是上海三十年代的时尚;《小众电影》中《大众电影》杂志同样引发了人们许多“对美丽和时尚的幻想”;《另类报人》中“老穆”的时尚则可以与美国三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男人的味道”相提并论。刘明霞怀旧之与时尚如影相随的特点,似可由此找到原因。“重温旧物一定要有一种寂寞的心态,才能唤起内心里温柔的情愫”(《用时尚解开水东街的情结》)。所谓“寂寞的心态”,乃是一种不受外界打扰的澄明的心境与审美的态度,这正是进入甚至拥抱对象的必然前提。而当我们常常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时,得到的就不仅仅是由“旧物”唤起的“温柔的情愫”了,那将是整体人格境界的提升与完善。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