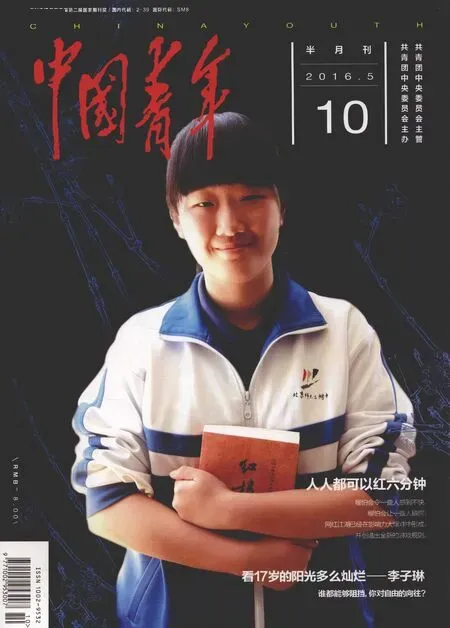我为什么写《红楼夜话》
文-郝永勃
我为什么写《红楼夜话》
文-郝永勃
一
写作像一个谜团。写之前,不知道如何收尾;写作时,既有灵性的妙笔生花,也有钝感的苦不堪言;写成后,自知甘苦,终究是勤勉的结果。
写一部书,像独自走夜路。看见星光,在空中闪烁;想象灯火,在内心点亮。每天一行一行地写,一步一步地走......摸索着前行。自我的激励,如影相随。
写作像植物的生长,有自己的周期律。该萌芽时萌芽,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该衰败时衰败。种子的品质很关键,适宜的土壤、滋润的雨露,也很关键。
二十年前,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做了一个梦,有种感应,想写与鲁迅有关的书,然后,创作《鲁迅肖像》;二十年后,曹雪芹诞辰三百周年,是巧合,也是天意,又做了一个梦,之后,创作《红楼夜话》。
二
书的命运,像人的命运。这其中有诠释不清的、无法破译的密码。
十来岁时,也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听母亲的同事提起《红楼梦》,如闻天书。少年时代,书籍是匮乏的,也没读过几本像样的书。
二十岁时,我买了一部《红楼梦》。恰好同名的电视剧热播,对照着看,最关注的还是爱情故事。一个结了婚的朋友说,他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林黛玉。我与他争得面红耳赤。现在想来,不值得。喜欢谁,不喜欢谁,是个人的自由。没有必要说服谁,也没有必要勉强谁。
三十岁时,读《红楼梦》。每天读一回,读了一百多天,才读完了。像当初读《堂吉诃德》一样,读进去,读出味道来了。
四十岁后,读《红楼梦》,百感交集,悲欣交集。看见几道门,以及几扇窗,向你关着,还是向你打开了。前有因,疑与不疑;后有果,通与不通。世事洞明的学问,需要一生去学;人情练达的文章,需要一世去做。能不能学好,能不能做好,那要看自己的造化了。
从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一个人读书和写作的过程,犹如在沙漠中赶路,缓慢的骆驼最终超越奔驰的骏马。
五十岁后,读《红楼梦》,从渐悟到顿悟,最有意义的事,是收获了这部《红楼夜话》:一部因爱而衍生的爱之书,一部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书。
三
欣赏原著,这是写作的一种源泉。反复揣测,寻找作家创作的脉络,发现小说背后的逸事——自己有话要说,至于说没说到点子上,写没写到心里去,一切都在书中了。
青春易老,韵华不再。曾经感动过,曾经爱慕过,曾经寻找过......
写作,不仅需要投入感情,还需要积累经验。歌德有句话:"只有不充足的知识才是创造性的。"我清楚自己没有读过多少"红学"研究的书,我仅仅是一个"红学"爱好者而已。我只能写有缘的,写诗性的,写绕不开的,写最有感触的人和事。与看不见的人聊天,与看得见的人对话。因为爱好读《红楼梦》,因为是喜欢做白日梦的人,因为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翻书,因为动笔写第一页时在午夜,便起名叫《红楼夜话》。
“说一个假的意象,以便了解一个真的实情。”小说背后的小说。人都不容易,同情之心是写作的前提,保持一种初创的感觉。而一部书最终有无存在的价值,还取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能否有机结合。
写一部好书,像做一场好梦。醒来以后,可企及的,不可企及的。曾经发生过什么,曾经爱过什么,曾经拥有过什么,曾经失去了什么?这是我写的吗?一切是真实的吗?假如原稿丢失,还能找回写作的激情吗?
曹雪芹说:“市井俗人喜看理论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红楼梦》像不像一只魔幻了的大口袋,里面装的东西,应有尽有。如果让你去拿,你会拿什么?这也意味着你是什么人。
春暖花开时节,写就了一部书,还了一个愿。
责任编辑:刘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