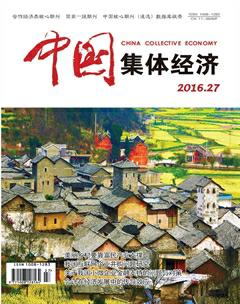运动式治理的社会效应探究
刘长生+裴越
摘要:运动式治理一直是中国政府进行群众动员和专项整治的主要方式,一方面,运动式治理以其快速高效、立竿见影解决特定问题的特点而使各级政府乐意为之并产生一定治理成果:另一方面,运动治理的诸如治理成本虚高、权力行使不规范、治理结果反弹等问题也日渐受到诟病和反思,文章通过辩证分析运动式治理的社会效应,以期引发人们对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社会效应;常规治理
一、引言
运动式治理一直是中国政府进行群众动员和专项整治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理论或模式则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公共突发事件中政府应急反应与治理能力的语境下提出的。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关于运动式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对运动式治理的概念界定与特征把握:2.从不同维度分析运动式治理的成因:3.关于运动式治理的优劣分析。在对运动式治理的社会效应分析方面,多数学者持“一边倒”的态度,得出运动式治理应向常态治理、制度化治理转变的结论。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在论述运动式治理生成的必然性时,注意到运动式治理的某些优点,指出,该种治理手段是“在现有国家治理资源贫乏的限制性条件下政府的一种必然选择”,有助于缓解转型时期因国家治理资源不足而造成的困境。
综合学界观点,本部分从正功能、负功能两个方面入手对运动式治理进行辩证分析。一方面,通过分析运动式治理在重大社会问题处理、疏导民意与向基层输送合法性、对政治运转的润滑以及对政治改革的催化等方面的正功能,对运动式治理予以有限承认:;另一方面,基于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对运动式治理从开展到效果反馈做出全面的反思,对其助长投机心理和规则虚无主义、权力行使不规范、治理效果的低经济性、与法治精神相悖等负功能予以揭露。在此基础上笔者做出简单的思考——对运动式治理有限承认,更对运动式治理与专业化、制度化、常态化治理的内在张力作出分析,同时对运动式治理活动化予以评析,最终说明运动式治理之于治理现代化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运动式治理的正功能
尽管运动式治理近年来饱受诟病,但基于中国制度化不足、社会资源匮乏的现实背景以及特有的政治、文化结构,这一机制也在治理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在疏导民意和重大问题处理方面彰显有效性
运动式治理是与“群众路线”密切相关的,在某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方面,运动式治理是民众议程设置的结果。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制定公共政策上的选择性。当一项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以致积重难返、民怨沸腾时,参与的制度化不足的背景下很有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此时政府以专项运动的形式自上而下集中整治、重点突破,“疗程短,见效快”,可以较为有效的疏导民意,满足民众诉求。同时,自上而下的动员也为广大民众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开辟了一个特殊渠道。当运动式治理是为作为利益相关方的民众而发动,那么其公共性就较强,且官方的治理目标与民众的预期结果越一致,公民的参与热情与参与程度越高。
从治理实践来看,主要分为两类:第一,对于社会顽疾的定期专项治理,第二,对于突发事件、公共危机的特别治理。以强力的方式修复被突发事件破坏的秩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群众心理秩序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彰显政府的权威和执行力。
(二)推动国家向基层输送合法性
运动式治理一定程度上是对基层意识形态自主性的挑战,有助于向基层输送国家政治体系的权威与合法性。长期以来,国家政治体系的权威与合法性都没有很成功地深入基层,基层民众具有自发的、异于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规则,尤其是当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与基层的传统观念存在冲突情况下,基层自发的规则秩序相比于国家的法律规章更具话语权。学者张静将之称为“乡规民约下的村庄治权”。每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也就成为国家政权向基层输送合法性,更新基层民主意识形态的过程。作为政治体系的末梢,基层受到运动式治理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很显著的效果,但每一次运动式模式的治理活动都冲击着传统的“乡规民约”,与城镇化相伴,日渐改变着基层的政治意识和生态,使得国家权力在纵向深度上推进。
(三)政治运转的润滑剂
首先,运动式治理提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缓解了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治理资源贫乏的状况,但面对超大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治理资源仍然比较紧缺,特别是建立在部门分割的基础上,用于常规治理的资源极其有限。运动式治理针对特定治理目标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自上而下实现国家意志,产生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效果,诸如奥运会、世博会以及近期举办的APEC会议,都是通过“大会战”式的运动式治理,举社会之力增强国家能力,赢得民众认同。
其次,运动式治理是对科层制下结构僵化、治理失灵的一种润滑与纠偏。常规治理是通过科层制的分工来完成的,但其在中国政治系统中的畸形发展造成结构钢化、边界高筑,运动式治理正是因为常规机制的失败而启动。第一,为达成治理目标,运动式治理以其全面联动的形式较为有效的促进了各部门的合作,弥补了官僚体制内条块矛盾、机构冗杂重叠、职能划分不明确等一系列缺陷:第二,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贯彻国家意志的治理行为,有助于克服中国官僚体制的人格化倾向和部门政治利益,打破因信息不对称、权力寻租等而形成的官僚自主性,一定程度上保证政令的畅通,是对“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现象的回应。
(四)政治改革的催化剂
由于长期积弊和制度创新的成本,偶发的运动式治理作为常规治理的辅助手段和外部救济措施,还承担着探索更优治理路径的功能,期间有可能孕育着新的规则,为制度改革和治理的专业化、常规化扫清障碍。因为运动式治理集中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以暴风雨式的行动对某一社会问题专项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和格局,从而为构造新的治理秩序铺设道路。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好比“治标”与“治本”的关系,“治标”为“治本”扫除障碍、铺平道路。
三、运动式治理的负效应
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治理手段,运动式治理从发起到过程开展,再到效果反馈,都显现着对治理制度化、现代化的负功能以及对法治精神的相悖。
(一)助长投机心理,漠视规则制度
“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治理为治理主体与客体都创造了投机取巧的机会。首先,由于运动式治理具有“疗程短,见效快”的特点,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在畸形政绩观主导下,治理主体往往对一些潜在问题不闻不问,对已经显露苗头的公共问题视而不见,直至他们恶性发展至一定程度,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时才开展专项治理活动,通过宣传造势与集中行动博取眼球,营造大政绩。其次,对于治理治理客体而言,由于把握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运动偏好和运动周期,所以会有策略的与治理主体“打游击”——运动尚未开展则肆意而为,扰乱社会正常秩序,运动开始前又因大张旗鼓的宣传可以闻风停止作案、销毁证据,运动风声一过很快死灰复燃。这也是为何一些社会问题屡治屡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更为恶劣的影响是运动式治理模式下的社会将产生一种对规则、制度的漠视。政府有能力却不作为,只等问题突出、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焦点才重点整治一番,这等惰政行为使得已有的常规治理手段不被启动而柬之高阁,而在运动式治理过程中由于需要多方联动又会突破常规界限,使得制度精神很难发挥,丧失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另一方面,周期性运动式治理的对常规制度的打破还会使得制度在民众心中无足轻重、形同虚设,从而很难使民众产生对法律、制度和规章的敬畏,而这是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头号敌人。
(二)权力行使不规范,导致治理扭曲
运动式治理追求行动高效,必然打破常规制度,谋求权力的非程序化使用。首先,运动式治理的目标预定性导致主要负责人很可能根据主观臆断发号施令而不顾地方实际,造成压力体制下各级治理主体逢迎上级喜好,追求面子工程:其次,权力具有扩张性,运动式治理是一个自上而下任务层层分解执行的治理过程,这使得掌握全权的地方治理主体为超额完成任务或追求个人私利,层层加码,不断扩大目标范围和执行的力度以至于达到严苛的地步:再次,权力的任意性使得治理主体在界定治理客体和治理范围上具有选择性。由于各级治理主体同时也可能是被治理对象,所以治理主体会设法打政策的擦边球,以种种借口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由于治理主体掌握着圈定治理范围的权力,部分既得利益者很可能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规避运动的风浪,不仅导致治理流于形式,还滋生了权力腐败。即使发起运动式治理的初衷是好的,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运动式治理的过程是将政治性凌驾于专业性之上,它极大地破坏了官僚科层制的稳定结构。治理的现代化将专业性至于首要位置,并一定程度上要求价值客观公正性。而运动式治理与压力体制的结合,致使“以红统专”,政治忠诚成为首要考核指标,而治理成效则置于其次,这与治理现代化背道而驰。此外,运动式治理打破了常规的行政系统边界,破坏了科层划分下部门的日常职能和稳定结构。
(三)治理效果的低经济性
常规治理是制度化、经济性的治理行为,十分注重治理的成本和效益。而运动式治理在治理的成本与成效的评估方面多是一笔糊涂账。首先,治理成本虚高,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运动式治理往往在缺乏对事态全面、科学评估的状态下就盲目调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专项整治,且随着治理的层层加码,投入的资源数量更加巨大。巨大的资源投入在调拨与使用中多没有公开、公示制度把关,不能不怀疑其中存在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行为。
其次,从治理效果而言,运动式治理虽然是立竿见影,但绝不能忽视治理结果的反复性。运动式治理的反弹与反复,不仅是一次次资源的重复投入与浪费,更是对政府威信的挑战,民众将因此质疑政府的施政能力,政府公信力受到威胁。而由于运动式治理造成的“规则虚无主义”,政府常规治理的权威也难以保障。运动式治理虽然为民众参与开辟了特殊渠道,也为国家向基层输送合法性提供了可能,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运动式治理行动、目标与民众预期一致的程度。当二者趋于一致时,运动式治理尚能发挥较为理想的效果,当二者不一致甚至有所冲突时,运动式治理不仅不能实现政治参与和合法性灌输的功能,还会威胁社会因公共问题而已经脆弱的正常秩序。特别是在制度化水平不足的情况下,被动员起来的民意得不到满足有可能造成政治秩序的动荡。巨大的资源投入与有限的治理成效共同构成了运动式治理的低经济性。
四、对运动式治理的总结与思考
首先,运动式治理基于特定机制而产生,应有限承认。运动式治理产生于特定的实践机制,是既有体制下治理资源不足的被迫选择,在危机应对、重点公共问题处理以及民众动员、统一行动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部分运动式治理其次,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存在张力,悖于治理现代化。
其次,常规治理即治理的专业化、制度化、常态化,运动式治理在这几方面都对治理现代化构成挑战。第一,运动式治理的“以红统专”使得政治化凌驾于专业化基础之上,可能导致外行指挥内行,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泛政治化。第二,运动式治理在助长投机心理的同时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对规则的漠视,治理本身也是对日常制度的打破。此外,常规治理要求权力有限制、受监督,这与运动式治理权力的全权性、随意性以及不受监督形成反照。第三,运动式治理由于集中力量,从严从重,很可能在打破沉疴的同时波及正常社会经济秩序,其对法律、规则的态度也是工具主义的。运动式治理与常态化的现代化治理具有内在的张力和冲突,这也决定了运动式治理向常态治理转变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再次,要密切关注运动式治理的“变体”——活动。由于运动式治理近年来饱受诟病,各级政府也在有意识的规避这一治理手段的称呼和使用,但在探索制度化治理的过程中,运动式治理与活动相扭结,有“移花接木”的可能。为运动式的治理手段套上活动的外衣,以活动的方式来整肃秩序、整合资源,之后又力图将经验成果模板化,尝试建立类似日常化的长效机制,这点在执政党作风建设和意识形态宣教方面表现得尤其典型。作为运动式治理的翻版,活动的经验诚然能为日常化治理提供借鉴,但不可忽视其中政治权威的推动力以及短时期对物质、人力资源的聚集,而日常化的机制则无法时刻运用领导的权威来集中大批资源用于全面治理。所以,实现治理现代化要转变运动思维,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人手,打破路径依赖,而不是“老树开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