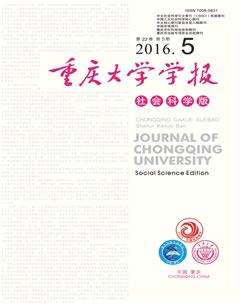弹幕的传播效果及其影响研究
汤天甜++陈卓
摘要:
弹幕是基于互联网技术支持而对视频文本进行的再创作,其给受众营造了一场以弹幕视频为场域的狂欢盛宴。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内容分析方法,文章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弹幕的发展现状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同时以巴赫金提出的狂欢理论为研究视角评析了弹幕引起狂欢的机制和效果;旨在以狂欢理论为框架剖析弹幕满足受众追求自由平等对话与自我身份认同的使用价值并探讨弹幕的语言不规范与吐槽功能等可能会导致的娱乐至死及其目前用户小众化特点的局限性。
关键词:弹幕;传播;狂欢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5017207
之前仅出现在弹幕视频的弹幕因近来被相继应用于电影营销和淘宝网的“双十一”购物节活动且引起大众狂欢而备受关注,同时,学界也展开了针对弹幕这一新生网络文化现象的研究。笔者的关注焦点在于,基于视频的弹幕如何营造狂欢,怎么评价弹幕营造的狂欢,弹幕在其他场域是否具有利用价值,等等。
一、研究缘起与理论梳理
“弹幕”一词最早仅为军事用语,之后被引入ACG(Animation, Canton & Game)文化并得到推广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弹幕滑过视频所引起的视觉冲击效果和其“吐槽”功能使ACG迷们置身于一种狂欢之中,这种狂欢也促使弹幕的应用场域不断扩大,内涵逐渐丰富。因此,解读与评价狂欢便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概念界定
20世纪末以《东方Project》为代表的同人游戏因使用弹幕射击而将弹幕引入ACG文化,之后弹幕概念被平移至视频。日本niconico网站播放器的评论功能与横版弹幕射击游戏类似,当视频的评论较为密集时,就会产生如同无数子弹横飞的画面,这种现象也被称作弹幕。随着ACG文化的介入与流行,中国第一家弹幕视频网站AcFun(A站)于2008年成立,弹幕由此在中国开始被使用并逐渐流行。目前国内的AcFun(A站)、Bilibili(B站)和Tucao(C站)等均是以弹幕为特色而发展起来的弹幕视频网站。
随着弹幕用户群的不断扩大,弹幕受关注度日益提高,学界对于弹幕及其应用的研究也逐渐升温。笔者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之后发现,目前关于弹幕的研究多集中以下几个方面:弹幕现象的引介与内涵分析、弹幕载体的多传播渠道探究以及弹幕之于营销学、广告学等跨学科研究等。
日本学者滨崎雅弘等认为,niconico网站能够迅速积累用户就是基于其直接覆盖于视频画面(direct overlaying of comments on video)的评论即弹幕的存在[1]。也有研究者将“弹幕”描述为视频中同时出现大量评论时的画面效果,认为弹幕可以分为普通弹幕、空耳弹幕、解说弹幕三类[2]。随着弹幕用户数目与相互之间交流的增多,作为弹幕最初载体的niconico网站、A站和B站等弹幕视频网站已逐渐发展成为新型的社交媒体。有学者通过量化研究认为,niconico弹幕视频网站作为社交媒体的一种,在紧急情况下具有担当可靠信源的功能,可以帮助传播官方信息[3]。弹幕的发展与ACG文化和御宅族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研究者从青年亚文化的视角出发,认为弹幕视频网站所形成的青年亚文化网络社群实现了内部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强化了边界意识和族群认同,因此,须警惕该网络群体的民粹倾向[4];马志浩等以准社会交往理论为框架,通过对弹幕评论长度的分析探讨了日本动画对于受众的影响以及受众间、受众与动画角色间的互动[5]。基于弹幕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等功能,国内在近两年也出现了《秦时明月》和《小时代》等弹幕电影、“节操精选”APP中用于评价静态图的动态弹幕以及湖南卫视的电视直播类弹幕等,同时学者们的研究也打破了弹幕仅存在于视频的局限并开始研究“弹幕+图片/电影/电视”等现象,即研究弹幕使用场域的转换形式及效果等;Ichimura 认为在图片数字化框架下,弹幕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可以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6],诸葛达维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互联网时代的弹幕电影并揭示了弹幕电影背后的文化与经济原因等[7]。在弹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中,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将弹幕用于营销策划、广告或教学方式改革等,这不仅体现了新媒体技术的优越性,同时也是互联网思维的落地与物化的成果。
作为一种新出现的互联网思维物化事物,以弹幕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正在逐步增多,且其研究更趋向于“弹幕+”模式。纵观现有的弹幕研究可以发现,研究人员多为中日两国学者,其研究都侧重于弹幕的传播效果尤其是正面效果研究;但两者的研究方向也会有些许不同,日本学者的研究多在于将弹幕视为一种社交工具并研究其所引起的受众间的交互传播机制及效果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弹幕的使用场域尤其是弹幕之于电影营销等方面的研究,着重探讨了弹幕电影的发展前景以及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等。总体来说,国内外关于弹幕的研究已然呈现多领域、多角度的特点,但是在以理论为支撑对弹幕进行批判性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依旧稀少。以源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的理论为支撑对弹幕进行分析是更好利用弹幕这一新媒体手段的基础,因此,本文尝试从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弹幕进行分析,探讨弹幕的传播效果及其影响。
鉴于以上研究评述,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外关于弹幕的界定并不能完全地概括弹幕的内涵,尤其是在弹幕中国化后内涵等不断丰富的情境下。与此同时,笔者还发现,就出现频率最多的视频弹幕来说,虽然其在日本被称为评论,但它又与常规的视频评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是呈现方式不同,常规视频评论多带着受众的昵称等出现于视频下侧,而弹幕则仅将受众所表达的内容漂浮于视频画面中;二是时效性不同,不同于常规视频评论呈现时的以发表时间排序,弹幕的出现与其被发射时间点的视频具有同步性;三是地位不同,常规视频评论是受众针对视频的观点的呈现,而弹幕在呈现受众观点的同时也充当了视频的文本。因此,为了使后续的研究对象更为明确,本文在归纳总结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作为新生网络语言现象的弹幕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较为抽象,指视频中出现密集的类评论话语这一情形;第二层为实指,指代视频中飞过的任一条评论即语言符号。
(二)理论梳理
狂欢理论(the Carnival theory)首先出现于苏联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的文学研究中。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巴赫金提出了“狂欢化诗学理论”,并指出狂欢是一个重要术语,可用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因此,使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分析弹幕为受众营造狂欢这一文化现象也是较为合理的。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念源于西方的狂欢节。在狂欢节期间,摒弃世俗间陈规戒律并打破阶层界限的大众在狂欢广场上通过一系列“脱冕”与“加冕”的仪式性表演制造欢乐。这是一种可以短暂地满足大众内心对自由平等与乌托邦理想国的追求的欢乐,也就是说,“狂欢节上的主要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这一仪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狂欢式的所有庆典中”[8]。弹幕是受众基于视频文本进行再创作的产物,其中暗含着消解弹幕视频制作者独创权并赋予受众创作权的行为,这种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脱冕”与“加冕”的仪式。
巴赫金提出:“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9]184其中的“另一种”生活即“第二种生活”是基于狂欢节而提出的,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中的狂欢式或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涵盖了狂欢节型庆典活动的礼仪、形式等全部总和[9]175。在弹幕为受众营造狂欢的过程中,弹幕的应用场域即弹幕视频扮演着“狂欢广场”的角色,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尽情表达的生活场所。巴氏还认为,狂欢式的外在特征是全民性与仪式性,其世界感受的内在精神即自由平等的对话精神、双重性与相对性则通过巴赫金提出的狂欢式四种特殊范畴,即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插科打浑、俯就和粗鄙来体现[9]176-177。
因此,狂欢理论不仅阐释了狂欢形成的机制和大众平等参与及其表达自由的重要性,还强调了狂欢是对人性解放的追求之表达。但是,随着文化多元化与文艺批评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对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理论只是巴赫金想象的产物,且这种想象极大地歪曲了狂欢节的真实面貌和文化功能,虚构了狂欢节与官方文化、宗教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对抗,在历史和逻辑双重意义上都有着根本性缺失,是一个体系性的文化史虚构[10]。鄢鸣甚至直接抛出了“中国是否有狂欢理论”的问题,他认为鉴于中外文化语境的差异,典型意义上的狂欢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此,在运用狂欢理论时,必须注意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在对话中实现新的文化形态的构建[11]。
近年来,鉴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网络传播的系统开放性、内容集成性与传递方式多样性等特点且网络传播具有狂欢本质[12],因此,狂欢理论之于互联网传播方面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叶虎认为,网络传播与狂欢理论无疑具有紧密的关联,网络传播的自由开放性和交互主体性、虚拟性都契合了狂欢节的全民性、仪式性和平等对话精神的特点,构成了人们的第二种生活,且狂欢理论也是我们为改变不合理的旧的信息传播秩序而斗争的理论武器[13]。庞宏同意网络狂欢可以被界定为网络空间中出现的一股不分等级、全民参与、高度自由、快乐至上的狂欢化浪潮,并指出“网络狂欢”为人性的彰显与解放提供了平台,高度平等的全民参与、高度自由的表达为网络狂欢的兴盛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人性解放提供了机遇和途径[14]。然而,将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而形成的弹幕至于狂欢理论视域之下时,笔者不禁提出疑问:弹幕在弹幕视频网站中营造的狂欢是否就是巴氏所提出的狂欢?如果是的话,弹幕引起狂欢的机制是怎么样的?弹幕所引起的狂欢对于受众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引起狂欢的功能又是否可以被应用于其他场域?
二、弹幕:营造基于网络的“狂欢”
弹幕视频网站的出现与推广都是基于网络兼容并包的特性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因此,弹幕引起狂欢的特性也是在此背景下才得以实现。
(一)“脱冕”与“加冕”:弹幕的生成机制
国王加冕与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变更的精神[9]178。弹幕是弹幕视频受众在观看视频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对视频文本进行的再创作,即弹幕的生成机制是再创作。这一再创作过程不仅使受众的观点得以表达,增加了视频的文本内容,一定程度上“脱冕”了创作者的权威,同时也为受众“加冕”了创作的权利,增强了传受双方的互动与交流。
视频原是编剧与制作者等创作者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创造的文化产品,其文本具有相对稳定性。弹幕出现之前,对于受众来说,只能选择观看已有的内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传播属于直线传播,二者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即相对受众而言,创作者处于“权威”的地位。基于对视频文本再创作而产生的弹幕中经常会出现类似“亮点在”、“加特技动作太魔性,注意手势”等细节提示,这种对创作者无意为之的细节挖掘不仅丰富了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创作者的创作特权,同时也打破了受众不能更改视频文本的桎梏,受众的地位也因其被赋予了类似创作者的“权威”而得到提高。从弹幕的内容而言,除发表与视频有关的外溢想法,受众还尝试通过有指向的喊话形式与创作者、视频内容尤其是视频中人物角色甚至其他受众产生交流,即马志浩等所谓的准社会交往。鉴于弹幕具有视频文本的属性,因此,当受众发射有指向的喊话弹幕时,实际上也与其喊话的指向对象发生了交流。例如,当视频内容令受众始料未及时,受众可能会发表类似“编剧,请收下我的膝盖”等有指向的弹幕,这种喊话弹幕是受众对编剧企图吸引受众的创作心理的反馈,也就是说,弹幕使得受众拥有了与平时接触不到的编剧等创作者进行平等对话的权利。同理,受众所发射的企图与剧中人物等进行交流的喊话弹幕如“哈喽,雷军。油英个嘞去一吃古德”(源自雷军在印度举行的产品发布会上秀英语视频,此弹幕意在调侃雷军不标准的英语口语)等也可以缩小在此传播过程中受众所感知的自身与明星的心理距离。弹幕再创作的生成机制鲜明地呈现了受众在观看过程中的地位变化,即受众处于一系列互动链性结构中,其既是内容的创作者也是内容的消费者,一个受众对于现有内容的创作可以激发他对其内容再次进行创造性的调整与更新[15]。这种机制一方面通过为受众“加冕”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受众的自我认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视频创作者的权威,拉近了受众与创作者、剧中人的心理认知距离。鉴于巴赫金认为“脱冕”和“加冕”是狂欢节的主要仪式,因此,当受众采取弹幕形式在视频中展示自己的地位变化即颠覆了其之前的被动地位时,以视频为狂欢广场,弹幕为狂欢仪式载体的话语狂欢便有可能会迅速形成。
(二)狂欢广场:开放而自由的互联网语境
20世纪出现的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等特点,其技术的日益发展与成熟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便捷、自由的平台,大众的观点表达途径也变得日益多元与顺畅。巴赫金认为狂欢广场是一个既理想又现实的世界,现实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理想则是因为在这个新世界中的人们可以忽略性别、身份和地位等世俗因素,平等自由地进行交往与狂欢。
在弹幕视频中,受众可以通过弹幕表达自己在观看过程中的观点意见与想法,同时,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出现的弹幕视频作为弹幕的载体,也为观点的呈现提供了新的场所。2015年2月底风靡网络并使“duang”和“加特技”等成为网络热词的“我的洗发水”视频最早就出现于B站,而后迅速受到B站会员的热捧并纷纷发弹幕“妈妈跪系列,洗脑系列,金坷垃系列!金坷垃,有了他。全国人民笑哈哈哈”、“放我出去循环十多遍了!!!”或“阿婆主是有多爱成龙大哥啊”等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B站中也迅速出现了几十条基于成龙洗发水广告的改编视频,这些视频中多数点击量过万,弹幕条数更是数不胜数。此外,通过对弹幕视频网站的观察可以发现,弹幕的发射呈现即时性和匿名性的特点。即时性是指弹幕的发射与受众选择发射的行为几乎处于同步状态,因此,受众可以不间断地发射“摇*1”、“摆*12”……“摆*23”等数数弹幕以同步计算“我的洗发水”中成龙摇头的次数从而营造出狂欢的氛围。匿名性则体现为无论是在弹幕池还是在视频中出现的弹幕都是匿名发送的,这一匿名性特点为受众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了保障。例如,在弹幕视频中经常会出现“前方蓝字的”或“说女主麻麻要洗白”的“给我站住”等受限于匿名性而只得寻找替代称呼的打招呼弹幕。再如,当《匹诺曹》中的男主角出现时,匿名状态的弹幕用户可以毫不避讳地发射“二硕,我们结婚吧”等求爱弹幕等。
因此,互联网语境下的弹幕视频不仅为受众迅速表达观点意见提供了理想场所,而且还因其匿名性等特点而为受众提供给了一个较为宽松的表达语境,使其在编辑弹幕时不必拘泥于现实的身份等因素,也就是说,弹幕视频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类似狂欢广场并能最大程度满足受众即时自由表达观点诉求的平台。
(三)狂欢语言:组成弹幕的语言符号
在巴赫金所说的“第二种生活”中,“充满了一种特殊的言语,不拘形迹的言语,它几近于一种独特的语言”[16],这种语言是“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9]175。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弹幕视频类比为狂欢广场,那么充斥于视频中的弹幕是否就是巴赫金所谓的狂欢语言呢?
通过在国内较为著名的弹幕网站哔哩哔哩网站(B站)中的参与式观察与统计分析,笔者认为弹幕语言的狂欢“来自挣脱语言法则的创造力”[17],而其语言特点可以总结为:多元随意性、简洁性、粗鄙诙谐性和双重性。多元随意性是指组成弹幕的语言符号不仅包括汉字、数字、英文字母和文本符号等,还包括“料事如神的麻麻(*ˉ︶ˉ*)”、“(#‵′)凸”(表鄙视)或“最右→_→”等类似此类语言符号的随意混拼;其简洁性则表现在弹幕的长度方面,弹幕语言尽可能用较少的语言表达完整的意义。
为了证明观察的正确性,笔者在B站随机截取了热播韩剧《匹诺曹》中的736条弹幕并对组成弹幕的语言和语言的字符串长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当将组成弹幕的语言符号按照汉字(包含单纯表示数量的数字)、非汉字符号(由汉字以外的符号构成)和混拼(由汉字和非汉字等符号混合而成)三个标准进行分类,可以得到以下数据:汉字类569条,非汉字类65条,混拼类92条(如图1所示)。然后,笔者通过Excel中的LEN函数对每条弹幕的字符串长度进行了计算与统计,其中,组成字符串的字符个数<7的弹幕为281条,7~15之间的弹幕为310条,16~25之间的弹幕为104条,>25个字符的弹幕为35条(如图2),三类所占比例分别为39%、42%、14%和5%(如图3)。由此可以看出,组成弹幕的字符串长度多小于15,而B站规定普通弹幕的字符串个数尽量小于25个。上述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笔者通过观察所得出的弹幕语言具有多样性和简洁性的观点。此外,通过对弹幕内容的观察也不难发现,弹幕中有很多通过双关、戏谑等对现实世界进行恶搞或调侃的话语,甚至是直接使用含有涉及性或身体器官的低俗话语来达到诙谐的效果。弹幕语言的双重性可以理解为弹幕语言语义的双重性或弹幕语言的圈子化,即弹幕中的一些特殊语言是基于弹幕视频的场景而创作出来并被使用的,如当表示一段背景音乐很好听或令人印象深刻时,会出现“BGM好燃”或“燃”等弹幕;在B站上传视频的人即up主会被亲切地称为“阿婆主”;再如对于“金坷垃”化肥的恶搞致使其“金坷垃”由化肥名字变为了威力大等意思的代名词。因此,对于不了解弹幕的人来说,仅从字面意思判断可能会造成对弹幕意义的误读,同时这种类似于隐语的弹幕也使得弹幕用户产生了一种群体归属感。
弹幕的语言特点使得受众间的接触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礼数规范,一方面打破了现实生活中因性别、年龄和身份等因素带来的约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弹幕语言的粗鄙诙谐性和双重性也使得受众间的言语不再遵循文明规范的要求,并通过弹幕用户间的相互协同创作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媒介生态圈[18]。可以说,具有这些特点的弹幕语言正是巴赫金提出的关于狂欢的四个范畴的具体体现,因此,弹幕也是属于狂欢语言的一种,且是基于弹幕视频这个狂欢广场而形成的。
三、基于弹幕的狂欢之评析:辩证的视角
在狂欢理论框架下对弹幕的生成机制、使用场域和语言符号等进行阐述,并证明弹幕具有引发受众狂欢的功能基础上,辩证地评析其在弹幕视频中营造的狂欢则是充分挖掘弹幕发展潜力的条件。
(一)受众心理的多维度满足
正是通过全民不拘形迹的交往,才使得人们享有了狂欢带来的自由。在狂欢节的广场上,形成了一种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人们之间没有任何距离、不拘形迹的在广场上的自由接触[16]19。在弹幕视频这个狂欢广场中,弹幕营造的狂欢不仅缩短了受众间的心理距离,同时也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自由交际与宣泄的机会,使得受众得到了多维度的心理满足。
通过发射与阅读弹幕,受众间彼此给予的虚拟在场式陪伴和交流为受众提供了轻松愉悦的观影体验;弹幕作为视频文本的一部分使得发射弹幕的受众在视频的传播过程中具有了双重身份,自我效能得到开发,提高了其身份认同感;弹幕是受众在观看过程中匿名、即时发送的,不仅实现了受众的平等参与和自由表达即平等自由的对话精神,更是对狂欢理论所追求的人性解放的满足。
具体而言,受众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总会产生表达自己的观看想法或与其他受众交流的渴望,弹幕的出现使受众想法的表达成为了现实,受众通过弹幕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与自己产生思想共鸣的人。在弹幕发射的匿名性和即时性消除了受众间社会地位、性别和职业等属性差异的同时,组成弹幕的语言符号的多样性等特点也使得受众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更加自由贴切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在这种情形下,受众的参与感得到了增强,而且其追求平等自由对话的心理也会更容易满足。当受众的观点得到其他受众肯定亦或是与其他受众观点相似即受众间针对视频内容产生共鸣时,自我效能感便会得到释放,一种以弹幕视频为狂欢广场的虚拟在场式的围观狂欢便会产生,这种狂欢为受众构建了既理想又现实的人际交往。由于参与评论者在实际地理位置的分布上较为分散,在真实世界里永远无法面对面接触,对着电脑屏幕吐槽正是“刷存在感”的方式之一[19]。这种基于弹幕视频的虚拟社交在为受众提供娱乐与使用满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受众的观影孤独感,增强了受众的自我认同感与群体归属感。
除此之外,弹幕视频的创作者也可以基于弹幕的出现频率判断出受众对于视频内容的感知以及受众所欣赏的“槽点”的类型,并基于判断结果创作出更能引起受众兴趣的内容[18],从而更好地满足受众的观影需求,为受众提供更多的观看乐趣。
据此,弹幕通过其营造的狂欢不仅提高了受众在弹幕视频文本创作中的参与感,满足了受众追求自由平等对话的心理,而且还为受众在虚拟世界中重构趣缘群体提供了可能。进一步说,弹幕的这种特性不仅增强了弹幕视频的受众粘性,也提高了弹幕用户的数量及其使用忠诚度,甚至使弹幕资深用户产生看视频必开弹幕或为了看弹幕而看视频的行为。
(二)狂欢过度而娱乐至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作为互联网语境中新媒体发展产物的弹幕通过其营造的狂欢为受众带来了多维度的愉悦与深度体验,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于参与感和自由平等对话的追求,也彰显了其自身的发展潜力与利用价值。但是,在享受弹幕营造的狂欢带来的心理满足时,我们也必须冷静地看待隐藏于这种狂欢之下的危机。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20]以这句话为背景再观弹幕及其营造的狂欢则不难发现,伴随着弹幕的发展而出现的语言符号创新速度过快、语言使用不规范及倾向于无厘头或去中心化的庸俗甚至恶俗式语言表达等问题也对人类语言符号的健康发展和受众心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在语言符号方面,过快的创新将会一定程度上缩小传播的实现所需要的共通语义空间以致人际交流受阻,而语言表达的不规范与庸俗化等则会对受众的语言表达产生消极作用;在语言风格方面,弹幕中含有很多“绰号、嘲谑、戏仿、反讽、怪诞乃至在书写中遭到贬抑的粗俗猥亵的脏话”[21],例如“刚入宅,你们说的金坷垃是什么意思?”或“什么是384”(384代指日本动漫《黑执事》中男主角“塞巴斯蒂安”)等问询弹幕或“炒鸡”(=超级)、“沙滩”(=bitch)、“撕逼”(=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尤指女性间的争斗)等庸俗或破坏语言规范的弹幕的出现。这些宣泄式的话语虽然可以暂时为受众提供发泄情绪或释放压力的方式,但是从长久来看,其对受众精神文明的影响方面弊大于利,这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亵渎。从更深层次来说,弹幕的现有功能主要是用于“吐槽”,这项功能在帮助受众实现情绪宣泄的同时也可能以涵化的方式为受众营造一个充满戏谑与负能量的拟态环境,致使受众在面临现实真实环境时仍单纯地以追求戏谑和狂欢为目的,甚至呈现出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心理与消极心理。这种消极影响已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重视。2014年12月2日,文化部宣布将开展第二十二批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动查处工作,以打击提供含有宣扬色情、赌博,违背社会公德等违法违规内容的互联网文化活动。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刘强就明确指出某些动漫网站设置了“吐槽”功能,网友可以在动漫产品的任意位置添加任意评论,却未对内容进行限制和过滤,网友的语言伴随着低俗的画面越发露骨和下流。观看同一作品的其他网友看到评论后,形成影响恶劣的连锁互动反应。由于网络动漫产品的主要受众群体是未成年人,网络动漫的低俗之风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22] 。
巴赫金把以严肃与禁欲为其常规内容的生活看作“第一种生活”,把每年长达三个月之久、以民间节日形式(主要有农神节、愚人节、狂欢节、复活节等)出现的生活叫作“第二种生活”,且狂欢化世界的形成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23]。也就是说,他认为狂欢是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人们在“第二世界”寻求平等自由与人性解放的行为,但是“相互间有严格的时间界限”[9]184。因此,如果将巴赫金所说的“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相互混合,不分场域、不分时间节点地单纯追求狂欢,不仅可能会导致过度狂欢而影响正常生活,更有可能致使文化萎缩即娱乐至死。
四、总结
在对以弹幕视频为狂欢广场,弹幕为狂欢语言而产生的狂欢的生成原理和效果进行深入评析后,我们认识到了弹幕的两重性,上文不但肯定了弹幕为受众带来的积极效果,也指出了在其使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与问题。
随着弹幕使用场域的不断扩大,我们肯定弹幕在其他场域具有利用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即目前弹幕用户的局限性。通过在百度指数中对“视频”并“弹幕”的人群属性进行检索可以得出视频的用户百分比分别为19岁及以下占9%,20~29岁占33%,30~39岁为42%,而弹幕的用户百分比分别为19岁及以下占28%,20~29岁占46%,30~39岁为18%,即作为消费能力较强的30~39岁年龄段的人对于弹幕的使用率并不高,弹幕的用户群多集中于29岁以下这个消费能力一般的人群。因此,在扩大弹幕的应用场域如将弹幕用于营销等活动中时,策划者应首先对潜在受众进行充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而有针对性地使用弹幕;同时,如何优化弹幕从而扩大弹幕的用户群及影响力以使其被更多年龄段的人所接受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HAMASAKI M.Network analysis of massively collaborative creation of multimedia contents:case study of hatsune miku videos on nico nico douga[C]//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signing interactive user experiences for TV and video.ACM,2008:165-168.
[2] 张枨枨.未来我们如何看动画——浅谈动画视屏弹幕网站的兴起和发展[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4 (4):183-184.
[3] JUNG J Y.Social media use and goals after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J].First Monday,2012,17(8).
[4] 陈席元.弹幕话语建构的青年亚文化网络社群研究——以哔哩哔哩网对Keyki事件反应为例[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4(20):15-18.
[5] 马志浩,葛进平.日本动画的弹幕评论分析:一种准社会交往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4,36(8):116-130.
[6] ICHIMURA S.A proposal of digital photo frame sharing photos and comments[D].santiago,Chile,2014:31.
[7] 诸葛达维.互联网时代的弹幕电影分析——基于互动仪式链视角[J].新闻界,2015 (3):2-6.
[8] 马大康.虚拟网络空间的话语狂欢[J].浙江社会科学,2005(4):148-154.
[9]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84.175.176-177
[10] 阎真.想象催生的神话——巴赫金狂欢理论质疑[J].文学评论,2004 (3):56-62.
[11] 鄢鸣.中国有狂欢吗?——狂欢理论的应用与反思[J].山东社会科学,2011 (1):159-162.
[12] 胡春阳.网络:自由及其想象——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1):115-121.
[13] 叶虎.巴赫金狂欢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传播[J].理论建设,2006(5):020.
[14] 刘晓伟.狂欢理论视阈下的微博狂欢研究——以新浪微博“春晚吐槽”现象为例[J].新闻大学,2014(5):014.
[15] RICK MASUZAWA. Niconicos commentenhanced videos build fervent young community[ED/OL].[2014-11-06].http://www.nippon.com/en/column/g00218/.
[16]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52.
[17] 约翰·菲克斯.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36.
[18] HAMASAKI M,TAKEDA H.Network analysis of an emergent massively collaborative creation community[C]//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ICWSM Conference.2009:222-225.
[19] 张承宇.在大银幕上交流与游戏——观弹幕版电影《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J].当代电影,2014(10):048-050
[20]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2.
[21] 马大康.虚拟网络空间的话语狂欢[J].浙江社会科学,2005 (4):148-154.
[22] 张贺.整治网络低俗文化部再出重拳[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2-3(4).
[23]朱云涛.断裂还是延续——论现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民间文化的历史关联[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6):9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