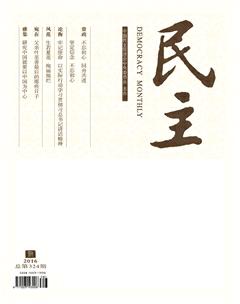周作人的苦茶庵与鲁迅故居
洪烛

说起八道湾,很自然要想到周作人,以及他的苦茶庵。八道湾仿佛是因为苦茶庵出名的。梁实秋曾写过闻一多、潘光旦、宋春舫等人的书房,当然,也无法回避苦茶庵而不谈:“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文笔简约,像建筑师般把苦茶庵的横截面临摹在纸上——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缩影。所以写到这里,梁实秋也不禁扼腕可惜:“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没用任何感叹词,但我分明听到了一声历史的叹息。苦茶庵后半个世纪的穿堂风都是由类似的叹息造成的。
沈尹默书写的横额,早就毁于烟火,据传说内容为“且到寒斋吃苦茶”——是周作人原诗中的一句。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辞令与语气邀请访客呢?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抄录全诗如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依然语焉不详。随你怎么猜测吧——就像茶叶的滋味高深莫测。或许只有滚沸的开水才能不断冲淡、稀释它——千言万语,尽在杯中。
我又想,周作人为什么把好端端的苦雨斋易名为苦茶庵呢?或许表明天意与人事的变迁:早年一封封《雨天的书》,无法逆转地误入旱季,需要人工兑水,沏成薄暮的晚茶,来刺激板结的舌苔?更关键的还是心情。心如枯井,抑或死水,借载沉载浮的一枚巧叶苦渡余生。入世与出世,是两种态度;文质彬彬的斋主与萧瑟憔悴的庵主,也自然是两种身份。山阴道上的一代名流找个趔趄,就这样拖着长长的背影遁入空门。
八道湾实际上也和鲁迅有关,1919年年底鲁迅携全家从北京菜市口的绍兴会馆搬来,周氏兄弟及家属亦同时迁抵。所以解放后,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一度被称为鲁迅故居。而苦茶庵的名称,则几近于失传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人都在回避周作人这个名字。甚至努力将他的文本从记忆中淡化掉——历史以这种措施处理尴尬。其实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当时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的,几天后鲁迅收拾行李和母亲迁出,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也就是说鲁迅只在此生活了几年,周作人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并以此为一生的归宿。
张中行老人说:“我由上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他兼而分析:“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种近真?也不好说。但从受用方面看,疑总难免小有得而大失。”如此裁判已堪称勇敢了。更勇敢的是,张中行在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后,还多次以学生的身份前去拜访:“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也一变而凄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北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是自己或羽太夫人。”苦茶庵给张中行的印象是萧条困顿的,他甚至引用了“门可罗雀”的成语——其风格大大迥异于梁实秋眼中的。毕竟是两个时代了。就像有两个苦茶庵一样。那么,哪一种真实呢?这同样不好说。
我曾好几次路过八道湾,很想下车去那一大片低矮密集的胡同地带找一找11号院。谁若问我:究竟是想找鲁迅故居呢,还是周作人的苦茶庵?肯定无法回答了。私心里恐怕更倾向于查看苦茶庵模糊神秘的面貌——以及究竟颓败到什么程度。因为自家书架上毕竟重金购置了一整套新版《鲁迅全集》,金碧辉煌,以供奉敬仰与怀念。而庭院一角的苦茶庵呢,则肯定夕阳衰草,无人问津——我为什么不去踏访那些闲适恬美的文字的产地,以打破持续多年一纸之隔?要知道,周作人的一系列著述,几乎都是在八道湾写下的。后来一想,即使置身于落叶遍地的深深庭院,难道真能看出点什么吗,空惆怅一番物是人非又有什么意义?最好模仿那种魏晋风度吧:“乘兴而来,尽兴而去,何必见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