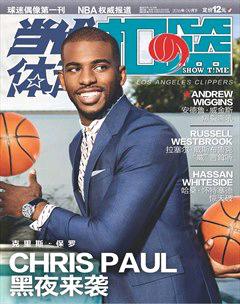功夫少年
张丽娜
1
我生长于一个热爱功夫的家庭。直到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家庭并不会在餐桌上谈论有关少林寺或者是成龙的话题,而这是我们家吃饭时的常态。
在我的记忆中,一部叫做《五毒》的中国老片子应该是我看的第一部功夫电影。那是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和爸爸坐在我们家客厅的电视机前看得相当入迷。这部影片开始于一对师徒,他们住在某座寺庙或者是类似于洞穴之类的地方,画面中,烟雾从火堆上缓缓升起。徒弟正在火堆上烧热水以服侍师傅沐浴,垂垂老矣的师傅则感觉自己大去之日不远了,但他还有最后一个未了的心愿。老师傅之前还曾收过五个徒弟,但这五个人出师之后却开始为非作歹,于是他给自己的小徒弟下了遗令,命他前去清理门户。那五个坏徒弟每个人都有一套以动物的名字命名的独特武功——分别是蜈蚣、蝎子、蜥蜴、蛇、蟾蜍——为了能分别击败五个人,老师傅让小徒弟去学习全部五套招式。
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但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中国武侠电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我未必能从头到尾理解电影里的所有对白,但这并不重要,我只是很钟爱这类型的电影。即使它们都是经过译制后期配音的,但我依然觉得很酷。这些电影让我产生浓厚的想要去了解那个遥远的国度的兴趣,在那里,人们能飞檐走壁,能用铁头功撞破木门,这些对于当时还是孩子的我来说,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但对我和父亲来说,看功夫电影时最好的部分就在于它总是能引起我们之间的对话,我们从来不是为了好玩才看的。
“你看到他的平衡能力有多好吗?”父亲总是会注意到这些特殊的细节。而这提醒我可以在任何事情中学习、积累经验。
我最喜欢看的是那些打斗的场面,而引起我们父子讨论最多的是李小龙。我常会要求父亲倒带回放李小龙的武打镜头,用慢动作再仔细欣赏一遍。他使用双截棍的样子,就好像它们本身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样。而父亲则会鼓励我更多地去留意打斗之外的东西。
“注意看他的步伐,注意看他蓄势待发的状态。”他会凑到电视机前,指着屏幕里的李小龙说道,“他的控制力真的太强大了,好好观察他是如何用他的智慧和策略击败敌人的。”
父亲总是喜欢强调李小龙“很瘦小”。事实上他很强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没有足以压倒对手的体型和肌肉。而武术中的精神和意志部分才是我父亲对其钟爱不已的主要原因。
学习冥想也是我早期的记忆之一,大概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在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在冥想,只是觉得那是我爸爸发明的一个奇怪的游戏。我会端坐在沙发上,尽可能地保持静止不动。说实话,那并不是很难。然后我的爸爸会想尽办法让我发笑,他会做各种鬼脸,会用花样百出的方法来试图分散我的注意力。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控制住自己,面对他的干扰不做任何反应,尽可能地假装他不存在。但父亲的目的并不是如此,他希望我在面对干扰时,也能头脑清楚地去感知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
通过不断的训练,我感觉自己收获了很多。之后,父亲为我增加了冥想的难度——把地点从家里改到了公共场所,比如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者是在喧闹的餐馆里。即使只是让我的大脑清静两分钟,我也觉得自己是在做一种别人看不到的特殊的肌肉练习。没有人真正了解它,而我也是在以一种自己并不熟知的方式进行训练。
2
篮球是我的初恋。我成长于安大略省的基奇纳市,这是一个距离多伦多有一小时车程的小镇。有些人可能听说过我的家乡,那多半是因为那里也是前世界重量级拳王伦诺克斯·刘易斯的故乡。当然,冰球才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毕竟这是在加拿大。说真的,我不太会滑冰,所以在学校打冰球的时候,我都会担任守门员的角色,而且我的表现很不错。但对我来说,能唤醒我内心激情的永远都是篮球。我最开始被大家所熟知,是因为我是“那个手里总是拿着篮球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我会带着篮球去学校,然后不停地在两腿之间运着球,放学时再一路拍着球回家。有时候,我甚至会抱着篮球睡觉。我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学会指尖转球的——我妈妈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在我学会之前,已经打碎了好几块厨房的玻璃。
我的父亲总是喜欢在我的训练中加入一些功夫的元素。“戴上眼罩。”他对我说道,然后我们会在后院的户外球场进行训练。
所谓“球场”,只不过是几块草皮和一个篮筐。我在那儿打了太长时间,以至于草皮都被踩踏成了硬实的泥地。我甚至还自己画了三分线,测量出来后用木棍来做标记。我爱那块“球场”。
最初,我真的很不喜欢蒙眼练习。“爸爸,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抱怨道。我对他说,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会和他们的爸爸一起做这种练习。
“当一切都不在你的控制之内时,你是什么感觉。”他回应道,“你是在感受失控的状态。”听起来像是功夫电影里的桥段,但我并不能明白这种训练要比投篮练习高明在哪。
爸爸还会让我进行蒙眼的罚球练习,他负责捡球和传球。他会站在我耳边,提醒我方向和力道等等,而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在脑海中刻画出画面,以进行调整。
“也许你还没准备好!”
“现在就是你放弃的时间了。”
“你可以去钓鱼了。一切都结束了。”
有时候我会投出三不沾,但大多数时候都能碰到篮筐,只是没有命中很多球。而我父亲会时不时把球在自己手上拿一会,让我空等着。他会让我拿下眼罩,睁眼投几个篮,然后再把眼睛蒙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练习,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尽力去感受投篮过程中所有需要发力的肌肉,而随着我们练习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感觉就越舒服,对眼睛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小。到我上高中的时候,这样的训练我们已经完成了数百次之多。那个时候,我父亲对我的干扰已经完全不能让我分心,他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在我的脑海中,我已经可以感受到篮筐的位置。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父亲那些关于精神训练的方法似乎变得不是那么奇怪了。我还记得在我10年级的时候,父亲开着凌特面包车载着我和我的队友们前往市篮球赛的半决赛现场,当时我坐在后座。车里放着音乐,所有人都在互相开玩笑,打闹着,气氛非常嘈杂。我们紧张但又兴奋的情绪在车里不停转换着。
半路上,父亲突然转过头来,狠瞪了我一眼。“给我安定下来,集中你的注意力。”他的声音足够“响”,所以只有我听到了他说的话。
我闭上眼睛。面包车还在公路上不停地颠簸着,我的队友们还在唱着歌,一刻不停地大喊大叫着。我尽可能地集中精力,在脑海中描绘着系好鞋带,穿上我的球服,倾听教练赛前动员的场景。我想像自己步入球场之中,头顶上的灯光照在我的身上;我想像观众席上有人大喊我的名字;我设想着自己第一次跳投出手的感觉;我能看到对方阵中最好的球员——之前我们已经观察过他很多次——我向他走过去,并把他的习惯性动作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当面包车停止了颠簸,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球馆。是时候上场了。
那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所以整场比分都很焦灼。比赛还剩40秒的时候,我投进了一记三分球,追平了比分。而后对手获得了走上罚球线的机会,但他们两罚全失。在下一个回合中,我们也没有命中投篮,对手抢下了篮板球,随后他们叫了暂停,比赛时间只剩下5秒。两队打平。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真的非常平静。我的大脑并没有任何混乱,而是全神贯注的。当他们开出底线球时,我纵身一跃挡在了传球路线上,抢断得手。所剩时间不多了,我需要推进到前场。说实话,我已经不记得后续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从我手里出去的球最后压哨命中。我们闯进了市篮球赛的总决赛。
之所以特别提起这场比赛,并不是因为我投进了那个制胜球。当然,能完成绝杀的感觉确实很不错,但更让我骄傲的是那次抢断。我就是让自己恰如其分地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
在拉普体育馆——肯塔基野猫队的主场——等待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也总是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我要去“品味”所有的一切:狂热的学生、来看比赛的校友、季票持有者,到处都是蓝白相间的颜色。肯塔基的球迷完全是另一个级别的。在加拿大,篮球正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但对于肯塔基的球迷来说,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专属于野猫队的蓝色。身处那样一个狂热的氛围中,想要静下心来可没有那么容易。
卡利帕里教练和佩恩教练是我当初选择肯塔基的最主要原因。他们开放的执教风格,让球员们和教练组沟通变成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很多人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并不了解他们真实的一面。作为教练,他们其实既严肃又活泼。他们都是乐观开朗的人,但一旦转到球队事务上,又会变得非常严谨专注。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待球员就像对待家人一样。
4
在肯塔基的一年时间里,莱克星顿已经变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我的大学非常棒,在那里我们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我想对所有支持我的肯塔基球迷说,我喜欢在你们面前打球,我能接收到来自你们的能量。从心底感谢你们。
虽然我离开了学校,但我肯定会继续关注我的母校,关注他们迈向成功之路的每一步。我知道他们会实现伟大的目标,去创造属于肯塔基的新传统。
我知道自己会非常想念我的队友以及专属于我们的庆祝方式。那是在对阵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比赛中,我命中了一记三分球后迅速回防,而我的队友弗洛雷亚尔做了一个拉弓射箭的动作,然后潇洒地将箭射出。之后,我们的整个板凳席都开始模仿,只要场上有人投进了三分球,大家就会集体做出这个庆祝动作。一个属于我们的传统,一个新的庆祝方式,就这样诞生了。
不久之后,我将在丹佛掘金开始我NBA生涯的第一个赛季。对我来说,无论是新的地方,还是即将开始的新的旅程,一切都充满了未知性。我知道自己无法去掌控一切,但我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专注,不管是身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在比赛最后时刻,我想要去防守对方最好的球员,或者是球在我手,由我来终结比赛。希望自己会成为决定比赛的那个人。
我期待着下一次命中靶心的时刻,不管我有没有被蒙住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