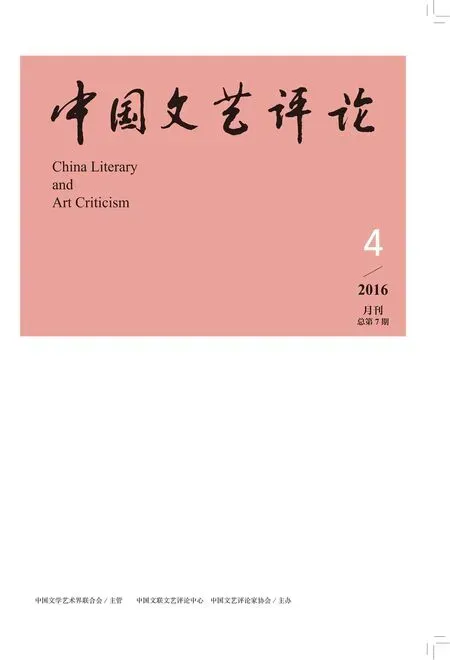21世纪话剧“西潮”景观初探
李扬 张小玲
21世纪话剧“西潮”景观初探
李扬 张小玲
中国话剧是在西方戏剧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又在西方戏剧潮流的影响下发生、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中国话剧史上出现过两次西方戏剧来华高潮。尽管这两次高潮在创作方法、戏剧理念、表现形态上有差异,但有一点极其相似: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观众很少能够观看海外剧团的专业演出,人们只能通过话剧理论文献和剧本认识西方话剧,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依靠想像来还原西方演剧的场景。这种接受方式,多少总给人以“隔”的感觉。进入21世纪,这一窘况得到很大改观,西方很多顶级话剧院团来华演出,中国观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西方话剧,这对国人认识西方话剧艺术、客观评价中国话剧的演艺水准,进而推动中国话剧的发展,无疑会起到与前两次不同的作用。
回顾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能够欣赏西方专业戏剧表演的中国人,大多是驻外使节、留学生。在外国的土地上,他们平生第一次与西方剧场相遇。在欧美,他们或感于剧院之壮阔、戏剧寓意之深远;或讶于英国剧人身份之高、剧院之富丽堂皇;在日本,李哀等留学生在新派剧感召下成立了春柳社。由此可见,在中国话剧蕴酿期间,欧美及日本的剧场演出就已对国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此后,中国话剧在本土萌发生机,渐渐走上了正轨。但当时西方专业演出团体很少到中国演出。即便是专门从事戏剧创作的人,在其从艺初期,也很少能看到西方的专业话剧演出。这也造成相当长时期内,西方话剧对华传播的主要载体是话剧理论文献和剧本,很多时候,这种传播还需借助翻译实现。可想而知,在没有西方剧场艺术作为参照物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舶来的话剧的认识难免不够准确,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话剧表演艺术的交流实际上也处于停滞状态。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境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随着中国话剧团体走出国门,西方世界开始领略中国话剧的艺术水平和表演实力。比如198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茶馆》剧组用50多天时间里访问西德、法国、瑞士,在15个城市中演出了25场,以自己精湛的表演技艺征服了西方观众,受到热烈欢迎,被西方评论家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这次巡演打开了中西话剧艺术交流的大门,中国话剧在西方人眼里不再陌生,中国话剧人也对自己国家的话剧艺术水准有了充分的自信。这为中外话剧奠定了平等交流的基础,中国导演也有了在西方舞台上排演中国戏的自信和底气。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话剧市场渐趋成熟,以及政府扶持戏剧演出政策的出台,中国终于迎来了有别于此前中西戏剧交流方式的别样景观,世界范围内的顶尖表演艺术团体纷至沓来,在舞台上为中国观众演绎莎士比亚、梅特林克、高尔基、霍夫曼斯塔尔、高尔基等名家巨匠的戏剧作品,中国观众也由此欣赏到了精彩的话剧演出,真正领略到了世界话剧艺术的发展潮流。一波新的“西潮”就此形成,尽管其影响目前尚未完全显现出来,但它必将对我们的导表演理念、中国话剧艺术的自我体认乃至观众对话剧艺术的理解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几十年后,当我们回望这股潮流的时候,或许会发现它对中国话剧艺术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其一,叩问灵魂的人文关怀。在这一波西潮之中,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波兰华沙话剧院、柏林列宁广场剧院、汉堡塔利亚剧院、柏林邵宾纳剧院等国外著名院团先后来华演出,绝大部分剧目都属于经典名剧。比如,汉堡塔利亚剧院以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耶德曼》作为自己在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的参演剧目,通过耶德曼面对金钱、善行和信仰时的选择,拷问人的灵魂,也追问着生命的意义。这部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剧作,依然震撼着当代观众的心灵,每个人似乎都不能置身事外,难免扪心自问:我是否也充当了金钱的奴隶?中国观众似乎不用去特意熟悉剧作的时代背景,仅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即可以填充艺术家留给我们的空白。而克里斯蒂安·陆帕(Krystian Lupa)带来的《假面·玛丽莲》(Persona. Marilyn)、《伐木》(Woodcutters),皆是拷问灵魂的杰作,经由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把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这不但对观众产生了震惊效应,而且也促使人们对国内话剧界娱乐之风作出深刻反思。当然,在揭示人性的剧目之外,以后引进剧目时或许可以适当关注那些直面社会现实、凸显批判意识的作品。一段时间以来,对人性的展示、对形式的探求成为艺术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这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漠视生存苦难,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就难免走向偏失,甚至使我们的舞台陷入了一种深度的空心状态。
其二,与时俱进的表演理念。而引进剧目带来的新的表演理念,则给国内话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拓展了舞台的表现空间。近年来,英国伦敦国家剧院一直致力于将优秀的舞台剧现场制作成电影在电影院播出,推出了“英国伦敦国家剧院现场” (National Theatre Live)计划,其中的代表作就是《弗兰肯斯坦的灵与肉》(Frankenstein),它“让观众看到带有400名现场观众拍摄的高清舞台演出,连换场、出场甚至检场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但6台摄像机,经过精巧的设计,使舞台剧在大银幕上呈现得另有风味。”《伐木》《假面·玛丽莲》《朱莉小姐》等剧目在这方面都有精彩的表现。陆帕执导的《伐木》就是从影像开始的,戏剧开场时,乔安娜生前接受采访的录像出现在幕布上,回答着记者的提问,而舞台上一些艺术家缅怀乔安娜的场景,舞台上出现了异度时空,形成了别有意味的对话关系。柏林列宁广场剧院的《朱莉小姐》在这方面走得更远。这部话剧将话剧与电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观众见证了舞台表演和“电影”制作的全过程,观众也可以在银幕影像或舞台表演间自主选择。“舞台上有6台摄影机,由摄影师和演员轮流操控,而正常演出就是一个电影实时拍摄与实时剪辑的过程。摄影师、演员、拟音师和幕后的剪辑师就像一台精确的钟表,像齿轮一样在舞台上完成一个个镜头的表演和拍摄,这些镜头在舞台上方的大屏幕上构成一部连续的电影。”这近乎是一场话剧表演领域的革命,既拓展了舞台的表现空间,也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戏剧的主题呈现。此前,尽管已经有中国导演将新媒体引入了话剧舞台,但新媒体如此全面、系统、深入地介入话剧创作,在中国观众眼里还是第一次。新媒体与话剧的高度融合,这是这波西潮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课题,为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话剧拓展了发展空间,必将加快中国话剧融入世界戏剧发展潮流的步伐。
其三,对剧本的重视和坚守。综观近年来华演出的剧目,有一个共同特点:无论他们秉持的是什么导演理念,属于什么表演学派,其所演绎的大多属于历久弥新的名家名作。在观看他们的演出之前,观众已经对作为文学作品的剧本有了了解,并在剧本的感召之下走进剧场。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剧本的存在,使这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艺术交流变得简单容易。自莎剧诞生以来,有成千上万的导演、演员在舞台上呈现过莎士比亚剧作,其中绝大多数已经湮没无闻,而唯有莎剧永恒。或许有评论家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任何一部舞台艺术作品,都可以通过录像传之久远,但受其传播途径和接受条件的限制,它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肯定难以和作为文学作品的剧本相比拟。毋庸讳言,在当下的话剧界,剧本创作遭到轻视。一部话剧,经由领导的策划、导演的处理、著名演员的舞台呈现,可能会引起轰动效应,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票房记录,可是如果剧本缺少话剧文学应有的艺术魅力的话,它又能传多远?比如,有业内人士指出,《窝头会馆》剧本的“语言仍旧属于文学语言,台词的戏剧动作性比较弱,因此初稿读起来颇费力气。”又如《我们的荆轲》中,剧作家对中国“侠文化”的理解,与剧中人物处理互相矛盾,使人物性格飘忽不定,失去了应有的行为依据,直接影响着戏剧的主题呈现。实际上,即便剧作者倾向于以所谓“个人叙事”拒斥“宏大叙事”也应按照人物自身的逻辑来创造人物。1983年4月23日,《小井胡同》上演后,陈白尘在写给李龙云的信中写道:“有的戏是演员捧出来的,有的演员是戏捧出来的。你要争做后者。”30年后,再读这段话,更觉意味深长。放眼新世纪的话剧舞台,很多成功的戏剧皆属于“演员”捧“戏”之作,如果没有明星阵容的加入,有些作品很难取得轰动效应,也不会有多少票房价值。当然,“导演”“演员”捧“戏”确实表明导演、演员的高明,但这不应该是我们轻慢剧本创作的理由。毕竟,一个剧作家的历史地位是靠自己的剧本而不是靠导演、演员确立起来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剧本乃一剧之本,一部舞台作品的流芳百世,剧本将永远是至关重要的元素。因此,剧本创作之衰,这是我们应该特别警醒的问题。
总而言之,近几年来西方话剧院团来华演出热潮,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气息和启示,它必将引导中国话剧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到世界话剧艺术大潮中。同时,它也让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话剧人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报纸文艺副刊检索系统”(14BZW119)的中期成果。
李扬: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小玲: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