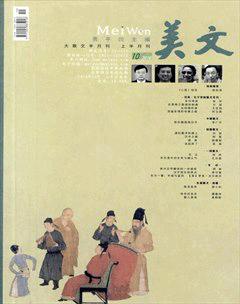阁西一夜听落月
已近岁末。阴阳昏晓被时光的长鞭一抽,分明变幻,恍若发生在一夜之间。日光渐短,暮色却随着愁绪越拉越长。飘泊无依的我,无言地听着黄昏奏出那一曲绵长的挽歌,看着边城的霜雪渐衰渐弱,数缕银魂空留下无边的落寞,恍惚间,便已觉到了天涯。
自然是无心入眠了。那么就这样吧,独卧于一床枕席之间,听那一夜落月。
我疯了吗?也许吧。但是旅居见闻告诉我,这里的夜带来的大都是恐惧,而非睡眠。这里的人们,家中都有亲人,在边境驻守。区区两里地,便是从民居到战场的距离,每近一步,危险便增一分。
让我听一听那落月吧!白日里我已听惯了兵刃与马蹄声。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我醒着,月亮偏西的时候,光芒从西阁的床照到了我的脸上,我听见它温柔的低语,心稍稍安定了一些。
一切归于沉寂,但我忘了,过分的沉寂永远是爆发的前奏。
短促急切的号角声尖锐地划破了静溢,接着响起的是沉闷的战鼓。我惊坐而起,开始已经老花的双眼看见天边清晰地燃烧着一片火焰。抬头仰望明月,现在才刚过五更,天还未明——天还未明啊!然而战事已起,除了遭偷袭,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吗?
再一次听见兵刃与马蹄声,伴随着我的月亮渐渐偏西。光芒依旧皎洁,似能照入心灵,抚平伤痛。
但是它温暖不了我啊!
冰冷的天幕坠落于三峡,星影在湍急的江流中摇曳不定。然而另一边,在不远处的战场,战士们的血液已汇集成另一个山峡。鲜血裹着夜空的清冷,在这黎明时分染红了广袤的大地。
我呆坐着,望向窗外,如同千百夔洲人家一样,惊得发不出一点儿声音。
悲壮的鼓角停滞。一片死寂。在这死寂中,我听到了月亮的一声叹息。待回头去寻,它已不知何时悄然隐没。
前方战地的大火咀嚼着余烬渐弱,同一个方向升起的初阳灼伤了盼归者的眼。信使纵马奔回,却只在村口面对众人神色凝重地摇了摇头。旷野里,不知是谁哭出声来,弥散开的声音很快连成一片,这是一种直入肺腑的伤。
哭声中响起了微弱的歌声,温柔,婉转,似能抚慰人心。人们随着低吟浅唱,他们所熟知的歌曲此时竟焕发出无穷的力量。他们唱着,哽咽着,忘情着,百感交集却偏偏无人记得,这是一首夷歌。
我真的想过,也冲上战场,佩剑披甲,在喊杀震天中挥洒豪气,在铩羽而归时横刀长啸。然而那只是少年人轻狂的幻想罢了。现在的我只剩下老朽的身躯和简单的笔墨书籍。作诗写文不能平复蜀中大乱,何况我也是黄土没到下巴的人了。人啊,这一辈子到头不就只值那一个土坑,一块石碑么?
难道不是吗?不论当年运筹帷幄的卧龙诸葛,还是汉末跃马称帝的公孙述,他们早已没于黄土,枯骨暗锈。对于生老病死的轮回,我又能说什么呢?承认。只能承认。
我的亲人中,没有人上战场。他们都健在,此刻我本应庆幸,但却感到了更深沉、更可悲的寂寥,寂寥得就像昨晚听的那轮月。
我徙然地再次将目光望向窗外。历经战乱的人们心中的月落了,太阳却迟迟没有升起,所剩的只有甚于极夜的黑暗与冰冷。在泪水燃尽了的空洞双眼中,再无光芒。
天已大亮。
黑暗,彻底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