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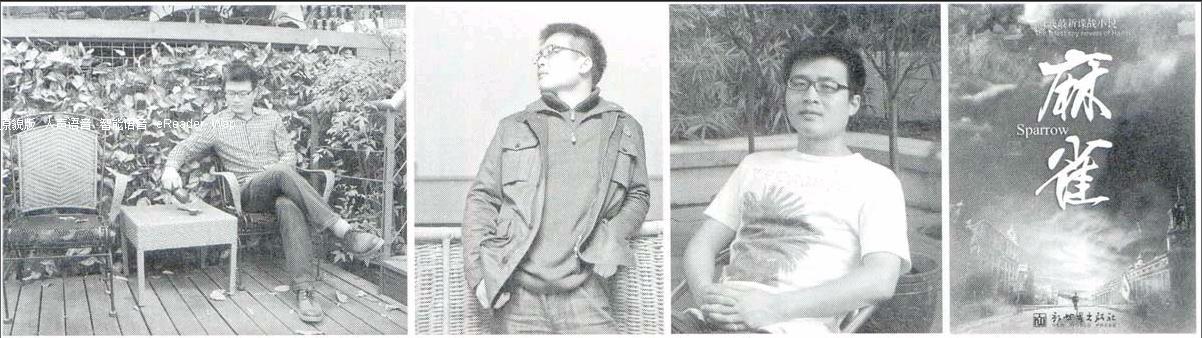
电视剧《麻雀》热播,也让70后作家、《旗袍》、《代号十三钗》等热播谍战剧编剧海飞成为热搜。
旧上海茶馆里,一个老到的说书人
文/郭嘉
海飞是个有温情的人,但他坚持认为自己欣赏残酷。奇怪的是,二者在他身上好像并不相悖。他凭着对文字的天赋和执拗,瞬间改变了既定的潦草杂乱的生活。误打误撞地进入编剧圈后,短短几年,《旗袍2》、《从将军到士兵》、《铁面歌女》、《隋唐英雄》、《花红花火》等,在屏幕上逐一呈现。他已然深陷其中无法抽身,这当中,属谍战剧陷得最深。海飞说这种感觉就像喝一盅温温的绍兴黄酒,几口下去,灯光柔美起来,眼神迷离惬意,微醺悠然自得,正是时候。
“《麻雀》不光展现那个时候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也传达了这样一种‘惟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的精神。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
对于谍战剧,海飞喜欢内敛与沉稳,喜欢不动声色的慢,喜欢那种暗流涌动的惊心动魄。这是一场海飞精心设计的触及人性深处的信仰大救赎,会有旧上海明媚而苍凉的阳光直射进来,平静的缓缓的节奏,“陈深”的剃头刀偶尔能反射出刺眼的余光,一切波澜不惊。然而若无其事的寻常背后,是无尽的暗流涌动、惊心动魄、你死我活。
宰相,麻雀,医生,这些幽灵一样的代号们,他们或沉默,或轻佻,或端庄地暗战在汪伪时代的上海天空下,他们从容赴死的那一刻统统明白,民族已经到了存亡时刻,我辈只能奋不顾身。
在他看来,尽管麻雀在飞禽中是属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种,但是他觉得“麻雀”两字里,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它普通而平凡的像共产党人,前赴后继。麻雀,是能叫得响亮的。所谓“一切潜伏都是人性的潜伏”,所以这必须是一种不起眼的暗流涌动的符号。
从四万字的小说到将近70万字的剧本,海飞说这里面有大量的内容需要扩充。“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十多个惊心动魄事件。各种烧脑的桥段,各种惊心动魄的设计都需要整体把握和创造。我常常在码字特别顺畅的时候,按捺住小小的激动,停下来小酌一会儿。我甚至可以想象观众看到一些精彩桥段时那种痛快的感觉。”
海飞总是把作品设定在上海,足见他对上海的情有独钟。回忆起在上海逗留过的童年,海飞始终有一种无法出戏的情感。“当我在三维电子地图查到曾生活过的杨浦区龙江路75弄早就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楼时,我不愿站在高楼的面前,甚至觉得自己像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所以我要做一些补偿,要把上海写进我的故事里,做一次文艺创作上的主宰。”
“沦陷后的上海仍有着她沧桑的美丽。精致的呢予人衣,旋转的舞厅,高档的咖啡馆,有人的地方就有欢娱。我觉得那时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那时的麻雀也是,它栖在屋檐上时,一定望着这座沧桑而繁华的城市百感交集。”
于是,海飞变成r旧上海茶馆里,一个老到的说书人。他的眼神扫过听客,醒木的声音响了起来,接着是他滔滔不绝的南方口音。他说《旗袍》里的关露萍,身姿曼妙,穿着名贵的九风旗袍款款走来,好似浣纱女西施,一身抵得百万雄兵。他说《麻雀》里的陈深,爱人死时他装作不认识;同志死时他装作无所谓,那么敢爱,爱得热烈;那么敢死,死得从容。他还说千千万万个与汪伪特工机关之间展开各种殊死较量的甲乙丙丁,在旧上海迷情温柔的气味里前赴后继,永垂不朽。
不愿拉煤而爱上写作
文/海飞
1994年我开始学写散文,当时有一本叫《启星》的文学内刊吸引了我。这本内刊的编辑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我真正开始认真而专注地写小说,应该是1996年夏天。我从一家县城国营化肥厂游手好闲的保安,下放到车间当拉煤工。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场特别大的打击。我不愿拉煤,所以我梦想着通过写作调到厂办写材料。我调到了另一家生产药品的企业办厂报,发现我真的爱上了文学。
其实从1986年我的少年辰光开始,我就接触到一些文学刊物。我不明白我那人老粗的工人舅舅,为什么喜欢捧着杂志看小说。我顺便帮助他看掉了一些小说,那时候我觉得写小说的人是如此伟大。我会抚摸杂志上作者的名字,想如果有一天我的名字也能印在杂志上该有多好。很多年后我开始在小刊物上发表小说,我望着小说的标题和作者的名字,会长时间地难掩喜悦之情。
我想象中的小说应该更好更精彩更有深度更令人激动,应该在文字里装满那种辽远的东西。
我的生活经历有些复杂,十四岁开始进入社会,换过许多工种。我并不是因经历多而沾沾自喜,我只是学会了在少年时就以一个社会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
我特别喜欢使用我惯常的叙述方式,一是从容,二是镜头感。我喜欢把自己悬置在半空中,以一个坐在摇臂上的电影摄像的角度来描述事件的发生与进展。我想象黑暗与明亮中的场景,想象孤独者的模样,想象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我甚至想象时间静止的时候,一滴水以怎么样的姿态滴落;想象一个女人在痛苦的时候,怎么样慢慢露出微笑的过程。我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中不能自拔……
历史的“本质”究竟如何,谁也无法说清。我以为我一直都乐此不疲地想要触摸到的就是历史的“本质”,这是一件令人兴奋并且产生无穷动力的事。我眼中的本质大约是——风生水起背后的苍凉。
我们像两羽同类鸟
文/朝潮
海飞有着一颗相对饱满的头颅,这颗头颅热爱想象,喝了酒以后,那些想象就会发出光亮来。
最近一次见海飞,是在年初的一个暖暖的下午。此前下过两场雪,这天是气温回升的第一天,暖的印象格外强烈地提到我的感觉日程。海飞问我要不要开空调。我说不用,我感觉很暖。然后,一人一杯清茶,两人像两片纹理绵密的木板,暖暖的烘晒在语言的光亮里。
海飞当过兵,复员后在一家国有化肥厂做经济民警。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当时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叫作诸暨的小城市,三天两头栖在一处,像两羽同类鸟。那时的我们太年轻,无知而无畏,以为这个世界所有的房间对我们来说都是敞开的。海飞的出生地叫丹桂房,听起来像一个诗意命名的房间。他的小说和散文里经常会提到这个梦幻格式的地名。
写作接近于祈祷,这是海飞感情细腻而强烈的意志行为,然后才是勤奋——这可以成为他的速度的注解之一。他跟人说话时经常“呵呵”,是一种宽容的态度,宽容生活和他人,也宽容他自己。
“让我们保持握笔的姿势,直到日落西山。”这是新千年的第一天,海飞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话。这封信很动情,海飞没有寄给我,他寄给了几家日报晚报,全都刊发在副刊的头条,在新千年的第一天。
没有一种东西是长生不老的。当一个人日落西山之后,身体和身体以外的房间之类都将随之失去,某些文字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