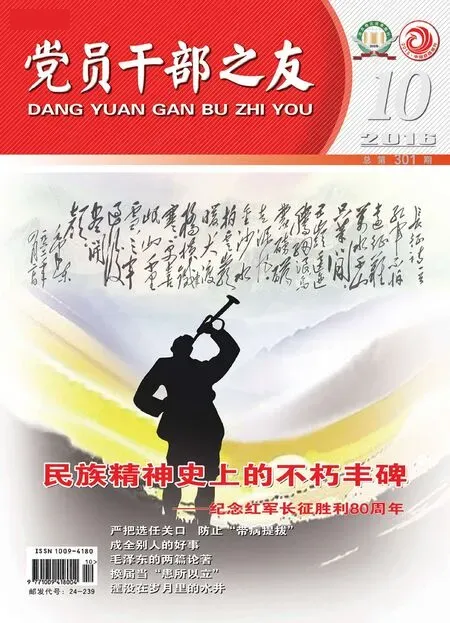湮没在岁月里的水井
□ 李继峰
湮没在岁月里的水井
□ 李继峰

井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远古的人逐河而居,水井使人类可以远离江海湖泊繁衍生息。井水经过了大地的过滤,变得清醇甘洌,更适合人类饮用。井是故乡的象征,古人用“背井离乡”来比喻游子的远离。长满青苔的水井,古老破旧的院落,高大歪斜的树木,总能牵动游子的思绪。
老家街上有眼井,临着主街道,各家挑水都不远不近。井口直径有两米多,幽深,粗犷。井挨着坑塘,洗衣服、冲凉的污水可以流进坑塘,不至于弄湿水井周围的空地,特别是冬天,避免了井口周围结冰。这水井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村人,如今,它像一位久别的亲人,已变得非常陌生,偶尔到老院大宅的景点参观,见到一些很精致的古井,就会想起家乡已被废弃、填没的水井和关于井的种种往事。
这眼井大概在我六七岁时挖的,现在想来已40余年。一个深秋的清晨,一通鞭炮过后,村人簇拥着从邻村请来的打井专家开始挖掘工作。先挖出一个深四五米,直径两米多的深坑,底部放入一个直径两米半左右的木质圆盘,铺平放稳,沿着圆盘,边砌砖,边往井筒外围回填泥土。待井筒超过了地面,便搭起六米多高的井架。井架由三根直径40多厘米的榆木搭建,斜插入地,顶部交叉处用铁链与绳索捆绑。井架顶上安装两个巨大的滑轮,分别挂有铁制大桶,一个是用来站人,另一个用来盛泥水。挖井是个大工程,需要团队合作,生产队长事先已将人员周密分组。挖井者在挖掘脚下泥土的同时,要小心均匀地挖取木盘下的泥沙,使井筒均匀下沉。地面上的人,则要十分精准地砌好不断下沉的圆形井筒。挖井者每隔一段时间必须上来喝口酒暖暖身子、透透气。井上人赶紧用清水替他们冲洗、揉擦,直到遍体通红,再裹上棉被,恭送他们去休息、吃饭,紧接着下一组继续下去干活。挖井,要经过泥层、沙层,再到泥层,掏到几股较大的泉洇(普通话应为水脉、泉脉),才会完成挖井工作。在大地的重压之下,柔软无比的水,竟然能在几十米下安然流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水脉,像地球的血管,是水井,联通了人与地球的血脉。
打成的水井有十五六米深,井台用青色的条石铺成,石头镶嵌在土里,稍微露出地面。井口很大,且特别深,趴在井口往下看,清澈见底,光洁如镜。当然,大人们是不允许小孩往井里伸头张望的,总用一些传说来吓唬我们。谁敢往井里伸头张望成了我们打赌比勇敢的游戏。见大人打水上来,小嘴啜在筲沿,稍一倾斜,水就顺着进到嘴里,当然,胸前肯定湿一片,凉凉的,甜甜的,肚子里,肚皮上,成了里应外合的清凉。谁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小伙伴们都会背着大人偷偷地用纸包出来在井边分给大家吃,喝一口井水,尝一下美味,成就了最美好的回忆。
挑水是一件很繁重的家务。煮饭泡茶,洗洗涮涮,猪牛羊鸡鸭鹅狗,都需要用水。即便再穷,每家也必备一对洋筲,一副钩担,一口可以盛好几百公斤水的大瓷缸。洋筲开始是很沉、很厚的铸铁打制而成,后来变成了薄薄的白铁皮。洋筲的上端是用钢筋做成的“弓”形把手。柞木钩担柔软光滑,富有弹性。小孩子看着大人颤颤悠悠地担着一担水进了院门,赶紧跑过去掀开瓷缸上盖子,取下外挂在缸沿上的水瓢,撇去上面的枯枝浮叶,舀半瓢新水,咕咚咕咚喝几口,滋心润肺般的凉爽!男孩子十二三岁就要学习挑水。由于个头矮,要把扁担上的铁链折叠、减少高度,才不至于水筲着地。当把水筲扔进黑森森的井里时,那种兴奋、胆怯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井边最热闹的季节是夏季。洗菜的,洗衣的,老远就能听到朗朗的笑声。赶路的外乡人,经过水井,搬过洋筲,俯首痛饮,甘洌的井水顿扫一身的疲劳和风尘。到了夜晚,井边的大树下坐满了乡亲,小孩们一旁奔跑玩耍,大人们你一言我一句,古今中外,天南海北,胡聊海侃。有的人热得受不了,扯张席子到这儿睡。半夜三更也有人从水井中打水冲凉。那些小姑娘、小媳妇则要挑回去,用透凉的井水冲去一天的辛劳与疲惫。
从井里打水是一门学问。开始不会打水的,在水筲外侧系上一小块砖头,使其倾斜,下井后就很容易进水。水深的时候要用井绳,双腿叉开,两手紧握粗粗的绳子。绳子的前面有个钩,钩挂在水筲的提手上,双手用力左右摆动起绳子,水筲随着绳子的摆动,筲口偏下,进入水里,井水则趁势灌入筲中,渐渐沉下去,等水筲装满了水,再用两只手上下用力地轮番提升,将筲拉上来。那些年,日子虽穷,雨水却大,一场大雨过后,井里的水和井口只差三四尺,打水都不用井绳,只用钩担挂着水筲朝井里一扣,一提,满满的一筲水便上来了。也有人技术不过关,筲掉到井里,被村人嘲笑。只好用井绳绑着抓钩子捞筲。碰巧水筲倒到井底,只能用井绳绑着大块的吸铁石打捞。打水不仅需要力气,也需要技巧。低头打水时,最好不要往后看,从叉开的裤裆往后看,世界是倒的,这时,人会有片刻的晕眩,弄不巧会一头栽倒井里。打水人不慎坠井的事常有发生。老弱病残者,是万万不可去井上打水的。挑水很辛苦,我们的革命传统教育也离不开水井。八路军给老乡挑水、地道战等故事,都与井息息相关。江西瑞金的那口井,因为有毛泽东的题词“吃水不忘挖井人”,更是闻名遐迩。
生产队用来喂牲口的,则用一眼井口更大的井,上面有一个很先进的辘轳,是生产队的一件重器。辘轳上面缠着一圈又一圈粗壮的麻绳,绳子头上拴着一个弯弯的铁钩子,吊着一只巨大的柯篓。生产队喂牲口淘草,饮牲口,送饭送水,洗地瓜、吊粉条,都靠它。打麦场使用完毕,要翻起来种一季萝卜、白菜,这个菜园子浇水,也用这辘轳提水。因为水桶很大,在提水时,注意力都很集中。往下放桶放绳,惯性太大,一不小心,也有人被摇把打了脸、打了下巴。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各家开始陆陆续续打压水井。压水井在自家院里,方便,快捷,省力。井杆有铁杆的,也有铁筒插入木杆的。放学回来,便往井筒里倒一茶缸子引水,上上下下十几下,觉得很沉了,水就流出来了。那时身材瘦小,力气不大,有时需要跳起来才能压下井杆,但乐此不疲,邻居家孩子也有不小心被反弹的井杆打了下巴、打了脸的。打了压水井,也买了电风扇,家人从挑水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很少有人再到水井挑水、冲凉,也没人再到那儿凉快,水井慢慢成了孩子们嬉戏的潜在危险,水井,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后来,县里派来钻井队,竖起20多米高的铁质井架,打了近百米深的机井。机井打好了,生产队也买来了用黄纸点火、摇轮启动、威力巨大的柴油机。接好管子,水泵上挂上柴油机宽大的皮带,煞白的水柱便喷射而出。机井的水似乎更清,更甜,附近的村人都愿意走远一点的路来机井挑水。听到机器响,我们便跑过来玩,趴在出水的黑色、粗大的橡胶管上喝水、玩水,大胆的还跑到水垄沟里撩水、泼水。垄沟多年使用,长满茅草,因浸透了水,我们的美食茅根变得好挖多了。有了机井,村支书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兴奋地高呼:我们野庄率先实现了灌溉农业!
随着田野里机井数量的不断增加,乡亲们发现,压水井慢慢不出水了。压水井只能抽上来地下13米多水位的水,后来学初中物理才明白这个道理。父亲花了1000多元请来专业打井队,他们在院子里选位置,搭井架,调钻头。随着钻杆的转动,一段段碗口粗的泥条从地下掘了出来。当钻到30多米时,湿漉漉的钻头上沾满泥沙,井总算打成了!这口小机井直径不过30厘米,放入机井的水管末端,是一个微型高压水泵。推上电闸,在电机的轰鸣中,一股清泉从水管喷薄而出。不几天,周围的邻居都隔着墙头接来管子,对好管口,不到五分钟就接满一缸水。又过了不久,县乡采取农民自筹与财政资助相结合的方式,打深水井,铺设管道,村人家家吃上了自来水。只有在冬天水管偶尔被冻住的时候,我家那口电动机井才能派上用场。如今回老家,在田野里常见整齐划一的机井房,水垄沟却不见了,变成了埋在地下的导水管,打开责任田的水龙头,清水就汩汩地流入地里,浇地已变得非常轻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的禀赋性情里总带着井水的特质,背井离乡是一场寻找希望的漫漫旅程。出门的游子,家可以搬,井却搬不动。喝不惯别处的水,总要闹几天水土不服。研究生毕业后,留到泉城工作。虽然“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已成往事,济南的水,却是名不虚传。“天下第一泉”的“趵突腾空”胜景多次看到,墨泉、百脉泉等竟能一泉成河。黑虎泉、琵琶泉一带,早晚提水的人络绎不绝。泉边提水的,多是中年人与老者,这源于他们对水井时代的留恋与怀念。
井,是一部无字的书,记录着人类的历史。前些年,长沙一口古井里,发现近万枚东汉早期的竹简和木牍。井的消失,也许是一种进步,但同时也填埋了一段段生动的人类故事与历史时光。井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几乎以一成不变的面目来到现代社会。30多年来,井的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我们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窗口和缩影。如今,井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与视野,我们离大地的水脉越来越远。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精细、精致,甚至高档,桶装水、瓶装水已成为主要生活用水,这是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丰厚馈赠,但在内心深处,我们依然眷恋着那口水井,偶尔会想起趴在水筲沿上大口喝水的畅快淋漓和那带有家乡味道的井水,打水、挑水的劳作之苦早已被岁月冲淡,它的甘甜之美却愈久愈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