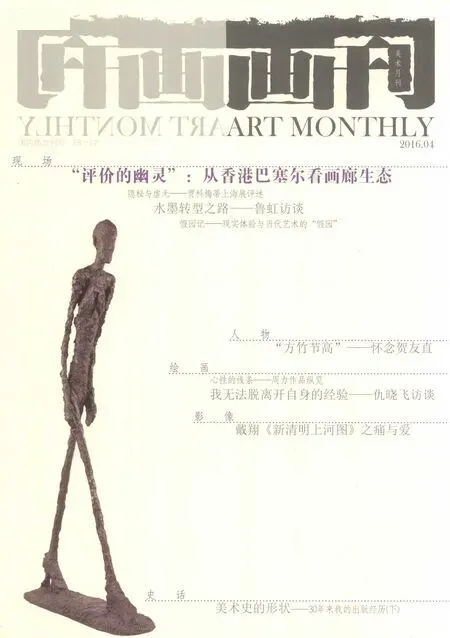切片
切片

《棠樾之贰》 董小明 纸本水墨 130cm×96cm 2016年
孙振华:今天,我们如何面对“中国画”和它的传统?
明末清初,画界出现了“吾国之画”、“中国之画”的说法,但是,它还并没有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对于绘画,人们更习惯以“丹青”、“图画”的名称来描述,或者使用“士人画”、“院画”这些具体的名称。“中国画”到二十世纪后才真正确立为一个学术概念。
中国画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由“天下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由文化中国变成现代中国。其最大的区别是,“传统中国”是一个依据文化认同建立起来的文化共同体, “现代中国”是一个依靠政治认同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前者是封建的、专制集权的;后者是共和的,倡导民族平等、个人平等。
中国画概念的出现,与中国的现代性有着密切关系,把中国和西方并置、对比起来谈,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知识。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就需要建立新的主体性,这就是“中国画”概念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这就需要在新的国家框架中,回顾我们的过去,梳理我们的传统,重新建立中国的历史叙事、文化叙事、图像叙事……一门学科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最好的办法就是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整合、建构自己的传统。从世界范围看,到近代,随着民族国家纷纷出现,每个民族都开始确定自己的语言,根据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愿望来重新书写历史。
中国画概念的流行、中国绘画史的书写,正是现代性的产物,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的现代转型,它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整合中国的传统资源,以便走向未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自身的主体性,就会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西方时间中,就会失去自身的民族自主性。
面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多次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碰撞,如何在新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中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是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其实是一种“再发现”、“再创造”。 正如史密斯所说,“只要进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一种‘被发现的传统’,这种‘被发现的传统’其实是对过去历史的‘重新建构’”。所以,“中国画”概念的出现,也意味着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传统、评估传统、改造传统。
由此可见,“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想象的过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传统水墨画的时间和空间意识观就显出局限,显得狭窄了,它充其量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的传统,是一个中原文化的传统;而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重新想象传统,就需要我们突破原有文化疆界,为中国画增添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因素。
周京新:水墨不要割断历史
“新中国画”和“新水墨”是前后交替的,新或者不新,这个说法并不重要,我觉得关键还是看画。我理解这个展览的主题,也许圈内有一种想法,试图把中国画和水墨区分开,认为中国画是从传统走过来的,而水墨虽然是中国原有的,但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国画的异化,是一个变种。也许是这么一种定位。至于认不认可这种定位,我觉得不重要,别人看我是“新中国画”也好,是“新水墨”也好,我都不在乎,我就是画画的。可能在我心目中,中国画是包含水墨的,它的体系大于水墨,包括壁画和古代木板画等等。
至于边界问题,这次有很多别的材料的,比如用手指蘸水墨,或者一些外国人用水墨、彩墨等画的。我看到很多人在争论这个事情,认为它不是水墨。我觉得这既然是一个国际水墨双年展,那这个问题就无所谓了。
水墨能否国际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再咬牙跺脚,再拼命宣传,都没有用。当我们成为了强国,把优秀的作品拿出去,自然会被认识到。我们并不缺少好作品,也不是缺少外国人能理解的元素,我们走出去了,被看到了,就会有人来理解我们。到那时,我们的纠结就不是问题了。

《羽人-3》 周京新 纸本水墨 48cm×180cm 2011年

《养蚝场》 苏珊·雷金德斯(Susan Reijnders ) 纸本设色 68cm×138cm 2011年
不过,我认为水墨还是不要割断历史,有相对规定的材料和技术语言的标准。你可以随意去突破它,但是标准一直在那儿。我自己的实践一直在面对这个标准,挑战这个标准。当然,我所谓的水墨是指从中国画衍生出来的水墨,跟这次展览的水墨概念还是不同。它们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儿,也不是对立或者取代的关系。以前,有人认为油画写实,中国画不写实,但我们看看艺术史,不是这样的,写实是写意的根本,写意从来没有脱离过写实。我觉得这个展览好就好在有包容性,不管“新中国画”还是“新水墨画”,不需要搞出个你死我活、你对我错,没有必要,艺术不是这样的。
毛建波:写生的异化与中国画写意精神的消亡
在20世纪的时候,潘天寿等先生提出中国画和西画是世界艺术的两个“高峰”。这两个高峰实际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们对应的文化背景、观察方法、写生方法、临摹和创作的方法都有不同的思想和哲学基础。
中国画家的写生是一种游观的方式,人置身于自然,领悟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对自然的感受和想法最终都贯穿到作品里。比如《富春山居图》,我们知道它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场景的表现,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具体的场景。黄公望把江南山水的绵延茂密以及隐居山水之间的舒畅和缓的心情都融入了进去;西方的写生本着科学实证的态度,更多地努力表现、呈现自然。所以他们写生时的场景、情境等因素几乎是不变的。比如今天是画八点钟的场景,当光线变化了他们就不画了,第二天还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光线、同样的角度再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后来吸收了一些中国等东方因素才进有所改变,出现了印象派那样的画。
而我们现在,一代一代的学生接受美术教育时,大都是用西方的方式去写生,因此忽略掉了很多中国画的精神和思想。我们现在画的雁荡山也许可以比潘天寿画的更像,但是缺少潘天寿画里雁荡山的那种雄强、壮观和对东南山水奇秀的这种美的体悟。中国文化是体用一致的,也就是说精神跟物质是合二为一的。中国画的三远:平远、深远、高远,既是观察方法,又是布局方法,更重要的是对绘画意境的表现。现在我们用西方的方法,把写生割裂出来,只作为一种观察方法,就是将中国画矮化了。
西方写生方式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原来游观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写意精神的改变。这个写意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绘画的写意性,一个是写意精神,也就是画家的个人生命体验。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最后成“画中之竹”,包涵了很多思想和情感的东西。写意是精神性的,我们看中国画通常画起来很快,实际上这是一生的经验、精神和思想的浓缩。从这个角度看,写意精神的消亡虽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写生的转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人的写生方法更多对应的是自然跟心源,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国人说造化即自然,这个自然不是现在英文的“nature”的概念,而是一种关注情感体验的天道自然。我们面对造化和自然,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二三枝”(清李方膺《梅花》,编者注)。造化本身就带有很多情感和思想的因素,中得心源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眼光进行的浓缩。所以中国画家即便看到同一个场景,但根据个人的学养、经历、个性和思想,表现出来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西画虽然在一些笔触技法上有变化,但表现出来的画面基本是一致的。现在的美术教育中,从招生开始,中国画的考试就是用素描、色彩等西画技法来考核,学生已经形成了一套西画的眼光和方法,即便拿起毛笔,也是用的西方的表现方式。表面看起来,这是有利的,对造型和写实的能力有很大帮助,但弊端也很明显,写实能力的提高,并没有办法掩饰技法的贫乏,思想的贫乏,更没有办法掩饰画家对对象感悟能力的退化。
注:本文部分内容根据访谈整理而成。

《世界 中国》 杨诘苍 现场装置(印刷体)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