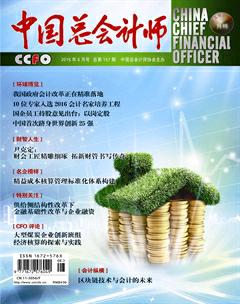金融基础性改革的未来走向
金融基础性改革就是要在金融整体框架的利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等维度进行实质性改革。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力推进,金融基础性改革的步伐必将更快,取得的实质进展也将更多。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持续推进并最终完成
市场化利率定价机制是金融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前提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进入宏观和微观联动的新阶段。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应该对利率市场化的宏观绩效(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以及不同改革发展形式(表内市场化和表外市场化)进行持续观察和评估,这事关我们对潜在改革风险(金融危机)的研判。
二、直接融资市场将得到更大发展
(一)股权融资将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规模将合理扩大
日前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指出要完善证券交易所市场股权融资功能,规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发展,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改革完善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合理扩大债券发行规模,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在投资者分类趋同的原则下,分别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发行准入标准和审核规则。加快债券产品创新,发展股债结合品种,研究发展高风险高收益企业债、项目收益债、永续债、专项企业债、资产支持证券等。加大信息披露力度,规范债券发行企业信息披露行为,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强信用评级制度建设,强化市场化约束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债券市场开放。
(二)金融创新将持续,普惠金融有望得到较快发展
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持续增长,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从而更加开放包容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开放金融体系,在适度监管的情况下鼓励金融业综合经营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创新活动。应该在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建立多种所有制、多种业态和大中小型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
三、宏观调控框架的重构
应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建立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不懈地逐步扩大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市场化成分。在以宏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限制使用(软预算约束部门)扩张性投资计划作为刺激工具,而更多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根据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经验,这样的政策组合具有正向总量效应和正向结构效应,能够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结构优化。
二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改变长期以来侧重GDP的中央对地方考核机制,在关注生产性指标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居民收入、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社会保障、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因素。
三是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处理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关系。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某些阶段中,财政因素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导因素。今后的改革中,应进一步明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职能定位,完善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机制。此外,还应注意掌握财政资产负债真实情况,提高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透明度,切实防范财政负债隐性化的潜在风险。
四、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三位一体的金融管理体制的构建
当前,中国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和金融机构杠杆率高企并存,这也对协调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危机后初步建立起来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实际上由分散于不同管理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各种政策工具组成,彼此目标并不一致,工具使用也缺乏协调,难以有效应对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放缓和系统性风险积聚造成的双重挑战。所以,应在条件成熟时,对金融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构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三位一体、彼此协调的新金融管理体制,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
五、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简政放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即将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备受各界关注:一是金融监管机制改革将是一大亮点,二是当前金融混业、交叉综合化运营趋势已遍地开花,跨界金融创新使基于事前的产品审核的监管模式难以适应。如何构建顺应市场秩序的金融监管秩序,实现事中和事后穿透式监管,推动过程监管和护卫程序正义,无疑是目前当务之急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金融监管机制改革存在五大方案之争:超级央行模式、一行一委模式、一行两会模式、一行三局模式,以及在现有金融监管框架基础上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模式等。
具体分析,超级央行模式存在政策制定与金融监管等的职能混搭问题,而将央行与银监会合并、证监会和保监会保留的一行两会模式,则类似于走回头路,一行三局模式和在现有监管框架上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模式,更多是在现有监管框架上打补丁。
其实,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不是单纯的机构间分合,而是行政机关监管理念上的一场革新,是通过监管机构的机制设计,使金融监管体系向更适应市场机制的方向搭建监管框架。央行和三会合并为综合金融监管委员会的一行一委模式,更直接地将货币金融政策制定与金融监管职能有效分离开,各司其职;同时又有助于愈合现有分业监管的漏洞,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需求;此外,还将使金融监管链条更清晰,更加注重于市场过程的合规监管、程序正义,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改革,而非将监管中心放置在实质内容的监管上。
当然,要真正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态势,构建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从监管机制设计上要尽可能摒弃分业监管,避免任何形式的山头主义监管问题;从监管理念上,树立负面清单管理理念,走出重实体、轻程序的实质内容审核,更加注重过程合规监管和程序正义的护卫。
金融监管机制的设置是护卫“正确地做事”,还是“做正确的事”,这决定着今后监管的走势,也决定着市场与政府边界的厘清程度。护卫“正确地做事”的秩序,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金融监管才能真正从金融活动中独立出来;而监管的目的若是监督金融机构“做正确的事”,那么,监管将很难从金融活动中独立出来。而且,在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中,要让监管机构厘定什么是“正确的事”,无疑也是勉为其难的,这将导致监管无法走出实质内容监管的繁琐,这其实是任何监管机构都无法胜任的。
因此,彻底将金融监管理念定位为“正确地做事”,进行合规和过程监管,护卫程序正义,才是当前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正途,也才能真正使权力与权利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因为立足“正确地做事”,不仅可有效规范权力的行权边界,而且合规下的金融行为可带来最不坏的结果;而“做正确的事”,使监管本身就带有了价值判断,会导致金融行为的结果无法判断,除非监管机构是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