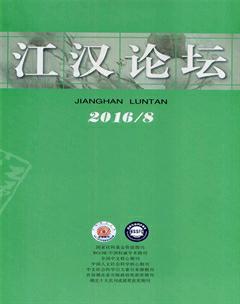道德滑坡只是传读之误吗?
韩东屏 李海平
摘要:郁乐先生关于当下道德滑坡只是传读之误的观点需要商榷。今天国人所说的道德滑坡,在时间上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状况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道德状况比较而言,但郁先生却把它变成了将我国当下的道德状况与整个历史中的道德状况做比较。这样的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传媒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但并非现代技术凸显和放大了道德问题,并非传媒推动了人们的道德焦虑,并非受众的误读虚构了道德滑坡,而是道德滑坡确实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此外,郁先生推论我国当下应该是道德爬坡的三个根据也不成立。实际上,考察一个国家的社会赏罚机制的扬善抑恶功能是否有效,就能对这个国家的道德状况作出判断。
关键词:道德滑坡;道德爬坡;道德焦虑;现代传媒技术;社会赏罚机制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8-0060-05
郁乐先生《信息嬗变、道德焦虑与道德滑坡论》(以下简称《郁文》,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一文,从信息嬗变的角度切入,解析今人道德滑坡之叹的传读之误和道德滑坡的虚妄,意在缓解国人的道德焦虑,其论证视角之独到值得关注,其用心之良苦值得肯定。然而在笔者看来。在道德滑坡问题上存在误区的正是郁先生自己。只要实事求是地考察,“道德滑坡”就绝不是什么传读之误,而是对真实状况的形象概括。
一、如何界定“道德滑坡”?
《郁文》的总观点,就是今人所谓“道德滑坡”的感叹,是由道德事件信息的传播、认知与解读过程中的筛选、扭曲与失真造成的误读。然而,《郁文》对这个观点的论证,在根本方法上就存在严重问题。
何谓“道德滑坡”?
显然,要想讨论清楚我国当代道德是否存在滑坡的问题。必须对“道德滑坡”概念有一个明确而严格的解释,并且以其为开展讨论的必要前提。因为我们只有厘清了“道德滑坡”的所指、判断方式和时间节点等要素,才能继而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论说道德是否存在滑坡。否则,要么大家说的“道德滑坡”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要么大家说的道德滑坡的参照系并不是一回事。结果不论哪种情况,都会使讨论变成无谓的自说自话。
反观《郁文》,尽管在道德滑坡的判别问题上,有存在与认识之关系的厘辨。有媒体认识论效应的分析,也有受众识别与评价媒体信息的心理机制等方面的解剖论证,却独独没有对“道德滑坡”这个最为重要的概念的界定。既然如此,《郁文》又怎么能断然否认道德滑坡的存在?不究其所是就断言其不存在,这是极成问题的,可谓无厘头之说,必然导致最后结论的不可靠或无意义。
笔者认为,道德滑坡应是指一个社会近一时期的道德状况发生了明显不如上一时期的变化。这个“道德状况”不是指该社会主流道德规范体系的水平如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而是指该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平如何,是高还是低。由于任何社会的大众道德水平只能是由所有个体的可感行为而非不可感心思构成并体现,所以道德滑坡就是指社会近一时期的道德失范行为变得明显多于上一时期。据此可知,历史中。凡是有近一时期大众道德水平不如上一时期的状况,就都属于出现了道德滑坡。
同时可知,讨论道德滑坡的问题,必然要有“近一时期”与“上一时期”或“今日”与“往日”的比较。就我国当下关于道德滑坡问题的讨论而言,就是只有通过我国今日道德水平与往日道德水平的比较,才能够得出我国当代道德水平是否滑坡的结论。而要做这种比较,就得先确定我国道德水平的“今日”。和作为其参照系的“往日”,究竟是哪两个时间段,其分界线又在哪里。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根据“道德滑坡”的说法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并讨论的实际情况,这两个时间段分别是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今日”与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往日”,而分界线就是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如是,我国当代“道德滑坡”的说法,就是意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众的道德水平明显不如改革开放前的道德水平。实际情况亦如此,国内伦理学界自1980年代就开始并持续进行的有关“道德是滑坡还是爬坡”的讨论,无不在时间上以改革开放为界来区分“今日”与“往日,。当然,《郁文》对我国道德状况的分析也有时间维度的比较,只不过与大家公认的大不一样,是用没有任何明确时间上限划定的中国“今日”的道德状况,与中国此前整个历史中的“往日”的道德状况相比较。这种比较法是荒谬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照这种比较方法,不仅“今日”与“往日”、“现在”与“过去”的边界模糊不清,而且现在的道德状况永远不会比过去差,也永远不会比过去好,因现在所有的道德现象,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能在漫长的往日中找到同类项。
《郁文》在方法上的错误还体现为自己说法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极力论证今人关于道德滑坡的感叹是传读之误;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没有量化抽样调查和统计的情况下,很难对当前整体的道德水平与过去的道德状况进行比较,因此道德水平是否滑坡难以判断。这就不免让人发问:既然道德水平是否滑坡难以判断,那又凭什么说人们关于道德滑坡的说法是传读之误呢?
其实,只要研究方法得当,道德是否滑坡的问题并非如《郁文》认为的那样难以判断。因为我们既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做量的比较而得出客观判断,也可以通过分析道德失范行为产生的原因来推出这种判断。而本文以下论述,就包含有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现代技术凸显和放大了道德问题?
毋庸讳言,相对于保守封闭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信息流传速度是要快得多,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及传播方式的变化,对道德事件的广为人知也的确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郁文》由此就认为现代技术凸显和放大了道德问题,并影响了公众对道德现状的判断,却有夸大其词之嫌。
首先,郁先生为了坐实所谓现代传媒技术放大道德问题之“罪”,有意识地忽略了现代传媒技术对道德事件的正效应。他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得的信息量呈爆炸性增长之势,“负面信息随之也必然有爆炸性的增长”,由此加重了公众的道德焦虑,导致道德滑坡之感。但他没有意识到,或者虽然是意识到了却故意悬搁不提——在信息总量爆炸性增长的大背景下,虽负面信息爆炸性增长,但正面信息同样也有爆炸性增长。一方面,假冒伪劣事件、食品安全问题等负面信息在现代社会传播更快;另一方面,道德榜样、社会正能量等正面信息在现代社会传播速度同样也不慢。因此,今昔的正负信息数量之比应无明显变化。人们的道德感知也不会由于信息总量的大量增加而发生变化。
其次,为了论证“现代技术凸显与放大了道德问题”这一结论,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区分。即“存在”与“知晓”的认识论区别,也即存在未必知晓,知晓未必存在,并特别强调技术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就是说被现代人认为是道德滑坡的事情,其实在传统社会也同样存在,只因当时技术落后,不仅没有现代传媒技术,而且没有现代检测技术,所以传统社会中的同类事件要么难以被检测发现,要么影响范围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不道德的情况。他以食品安全说事:以往食品即便存在卫生、质量与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可靠的技术手段予以检测而加以发现:即使能够发现这些问题,也因为缺乏信息技术而无法让更多公众在短时间内知晓。然而,这个论证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其一,仅以一个食品安全方面的例子来证明现在的各类不道德现象其实都是以往就存在的,只是因技术落后检测不出,这种论证在方法上属于严重的以偏概全。因为现代社会在其他方面所出现的各种不道德现象,如坑蒙拐骗、偷盗抢劫、官员腐败、黑黄赌毒之类,都与技术检测水平的提高无关。其二,即使在食品安全方面,也不是现代技术把原来不是问题的事情变成了道德问题。因为当今食品安全方面的不道德,并不在于没有采用现代的制作方法生产食品,而是在于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在明知食品安全不达标的情况下,仍在继续生产或销售。没有人说用传统食品制作方法生产食品就注定不道德,而是说在有了技术检测手段和标准之后,那些明知食品安全不达标而仍要欺瞒顾客继续进行生产销售的行为不道德。也就是说,以前即便有生产或销售不安全食品的人,也是因为不知食品不安全;而现在生产或销售不安全食品的人,则绝大多数是知道食品不安全还在继续生产、销售。而这个差异,就是今日与往日相比的一种道德滑坡。
第三,郁先生还以假冒伪劣现象为例来论证道德滑坡的不存在:“对道德焦虑影响较大的社会现象有假冒伪劣、骗子骗术与人情冷漠。事实上,这些社会道德现象并非是全新的,规模与性质的比较也没有客观标准,很难说现在就‘滑坡了。”然而,郁先生的论证有点事与愿违,尤其是他对假冒伪劣现象所做的几点说明,恰恰证明了道德滑坡的存在。其一,郁先生自己也承认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假冒伪劣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其二,郁先生认为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当下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同于此前的传统社会。一是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自己生产的生产者没有制假动机。二是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少数为别人生产的小商品生产者面对熟人顾客造假成本高。既然如此,岂不就等于是说,现代社会造假成本不高,现代社会为制假动机的存在提供了更适宜其生长的土壤?而这岂不就是对现在不如从前的道德滑坡做了原因方面的论证?其三,还需要纠正一点,假冒伪劣并不是只有绝对数量的增加,而没有相对数量的增加。相对数量是指什么?郁先生没说。按正常理解。应该是指所有为别人生产的生产者中,搞假冒伪劣的人数只占一定比例,而这个比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既然作者承认为别人生产的生产者的造假风险,在现代的生人社会要明显小于传统的熟人社会,那这个比例又怎么会没有变化呢?其四,道德滑坡或行为失范,并非今昔在比例上一样。因为,卖吸毒品、黑社会、大量半公开的黄色产业和医生收红包等,都是前所未有的状况;而官员腐败、社会失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考试舞弊、食品安全之类,则是比过去更甚。据统计,世界70%的假冒伪劣商品出自中国大陆,而改革开放前,我国则基本上没有假冒伪劣的问题。又如腐败,改革开放前虽然也有贪腐官员,甚至出现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高干,但从没有像今天这般常见的“腐败窝案”、“腐败串案”和“塌方式腐败”。再从犯罪率上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犯罪率一直很低,犯罪率维持在每10万人30起至60起刑事犯罪案件的水平,每年刑事犯罪案件不过20万起至30多万起,是世界上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78年以来,中国的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呈加速度发展的趋势。仅以公安机关立案的犯罪案件为例,1978年全国发生的犯罪案件只有53万多起。犯罪率为0.56%,(每10万人56起刑事案件);1990年全国犯罪案件猛增到221万多起,犯罪率上升为1.94‰;2000年全国犯罪案件增加到363万多起,犯罪率上升为2.87%0;2001年突破400万起大关,达到445万多起,犯罪率进一步上升为3.49‰;2003年为439万多起,犯罪率为3.4%。”综上可知,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不道德行为的比率,要明显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期。
三、传媒推动了人们的道德焦虑?
《郁文》认为,在公众产生道德焦虑及形成道德滑坡结论的过程中,媒体对相关事件的筛选与传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了经济效益,媒体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服从“经济的注意力运行机制”,对有影响力、接近性、冲突性、新奇性、异常性的消息异常青睐。甚至,为了凸显或制造新奇性,部分不良媒体将相关事件娱乐化或戏剧化。更有甚者则直接编造充满冲突性与戏剧性的假新闻来吸引公众的眼球,这就致使普通受众因看不到真正发生的事实而普遍感觉世人无德,才误认为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这个分析看似有理,实则不然。
第一,在市场经济社会,媒体筛选消息的确会有很强的经济色彩。道琼斯公司业务发展总监张延在谈到新闻媒体的宗旨时就明确指出,媒体运作会关涉各方的利益,如股东希望获得最高的经济回报,而广告客户希望推广自己的品牌,公众则需要对自己最有用的、最能帮助自己成功的信息。因此媒体筛选信息倾向于选择有影响力、接近性、冲突性、新奇性、异常性的消息实属正常——既能娱乐公众又能帮助公众,既能拓展产品渠道又能为股东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问题是,世界上属于市场经济的国家非常之多,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媒体都没让本国大众产生道德滑坡的误判,唯独我国的媒体造成了这样的误判?
第二,就各种媒体而言,它们在筛选信息时,也不可能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而只关注不良事例。如前所言,新闻媒体不仅会积极报道负面道德事件,也会积极报道正面道德事件,只是不会报道循规蹈矩、平淡无奇的平凡事而已。显然,正面道德事件同样可以具有影响力、接近性、冲突性、新奇性、异常性等特征。所以,板凳哥、托举哥、暴走妈、最美医生、最美乡村教师、感动中国的人物等等,同样成为媒体热点。再比如汶川大地震后,新闻媒体在谴责只顾自己逃生的教师范美忠的同时,也以更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谭千秋、王光香、张米亚、向倩、苟晓超、吴忠红等老师的英勇事迹。
第三,在我国,绝大多数媒体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遵循宣扬主旋律的原则。这个特点表明,我国的传媒还会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注重正面宣传。因此,尽管媒体及其传播技术在现今世界普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国传媒报道正面道德事件的比重仍会高于世界上许多没有出现道德滑坡之叹的国家。这也说明,我们不能用传媒及其技术的变化来解释我国大众为什么会有道德滑坡的感觉。
由此可见,媒体在宣传时的筛选信息根本就不是致使公众产生道德焦虑感和发出道德滑坡之叹的主要原因。相反,若没有事实上的道德滑坡,在遵循主旋律原则的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下,公众对当下道德状况的感知,即便不是道德爬坡,至少也会是道德风气正常,而非道德滑坡。
四、受众的误读虚构了道德滑坡?
《郁文》为了进一步强化其道德滑坡只是误判的观点,还从受众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公众之所以产生道德焦虑。也有其解读与评价道德事件的心理机制方面的原因。在他看来,影响与支配受众对道德事件的解读和接受的心理机制主要包括:经验替代、泛道德化思维方式、“诺布效应”和“塔西佗陷阱”。经验替代指公众在评价道德相关事件时将记忆中的道德感知(尤其是幼年道德记忆)与过去的道德状况相混淆,由此患上了道德思乡症。泛道德化思维则导致公众面对社会事件时专注于道德评价,而忽略了对当事人具体行为情境的理解。“诺布效应”致使公众倾向于从负面去解读与评价行为者的动机。“塔西佗陷阱”指公众可能对有不良记录者先人为主,想当然地负面解读主体行为及事件。正是因为这些心理机制的存在,使公众在并非真正存在道德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妖魔化了道德现状,虚构了道德滑坡。
这里不排除某些人在面对社会事件时偶尔有以上心理倾向,但如果将这种心理倾向普遍化,将其当作人们看待社会事件的必然结果,则完全经不起推敲。
首先可以说,《郁文》的这套所谓心理分析是对公众的明显贬低,它无异于宣称大众连客观地辨识社会基本事实的能力也没有,无异于在自诩“众人皆醉我独醒”。
其实,对自己长期生活其中并有切身感受与体验的社会实际状况,出现误判的大众只可能是极少数。何况,现在不仅是大众如此判断,学者专家亦如此判断。如许启贤教授就说:“只要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不存偏见”,就会发现“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这种道德‘滑坡现象,不仅表现在不少人道德理想的淡化,道德意识的淡漠,而且表现在不少党政干部道德理想的淡化及道德意识的冷漠,同时,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道德观念浸入了不少人的灵魂;不仅表现在社会公德的失范,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爱情婚姻和家庭道德的失范,等等。”刘语民教授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精神文明建设取得较大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亦有这样的看法。邓小平说:“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在整顿风气中确实有些人要开除党籍,要清理一下。”2011年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也因“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而愤怒感叹“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其次要说,如果人们都存“非今是古”之心态,皆受“诺布效应”与“塔西陀陷阱”的影响,那么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恐怕都会抱怨今不如昔,而人类历史上,也绝不会有什么“盛世”和“乱世”的区别。可事实均非如此。还有,为什么国人只有道德滑坡的感叹,却没有其他方面,如经济滑坡、文化滑坡、科技滑坡、军力滑坡的感叹?难道“诺布效应”与“塔西陀陷阱”在这些方面不起作用?这又是为何?
或许是为了预防有以上诘问的出现,《郁文》专门从性善论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及儒家道德教育方式入手,来证明华人有泛道德化思维方式,所以在“今不如昔”的心理机制下。更容易发出道德滑坡的惊呼。先不说这个说法对不对,就算华人普遍具有所谓的“泛道德化思维方式”,为什么同样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新加坡和台湾、香港等地的华人,至少在当代并没有发出道德滑坡的惊呼?如果郁先生还想说这是因为中国大陆情况更特殊,那为什么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一直也没有道德滑坡的误读及焦虑,仅仅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
五、决定道德爬坡滑坡的因素是什么?
《郁文》不但认为道德滑坡在我国当下是传读之误,还作出我国当代社会的道德水平要高于以前任何时代的判断。因为在他看来,当前社会“一定的经济水平”、“基本的教育程度”和“平和的道德理性”这三点都要优于以前的任何时代,而这三点正是可形成良好道德生活状况的必要条件。
然而这个说法太过轻率,造成道德爬坡或滑坡的决定性因素另有其他。
可以承认,“一定的经济水平”、“基本的教育程度”和“平和的道德理性”这三个条件,是会有利于改善道德生活或有利于道德爬坡的。具体说来,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构建一种“马伽利特式”的优雅社会,从而为公众提供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基本的教育尤其是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有益于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平和的道德理性会减少因感情冲动而导致的道德越轨。但是,这三个条件并非道德爬坡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和决定性因素。因为大量事实证明,许多没受什么教育自然也没有多少道德理性的穷人,往往也很讲道德;许多有文化有理性的富人却唯利是图,不讲道德;而荒淫奢靡堕落之风,也经常出现在经济文化都较发达的时期。
为何如此?
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利人,都有怀赏畏罚的心理,所以影响一个国家道德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只能是该国的社会赏罚机制。“一种特定行为,一旦被社会明令禁止并配以相应的罚则,其发生率便会大幅度下降;一种特定行为一旦被社会提倡并配以相应的奖赏。其发生率就会大幅度上升。”④比如因自律能力差等原因对他人和自己都造成致命伤害的酒驾行为,在社会明令禁止并配以相应的罚则之前,尽管舆论一直呼吁严禁酒驾但效果并不明显。而当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纳入刑法并设定刑罚后,酒驾的发生率就大幅减少了。“法律实施两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87.1万起,同比下降39.3%,其中,醉酒驾驶机动车12.2万起,同比下降42.7%,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行为总量大幅下降。”再比如,在见义勇为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状况下,社会大众见义不为或见不义而漠然处之者屡见不鲜,而当社会有了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以及大力褒扬见义勇为者的举措实施以后,见义勇为的发生率就逐渐有了较快而明显的提高。
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赏罚机制基本上能普遍有效地做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该社会的道德状况就好;如果不能,就会形成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赏罚倒错,客观上会起到鼓励恶人恶事的结果,这样该社会的道德状况就糟。为什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官员腐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黑黄赌毒愈演愈烈?就是因为构成社会赏罚机制的相关制度安排效果较差,不仅不能及时有效地打击这些恶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相当于鼓励这些恶行得逞,达到其作恶目的,这才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持续滑坡。
由此可知,一个国家的社会赏罚机制或社会制度安排的扬善抑恶功能是否有效,才是正确判断这个国家的道德状况是好还是坏,是爬坡还是滑坡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