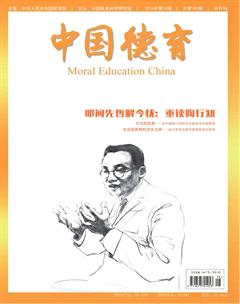《庄子》:人生困境与审美应对
李生龙

《庄子》分内、外、杂三部分,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外杂篇可能是庄门后学所为。后学与先生必然有一致之处,我把他们统称为老庄学派(此文有时以庄子代指这一学派)。这个学派所关注的核心是人生问题,由人生问题而及于社会、政治、伦理与其他。人生问题的核心则是人生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相应对策。庄子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他不仅仅指出人生具有悲剧性,而且积极地开出药方,教人们怎么超越,怎么提升,使人生实现哲思与诗意的合一,精神与品格的脱俗。
困境:生命之短暂、微渺与诸多尴尬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以其思维的逆向而属于另类思想者。相较于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等关注政治、伦理、法律等社会问题,老庄更关注人生,庄子则更关注个体生存的矛盾与苦痛。儒家把人说成是“三才”之一,与天地日月星并列,把人说得既崇高又永恒,庄子则冷峻地、无所掩饰地道出生命本身的卑微、渺小、脆弱及面临的诸般困境与无奈。
《庄子》指出的人生第一大困境,就是人在宇宙中微不足道,变化难知。《庄子》第一个把人类放在浩瀚无垠的时空背景下来定位。人类生命同漫长的宇宙时空相比,既短暂又渺小。孔子曾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含蓄地道出生命消逝的迅疾和人生的短暂,《庄子》则非常直截了当地说“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为生,又化为死”,(《庄子·知北游》)“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蚁穴)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秋水》)人生不仅短暂、渺小,而且作为构成世界统一之物质形态——“气”,其离合聚散变化难知,因而生命极端脆弱、无常。
人是自然之子,为了维系、改善生存少不了要向自然界索取。然而,这种索取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使人类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庄子·在宥》借广成子批评黄帝说:“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庄子·胠箧》也指出人类凭着所谓知识毫无理性地向自然进军,造成了“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毁四时之施,喘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的灾难性后果。
庄子对人类生命困境的揭露、定位虽然残酷,后人却颇多共鸣。《古诗十九首》说“人生寄一世,淹忽若飚尘”,曹植《赠白马王彪》说“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苏东坡《赤壁赋》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等等,发的都是这种生命短暂、渺小、脆弱的浩叹。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一生下来就面临各种人伦关系制约。所谓“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就是这一困境的具体描述。父子缘天性,君臣有义务,这些都对人构成命定式制约,使人无处可逃。另外,在庄子时代,法律的残酷性、道德的虚伪性,学术的垄断性,知识的工具性,都使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加无理无序、凶险难测。
《庄子》轻薄名利,实是看到了名利与精神自由之间存在牴牾。《庄子·人间世》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追求名利是以生命、天性、精神为代价的。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在为各种欲求付出沉重代价。《庄子·骈拇》把这种沉重称为“以身为殉”。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及饥渴、寒暑等等,都是切身之事,人们根本无法回避,陷入困境饱受煎熬实属必然。
在《庄子》看来,真理是相对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喜欢独断的天性使每个人对真理的认知与判断都具有主观性。人们为了争个是非高下,耗去多少心机都在所不惜。这就使自己不知不觉地陷入疲苶危殆之中。“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庄子·齐物论》)在找不到裁判的是非之争中,彼此都无非在参演毫无意义的闹剧,白白地使自己“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 。(《庄子·齐物论》)
求知是人类的天性。然而知识无穷、人生有限,求知也容易使人陷入尴尬。《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殆而不已者,殆而已矣”一段,很多人只截取前两句,以为庄子是教人努力求知。实际上,庄子认为追求知识不仅使个体生命陷于困顿,而且也使整个人类陷入纷乱。《庄子·胠箧》:“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
总之,庄子对人生的诸多困境都有所披露。他仿佛时时都在提醒人们:人生受诸种生存悖论的困扰,简直就是一场悲剧。从这个角度说,庄子及其后学是一群清醒的、冷峻的现实主义者。
“悟道”:自我的超越与脱俗
如果我们只看到庄子披露悲剧的一面,我们可能并未真正读懂《庄子》。事实上,《庄子》揭示人生的悲剧性,并不是要把人们带入悲剧渊海而心死意绝,而是为了警醒人们,教人们怎样从悲剧怪圈中跳脱出来,实现自我的超越与自由,使生活更有质量,生命更有品位。
《庄子》最重要的人生策略是“悟道”。“道”这个东西,是从老子那里继承过来的,《庄子·大宗师》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於上古而不为老。
对老庄的“道”可以作哲学的解读,当今的哲学史研究者都作如是观;也可以作宗教解读,古今道教界就常作如是观。从哲学或宗教角度阐释多少都有些玄奥甚至神秘。但从“悟道”的作用说,其指向却是明确的:即只有体悟了大道,才能深刻地认识到自我与宇宙的统一。宇宙的永恒性即是自我的永恒性,宇宙的绝对性即自我的绝对性。这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含义。
我认为庄子的“道”包含着审美的意蕴,包含着庄子的人生审美应对。结合《庄子》中对“道”的诸多其它论说,我以高、大、深、远、真来概括“道”的特性。对“道”的这些特性的领悟,也就是对人生应当追求的精神境界与生命品格的领悟。
庄子说“道”在“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可见“道”有高的特性。从“悟道”的角度说,所谓高,也就是要超然于万事万物之上,居高临下、鸟瞰式地观察事物,俯视人生。《庄子·逍遥游》里的大鹏抟扶摇而直上九万里的高空,它从天上往下看,一切都那么微不足道。那嘲笑大鹏的什么学鸠啦,斥鷃啦,蜩啦,统统可笑得很。所以从高处看事物容易使自己产生超越感,升华出一种高迈、豪壮的情怀与境界。
《庄子》中每每说到“大”。大指空间,如寥廓无垠的天地四方;也指体积或重量,如大鹏、大树、大块、大风、大海、大龟、大鱼等。庄子有明显的“以大为美”的取向。从“道”的角度说,“大”体现为眼界阔大,胸怀广大,境界宏大,以宏阔之气度对待他人与自我,以大手笔书写事业与人生。大与高是有关联的:能高方能大。高大状写“道”之超越性与包容性,落实到人生层面则为高迈、高雅、宏大、洒落、大气、雄浑、豪放,古代诗文中的豪放派即是此种胸襟格调。
庄子说“道”“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深跟高走向相对,高是立足点高,深是切入度深。扬雄说他的《太玄经》“高则出苍天,深则入黄泉”,就是这个意思。从悟“道”的角度说,“深”就是看问题要深入、深刻。人生充满矛盾,甚至充满悲剧性,但矛盾、悲剧就真的不能摆脱、超越吗?《庄子·天地》说“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意思是说,得“道”的人,能在无象中看到形象,于无声中听到声音,能在深之又深的境界中看到物事,于神之又神中体现精神。深,能使人产生纵深感,同样也能使人产生超越感。高深不仅是一种探究功夫,也是一种精神境界。
《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庄子·逍遥游》说“其远而无所至极邪”,都是说“道”有“远”的特点。从悟“道”的角度说,《庄子·大宗师》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浅,就是短浅,跟长远相反。“远”常跟内心的宁静、情欲的淡泊联系在一起,故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说。内心深远、出俗,行为举止自然就洒落、飘逸,所以“心远”的陶渊明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父》)所谓真,与伪相反。真就是不世俗、不伪饰,不矫揉造作,喜怒哀乐发自内心,包括情境之真实,个性之真率,情感之真挚与感悟之真切。真表达的是道家归朴返真的全部社会人生理想,也是解决上述人生悲剧的重要对策:能超越世俗,灵府不为是非、毁誉、穷达、贫富、生死、嗜欲等困扰人生的矛盾所撄扰,就是有“真知”的“真人”,“真人”即是悟得了大道的人。
“顺命”:自我的适性与自然
《庄子》提出过的诸多人生对策中,还有“顺命”这一条。《庄子·达生》说:“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庄子·大宗师》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所谓“命”,按上文所引《达生》的说法,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却偏偏这样了,所以“命”是无法讲清原因的结果。人生确实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原因的。有些事情的发生具有必然性,有些却纯粹出于偶然。总之是结果在预想之外。需要说明的是,庄子讲的“命”,并不指所有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人力能够解决的,这不属于“命”范畴。至今还有些人把一般的事情归之于“命”,这是不正确的理解。只有那些人力无法掌控、解决的事情,也就是庄子所说的“不可奈何”的事情,才能归之于“命”。什么是不可奈何的事情呢?从《庄子》全书看,主要指生死和无法治愈的疾病,以及因偶然事件触犯法律而导致受刑等重大人生遭际。生死问题主要是死亡问题,自古皆有死,谁能解决呢?现代医疗水平越来越高,但仍有很多无法治愈的疾病。突如其来导致重大灾难的事情也时常见诸报端。“安之若命”的“安”,是“顺”的意思,“若命”就是“顺命”。对那些人力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与其伤感、悲观甚至采取非理性方式了断,还不如采取“顺命”的理性态度。理性,庄子认为是很高的道德境界,这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的完整含义。
“顺命”的积极意义在于对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持放任态度,转而进行自我心理调适,以达观态度处之。顺命有利于心理的自我修复,也有利于人生朝积极方面发展。但“顺命”可能会导致人成为命运的奴隶,逆来顺受,缺乏应有的进取精神。这一点,胡适早年作的《先秦诸子进化论》有所批判。他认为庄子的“达观”和“乐天安命”“流弊甚多”,第一是“命定主义”,第二是“守旧主义”。我们应该对“命”的含义作正确的理解,万不可把什么事情都看成命定的,蔽于天命而不知人事。同时,对“顺命”的弊端也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顺命”也包含着某种审美的含义。“顺命”的原理就是道家所推崇的“自然”。所谓“自然”,就是自己而然,不假人力、神力或其他外力的意思,任凭事情朝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只顺应而不背逆,所以又叫作因任自然。从应对生命困境角度说,因任自然可以使人随缘而动,随遇而安,不焦不躁,不温不火,能进能退,能屈能伸,善于克服因陷入困境而导致的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平和、稳定、达观的良好心态,这不仅有利于跳脱困境,而且有利于身体的健康,特别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且能培养自己坚毅、柔韧、沉着、稳重的良好品性。这种人每临大事有静气,虽有风波无险情,具有独特的深沉、厚重、通达之美。
面对人生悲剧,庄子不是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技术层面去思考解决之道,而是通过心理学、哲学、宗教学等方式来解决。审美可能不是庄子的本意,可是庄子的人生对策确实可以通向审美。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人生,使自我从矛盾性、悲剧性的渊海中跳脱出来,从哲思与审美中找回自我,找回诗意,找回美感,找回愉悦。这样不仅可以使自我形成积极的生命理念与人生态度,还可以把人生与艺术贯通起来,使生命境界与审美境界合而为一,内化为高迈、豪壮、宏大、深沉、清远、真淳、自然等良好的生命品格。从这个角度说,庄子及其后学是一群超世离俗的、融哲理与诗情为一的浪漫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