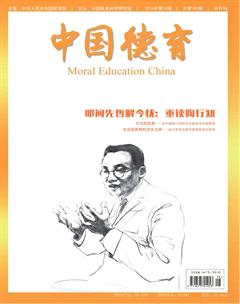道德教育中的知行关系:从杜威到陶行知
丁永为 孔德琳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濬。1911年,他在金陵大学求学时,由于推崇明朝大哲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遂更名为“知行”。“知行”之名一直用至1934年7月,在主持山海工学团时,再易为“行知”。[1]陶先生更名,实则是其思想观念变化的反映。有陶研专家曾指出,自20岁起至55岁去世,“知行问题始终是他关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在他一生的道路与事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2]而关于知行关系一直不断的讨论,也正是陶先生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所在。观其一生的文章与活动,我们可以发现,陶行知实际上一直有着深刻的道德关怀,对一个人何以成为有德、大德之人,何以过上有道德的生活始终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
一、陶行知的早期知行观:
王阳明“知行合一”
我们从陶先生在《金陵光》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当时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和知识阶层的自我修养问题的关心,从在金陵大学求学时便已开始了。他发现,在道德的认知和道德的行为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并且无论是在知识阶层还是在其他社会阶层中,这一问题普遍存在。
为了解答如何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这一问题,陶行知最早信奉的是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的学说。针对当时的教育流弊,阳明先生主张知行合一,反对知行的断裂,把知行合一作为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根本方法。这与传统的重视读经典、鄙视实行的教育学说相比是进步的,但仍然存在些错误。一是错在误解了知和行的先后关系。如果说行动是从认知开始的,要按照正确的认知去做正确的事情,那么,正确的认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王阳明认为,正确的认知乃人“心中固有”,这是不正确的。知识源于行动和实践,源于人们的生活和经验。二是错在把知识当作是一劳永逸的、永恒的。实际上,知识是变化的,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成立的。这就是说,知识是相对于某个问题或困境而成立的,当这个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条件发生变化时,作为问题答案的知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1915年之前的陶行知对王阳明学说的错误其实并不自觉。实际上,他正是带着这个学说和这个学说背后所持的信念教与众人的。即在寻得一种真理之后,便把此不易之真理即刻教给四万万同胞,以期使国人不再受贫穷落后之苦、不再受外辱而能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陶行知知行观的发展:
杜威“做中学”
1914年秋,陶行知赴美留学,在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之后,遂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继续深造,并选修了当时在欧美思想界和教育界声名正盛的约翰·杜威教授的“学校与社会”课程。
“学校与社会”这门课的名字取自于杜威在189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学校与社会》。在此书里杜威指出,美国学校还在沿用过时的、错误的教育哲学,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它们所存在的社会正在发生的惊人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理智和道德上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社会变迁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正确的、迅速的和有效的反应,而这正是学校教育在理智上和道德上失败的根源。[3]
在《学校与社会》出版之前,由于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和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杜威已从早年的观念论者成长为一位工具主义者。[4]工具主义者把知识作为经验的产物,它并不神秘,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认为,知识来自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知识本身并不具有凌驾于人的现实需要之上和之外的神秘价值。杜威是把知识从神坛上拉下来,让它接受来自新生活的检验,使其成为人类改造现实世界的仆人。在后来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杜威曾多次指出,错误的教育哲学认为知识是行动的主人,知识是永恒不变的。但他认为,这样的知行观是经不起科学的检验的。
从科学上看,知识最初来自于应付行动的困境。人生活在世界上,就会遭受很多危险,比如饥饿、战争、疾病等。为了生活下去、获得安全,就必须想办法来解决这些危险。有的人诉求于神灵的庇佑,于是有了宗教;有的人诉求于理性的指引,于是有了哲学;有的人诉求于经验的启迪,于是有了技艺。前两种知识只有和第三种知识配合起来才能够使人获得安全。由于阶级社会的出现,社会被人为分成劳心、劳力两大对立的阶级,前两种知识为劳心者也是统治阶级所把持,后一种知识由于其持有者身份卑微,因而也就被驱逐出“真理”的庙堂。于是,由统治阶级所设立的学校要么被宗教所把持,要么被哲学家所把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学校里重视思辩和记忆性的“旁观者”知识传统,具体的、与行动有关的各种技艺被排斥,知识和行动被人为割裂开来。
杜威认为,知识和行动的内在统一性需要被确认,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的传统应该被抛弃。我们必须构筑新的知识观,重视行动,确立行动在知识中的合法地位。应当将一切知识置于行动的检验之下,让它能够服务于有效的行动需要,服务于进步的生活需要,从而在生活和行动中持续创造新的知识,这样知识和行动才能生生不止,前进不息。
从陶行知在1918年之后发表的文章和演说来看,他受杜威的影响十分深刻。归国后的陶行知在知行观上相较于赴美之前有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的证据是他对王守仁知行学说多次公开的批评。20年代中后期,陶行知清楚地看到阳明学说的两个错误。他对听众和读者反复讲到,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5]4陶先生枚举西方近代科学史中的著名人物,如伽利略、富兰克林、牛顿、达尔文的故事,以说明近代西方科学的昌盛,说明行动和“做”的重要性,说明新知识的产生正是科学家不断试验的结果。由此可见,知识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在遇到新的行动困境时,旧知识的效用体现在为困境的解决提供一个假设,假设是否成立全要看行动的效果是否可以解决困境。
三、陶行知知行观的成熟:
“教学做合一”
陶先生曾痛心地批评建立在错误的知行关系学说之上的旧中国的学校教育,说它只会教人读死书、死读书,教人做只知不行、只说不做的老爷、少爷、小姐和太太。在指导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的工作中,陶行知耐心地讲解了他的“教学做合一”的观点,认为“教学做”其实是“一件事”,它是“创造”,是过“前进的生活”,是“在劳力上劳心”……这些说法在根本上反映了陶先生对知行关系问题的新理解。
在《民主与教育》的最后一页,杜威说道:“学校中道德教育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知识和行为的关系。”“除非从正式的课程所增长的学识足以影响性格,就是把道德的目的看作教育上统一的和最终的目的,也是无用的。如果知识的方法和题材与道德的发展没有密切的、有机的联系,就不得不求助于特定的修身课和特定的训练方式:知识没有和寻常的行为动机和人生观融为一体,而道德就变成道德说教——成为各自独立的德行的组合。”[6]杜威还批评直接的伦理教学和学科化的道德训练,批评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分重视竞争而不重视合作,以至于忽视了学校集体的道德作用和学科的社会性质本身的道德价值。学校与社会的可悲分离、教学与德育的可悲分离、个人与集体的可悲分离、身体和心灵的可悲分离,具体就体现在学校师生的知行分离之上。因此,知行关系是道德教育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知行观,便会有什么样的道德教育观。在这点上,陶行知对老师杜威思想的传承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传承并不是守旧,也有发展和创新。考察陶行知中后期的著述,我们可以发现,陶行知对杜威知行关系思想的发展,至少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陶行知把杜威的知行关系思想与中国古代的知识学说融会贯通,提出了“行知行”的新观点,完善了杜威的知识论。后来,陶行知曾对杜威的思维五步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杜威对“行”的重视不够,认为只有从“行”到“知”再到“行”才能形成一个思维闭环。他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乃是受到墨子的“亲知、闻知、说知”观点的启发。[5]21第二,陶行知把“知行”的场域由实验室生活扩展到了真实的社会生活,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观点。依照杜威的知行学说,理想的教育应该在学校中进行,学生在学校中接受的知行训练更接近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实验。陶行知则批评说,杜威式学校里的生活是虚假的,那不是真正的生活。通过虚假的“行”是获得不了真“知”的,而虚假的“知”也无助于真实的“行”。他认为杜威和其追随者在知行合一、行先知后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勇敢。陶先生曾生动地比喻说,这样的学校就像一只鸟笼,师生的知行活动被限定了范围,只许教育家们从社会生活中挑选几样,放在鸟笼里供鸟儿使用而不允许鸟儿自由飞翔。[5]399这样一来,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一到了真实的生活里就用不上了。因此,陶行知把横亘在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围墙彻底推倒,“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彻底融通”。[7]相比杜威,他在以真行动求得真知识,以真知识求得好生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更勇敢。
陶先生之所以能够结合阳明学说和杜威的教育思想做出创造性的发展,既有个人天赋的因素,也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困境有关。留学归来的陶行知很快就发现,在一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时代里,指望通过普及学校教育和渐次改良来启蒙民众是行不通的,必须到最广大的乡村去,必须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无产者中间,必须让四万万同胞都来“教学做”,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中华民族的解放才有希望。费正清教授曾正确地指出,陶行知“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他异乎寻常地同情普通人民的需要。”[8]我们对陶行知知行观的任何解读,若离开了他所生活、行动的语境,必定是不得要领的。在知识论上,这是犯了杜威和陶行知都指出过的错误。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3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487.
[2]吕天纵,程学贵.我们的老校长陶行知[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2:14.
[3]丁永为.工业社会、民主与教师专业精神——纪念杜威名著《民主与教育》出版一百周年[J].教育学报,2016(1):94-103.
[4]丁永为.论前哥伦比亚大学时期杜威教育思想的社会和哲学基础[J].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49-53.
[5]陶行知.陶行知全集: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
[6]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2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344.
[7]毕明生.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德育理论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1):43-45.
[8]周洪宇.欧美陶行知研究概况[J].国外社会科学,1991(10):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