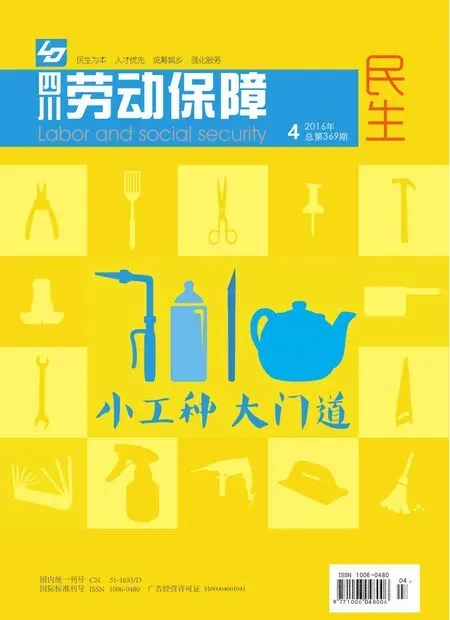突破困境让农民工从“城市过客”成为“城市主体”
——专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进
文本刊记者 蔡兰
突破困境让农民工从“城市过客”成为“城市主体”
——专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进
文本刊记者蔡兰

无论是“十三五”规划,还是2016年的政府工作安排,都在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方面,做不遗余力的努力。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现实困境。
黄进是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承担了有关“新形势下农民工社会政策转型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合研究课题,他立足农民工的发展诉求,深入寻找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以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日前,黄进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探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分析如何突破困境,让农民工从“城市过客”成为“城市主体”。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记者:您认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何在?
黄进: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农村凋敝,农业不景气,农民日子清苦。事实上,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得到解决。首先,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市民化之后,农村人口减少,土地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业的问题可以得到改善。其次,农民工市民化之后,生活水平提高,农民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最后,农民工市民化,加上新农村建设,农村的问题也随之得到改善了。
另外,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既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享受不到城市市民应有的权利。还有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流动儿童等都成为重大的社会不和谐问题。只有农民工市民化,才能让农民工在城镇定居安家,认同城镇,增强对城市社会的责任感,促进新市民与老市民的和谐。
当然,农民工市民化也是产业转型发展、扩大内需、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阶段,我们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不愿农转非 需除后顾之忧
记者: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使农民工真正市民化,将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但四川省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四川农民工市民化调查现状》显示,半数以上农民工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进:农民工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主要原因之一还是不愿放弃农村土地经营权。对农民工来说,最大的物质资本就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土地承担着农民多项社会保障的功能。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带着美好的愿望离开家乡投入到城市建设中,因为无法在城市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而没有真正地离开农村,割舍对土地的眷念。这就需要促进农民工在农村的存量资产转化为市民化的资本,如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等。
在实践中,要探索实行股份合作、“大园区+小业主”等多种形式,依法自愿有偿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搭建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维护农民工在农村的利益,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同时,宅基地在本质上是农民作为国家公民应当享有住房保障权的体现,也是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经济权利。农民工进入城镇也应当享有住房保障的权利,但实际上一旦农民离开农村,其住房保障权利处于实际的“落空”状况,因此关于农民工在务工地的住房保障问题,是其公民权的体现,是解决农民工发展诉求的必然环节。
提升社会资本 让心理同步“进城”
记者:多数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虽然人已经进城了,但他们在思想观念、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等方面并没有同步“进城”,这样的状况应如何改善?
黄进:我认为我们常说的市民化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职业的市民化,从农民到工人;其次是身份的市民化,从农村户籍到城市户籍;最后是心理的市民化,在文化、心理层面融入城市。最后心理市民化阶段才是市民化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最难实现的。
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农民工自身都需要努力。首要是农民工要实现稳定地就业,才能让其在市民化之后体面地生活。其次,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最后,不能将农民工孤立起来,政府为农民工修建的廉租房、公租房不能太偏远,应该跟城市居民融合居住,加强交流沟通,增强城市认同感。帮助其构建城市网络、社会关系、实现稳定就业等。
新生代农民工是“漂泊”的一代
记者: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有哪些特点?
黄进: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阶段里,国内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与此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全球化的步伐也在加快,令年轻一代农民工身上带有这个时代特有的色彩。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各类信息,相对父辈眼界宽广,对个体的发展诉求强烈,有很强的自我实现意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质量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有更高的期待,市民化诉求更高。一方面,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已经趋于城市化,对土地的情结也日趋弱化。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在城市维持生存,不再仅仅注重薪酬,而是开始关注掌握一门可在城市立足的技术,关注工作环境和权益保障,关注个体的精神感受。
记者: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有哪些困境?
黄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生代农民工更趋向于“双重边缘人”,出生在农村(也有的出生在城市),生活在城市,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我们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距离越来越疏远,无任何务农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为50.7%,在15—30岁的农民工中,无务农经历的比例高达56%。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已经没有了留置的物质依托。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城市,却遭受排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和主流生活,而他们又不愿意回到农村。调查结果还显示,24.58%的农民工非常愿意到城镇永久居住,25.42%的农民工比较愿意到城镇永久居住,二者合计达到50.00%,高达72.42%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
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资本缺乏、能力贫弱,是导致农民工问题仍然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与城镇青年的受教育程度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单一的社交关系并没有帮助他们建立起以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其并没有建立起再生性社会资本。
需要制度顶层设计
记者: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涉及公共服务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财税制度、土地制度及户籍制度等方方面面。对此,您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黄进: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适合时代发展需要和农民工自身需要的农民工政策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目前关于农民工市民化很大的问题在于政策的区域性和分散性。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纲领性文件,但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这一基本诉求的具体政策性文件还非常少。
举个例子,一个农民长期在广州务工,现在他想回到四川发展,可是他在广州这么多年缴纳的社会保险怎么办,能不能转回四川?在现实中转不了。他最多只能将自己缴纳的部分提取出来,单位缴纳的部分只能被放弃。
不仅如此,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在全国存在多种不同的模式:以成都、上海为代表的独立型综合模式,专门给农民工建立了单独的社会保险,独立于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体系。深圳、广州是另一种模式,将农民工社会保险统一合并到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当然这种模式在近期已经改变了。
区域性的政策不能适应农民工的流动性需求,这就要求系列化的顶层设计,从国家、中央层面进行政策的保障和完善,给农民工市民化确定的预期,这才是未来农民工市民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