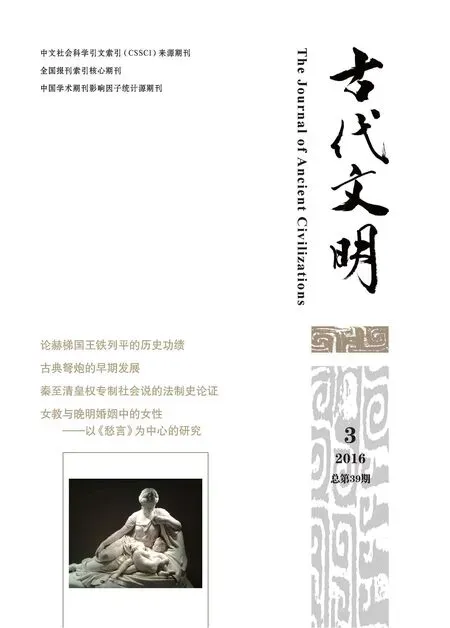以“小华”观“中华”——壬辰倭乱后朝鲜战俘鲁认的中国之行
杜慧月
【比较文明史】
以“小华”观“中华”——壬辰倭乱后朝鲜战俘鲁认的中国之行
杜慧月
提 要:万历二十七年,壬辰倭乱中的朝鲜战俘鲁认在明人援助下从日本逃至中国福建,并与当地士子和官员进行文化交流,其《锦溪日记》和《锦溪集》生动地记录了这段传奇经历。鲁认选择迂道中国,他对忠孝节义的诗文表达、对《朱子家礼》的恪遵、对“止修”学说的接受、对佛教的排斥,皆表现出朝鲜士人强烈的朱子学背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小华”观念,使鲁认的中国之行,成为“以小华观中华”的文化之旅,藉此可以考察朝鲜和明朝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
鲁认;《锦溪日记》;文化交流;以“小华”观“中华”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丁酉再乱中被俘至日本萨摩岛的朝鲜冰库别提鲁认,在明朝差官林震虩等人的援助下逃至中国。在福建滞留的近四个月间,本是逃亡战俘身份的鲁认自觉担当了中朝文化交流的使者,将目睹耳闻诉诸笔端,并通过笔谈的方式,与福建士人、官员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且在福建右布政徐即登的推荐下入两贤祠书院留馆参讲。最终,万历皇帝颁诏,鲁认自福州启程,经浙江、南京、山东、北京、辽东归朝鲜。鲁认(1566—1622年),字公识,号锦溪,其《锦溪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有写本传世,现存部分始于二月二十一日,迄于六月二十七日,生动地反映了这段传奇而温情的经历。1《锦溪日记》写本(或疑为鲁认手稿)为鲁认后孙韩国鲁锡俓氏所藏,原稿多残阙漫漶,日本《朝鲜学报》(第56辑,1970年)据以影印。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国译海行总载》收录另一写本,疑今人据影印本抄录。又,鲁认《锦溪集》卷三所载与《日记》略同,盖其后人据《日记》增删改写而成,文中称鲁认为“公”,将《日记》所载分拟“壬辰赴义”、“丁酉彼(被)俘”、“蛮徼陟险”、“倭窟探情”、“和馆结约”、“华舟同济”、“漳府答问”、“海防叙别”、“兴化历览”、“福省呈谒”、“台池舒怀”、“院堂升荐”、“华东科制”、“圣贤穷亨”等14个小标题,补充万历二十年壬辰倭乱开始至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结识陈屏山、李源澄等人之前,鲁认抗倭、被俘、在萨摩岛之概况,以及六月二十七日后鲁认返归朝鲜之事。与《日记》现存部分按日记事不同,补充部分偶涉逸闻,极为简略;而对《日记》累次述及之事,则标明“删烦”之处。本文征引的《锦溪日记》,依据《朝鲜学报》影印写本;征引的《锦溪集》,则依据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年出版的《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1册)。其后人编纂的《锦溪集》中,亦收录了不少鲁认与明朝文人的酬赠诗文。
鲁认为何以逃往中国为首选?鲁认的身份使其与中国士人、官员的诗文交流中呈现了怎样的心灵对话?在鲁认与明人的文化交流中,彼此有着怎样的共识与分歧?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认识壬辰倭乱时期朝鲜两班战俘的复杂心态,进一步考察明朝与朝鲜王朝的政治外交关系,以及双方文化的同中之异皆大有裨益。2关于鲁认《锦溪日记》,目前相关研究皆出于日本和韩国学者。日本学者关注较早,侧重于文献介绍、释读以及与日本相关史料的解析,如长节子「朝鮮役における明福建軍門の島津氏工作——《錦溪日記》より」(『朝鮮學報』第42輯,1967年)及「《錦溪日記》小紹介」(『朝鮮學報』第56輯,1970年)、內藤雋辅『文祿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第三章「《錦溪日記》釋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年);韩国学者侧重于考察鲁认的战争经历,并在与姜沆《看羊录》、郑希得《月峰海上录》的比较中确立其俘虏文学的价值,如金镇圭「임란 포로일기 연구 -「금계일기」를 중심으로-」(『새얼어문논집』제10권,1997)、鲁起旭「壬亂義兵將 魯認의 日·中遍歷과 對倭復讐策」(『한국인물사연구』제2호,2004)、朴永焕《鲁认<锦溪日记>里的诗歌研究》(载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2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朴永焕近年又有系列论文发表,将视野转向《锦溪日记》中闽文化的探讨,如「魯認《錦溪日記》裏記載的閩文化-以學術思想、書院文化以及科擧制度爲中心-」(『中國語文學』제61호,2012)、《十六世纪末闽地学术宗教思想研究——以鲁认<锦溪日记>记录为中心》(“创新与创造:明清知识建构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4年)、「朝鮮人筆下的十六世紀末福建面貌 -以魯認《錦溪日記》路線考證爲中心-」(『東亞人文學』第32輯,2015)。本文则从心态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在中朝文化交流乃至东亚政治文化的视野中整体观照,呈现鲁认之行的思想文化意义。
一、鲁认迂道中国的动机与心态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六月,朝鲜全罗道南原被日倭攻陷,时年32岁的鲁认因年轻健壮且是有文化的两班,并未遭遇杀身之祸,而是最终被押至日本萨摩岛,成为战俘。经历了残酷战争能够保全生命本该欢欣鼓舞,但鲁认和与他有相似遭遇的两班如姜沆、郑希得等却都有着保全生命后的纠结和痛苦。1姜沆有《看羊录》、郑希得有《月峰海上录》,人们常将鲁认《锦溪日记》与二者并提,但鲁认《日记》目前留存的部分主要为中国经历,与前二者主要记载日本有所不同。他们在这种痛苦折磨中想尽各种办法力图回到故国,其中一部分人通过日本人的帮助或是随同朝鲜官方派到日本的回答使最终回到朝鲜。鲁认返归朝鲜的方式和路径是这些朝鲜战俘中的一个特例,他选择迂道中国返归朝鲜。饱受恋土思亲之苦的鲁认逃归之时选择如此迂回之路径,不能不令人费解。当他抵达福建漳州浦港时,明朝将官即有疑惑:“你是何国人也?若朝鲜人,何不直渡本国,而枉来万万里他国乎?”2[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三月二十八日,『朝鮮學報』第56輯,1970年,第85页。事实上,对于逃归路线,鲁认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谋划的,迂道中国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复杂的动机与心态。
一方面,就政治现实而言,朝鲜战俘直接归国罕能被善待,或被疑为通倭间谍,或被邀功之官兵追杀,或即使未被问罪而余生却是如履薄冰。鲁认最初策划逃归朝鲜的方案时,至少考虑了三种选择:一是迂道中国;二是直向全罗道;三是直归釜山。第一种被鲁认视为“万全之策”;第二种则为“第一长计”;第三种虽最为迅捷,却被其直接否定。何以如此?虽然四五日航程即可抵达釜山等地,但鲁认担心被留在此地的明兵误杀。其实,遇见朝鲜本国之兵,又何尝能逃脱?郑希得就记载了壬癸年间(1592—1593年)被俘至日本的朝鲜人在丁酉年(1597年)随同日倭返归朝鲜作战,虽已到故国,逃匿甚易,但他们仍然重还日本的原因:
我等结约脱走,则我国伏兵见而追之。高声疾呼曰“我是被掳人逃还者”云,而追者益急,不得已还入倭阵,或不及于倭阵,则皆斩头持去。此不过我军献馘要功之意,岂不冤痛哉?我等为倭之用者,岂本心然也?3[朝鲜王朝]郑希得:《月峰海上录》卷1,《自贼倭中还泊釜山日封疏》,引文据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 http://db.itkc.or.kr。
对于朝鲜朝廷而言,这些返归的战俘非但未能履行忠臣节义,甚至带有日本间谍的嫌疑。4鲁认归国后,亦曾受到怀疑,如时在朝鲜的明朝通判沈思贤曾向朝鲜宣祖言:“顷者,走回人鲁认,心术奸邪矣。当初史世用,出入于石蔓子,备知贼情矣。”见《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二年十二月甲辰,《朝鲜王朝实录》第24册,서울: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因此,借助各方力量最终逃归朝鲜的战俘,如朴寿永、姜士俊等,不免受到残酷对待。5韩国学者郑出宪《壬辰倭乱和穿越海洋的战争俘虏——曲折的记忆和叙事的再构》一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载李海英、李翔宇主编:《海洋与东亚文化交流》,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4年。而如姜沆者则在回国后战战兢兢,唯恐动辄得咎。如朴太守意欲请姜沆作郡文学时,姜沆则曰:
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有时出门,恶声或至。犹不敢怨天尤人,而自恨赋命之奇薄,一死之不早也……今夫深居简出,犹且不免受侮。一行作吏,戴乌帽腰乌角,身红黑公服,与官人列坐公廨,则十手十目,必相指视,牵引笑侮,动必齿冷。民虽颓靡,性实狷狭,外虽甘受,而中有不可堪者。1[朝鲜王朝]姜沆:《睡隐集》卷3,《上朴太守书》,《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3册,서울:景仁文化社,1991年,第67—68页。
另一方面,就道德理想而言,劫后余生面临的节义困境使鲁认对直接逃归朝鲜顾虑重重。鲁认的时代,朱子学已扎根朝鲜士林的精神世界之中,人臣应尽节义,临难死节,以身殉国,成为士人应该遵循的普遍准则。如鲁认保全生命者,有悖对国君的忠义,不免受到贪生怕死之讥,这些情形应是鲁认能够预见的。如其诗云:“乱后流离未死身,生还只恐陷常伦”、2[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写怀示倪进士士和二绝》,《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1册,서울:景仁文化社,1991年,第186页。“虽存视息还如死,魂梦茫茫碧海长”正是其犹豫忐忑心态的表达。3[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和泉馆赠姜佐郎(沆)》,第185页。与鲁认同期被俘至日本的姜沆、郑希得等人亦常常有这种心态。如姜沆言:“吾辈被掳于不共戴天之雠虏,不以一死报国,渡海之日,鼎镬固其所。”4[朝鲜王朝]姜沆:《睡隐集》卷3,《与宋生(樯)书》,第64页。如果说鲁认、姜沆皆为进士出身,且皆曾作过朝廷六品官员(鲁认为冰库别提,姜沆为刑曹佐郎),故而有违背忠臣节义之困窘与不安;但尚未参加科举的郑希得,亦有如此之矛盾:“志违忠孝身犹在,羞向傍人说姓名”、5[朝鲜王朝]郑希得:《月峰海上录》卷2,《往见柳仲源寓所书怀以赠》,引文据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 http://db.itkc.or.kr。“报道王京近,王京是鬼关。非缘探虎窟,无路见龙颜。”6[朝鲜王朝]郑希得:《月峰海上录》卷2,《辛丑冬姜睡隐(名沆)来访骑吾马而归马还时示诗》,引文据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db.itkc.or.kr。由此可见,这些朝鲜两班战俘彼此交流之际很难避开这一话题,面临的道德困境是他们共同的纠结。因此,被浓郁的节义观念裹挟着的朝鲜两班一旦成为未能为国捐躯死节的战俘,他们的处境是可以想见的,他们的不安亦是情理之中的,这是一种自觉,亦是一种迫不得已。
相较之下,迂道中国是朝鲜战俘最为理想的选择。明朝是朝鲜的宗主国,作为壬辰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政治上置身于朝鲜本国的利害之外,可以为朝鲜战俘提供庇护,文化上又居于汉文化圈的中心,正是“小华”朝鲜眼中的“中华”。7“小华”一词源于宋人所刊高丽使臣朴寅亮等《小华集》,后成为高丽、朝鲜士人国族观念的重要部分。鲁认之行,正是“小华”之人的“中华”之旅。因为有明朝大船提供的物质援助和明朝差官林震虩等对其意欲上达倭情并寻求复仇之策的绍介与称许,鲁认的迂道之行不但可以衣食无忧,而且既能脱离孤帆返归朝鲜的凶险,又可避免成为可疑分子,甚或能在“中华”获得令名。对此,鲁认充满自信和憧憬:
我能汉语,又能文书,得见地方官,书示吾等来历根本与倭贼情势,地方官□必闻于布政司,因护送北京矣。如达北京,则非但壮观天下,顺归朝鲜,必仰叫天阍,细达日本事情,朝鲜俘民,庶几刷还,而中外青史,留我芳名。8[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三月十三日,第74页。
汉字这一在朝鲜被视为两班特权和身份的文化标志,可以说是鲁认迂道中国的敲门砖和不可或缺的交流媒介。藉此,他在日本结交了明人陈屏山、李源澄,并由二人推荐给明朝差官林震虩,顺利得到救助而抵达福建。借助娴熟的汉诗文,鲁认与福建的士子、官员多方交流沟通时,通过阐述自己的忠孝之心,赢得了他们的理解与同情,并最终得到万历皇帝“尔忠如祥,尔节如武,苦渡鲸波,欲叫天阍,其命贵得紧贵得紧”的诏书和赐马,9[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4附录,《催归原情疏后》,第221页。兵部随即派遣员外郎史汝梅护送其至鸭绿江。
在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中,朝鲜国王即位、王妃及世子册封等皆需有明朝的诏敕才具合法性。因此,获得皇帝诏书的鲁认犹如得到了庇护伞,使其归国更多了一份荣耀。如鲁认诗曰:“皇恩赖免殊方鬼,贱质还为故国臣。去路拜乘天赐马,青山万里首回频”、10[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谢行人司行人李汝圭》,第189页。“几年殊域任焦枯,恩诏生还半死躯。”11[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谢进士徐》,第189页。归朝鲜后,宣祖亦下教书曰:“别提鲁认,自日本至中华而生还,得全素节,皎然本心,天监所烛。”12[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4附录,《东还本朝后》,第221页。至此,鲁认的战俘身份已无需追究,彻底实现了身份的转换。
二、鲁认与明人的诗文之缘
鲁认的中国之行,留下许多诗文,散见其《锦溪日记》及《锦溪集》。《日记》中保存者除鲁认诗约30首、呈文8篇之外,又录明朝秀才黄大晋次鲁认诗韵1首,福建右布政徐即登书于两贤祠书院明道堂壁上文1篇。《锦溪集》中鲁认相关诗文按照体裁散见于各卷,诗作凡50余首,其中纪行诗之外,又有次韵明人赠别诗作19首等;文凡7篇,主要是向福建官员如军门、布政司布政、监察御史等所上的呈文。1《日记》较《锦溪集》所载呈文为多,有彼此重合者,有此有而彼无者,亦有呈文对象不同者。后者如《日记》四月十四日所写上军门呈文,《锦溪集》卷四题作《催归原情疏》,文字略有更易,成为上皇帝之文,《锦溪集》卷三述及此篇呈文时有小注:“盖此文先呈军门,而后自军门转达天门者也。”另,《锦溪集》卷二收有明人诗21首、文2篇。21首诗中,七言律诗19首,系福建两贤祠书院秀才倪士和、谢兆申、徐、陈荐夫等及官员金学曾、李汝圭、王毓德等19人赠别鲁认之作,鲁认后孙编辑《锦溪集》时将其题为《皇明遗韵七言律诗》;绝句2首,系护送鲁认至鸭绿江的史汝梅及其父史世用(壬辰倭乱时曾至朝鲜作战)之作。文2篇,一为陈仪《送鲁公识还朝鲜序》,一为徐即登《明道堂木屏风正论》。2明人赠别鲁认之作,散见于诸人文集,如谢兆申《谢耳伯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卷二存6首,陈荐夫《水明楼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卷三存2首,徐《鼇峰集》(《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一四存2首。其中,谢兆申诗六首不见于《锦溪集》,陈荐夫、徐诗四首皆见于《锦溪集》卷二,然各有一首不署二人名,盖酬赠之际偶有捉刀,当从明人本集。
尽管鲁认是逃亡战俘,但其朝鲜两班的身份和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使得他与明人的相交非常融洽。个人情感上,可谓“随处文人添眷恋,到头才子倍交欢”;3[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谢院执事孙昌基》,第188页。国家情感上,可谓“箕封自是小中华,天下均称一体家”。4[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谢进士马欻》,第190页。“小华”与“中华”在文化上的共通性,使得鲁认与明朝士子官员的诗文交流成为可能,以忠孝节义为中心,鲁认藉以剖白心志,明人藉以表达理解和同情。
忠孝观念的诉求集中体现在对官方的呈文之中。迂道中国本是鲁认选择返归朝鲜的万全之策,抵达中国后,却因各种原因被滞于此。为了早日报仇雪恨,实现对君亲的忠孝,鲁认不断请求速归。其文曰:
以君亲一念,不忍浪死于异域……万死隐忍,一息尚存,日夜揣摩者,归谒吾君,生聚教训,大举沼吴。上雪山陵庙社之耻,下洗全家殄灭之痛。5[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4,《再呈徐布政》,第220页。
哀哀一念,只在趁归。今冬雨雪之前,亡亲白骨收拾,招魂埋葬于先茔之下也。6[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四月十四日呈文,第108页。
兹以催归,先叫帝阙,次报故国君父之前,欲图预备复雠之策也。属国流乱之臣,回送故国,于礼当然,而于情最怜。7[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四月二十六日呈文,第124页。
鲁认的迫切,不仅是道德和情感的需要,也是一种政治策略,希望得到明朝官方的认可,进而获得朝鲜政府的宽宥。
节义观念的表达集中体现在与士人的诗歌酬赠之中。信奉朱子学的鲁认不远万里从日本逃至福建——朱子的故乡,在国家危难之际,苟活于世如何获得明朝理学士子的理解与支持,借诗言志成为一种巧妙的方式。“俘臣残命一毫轻,三岁漂流水上萍。天地常纲宜掷死,山河举目愧余生。身随万里皇朝使,路指三韩故国城。自是难忘君父耻,丈夫何必为英声。”8[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谢闽中兵备都司王继武》,第189页。战争漩涡中的人们生死无常,士可杀不可辱之类的舍生取义固然壮怀激烈成就令名,但君亲依然不能免除蹂躏之苦,若能忍辱偷活于世,寻求良策奇谋拯救家国于水火之中,未尝不是另一种忠孝节义。因此,忍辱负重的张良、苏武等成为鲁认最佳的榜样。其诗曰:
瓦全不改苏卿志,恋国丹忱质鬼神。9[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写怀示倪进士士和二绝》,第186页。
鲁连忠愤鸣东海,苏子旌旄掣北涛。10[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谢进士朱天球》,第188页。
恩深苏武终归汉,誓切张良快报韩。1[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谢进士袁敬烈》,第189页。
鲁认写下这些诗句,无论是真诚的倾诉,还是一种自救的策略,明人都对其报仇雪恨的壮志雄心寄予了赞美和期待,见于《锦溪集》卷二《皇明遗韵》者如:
绝似苏卿归汉国,还期范伯沼吴宫。(洪汝让诗)
还相旧君如范蠡,十年生聚剪夫差。(王毓德诗)
张良引去韩讐重,苏武生还虏气摧。(张秀英诗)2[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2,《皇明遗韵》,第192—194页。
与“小华”朝鲜相比,“中华”之大在于其文化之包容性更强。对于中国士人而言,为了节义舍弃生命固然值得尊敬,九死一生以图后报亦属难得。壬辰倭乱之时明廷派大兵支援朝鲜,对明人而言,向中国求助的朝鲜战俘既非间谍,即属吾族类,应当加以保护,这是明朝怀柔远人的自然反映。从社会阶层而言,明朝士人阶层的多元化背景相比朝鲜两班的相对纯粹化背景,也使他们有着更为融通的思想。当然,从人生哲学而言,与朝鲜纯粹以儒学尤其以朱子学立国不同,明朝的官方哲学虽是朱子学,但士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哲学背景远比朝鲜复杂得多。尤其在中晚明时期,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对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王艮即提出“明哲保身”之说,提倡尊身、安身、保身、爱身。因此,对于鲁认,明朝的士子官员几乎一致地体现了理解和同情。鲁认历经磨难,渡万里瀚海逃至中国,他们对鲁认的九死一生啧啧称赞,其中有对生命的珍视,亦是对节义的权变。
鲁认与明人的诗歌赓和,出于鲁认的主动诉求,明人陈仪称其“濒行而更徼余二三友人之言”,又言“此岂其夜郎骇汉,藉中华之绪余以自诩,夫亦孟氏所谓豪杰之士悦周公仲尼之道者也”。3陈仪:《送鲁公识还朝鲜序》,载鲁认《锦溪集》卷2,第194页。鲁认藉“小华”(所谓“中华之绪余”)以自诩,而陈仪则藉“中华”以自傲,视鲁认为《孟子》中自楚而“北学于中国”的陈良。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4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5下,《滕文公章句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06页。鲁认像陈良一样北学周孔之道,正可谓“用夏变夷”。正因为此,鲁认不遗余力地在明人之前表现其“小华”的一面,而明人则尽力对其示以宽待,以凸显“中华”大国的大度优容。朝鲜之为“小华”,不仅是相对明朝而言,还由于邻国日本的存在。被俘萨摩岛时,鲁认结识一日本僧人希安,鲁认亦用《孟子》之典称其为“北学而知礼者”,借其口对日本作了一番批判:
日本数百年来,未有干戈,不知师旅,而百官之改替、科目之取才及法令赏罚,与中国无异,自为一乐国矣。五十年前,南蛮海舶满载炮矢等物漂到日本,日本之人从此力学,皆为妙手,自成战国之习,而便作禽兽之域。5[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3,《倭窟探情》,第198页。
本来“与中国无异”,亦有望成为“小华”之国的日本,却因崇尚武力,而堕落为“禽兽之域”。对于倭寇,鲁认确实如前引诗中所言,有着强烈的沼吴雪耻之心,他凭借自己对日本的观察和从倭僧希安处所借《日本风土记》中探知了许多倭情;6《锦溪集》卷六有《倭俗录》、《畿内五国》、《东海道十五国》、《东山道八国》、《北陆道七国》、《山阴道八国》、《山阳道八国》、《南海道六国》、《西海道九国》等,涉海道险夷、兵民强弱、田畓结卜、地图风俗、路程里数等,皆鲁认被俘时所获情报之记录。即使不能沼灭日本,仍可报仇雪恨,即以对马岛人为间谍,请明朝参与作战,对其施加压力;鉴于日本擅长“土垒”之战,则需扬长避短,诱引日本出动大兵驾海而来,以朝鲜水战之长才攻彼所短,使其扁舟只卒不复再还。凡此种种,均可见出鲁认务实的一面。
三、恪遵《朱子家礼》与鲁认的中国观照
饱受羁旅楚囚之感的鲁认,凭借汉诗文素养,客观上成了中朝文化交流的使者。这一交流并非仅止于诗文往来,鲁认于深层的文化交流更为用心,而其前提是朝鲜与中国的深厚渊源。鲁认多次提到“弊邦虽偏在东藩,自三代时善变于华,故特封箕圣教之以八政,而后衣冠文物、礼乐法度灿然斐矣。秦属辽东,汉封郡县,至自晋时各分疆域,自为声教。然恭修职分,事大以诚,独居诸侯之首,僭得小中华之名久矣,而与诸夏无异也”之类的话。1[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四月二十六日,第123页。朝鲜文人普遍引以为傲的“小华”观念,明人看来颇不以为然,但这却是鲁认观照中国的精神立足点。也正是通过观照中国,他发现中国不那么合乎其理想中的“中华”,更增强了其“小华”观念——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朝鲜王朝在将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官方哲学的同时,以《朱子家礼》(以下简称《家礼》)作为行礼之仪,以期厚人伦正风俗,并逐渐将其制度化。朝鲜的两班不但学习朱子学,而且忠实地践行朱子学。两班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以实践名教礼法立身。2朝鲜两班的精神世界、生活文化与朱子学价值体系的关系,可参见潘畅和、何方:《论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东疆学刊》,2010年第3期。《家礼》中的冠婚丧祭之礼更是朝鲜两班谨遵的,鲁认正可看作《家礼》的忠实践行者。
九死一生漂流在外的鲁认恪守《家礼》,成为朝鲜礼仪之邦的代表者,由此,鲁认及其故国朝鲜令明人感叹不已。在萨摩岛期间,鲁认私意揣测家亲遇难,即以丧礼处之。抵达漳州时,对孙把总的盛情款待,鲁认决意推辞:“我国凡人一遵朱晦庵《家礼》。而况丧制三年,自天子至于庶民,无贵贱一也。我虽流离颠沛之际,何敢自毁于一刻?”3[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三月二十九日,第86页。对此,孙把总赞叹不已,以白衣白冠相赠。而鲁认的衣冠引来了不少福建士子的好奇与同情,亦引起了他们的从权保身以全生还忠孝之劝,鲁认坚持认为不可毁礼以遵夷狄之风。至此,鲁认已从己身守礼上升到了礼仪文献之邦的民族与文化高度,这使明朝士子不由得不感叹朝鲜的守法知礼。
当然,鲁认对本国礼仪的宣扬也遇到了质疑者。曾有秀才持《大明一统志》展示“朝鲜记”所载云:“朝鲜人,父母死则壑葬、水葬、瓦葬。而崇佛喜巫,户外脱屦,常坐地上。白昼市井男女携手并行,善淫使酒。”4[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三日,第144页。对此,鲁认更加详细列举朝鲜与中国自秦汉至元明之渊源关系,并特举丧礼以辩白:
虽奴贱之人,父母之丧,非独不用酒肉,至于居庐哭泣,啜粥三年,柴毁自尽者亦有之。或尝粪断指,流血入口,复甦父母,而旌表门闾者,比比有之。家夫死则终身守节齐衰,矢死不他,三纲五伦,礼义廉耻,可轶于三代之上,故得称“小中华”之名素矣。5[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三日,第146页。
总之,朝鲜实乃“小中华”,绝无违礼之俗。对明人的似信非信,鲁认以《家礼》丧礼细节书示,且现身说法:“其则不远,鄙虽以流离颠沛之际,尚不失丧礼,况平居无事之人乎?”6[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三日,第146页。的确,鲁认的示范作用,使明人对朝鲜的丧礼及衣冠文物、礼乐法度称赞不已。而鲁认并未止步于此,尚欲奏改《大明一统志》为朝鲜辩诬:“不佞当回国之日,特达朝廷,然后因转报天朝,必欲改正一统之志也。”7[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三日,第146—147页。其实,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朝诏使董越、王敞出使朝鲜之际,朝鲜远接使许琮即向董越提出《大明一统志》记载朝鲜风俗有误,请予改正。董越亦曾要求许氏录示朝鲜之淳美风俗,答应在撰修实录时奏达朝廷并改正。8见《成宗实录》,成宗十九年三月己巳,《朝鲜王朝实录》第11册,서울: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其后董越《朝鲜赋》中于此已有所更正,但或许拘于《朝鲜赋》未能广泛流传,明人对朝鲜风俗之认识仍限于《大明一统志》。鲁认对董越《朝鲜赋》更正朝鲜风俗之事盖亦不甚明了,不过,他义正词严要为朝鲜辩诬的态度已足以令明人侧目相视。
在极力宣扬本国丧礼仪俗的同时,鲁认也以《家礼》来衡观中国,比照之下,中国对《家礼》的践行显然不如朝鲜。鲁认曾观摩一户儒家丧礼,认为其丧服、丧礼布置等乃纯用《家礼》,但对其铭旌之写法“显考行年七十三岁李公之柩”有异议,对丧主与客以蔬菜相对而食,更认为是大违于《家礼》。《家礼》卷四“乃易服不食”下注云:“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丧三不食,五月三月之丧再不食,亲戚邻里为糜粥以食之,尊长强之,少食可也。”1朱熹:《家礼》卷4,《丧礼》,《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经部第4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立铭旌”下注云:“书曰:某官某公之柩。无官即随其生时所称。”2朱熹:《家礼》卷4,《丧礼》,《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经部第40册。以此观之,鲁认的异议确乎正常。不过,明朝士子对此并不甚在意,并解释云:“(《家礼》)大江之南则或纯用而或不同,江北则纯不用之,盖陆学乱之矣。”3[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六月二十日,第195页。由于陆王心学的影响,明人对《家礼》或部分不遵,或完全不遵,即便实施《家礼》,还要参考其他官私仪注、政典等。4参见王志跃:《推崇与抵制:明代不遵循<朱子家礼>现象之探研》,《求是学刊》,2013年第5期。但对恪遵《家礼》的鲁认而言,朱子之故乡对朱子之礼尚且如此,由此给鲁认带来的不平之感或可想见。也正因此,明朝士子对朝鲜的“小华”之名更是由衷赞叹:“信贵国文献天下素知,然守法知礼,岂意此极!晦庵《家礼》,中国虽不尽用,而大江之南则(大江,乃黄河也)用之者颇多。贵国则至于奴贱皆用云,盖箕子之遗教也。”5[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三日,第147页。部分明人认为,“小华”朝鲜在守法知礼层面上,比真正的“中华”甚至更胜一筹。
四、鲁认初触“止修”学说及其认知
如果说在礼俗层面鲁认所目睹之“中华”与朱子之本义有违,在学术层面,鲁认所接触福建学者的“止修”学说则近于朱子之学。从信奉朱子学的朝鲜的立场来看,二国之学风只是大同而小异了。由于地域的缘故,在阳明学风靡于世之时,福建还保留着比较浓郁的朱子学传统。相比而言,出使京师的朝鲜使臣,便要经常遭遇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冲突了,譬如学宗李滉的许篈,在万历二年(1574年)出使中国时,即对阳明学盛行于中国忧心忡忡,斥之为邪说横流,认为是彝伦灭绝、国家沦亡之兆,他对“中华”的批判也由此而生。6参见[日]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第一部第一章《万历二年朝鲜使节对“中华”国的批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壬辰倭乱爆发之次年(1593年),明朝经略宋应昌赴朝鲜,军务之暇与朝鲜柳梦寅、黄慎、李廷龟讲论《大学》,作《大学讲语》,犹可见程朱、陆王间不同学风的交锋。7《大学讲语》存李廷龟《月沙集》卷十九、卷二十。
鲁认在福建期间,恰逢徐即登任右布政且提督学政,徐氏不遗余力地传播宣讲其师李材的“止修”学说,师从其说者众多。8参见刘勇:《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1529—1607)为中心的研究》第七章第二节《谨守师传:徐即登的讲学与督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李材之学,本出于王阳明,但又有意立异,标举《大学》中“止修”二字,自认为其学上接孔圣,实则又回到朱子而已,其论多不出程朱之藩篱。《明儒学案》论李材之学曰:“以止为存养,修为省察,不过换一名目,与宋儒大段无异,反多一张皇耳。”9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1,《止修学案·中丞李见罗先生材》,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68页。黄宗羲的批评可谓一语破的。不过明末的学林生态使得这种“多一张皇”的现象司空见惯。徐即登作为李材的弟子,又在朱子故乡任职,宣扬“止修”之学,自当会有不少支持者。鲁认的到来,令徐即登有意让鲁氏传播“止修”之学到朝鲜去,或者也是考虑到朝鲜是个理学发达的文献之邦。鲁认致书徐即登倾诉急于返归之情,令徐氏心生怜恻,遣家人送《闽中答问》八卷、银子二两。鲁认回复谢文,将徐氏赠书视为开来学于万世的达德大道:
金囊而书阅,则皆是相国穷源洙泗,讨论义理,发明乎前古未发明至精至密之蕴奥。孔夫子相传止修之学,复明乎此……相国侧念弊邦兵燹之余,稀圣贤经传,恐吾道之残弛,因使认抱归,而求之得有其师之乐,又布诸国后觉小子者也。10[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一日,第138页。
或许由于鲁认对《闽中答问》中“止修”的认同,且乐意担当传播“止修”之学到朝鲜的使命,徐氏吩咐鲁认留福州两贤祠书院参讲。在两贤祠书院讲学的是倪士和,他原本为武夷山紫阳书院讲学大宗师,后追随徐即登来到福州。鲁认初入两贤祠书院,倪士和即鼓吹其学云:“孔门三千,登杏坛亲炙圣德。然若未透止修之学,则是徒登杏坛已而。”1[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二日,第143页。何谓“止修”?倪士和的解释是“止于至善者,修身为本之命脉也;修身为本者,止于至善之窍门也。”2[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四日,第147页。鲁认对此虚心接受:“已闻止修之学,怳然如亲见孔夫子之门墙。”3[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五日,第150页。十余日后,李材的另一门人——行人司行人李汝圭颁诏至福建,徐即登在两贤祠书院组织了一次讲学大会,鲁认参与其中,仍以“止修”二字互相质对切磋。其间,倪士和云:“鲁先生熟读《全闽答问》,付之梓人,传颁联朋讲学,则朝鲜人人向学,民皆孝悌忠信,尊其君亲其长,此所谓好谋而成者,故天时地利不如人和。”4[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二十六日,第167—168页。《全闽答问》即徐即登所赠《闽中答问》。倪士和明确道出徐即登赠书的用意,正可看出他们以“中华”自居的心理。
鲁认或许没有将此书在朝鲜刊刻,除了鲁认本集和《日记》之外,现存韩国文献中,亦未能发现关于《闽中答问》的更多信息。这并不能说明鲁认不重视“止修”之学,在两贤祠书院的两个月间,鲁认对于讲学的参与还是非常积极的,但对“止修”之学鲁认是否能够全然接受则未可知。从他的提问和辩难来看,“止修”学说与鲁认所理解的朱子学,至少有两处不同。其一,初学下工夫处不同。鲁认询问“初学紧切下工夫处,则先入《小学》乎?《大学》乎”,5[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二日,第143页。对于徐即登倡明道学之旨,倪士和这样阐述:“吾儒只宗孔圣,而孔圣之学,只在《大学》经一章。盖《大学》之道,论主意则只是止于至善,论工夫则却是教以修身为本。”6[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十四日,第147页。相较而言,朝鲜士人学习理学则是自朱熹《小学》入门,《大学》则在其次。朱子学在朝鲜王朝具有绝对的思想权威,朱熹删定的《小学》,在朝鲜初期即被作为科举考讲之书,是官方指定的乡学教材,也是王室教育的启蒙书籍,可谓家传户诵,在士人修身齐家和国家化民成俗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退溪李滉、栗谷李珥在教授门生之时,皆以《小学》为首。鲁认之问,正因为他看到明朝和朝鲜在学习次第上的差异。其二,对经济之功的认识不同。倪士和与鲁认有笔谈云:“足下识见高明,景慕晦庵,庶免泣歧之叹。然止修之学,今始医聋,必沉潜细究,惺惺于戒谨操检,然后八条之功自有归宿之所,而腔子常活活于人性之纲,施之万事,无处不活。此所谓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吾儒经济之功,亦在于此。”7[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六月三日,第177页。此论引起了鲁认的辩难。相对于朱熹概括的“三纲”、“八目”的内圣外王之道,“止修”之学只是以修身为目的,修身即经济之功,而于外在事功似不甚着意。但在鲁认看来,诸葛亮、狄仁杰、司马光之所为方可视为经济之功,尚且因诸人“区区乎讨贼,汲汲乎反正,眷眷乎革弊”而未能大成,孔子则是“非但未能经济,尚蒙盗蹠之垢”,濂洛关闽等宋儒则是“怀道抱德之士,未遇其时,而一未试经纶大手”。8[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六月三日,第178页。鲁认认为或因王风委草世道日卑,故上自孔子下至宋儒皆未实现经济之功,而未能使天下之民皆被至治之泽。倪氏则认为若以长远眼光视之,则孔子与宋儒之经济,实天下万世之经济,不可以一时穷达论之。二人的分歧,鲁认视之为“常道”与“变道”之别。鲁认重事功、崇权变,既有其性格上的因素,也与其所面临的国家危难有关,这种认识与其意欲在明朝上达倭情以求报仇雪恨之策是一致的。
总体而言,鲁认对“止修”之学是在朱子学的范围内来认知的。鲁认抄录徐即登题书院屏风文一篇,于其后论曰:“盖此文,排斥陆象山、王阳明学术之误,而倡明孔、曾传受经一章蕴奥之旨,与见罗李先生倡和一世,天下归宗焉。”9[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三十日,第172页。见罗即李材之号,朝鲜朱子学与李材的“止修”学说在排斥陆王之学上是一致的。10许筠《惺所覆瓿稿》卷十八《漕官纪行》言及鲁认在福建事有云:“认以最崇考亭为言,即登乃攻陆王者,喜甚,悉以其书付之,待之如宾。”(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서울:景仁文化社,1991年,第286页。)这或许是朝鲜人认为的鲁认被赠书及入两贤祠书院参讲的主要原因。“止修”学说来源于《大学》,但李材意欲与朱子学、阳明学有所区别而另立新说的用意,尤其是其出自阳明学,由此形成的与阳明学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盖是鲁认无从知晓的。但正是“止修”之学意欲开宗立派的传播讲学活动和争取更多信众的用心,使鲁认成为徐即登等人借以向朝鲜传播“止修”之学的角色。朝鲜柳成龙《西厓集》记鲁认回国时:“诸生各为歌诗以赠之,且云:‘闻朝鲜以为中原尚陆子,实不然。陆学间有尚者,如此处,专崇晦庵之学,须以所见归语朝鲜’云。”1[朝鲜王朝]柳成龙:《西厓集》卷16,《杂著·鲁认》,《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2册,서울: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326页。李瀷《星湖僿说》卷九引柳氏所载,且有论断:“后认还国传此事。以此数条推之,陆王之学,中国亦不甚盛。其所尊尚者,即间有之耳,何足为怀襄天下之虑耶?”2[朝鲜王朝]李瀷:《星湖僿说》卷9,《人事门·王阳明》,引文据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 http://db.itkc.or.kr。以鲁认《日记》及其与倪士和、谢兆申等人关于“止修”的讨论来看,福建“专崇晦庵之学”虽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些正是朝鲜士人愿意看到的。在他们看来,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立,甚至可以视为“中华”与夷狄的分野。因此,对于鲁认传至朝鲜的福建学者的“止修”之学,他们在内容上将其放大为朱子学,又在范围上将其放大为整个中国,所谓“中原尚陆子,实不然”、“陆王之学,中国亦不甚盛”,都是通过调整焦距,在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华”之中,确立其“小华”之国的文化认同。
五、排斥与包容:鲁认与明人对佛教的态度
朝鲜朱子学的中心地位是在与佛教的斗争中逐渐确立起来的。高丽时期以佛教为国教,佛教及僧侣地位甚高,而朝鲜王朝自立国之初即采取崇儒排佛政策,至明宗朝佛教基本遁入深山,学者称之为“山僧佛教”。鲁认对佛教持严厉排斥的态度,与明人对佛教的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鲁认对明朝士人官员的包容佛教甚为不满,但明人则认为接纳佛教无伤于儒家之道。鲁认曾亲眼目睹杨坐营的敬待僧侣之礼,心中的疑惑使他直言不讳:“虽素相善,若非道僧,不过惑诬之辈。堂堂大丈夫,必困辱而奴之者也,何必待之以礼乎?”3[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四日,第130页。在鲁认看来,僧人中只有遁世服食修行不问世事的道僧或可善为相处,其他之辈则容易蛊惑人心。这种认识正是基于朝鲜对佛教的严厉打击而形成的。朝鲜对僧侣的待遇,鲁认曾有描述:或隐藏山谷开寺讲经,或服食面壁观心,无论道僧、教宗法主还是俗僧,绝无恣行城市,更不可能像明朝僧侣那样可以“着足衙门,对椅相坐”,并且若遇两班,这些“僧徒恐惧伏地,而暂或不恭,则使奴仆结缚,捆打终日”,4[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四日,第131页。而对于读书于佛寺之士子,僧徒皆敬畏相待,朝夕尽心供给。显然,僧侣地位极为低下。由鲁认所举朝鲜僧宝祐因迷惑畿民被儒林上书言其罪过,充军济州岛,后被杖毙之事,更可看出朝鲜王廷对佛教僧徒的严惩不贷。正由于朝鲜儒学对佛教不遗余力的打击,“是以吾道堂堂,异端寥寥矣”。
5[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四日,第131页。
处于海东一隅的朝鲜,尚能使“吾道”光大,“异端”隐遁,而明朝士人却对佛教极为包容,甚或是纵恣。因此,鲁认极为震惊,不免有些愤慨:“(朝鲜)亿万苍生,只游于名教五伦中矣。夫何中国,以圣人之渊薮,礼义之根本,异端之著至此。而寺塔峥嵘于城市,而缁衣横行于各衙耶?”6[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四日,第131—132页。面对鲁认的质问,杨坐营淡然应对:“自梁武而后,弊痼已久。宋贤诸儒及我朝硕儒,虽极严治排斥,但风俗忠厚,只以虚文应接而已,岂可尊信那辈耶?且那辈虽有,何伤吾道哉?贵国之风若然,儒释悬殊严明,文献之称,果有所自来矣。”7[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五月四日,第132页。鲁认的质问是对“中华”的质问,他以名教、五伦、圣人、礼仪指斥中国异端横行;杨坐营的回答既是对“中华”何以如此的辩白,也是对“小华”朝鲜的恭维。确实,在许多明朝人看来,佛教与儒学并非势不两立,而明朝佛教的世俗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更是鲁认无法想象和接受的。
虽然鲁认似乎对潜心修行的道僧有所包容,但当他真正面对道僧之时,仍是充满挑战地对其坐定提出质疑。福州乌石山一位服食松药入定36年的老僧高坐榻上,对其一行视而不见,默无一言,此举与朝鲜僧侣相遇士林的卑躬屈膝截然不同,激起了鲁认的不满。他对老僧的入定提出质疑:“以入定观之,则分明面壁,未知道师已观心体乎?但定榻宜离市井,繁华满目,鼓角盈耳,恐非雪山少林之静也。”1[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六月十日,第186—187页。道师的“若一大观,则虽万物交前,岂累我心哉”之答,2[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六月十日,第187页。并未让鲁认信服,而是以老僧对秀才等人的来访视而不见再次发难,列举慧远远送陶渊明过虎溪之事,质问道师的坚坐不动与视而不见:“果若大观,则虽日应千万人,岂累方寸?”3[朝鲜王朝]鲁认:《锦溪日记》六月十日,第187页。其实,道师的淡定与漠然,并非仅仅对鲁认与秀才等一行,即使军门、布政以下各衙诸相亦是如此,这正是明朝佛教的社会地位与朝鲜甚为不同的一种自然反映。
六、余论
面对国仇家恨及自身的被俘,鲁认表现出了极强的积极用世精神。这从他主动选择迂道中国,以及在福建期间与中国士子官员多方交流可以得到证实。鲁认于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归至朝鲜,并向朝鲜宣祖上书启十条,内容涉及讲和假使、明朝军情、倭情等。4参见《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二年十二月庚子。几年后,曾于万历十年(1582年)中进士的鲁认又登武科,参与岭南唐浦对倭作战并取得胜利,鲁认的忍辱偷生报仇雪恨之志总算实现。或许由于鲁认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诏书,亦得到了宣祖的教书,返归朝鲜的鲁认没有姜沆那种动辄得咎的恐惧,亦没有杜门谢罪,或者仕途蹭蹬;相反,他仍然积极进取,并最终官至三品黄海水使。他在黄海水使任上时,寄姜沆诗有云:“十年憔悴未扬眉,奖激谁期得若斯。皇明盛德推俘命,幸奉君亲宛昔时。”5[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1,《赠姜佐郎》,第187页。返归10年后,鲁认对自己如今的位置感到欣慰,他也非常清楚迂道中国给他带来的潜在保护。
鲁认以战俘身份从日本逃至中国,而后由中国返回朝鲜,其经历是传奇的。虽非官方使臣,但鲁认与中国官员多有诗文酬赠,而入两贤祠书院留馆参讲,使他与中国士子在中朝文化的诸多方面有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流,因此可以说他的中国之行兼具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性质,从而使其《日记》及纪行诗文,无论与多属官方性质的“朝天录”抑或是民间性质的《漂海录》相比,都是极为独特的存在。鲁认的中国之行本出偶然,不可能如其他使臣作“朝天录”多有前人记录可供参考,其《日记》乃是通过亲眼目睹或与中国士子官员交流获得的更为真实的记录。而其行走路线贯穿中国南北,在其记录中可以看到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一地之风土人情和学术文化,这在有明一代曾经到过中国且有文字记录的朝鲜人中,实属罕见。
自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丰臣秀吉暴死之后,由于日本内部的夺权之争非常激烈,对朝鲜的战争也在不了了之中结束。但由于日本之前曾在丁酉年(1597年)再次发动战争,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与反复之态,使当时的人们对战争形势无法预测,即使丰臣秀吉已经死亡,他们也在时刻准备着。鲁认迂道中国,并向明朝呈上倭情形势,期间与徐即登等探讨对日作战,与福建士子交流战况,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朝鲜后期尊周思明的背景下,鲁认中国之行的意义愈加凸显。如吴翰源《锦溪集序》云:“游于闽之庠,睹朱夫子遗风,讲明吾东学问,以合乎三代之典则,于是闽人洒然起敬,发周礼在鲁之叹。陈辞帝廷,乞早东归,圣天子褒之以文山之忠、北海之节。公惟生长东国,习熟教化,故卒能秉国之光,宣于四方,耀于上都。此行虽公不幸,实国之大荣也。”1[朝鲜王朝]吴瀚源:《锦溪集序》,载[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第180页。所谓“周礼在鲁”,正是朝鲜士人藉以自傲的“小华”意识。鲁认的后孙们努力为其先祖博取朝廷的褒显之典,如请求为其建祠,全罗道罗州乡校、礼曹等皆有上书,高宗时领议政洪淳穆亦为其请言。2参见[朝鲜王朝]鲁认:《锦溪集》卷7,《请建祠上言》、《全罗道疏会发文》,第241—243页、第244—245页;《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年五月八日,서울:國史編纂委員會,1977年。最终,鲁认以忠节卓异被追赠为二品兵曹判书,3《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年五月十四日。这使鲁认成就了令名,其中国之行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鲁认与明人的文化交流,亦引发了朝鲜文人对明朝的别样情怀。如田愚曰:“是帖也,即武夷诸儒赠公东归诗及序也。公之后昆,持以示余。爱玩累日,怳若汛扫腥羶之气,而复见冠带之人。于是乎弥切风泉之感,为之太息而识其后。”4[朝鲜王朝]田愚:《艮斋集》前编续卷5,《跋皇明遗韵》,《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33册,서울:景仁文化社,2004年,第488页。任宪晦亦曰:“生于东表,限以鲽域者,乃得与中华文献之士,际接而周旋如此。此可谓稀有之快事也……呜呼!此等文字之不复渡鸭江,今已二百余年矣。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抑或有其日乎?”5[朝鲜王朝]任宪晦:《鼓山集》卷9,《皇明遗韵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14册,서울:景仁文化社,2003年,第228页。时移世易,二百余年之后,“中华”已满是“腥羶之气”,而朝鲜的“小华”意识则愈来愈强,这段中朝交流的历史记忆,在明清易代后令朝鲜文人感叹唏嘘不已。
[作者杜慧月(1979年—),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河南,焦作,454000]
(责任编辑:刘波)
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3.010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东亚汉文纪行文学中他国形象认知比较研究”(项目批号:15AZW006)阶段性成果。
201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