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了一颗子弹(外一篇)
陈云昭
1
我的童年是从那颗子弹开始的。这颗属于祖父的子弹,牵引过我一段童年时期的关注和朦胧的情绪。没有人知道这颗子弹对祖父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几乎从未在他的子孙们面前谈论过这么一个东西。他活着时,沉默的时间几乎和那颗子弹一样多。
祖父脸上的表情,就像农具上出现的锈迹,总是被家人所习惯而忽略可能暗藏着的表达。家人哪会有多余的心力和时间去注意这样的事情呢?他们的心思也像筛子那样,留下大粒的粮食,漏掉那些五彩缤纷的杂质。祖父的表情应该从未被家人注意过。自然,那颗子弹也不会被家人格外的注意过。
我拧开一只长满锈迹的半截手电筒(手电筒的灯头没有了)的后盖,看到了子弹,七颗。这只深埋在木箱子下面的半截手电筒,就像我曾经捕获过的一只鲫鱼那样,费了很大的力气,却让我兴奋不已。很多天里临睡之前,我都会想一遍那半截手电筒,那半截手电筒里的七颗子弹。
这半截手电筒是突然出现在我启程后不久的一个黑暗的洞穴。这个洞穴我只在识字课上听老师讲过,但它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它里面装满了童年时代的好奇和对奇异经历的渴望——这七颗子弹是不是代表七个秘密?它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有了子弹是不是就会有枪?枪又去了哪儿了呢?也许沿着这个山洞探寻下去我将什么也不会得到,但我并不会失望。
2
我常常在露水还未落尽的牵牛花旁想这件事儿。灰白色的老桥旁,蓝色的牵牛花盛开。它们像天气晴朗时的秋空,蔚蓝而深远,每一朵都像在宣告一个我当时还不能领会的秘密。我一直没弄明白,牵牛花的藤蔓是不是会经常绊住牛的腿,所以才叫牵牛花。我不敢把这些细碎的心事拿来问家人,这会浪费家人的时间,我还会被他们看成是一个痴子。这些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些事情不一定急着去得出答案,只要一个人去想就好了。于是在秋日的背景下,我一个人坐在东墙根下的小板凳上,看着半空中的云成群结队地走过我的头顶,我想告诉它们我的秘密,但它们不会听到。
父亲每天都会挎着他的医药箱出诊,到傍晚才能回来,有的时候是深夜。我看到他的时候,那只绣着红十字、黑色的、湿漉漉的医药箱总是挎在他的肩上。他的背影总是拖着湿漉漉的夜幕。他的那些病人、他的声誉比我重要。我不知道他一天都干了些什么,他也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这兴许是一件好事。我们彼此的不了解都给对方带来了某些自由,我很享受他对我的不关心。我每天可以从他的身上闻到酒精融在棉球上的味道,以及各种药水混在一块说不清楚的味道,这样我就满足了,我就可以获得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这也是我对他的了解。我有一次偷偷地看到过他年轻时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被镶在一只墨绿色的小镜框中,他坐在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有一盏老式的台灯(灰白的硬塑料底座,铜质灯柱),他手里握着笔,梳着那种“知识分子”式的头型,眼神忧郁地看着我,像是不认识我。他当然不认识我。
母亲忙着上工,田里的棉花比我重要。在秋日的阳光直射下——秋天的阳光也是蓝色的——棉花地里一片盛开的白,是深秋在大地上慈祥的发束。家乡的情绪也是白色的。一团团从棉花桃里炸开的棉花就像一张张婴儿的脸,他们掠夺去母亲的汗和仅有的笑。我曾看到母亲挎着竹篮采摘棉花时难得的笑。我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和这些孪生兄弟们相处。我拽着一根棉花杆开始学着迈开第一个步子,我倒在棉花地里深深地午睡,听到秋天在吃棉花叶的声音。秋天总会摔下母亲重重的身影,除此之外,我还能看到母亲什么呢?
祖父从隔壁村的一个大学生那里借来了几本很厚的书,里面好像有《红楼梦》《三国意义》和《七侠五义》。自从他把斧头、刨子、墨线盒、锯子,还有那七颗子弹放进那只木箱子之后,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读书和喝酒。我曾看到他蹲在西面墙跟下,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所有的书他都是在读,而不是看。喉咙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字句。只有这个时候他似乎才从沉默中走出来,或是走进更深的沉默,唉,谁知道呢?那是一本没有封面的书,很多油腻的东西粘在第一页纸上,被翻过很多次的书页,看起来潮湿暗沉,它们无力地耷拉在祖父右手的无名指下面。临近傍晚时直射过来的阳光,正好打在他的脸上,他的脸沐浴在一片红晕中,让他看起来有一种难得的神采。我不知道这本书叫什么,他看得很认真,像是在书本里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物,或是看到了自己多年前许下过的梦想。他的余生就是在这两样东西上度过的,除此之外就是沉默,面对祖母时也是这样。
3
祖父在看书或喝酒的时候,我总是不能接近那只木箱子,箱子里藏着我一桩心事。我总是想再次看到它们,再数一遍那七颗子弹。这些子弹引发出我的疑问和幻想,像一幕幕电影,每天临睡之前都在我眼睛上方的蚊帐上放映一遍。我没有地方可以找到答案。我从没想过把心中这些问题拿出来问祖父,我怕他,我怕他知道这些秘密后再也不会让我去碰那些东西了。很多的时候,我总是希望天气会变坏,下雨或下雪什么的,祖父就会出去溜达。这时,我就可以再次走进一个充满惊险的山洞。这是一个特有的洞穴,里面放着一个让我牵肠挂肚的木箱子,还有粮食——面粉装在布袋子里、蛇皮口袋里装着黄豆、大米盛在柳条编成的“笆斗”里。大雪碧瓶装着刚用油菜籽换来的菜油,一张黑色的箱子放在一个简易的木架子上,摇摇欲坠,它尤如童年之前的我,坚硬的黑色,一直拒绝我的进入。砖头铺成的地面,砖头与砖头之间的缝隙似一张张龇开的小嘴,脚走上去它们就开口讲话。一股陈旧的气味,让我的鼻子从酒精棉球味中苏醒过来。我蹑手蹑脚走进那只木箱子,所有的家什都被顺顺当当放在里面,斧子、刨子、锯子上还被上了一层油。我小心地拧开那半截手电筒,再一次看到它们,把它们再数了一遍,还是七颗,没有少。这次,我发现这七颗里面有一颗长了不少的铜锈,我决定拿走这一颗,因为它旧了、还有六颗,祖父应该不会在意。
我从父亲那只医疗包里扯了一块纱布,把那颗子弹包好,放在枕头下。我陶醉于一层层打开纱布,直到最后惊异的一幕出现在眼前:它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有待解开的谜题,也像一个让人急欲听到结尾的故事。我不厌其烦地反复做这样的动作,我喜欢这样给我带来的新奇感。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开始惦记起其它六颗子弹。在我临睡之前的那些活蹦乱跳的幻想中,又多了祖父沉默时的表情,以及他那只端起酒杯时颤抖不已的手,我甚至还想到他用这只颤抖的手拧开手电筒后惊异的表情。这些新加进来的幻想折磨了我,于是我决定把那颗子弹偷偷地还过去。可它不翼而飞了,丢下那块纱布之后。我惊慌失措地寻找它,但再也没找到过。在我的记忆力范围内我无法想到它去哪了,或是什么人可以拿走它,唯一的可能就是它自己把自己藏起来了。

我因此深深的懊悔。看着祖父不断衰老的脸和那双青筋暴露的双手,我的懊悔也在逐步生长。随后的日子,我总觉得有一个人用一种哀婉的眼神,站在我身后看着我,它让我沮丧并且深深自责。我感觉到祖父以更沉默的表情面对我,而我几乎不敢从他的身旁经过。我曾下了无数次的决心把这件事向祖父交代,但我怕他,我怕他的沉默。我也试图用另外一些方式弥补我的过错,比如我想把学校里小图书室的那本《封神榜》偷回来送给祖父,帮祖父烧火做饭,帮他把桌子擦的一尘不染,但这些我好像都没做到,祖父对我的沉默依然如故。是不是祖父已经发现丢失了一颗子弹并因此责怪我?我不知道,但我一直在这样猜想。后来,从年长的一些邻居那里隐约听到一些有关祖父的往事。
4
祖父曾是新四军乡游击队的队长。父亲说,那个时候一个乡只有三个人有枪,乡书记、游击队队长、游击队指导员;是否枪毙一个人,只要三个人中的两个人就可以决定。祖父自己也隐约在某次酒后,谈到一些他早年打仗的事情。他说鬼子把飞机开得很低,几乎要低到泡桐树的树梢。驾驶员的脸都能隐约看见。即便这样,也没有人敢用步枪去打。所有人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迫近,都慌不择路,躲进鸡棚、趴在床底下的都有。祖父就曾抱着步枪蹲在大水缸旁躲避盘旋的敌机。日本鬼子打完了,大部队要去开辟大别山,要祖父一起去,他拒绝了。随即,祖父的党籍被开除,行政职务被免去,枪上缴。三年自然灾害头一年,他带着三弟一路讨饭至临县的一个村,跟一个老师傅学了木匠。我小学课堂上的桌凳有一半出自他的手。我因此骄傲过,但也一直因为他是个逃兵而困惑不已。尤其当祖母说起邻村的某某老革命今年劳保又涨了多少多少,我就觉得这个逃兵当的太不值当了。
很多时候,我一直想知道祖父为什么拒绝去开辟大别山。在祖父大多数沉默的时间里,我站在一旁看他的眼神里一直有一种期待。我想了很多条理由来宽慰自己:也许他是家中的长子,也许是因为他刚娶了祖母,也许他受伤了……,其实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果,如果他去了当上将军,如果他去了做了英雄,如果他去了现在可以拿着很高的劳保……但祖父的沉默不会告诉我答案,父亲母亲对此更是一无所知,他们也没心情来满足一个孩子无所事事的好奇。谁知道呢?这也许是祖父一个人的秘密,和我有一个人的秘密一样,无法找到答案,也不需要得到答案。但我还是忍不住会去想这件事,希望能从对祖父沉默的凝视中得到启示。祖父会不会因此懊悔过?如果再次面临选择,他会怎么选择呢?在家人多有抱怨的年月里,他痛苦过吗?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他从未想过呢。
一个午睡后的下午,我端着小板凳坐在祖父身旁,含混地向他问了句类似“你没去,后悔吗?”这样的话。这句问话的由头我已经忘了,或者说我那样的年纪为什么能问出这样的话?但我确实记得有这么一个下午,我向他问起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许只有那个年纪的我才会这样唐突的问他吧。我还不能确定这样问他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这两句对白是我唯一如此清晰刻在记忆里的和他说过的两句话,它们是如此的弥足珍贵。后来我也没有机会再问,或者说我再也没有找到那样的一个下午,那样的一个年龄,那样的一个气氛,再去问他。我的问题几乎忘了,但他的回答我却一字不落地印在我的脑中,“去的两个人没有活着回家来”。我们两人其他的对话我都记不起来了,但那个下午的气氛却像我饥饿时泛起的胃酸那样一直伴随至今——秋天的下午似乎总是有鸭梨的味道,大朵的白云下,在朦胧的睡意并未完全退去之前,祖孙俩说着话。但是,我依然没有向他提起那颗丢失的子弹,告诉他我的自责,向他道歉,尽管我很想那么做。
当我再次看到当年被我偷走的那颗子弹时,我的愿望是把它放回去,把它放回那个半截手电筒里,和其它六颗一起再次变回七颗,但那六颗子弹连同那个手电筒再也没有出现过,它们永久的消失了。像祖父一样。
行走词典
行走——无家;双脚;时间;荒野;山水;古道;流亡……在行走的语义谱系里,它还能繁衍出更多的“词”(是词不是词语)。这些“词”既独立地构成一个语义历史系统,又可以是“行走”这个语义“蜂房”的一个个“窗口”。我们不是透过这些“窗口”朝里开——词的考古学只能满足知识的趣味——我们要在“蜂房”里透过这些“窗口”往外看,这样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和行走有关的世界,或者简直可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行走事件引发的世界——
无家。以行代寓。初唐诗人寒山说“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他的家宽敞到能延伸到天空的尽头,也就是说他是“无家”的;所以,“无家”在这里意味着“在整个宇宙的大家之中”。可以由此想象到的是,那些喜欢独来独往、喜欢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行走”中的人,他们并没有丧失他们“家”的完整性,他们把自己的家和他们行走过的道路、以及在行走过程中所领略到山水景致看作完全一样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明朝晚期出现的行走者徐霞客是一个彻底的“无家”者、是儒家价值体系的挑衅者,因为他把“家国天下”中“家国”给拿掉了,只剩下“天下”,这个天下还是抽掉了政治担当和道德责任的天下,这个天下几近是自然、山水、荒野……徐霞客用一种几近虚无的方式(有汉学家认为徐霞客的旅行是强烈的实用行为,对此我并不赞同。至少,在他做第二次长途行走之前,他的那些宏伟的“科考梦”还没有正式形成。对此的观察,除了从目的和结果来看,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是从该做法实际产生的意义,并且这个意义还应当被置入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来看。张骞、玄奘、郑和,他们都是在徐霞客之前的大旅行家,但他们行走的目的要么是一种政治的,要么是一种宗教的)完成了他作为一个“颠覆者”的形象。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古典时期徒步行走里程数最多的人,但他大约应该是整个大明王朝里徒步行走总里程数最多的人;他终生的志业是“行走”,如果这个大的基调被我们忽略,那么我认为他的那些自然知识“考古”将会毫无色彩。并且,我们对徐霞客整个“事业”的理解将会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从这个角度说,徐霞客即便不是明后期开放、多元、包容的市民社会价值体系的代言者,也应该是那个时代思想和行为领域内最为“时尚”的人之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大量的行走者把重走“霞客路”作为一个“时髦”并且“大胆”的做法;李约瑟称《徐霞客游记》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这句评价延伸出的意思应该是:徐霞客终结了古典行走者的形象,建立了一个现代行走者形象。从此中国古典行走者过于“漂泊性”和“文学性”的行走行为,多了一些更为复杂更为“现代”的意味。
双脚。双脚导向心灵。人类对“双脚”的迷思被完整地保留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中。那些保留古代人类足印(或者动植物的足印)的观看装置被设计成一条自然的钢化玻璃路。当你步入这条有钢化玻璃铺成的路面,不经意低头往下看时,玻璃路下就是那些古代时期留下的足迹。奇迹就这一刻发生:你的足迹不经意间和那些足迹重合。这意味着什么?博物馆这种哆啦A梦式的设计是一种深刻的信息沟通,完成这次沟通的是两只足迹。在此,由双脚踩踏形成的足迹就是一类“超级”媒介。这类媒介转译时间,也转译心灵。“我只能边走边思考,”卢梭在《忏悔录》第四卷中写道,“当我停下时,我的思想也停了下来。我的大脑只和我的腿脚一起工作。”索伦·克尔凯郭尔推断,心灵应该按照每小时三英里的步速运行才能发挥最佳效能;克里斯托弗·莫利在论及华兹华斯时说,他“将自己的双脚当作哲思的工具”;麦克法伦谈及自己的双脚则说的更为直接:从我的脚跟到脚尖是二十九点七厘米,折合十一点七英寸。这是我步伐的单位,也是我思想的单位。
时间。慢与快。对此, 昆德拉将之归结为一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蔡明亮在电影《行者》中则把这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推至到极端。他利用“慢与快”把我们所有作为“被观者”的现代人都推到了“尴尬”和“惊悚”的境地——电影中身着鲜红僧服的“比丘”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行走在川流不息的(香港)闹市区。在极慢的行走中,他在世界之外,或者说他在现代世界之外,在“快”的世界之外。“快”的世界在他周围成了一个“荒诞”而“尴尬”的存在,那些疾步如飞的“现代人”(“现代”这个词本身就包含某种制度或者机器制造的速度和进化的意思。但应该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称谓,我们该如何描述身在快速的我们呢?我们是一群没有准确指称的人吗?)在这个比丘身边快速经过,观看,但他们反而成了被观看者——
“速度是技术革命献给人类的一种迷醉的方式。和摩托车骑士相反,跑步者始终待在自己的身体中,必须不断地想到自己的脚茧和喘息;他跑步时感觉到自己的体重、年纪,比任何时候都还深切地意识到自我和生命的时间。当人被机器赋予了速度的快感之后,一切便改变了:自此之后,他的身体处在游戏之外,他投身于一种无关肉体的、非物质的速度之中,纯粹的速度、速度本身、以及令人兴奋的速度感之中。”(米兰·昆德拉《慢》)
让人“惊悚”的是,那些疾步如飞的“现代人”在身着鲜红僧衣缓慢行走的“比丘”周围,迅速地被“淡化”,被“渐变”,他们都成了这个“比丘”的模糊远景,或者可以说他们很快就消失了;昆德拉的“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在这里得到验证: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
荒野。荒野上的语言。“道路”是指有迹可循,引领你去某地的“线路”。但真正的快乐源自完全不遵循常人所走之路——行走最终通向的不是路的尽头,而是在这尽头之外的无名之地:荒野;通向发现;发现什么?语言——
自1979年3月
特朗斯特罗默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词不是语言
我走入白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碰到雪地里麋鹿的蹄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李笠译)
瑞典冬季的荒野是寂静的。寂静是一种完整的状态,一种无词的语言。从这里出发,既能更好地理解这首诗,也能更好地理解荒野,以及荒野上的充满生机勃勃的“语言”。
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语言则是用来表达或交流思想和感觉的一套声音及这些声音互相结合的系统,系统的文字表达,表达或交流的任何方式,如手势、标记,或动物的声音,等等。这里的语言遵循的语法是“棕色语法”。(“棕色语法”一词源自西班牙语gramatica parda,表示一种大自然母亲的智慧,一种极具野性的、幽暗的知识。棕色语法不仅属于语言,而也属于文化和文明本身。这样的语法规则就如同森林中长着苔藓的小溪,沙漠中散落的砾石)
《自1979年3月》给我们展开的是这么一副图景:大自然——荒野——敞开着,如空白之页,并向四方展开。“荒野,完整的体系,神秘的现实,在这里被看作语言的诞生地,和穿越它的动物发生感应,就像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穿越一座林子时体悟到的《感应》,一个神秘,包容一切的世界”(李笠)。当诗中主人碰到麋鹿的蹄迹,作为自然之魂的语言出现了,它充满了神性,启迪。语言——自然,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诗作,一种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悟的神秘。
谁在荒野上进入语言,谁就更接近自由。莫瑞斯·赫尔佐格在《安那坡那峰》描述了这种领略荒野之上的语言,而带来的自由和震撼的审美体验——
没有动物或植物可以在这里生存。在纯净的晨曦中,生命的缺席,这种自然的彻底贫瘠,只是加强了我们自身的力量。当人类的自然倾向向着大自然中一切富饶和慷慨的事物时,我们怎么可能期待其他人来理解我们这种来源于贫瘠的奇特兴奋呢?
山水。虽然我们早就有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式的山水化人格隐喻,但最终把山水发展为一种实践美学的是后来的“晋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自己的深情”,“好山水,爱远游”的晋人爆发了对山水的激情。他们用双脚丈量的每一寸山水都不可避免成了他们各自的一个精神空间,即在万物的迁徙流变中寻得一个静止点。在那里,人可以得到安然的休息而不会感到任何的威胁,他坦然接受四周自然环境的陶养,获得终极性的启迪。相较于东方,西方的“恋山史”则晚的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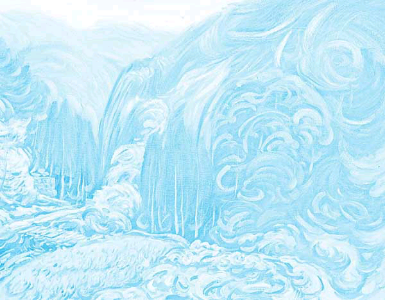
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之前,西方如果冒着生命危险去攀登一座高山会被等同于精神错乱。自然景观可能拥有某种吸引力,这种概念在当时的西方几乎不存在。自然风景被欣赏的程度基本上要看他和农业的富饶有多大关系;十八世纪下半叶,西方人第一次出于精神,而不是生活需要,开始向高山行进,与此同时,也开始发展出对高山景观的壮丽感受;必须注意到的是,对山水审美实践上,东西方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角度(当然,这两种角度偶有交叉,当杜甫写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时,他内心所感受到的“澎湃”很难说和乔治·马洛里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感受不同)。从一开始,中国人对山的观看视角就是“平视”的——山不仅是归隐之所,更是一种理想生命的外延;“仰视”则是西方人对山采取的典型视角。“因为山就在那儿”(乔治·马洛里在被问及为何想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回答说,“因为山就在那儿。”)这句话暴露了人类最为彻底的征服欲望和狂野之心。人与山的对立在此更为彻底;而在古典时期的中国,“山水”是一种表述整个自然过程的方式。正因如此,“山水远远超出了纯洁与污染、天然与人工诸如此类的万物二分法”(施耐德《青山常运步》)。
古道。那些背着高档的旅行行囊,手持铝合金手杖的现代人行走在“古道”上意味着什么呢?我的一个朋友刚走完“徽杭古道”,兴冲冲地说还要走“玄奘之旅”,再重走“霞客路”。好奇怪的说辞,徐霞客可没走过他们正在走的“霞客路”,可他们宣称自己在“重走”霞客路。我曾问她,你为什么要走这些“古道”呢?她说平时难得行走,走在那些古人曾走过的古道上很畅快。好精致的畅快呀,精致到足以出售;那些一条条被各大旅行社承包的“古道”同样精致,哦,它们本就是用来出售的,出售行走的畅快。
艺术家理查德·朗曾经创造过一条小径,他在沙漠中不停掉头,来回差不多数十次,终于走出一条笔直的路线。但这些充其量只是一堆脚印的排列,而不是道路。“从字面意义上说,它们连接的是不同的地方,而从引申意义上说,它们连接的是不同的人”(麦克法伦《古道》)。
那些“古道”还是古道吗?而行走呢?我明明已经感知某些东西已经消解了行走的意义。昆德拉说“在我们的世界里,悠闲却被扭曲为无所事事,其实两者完全不同:无所事事的人心情郁闷、觉得无聊,并且不断寻找他所缺少的动力。”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生存的每一个器官都被进行了“现代化”的整形之后,我们还能“悠闲”吗?也许,我们可能已经只剩下“无所事事”地重走“古道”了;阻碍行走的是行走本身。
流亡。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行走意味着对家的“舍弃”,成为一个“无家者”;对语言的舍弃,让“无家者”变成“流亡者”。有多少人已经是“流亡者”?又有多少人正在成为“流亡者”?或者说,是否整整一代人都会变成“流亡者”呢?我们在行走中首先失去的是方言,既而失去的就是整个汉语;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北岛《乡音》)。
长久以来,基督教传统认为,人人皆为宗教旅人,因为人之一生便是一场流亡之旅。这种思想在汉民族的农业文化传统里肯定是没有空间的。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对于我们这片土地来说,“流亡”已经是中国现代史课本上的一个显著“字眼”,只不过移民的主题词在各个时代略有区别,财富、冒险、雄心、事业、战争……这些都是迈开双脚告别“母语”的主题词,从这个角度来看,流亡其实还是在实践着行走的终极美学——时间、荒野、山水……这些所代表的一切精神憧憬,仍然是流亡难以克制的冲动来源。
《圣母歌》:流亡过后,烦恼全无;真的如此吗?——
我对着镜子
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
(北岛《乡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