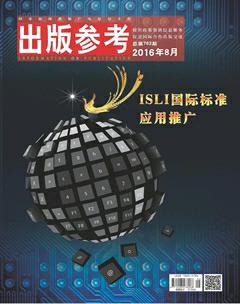中国书籍设计与出版核心力
周晨
“中国最美的书”评选对于提高当代中国书籍设计整体水平,成绩不言而喻,但对于当今图书出版业价值究竟何在?本文重点主要从当代书籍设计作为出版体系中的核心环节——编辑环节展开,梳理其对于书籍设计的价值与意义。
热词:最美的书 书籍设计 书籍装帧 编辑
2003年上海新闻出版局组织了“中国最美的书”评选,至今成功举办13届。271部中国图书送到莱比锡这个国际舞台交流,展示了中国书籍设计的风采,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当代图书出版的现状。通过这些图书能看到当代中国出版物在纸张、印制、装订等技术指标的长足进步,也能看到当代书籍设计在审美尺度把握上的多元探索。在2016年度“世界最美的书”的评选中,中国两书获奖:《方圆——订单故事》、《学而不厌》分获一金一铜,这是中国书籍设计界收获的特大惊喜!也是自2004年《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获得金奖之后,中国参加此项活动以来历年取得的最佳成绩。
“中国最美的书”评选倡导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体现在:凡我国正式出版的图书皆有资格参评,选送途径可以是设计师、出版社或者作者,且主办方不收取任何报名费;评审机制公开透明,每届评选工作由国内评委及部分国际评委组成,并有轮换制度;对接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沟通与交融都十分有益于专业的推动。开放的平台引发了开放的思维,2003年首届评选活动开展至今,开创了书籍创新设计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这一领域空前活跃。这个活动凝聚了一群优秀的设计师,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作品,开阔了书籍设计的视野,探索创新了纸质书形态构造、气质韵味、阅读感受的种种可能,在众人协唱纸质书夕阳之歌的当下,这些成果成为了一抹亮色,值得总结。
“中国最美的书”不同于表达纯概念性的艺术书籍,或国外的手造书,它的创新是建立在书稿文本基础之上,有作为正规出版物的要求,不是单纯的视觉形式变化,而是要依托于内容的形式创新,追求形式与内容的高度一致,“中国最美的书”已然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道独特风景。要论当下中国图书出版物品质的现状,可以金字塔作比,一方面大量塔基的大众图书整体设计印制水平还很低,一方面“中国最美的书”登高一呼,在世界舞,斩获各级奖项。
书籍设计是出版编辑环节中从无到有的原创性劳动
书籍设计不是简单的技能劳动而是创造性劳动。在书稿转换为书的过程中,书籍设计者与作者一样都是创作者、创造者,但设计师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在出版环节中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缺乏话语权,缺乏掌控图书生产全过程的权限,结果就是大部分书籍成品较为粗糙、貌合神离、形质脱节,这是对书籍内容的不尊重,是对作者辛勤劳作的无视。同样纸张印制成本的投入,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的物质存在,浪费了材料资源,结果却是全然不同,在现有的出版系统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把书籍设计者的工作作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来看待,觉得美编工作没有对错之分,似乎可有可无。事实上,几乎所有获奖的“中国最美的书”都是设计师全程监督下制造出来的,以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获得2016世界最美的书铜奖的《学而不厌》为例,美编设计师曲闵民在印刷厂足足熬了七天七夜,一跟到底,否则根本达不到现有的设计效果。因为在现有的出版社体制中,尽管有出版科作为负责印制的职能部门,但要如设计师般严守图书品质,客观上没有精力,同时也无法完全把握设计师的特殊要求,责任编辑中不乏优秀的文字编辑,大部分的精力与职责只在对内容文字校对负责,对于协调书籍设计的高品质只能寄希望于个别责任编辑的责任心与个人追求了。在这样的模式中,图书成型的关键环节恰恰有可能沦为真空地带。在现有出版环境中要提升图书的设计品质:一个方法可以在现有基础之上,扩大责任编辑的责任面,明确统筹协调跟踪的职能,把这部分责任负起来;第二个方法是可以尝试将一些信息图文较为复杂、印制要求较高的图书作为一个项目,由美术编辑担任项目负责人,整体负责,全流程负责,由文字编辑配合,各司其责,各展所长。书籍设计家速泰熙先生在很多年前,就认为书籍设计其实是书籍精神内涵的外在化,是书籍的第二文化主体。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曾在《江苏读本》一书的封面上打上设计者速泰熙的名字,体现了文化人对书籍设计师原创性劳动的高度尊重和充分肯定。
书籍设计是当代纸质书突围创新的重要力量
在阅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当下,纸质书普遍不被看好,书籍设计师群体曾一度有岌岌可危之感,但恰恰在此关键时刻,中国书籍设计师群体发力,依托“中国最美的书”平台,创作了一批佳作,作品水准上了一个台阶,这不得不引人深思。日本的杉浦康平先生提出书籍设计“五感”理论,认为完美的书籍设计形态应具有诱导读者视觉、触觉、听觉、味觉的功能。在吕敬人先生的倡导推动下,书籍设计“五感”理论,在中国纸质书设计实践中正发挥着作用。曾有读者看了“中国最美的书”获奖图书的照片提出“高见”,姑且不论是否有理,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最美的书必须拿在手上细细翻阅才能体会其妙处与匠心。以《方圆——订单故事》为例,封面选用书籍专用防潮包装纸,质朴至极,气质独特,能一下点明行业特征,全书阅读线索复合交叉,构成全书体例设计结构的变化,使读者产生多重视角,设计师李瑾说:“这里面有订单的故事,更有我同学的家族故事,还有几代人对书店的记忆。”作者吕重华提供了手绘的订单足有一万张,设计师精心整理出了独具个性的上千张,整理这些订单就花费了一年时间。为了调和书中的众多信息元素,李瑾尝试做了六个版本的设计。书籍形态有创新,装订形式由传统而来却有现代气息,内容编排多条阅读线索,编辑体例创新,订单上作者喜怒哀乐的自画像,最终被设计成四本小书,线装的左侧,可以快速翻阅,使人产生时光流转岁月流逝的联想。确实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在图文结合类的图书中,书籍设计的作用尤为突出,复杂的多元信息编织,大大增加了书籍设计的含量,在深度加工之后呈现出多彩的风貌,对图书体例创新及阅读感受的提升有新的贡献。如2015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由姜嵩设计的《温婉——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就是体现书籍设计之美的精心之作,大量类型各异,形态各异的原始图片素材,经过有序的编织,体现了设计师扎实的编辑水平,各类图文信息有序充分得以展示。书籍设计的过程,就是寻找有意味的形式的过程,探索有理由的设计,以形式反哺内容,甚至提升内容。与科技发明创造不同,文化创新的实质其实就是形式创新,功能或许没变,但感受的变化正在发生,从网络拍卖对毛边本、精装本、签名本的追捧,从一个侧面可以预测一个趋势,那些最终坚守纸质书阅读的读者对纸质书会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正如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前主席乌塔女士在文中所述:“在媒体不断细分、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传统纸质书完全可以发掘其媒体特性而获得新生。这些特性需要通过未来新的书籍设计理念和实践得到更好的发挥。传统书较数字化阅读的优势在于其感性的表现方式:实物感和现实感。”吕敬人先生在策划“新造书运动”时认为:“所谓新造书运动,旨在通过好的文本传达故事,向社会由表及里进行深度信息的传播。书籍设计师不再是简单的设计者,而是信息的传递者,书籍也不再是平面设计,而是传递信息的建筑。好的书籍是让信息诗意的栖息,为读者创造阅读的空间。在未来,书籍是电子虚拟和纸质文本两种形态存在,新造书运动唤起回归对物质存在的理解,对书籍美感的享受,让读者插上想象的翅膀。”
书籍设计是提升出版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2015年春随中国代表团参观莱比锡国家图书馆时获悉,1912年莱比锡这座城市从事与书籍有关行业中有:300印刷厂和排字厂,982家出版社和书店,173家图书装订厂,298家版画设计院,36家印刷机制造厂。莱比锡当时不光是德国的书业中心,也是欧洲的书业中心,在惊叹产业链发达完整之余,不难发现在其产业链中负责书籍美化的版画设计院占比相当高,可见其在图书生产环节的重视程度。整体性的书籍设计规划,以及文化风格的定位能有效提升出版社产品在市场中的整体形象,因此,老一代的出版大家十分重视书籍设计,北有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南有岳麓书社的钟叔河先生,这在业界是传为佳话的。出版社的书籍设计可以大大提高图书的识别度,如《汉声》杂志推出的系列书籍,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个性凸显,在众多图书中,一眼就能看出来。随着大众审美的提高,作者对于书籍装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优秀的书籍设计还是获取优质书稿的手段。同时设计师不满足于担任被动的配角,以设计为先导,介入内容策划,如江苏著名书籍设计师朱赢椿,多年前就开始尝试以设计师视角运作推出多部创意作品,《蚁呓》、《设计诗》、《空度》、《肥肉》、《虫子旁》等书都已然跻身畅销书之列。2015年度“中国最美的书”获奖图书《上海字记——百年汉字设计档案》(姜庆共)、《爱不释手》(洪卫)、《黑白江南》(沈钰浩)都是设计师介入图书内容策划的范例,既是设计师又是作者。每年获评的“中国最美的书”已经有了固定的收藏群体,形成收藏热点。从2015年获奖的“中国最美的书”看,文化公司对于书籍设计的市场价值嗅觉灵敏,关注度较高,如《痛》、《薄薄的故乡》都是楚尘文化推出的作品,好马配好鞍一定能推动图书销售。与此同时,主流出版系统也开始关注,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曾组织下属出版社高层携相关部门人员专程赴上海,观摩雅昌艺术中心举办的“新造书运动——书籍设计十人展”。然而,放眼整体,大部分的出版社对于“最美书”的认识其实还停留在“锦上添花”,重视不够。
书籍设计是当代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及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照排技术尚不发达,早期画册类图书与文字类图书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分属两个编辑系统,要在文字书中间镶嵌图片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直到图文结合的书籍排版软件出现,使得编辑精美的图文书成为可能,当代书籍设计也有了新的施展空间,图文关系发生变化,由原来的装饰、点缀,到作为文字的说明、补充、注释、链接,是内容的有机组成,乃至图片选择、图片质量都是出现的新问题,编辑问题与设计问题交织,复杂的图片设计编辑,复杂有序的阅读线索编织,整个成书过程就是图文关系的不断调整中进行的。美编工作不再是表面的装帧设计,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范畴。汉声注重实践,注重细节的挖掘编辑,所谓“小题大做”就是这个意思,以汉声编辑的《水八仙》与《大闸蟹》选题为例,皆非从成熟的书稿文本着手,而是由编辑深入田间地头、江河湖泊,考察采访,拍摄照片,绘制大量图表,集科学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汉声还有个特点,就是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的工作充分融合,都必须做到对选题有深入的研究,往往反复打磨,一本书的出版周期也较长,沉下心不浮躁几年出一本精品的精神值得学习,是典型的编辑设计实例。再如刘晓翔设计,获得2014年度“世界最美的书”的《2010-2012中国最美的书》一书,为三年间获奖书的合集,但细看倾注了设计师大量的心血,全书围绕体例内容做了整体的结构设计,折页装订方式特殊,运用编辑设计的手段与方法,除了原有的版权信息,还对每本图书的重量、尺寸及物像比做了记录,让读者能更深入了解原书、深度体会原书,细致的编排体现了编辑功底,这样的实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足以作为编辑学领域的研究素材,可以填补空白,依此甚至发展出设计编辑学也完全合理。
与图书文字校对细致严格的质检制度相比,对书籍设计的抽查还只是留于形式,标准过于陈旧,书籍设计发展已今非昔比,有些条条框框早不合时宜,已成为影响创新的阻力。书籍设计有其自身的科学性,不仅是简单的美丑,不仅是含糊的感觉,我们应当视粗制滥造等同于差错,就是对图书内容、对作者劳动、对资源消耗、对广大读者的不负责任。非常有必要在行政管理层面强化对于书籍设计质量的检查力度,可从每年的出版物中随机抽取,尝试由专家投票,公布最丑书籍设计榜单,从另一方面促动整个行业对于中国书籍设计的重视,提升整体水平,由此“塔尖”与“塔基”可以同时推进。
迄今为止送往莱比锡的“中国最美的书”共271部,这个数字相对于中国这13年出版物的总量,肯定是“星星之火”,但愿“中国最美的书”这枚星星之火在未来的中国出版界可以燎原!
(作者单位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