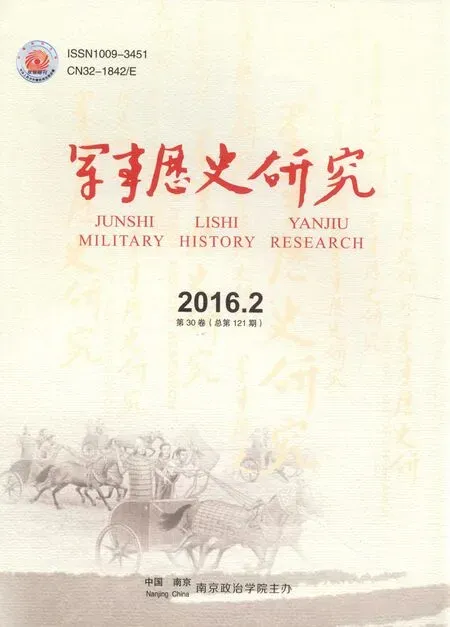记忆重构的必要与可能——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再讨论
谢迪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420)
·读书札记·
记忆重构的必要与可能
——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再讨论
谢迪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420)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的集体记忆是国际社会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作为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战,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一记忆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是由多重因素所造成的。今天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中国成为世界和平发展重要力量的进程中,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的抗战的集体记忆必须在记忆主体上进行调整,在记忆视角上进行转换,在评价标准上进行再造。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国际社会平等意识的日益增强,中外学者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为重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提供了可能性。
国际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战集体记忆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历史的形成既是社会运动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是社会主体对社会运动过程主观认知的反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全人类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之一。这种集体记忆的形成是以国际社会对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评价为起点,并在战后国际社会变迁中不断发展和演进,最终固化成以欧美为中心既定的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集体记忆。在这一集体记忆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战场之一的中国抗日战争(以下简称中国抗战),被置于一个事实边缘和价值低估的记忆定位之中。*张注洪:《国外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北京党史》1995年第5期。这显然与历史的本来面目存在一定差异。在当今新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已经有了重新建构的必要和可能。
一、他者的评判:国际社会中国抗战集体记忆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这一论断放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仍然是适用的,只不过要将阶级置换成民族或者国家而已。国际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思想。这在国际社会的历史记忆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近现代世界历史就是以欧美大国为中心的历史。这一特征在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的集体记忆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与印证。只要按照这一观点去考察中国抗战记忆的发生机制与逻辑起点,就会清晰地看到主导和影响这一记忆的国际社会背景和要素。这一记忆的最原始雏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评价,而这种评价不是中国人主导,也不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进行的。这是一种双重他者的评判:一是评判主体是他者;二是评价的视角是他者。这种评判直接决定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的最基本特征:不是中国人自己主导建构的记忆,而是他者主导的记忆。在这一记忆中,“事实上中国被忽略了,只充当一个次要的角色。”*[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6页。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是无可争辩的核心主导人物,他们关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和作用的界定,对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评价具有权威的引领作用。因此,他们的评判就直接决定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逻辑起点的方位。70余年来,中国抗战记忆可以说是在此三巨头思想的基础上扩展和上升成为美国、英国和苏联(俄罗斯)三个大国关于中国抗战的记忆,并由这三个国家弥散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发展,就成了当今国际社会(包括中国自身)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这就是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的发生机制。所以,研究中国抗战记忆的最原始形态,就必须分析这三位领导人的评价。
(一)正面评价下的隐含逻辑
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作用,欧美主要战胜国领导人在战时和战后对此都有一定的积极评价,这些对中国抗战作用的正面肯定性评价,是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记忆的亮点部分,但是总体来看,这些评价仍然低于中国抗战应有的地位。罗斯福的评价直接就是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出发的。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1945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80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实行“一边倒”外交战略,在日本向中国投降6周年的1951年9月初,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这样评价中国抗战:“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毛主席斯大林元帅互电祝贺》,《人民日报》1953年9月3日,第1版。丘吉尔对中国抗战的总体正面评价不多,但这不多的评价中,有一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如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阵地的全部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 卷(上)第1 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66 、626 页。
上述三位重要人物对中国抗战评价主要是从正面积极意义上的肯定,也是当下中国抗战研究学者用以证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地位作用经常援引的重要佐证,是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记忆中具有亮点的部分。从表面上看,这些评价都非常高,足以支撑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事实上,70多年来国际社会的历史叙事中,并没有在这一基础上建构起中国抗战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集体记忆。是不是后来的国际社会脱离三巨头的正面评价,而有意贬低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问题的真正原因还是在三巨头的评价(包括正面积极评价)上。只要对三巨头的正面评价进行认真分析,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修辞上怎么正面积极表达,但在立论视角特别是逻辑原点上,认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处于配合与边缘地位,而没有进入主导和中心地位。
罗斯福的正面评价中有两层隐含:首先,谁的记忆?记忆的主体是美国人,是美国忘不了中国抗战的作用,是从美国角度建构起来的“忘不了”。因为中国抗战对美国有利,所以美国“忘不了”,是不是蕴含这样的潜词:中国抗战如果与美国利益没有关系,只和中国自身利益有关系或者只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利益有关系,美国就“忘得了”中国的抗战?因为美国主导着战后国际社会集体记忆,美国的记忆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际社会的记忆,所以,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记忆只是美国“忘不了”的部分,美国“忘得了”的部分,就没有成为国际社会的集体记忆内容,而消失和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就是典型的他者理论的思维和表达结构。其次,记忆什么?美国“忘不了”中国“在亚洲大陆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罗斯福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抽调大量军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43页。牵制是罗斯福评价中国抗战的关键词,也是战后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记忆结构体系中的基石与坐标。中国抗战地位和作用哪怕再高,也只是牵制、配合、掩护,而不是主导和中心。美国只评价和记忆中国抗战的牵制、配合与掩护的内容,没有牵制、配合、掩护作用的中国抗战部分,哪怕是对中国自身有利的主导部分,都不会进入美国的记忆之中,当然也就进入不了国际社会的集体记忆之中。
斯大林的正面评价更值得研究,这是抽象的很高评价、具体作用的降低评价的典型代表。“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这句话的关键词就是“便利”。哪怕是大大的便利,也只是便利,中国抗战的作用就是为苏联等盟国提供“便利”,为苏联等国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条件。斯大林给准备来华的崔可夫元帅布置在中国的任务说:“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苏]崔可夫:《在华使命》,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6页。对中国抗战的定位已经清晰确立下来,这种定位在战后国际社会集体记忆中认为是合理的,连中国人自己都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评价。《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斯大林关于中国抗战评价的电报就是力证。
如果说罗斯福和斯大林的评价带有隐含的他者色彩,这种色彩包裹着一层修辞外衣的话,那么,丘吉尔对中国抗战的评价就是直接以英国为主体,以英国的利益满足程度为标准,将中国置于边缘与配合的框架下评价中国抗战:中国抗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是否牵制住日本,而有利于英国军队在西印度洋和中东地区的行动。如果中国抗战拖住日本军队,没有让日军进入西印度洋和中东地区,中国抗战就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反之,如果中国抗战没有拖住日本军队,日本军队进攻了西印度洋和中东,给英国军队造成了压力,那么,中国抗战就没有多大意义和作用。哪怕中国在其它方面打击了日本,哪怕是中国的行动对抗战胜利有促进,都是不重要的。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英国在太平洋战争前曾企图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达成妥协,以保证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当中国人请求英国不要关闭滇缅公路时,英国人一口回绝:“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能避免树敌,我们就不会去增加自己的敌人。”*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152.中国当时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英国对日寇这个助桀为虐的协定,不管以后是不是可以改变,但从当前看来,分明是在帮助日寇、迫胁中国投降的。…… 这种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慨,引起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士的愤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1949)》(第二分册 下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5—136页。英国在这种逻辑下展开的集体记忆,当然不会让中国抗战定位在应有的历史高度上。
(二)负面评价下的明确定位
如果说美、苏、英三巨头对中国抗战的正面评价只是暗含着边缘与配合的角色定位,那么,三巨头对中国抗战大量的负面评价甚至不满与指责的话语中,则更加清晰地展示出他们对中国抗战评价的价值标准与思维逻辑。这种评价不是基于中国抗战对于中国自身的意义,也不是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意义与整体价值,而只是基于边缘与配合地位的中国抗战的表现。价值主体仍然是美、苏、英三大国。这种主体和视角的评价,更加重和固化了战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边缘与配合地位的集体记忆。
首先看罗斯福对中国抗战的批评。罗斯福对中国抗战的批评相对不多,*如在史迪威问题上,在远征军问题上,罗斯福曾经使用严厉的措辞对中国进行了批评和指责。参见[英]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陆增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年,第6页;[美]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徐泽荣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15—116页。其中较为严厉的一次是1944年针对豫湘桂战役失败。这次失败引起一直对中国抗战有着正面积极认识的罗斯福的极大反感甚至愤怒。他对当时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孔祥熙直言不讳地提出质问:“我想不明白的问题,中国军队在哪里,为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国军队赶走到哪里就赶走到哪里。”*转引自王淇:《从中立到结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03页。豫湘桂战役的失败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国民政府消极的主观因素,也有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客观因素。但不管怎么样,日军在这场战役中,投入了50万的兵力,将最后一点机动兵力也投入到中国战场,强弩之末的困境已经显现。*沈永兴:《论二次大战中中国战场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4期。罗斯福的指责与批评不是立足于中国抗战局势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仍然是从美国或者盟国的主体地位出发,将中国抗战定格于边缘与配合的框架中来评价的。战争进程中的战役胜利与失败是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因为战役的失败而决定对其整体战争的评价,一个外来的主体更不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真正主体的具体战役进行评价和指责。试问,能因为敦克尔克的溃败,因为苏联红军在初期的全线溃退,甚至因为美军在珍珠港事件中的惨痛损失,就否定欧美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整体的地位和作用吗?罗斯福会不会或者敢不敢以这样的口吻去质问斯大林或者丘吉尔?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他认为英国和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体和中心,所以他们的具体战役就可以从其自身的视角去评价。而中国抗战始终只是边缘与配合,所以,配合得不好,主体和中心就可以进行负面的评价甚至是指责,哪怕这些战役的失利对中国抗战整体和长期的抗战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都不能有正面和积极的评价。
斯大林对中国抗战的负面评价分量较重,指责也是比较严厉的。斯大林对罗斯福“高看”中国抗战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一直不予认同,直接否定了罗斯福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的意向,他对罗斯福说:“无论如何,他不认为中国在战争结束时是非常强大的。”*[苏]尤·米·加列诺维奇:《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虽然二战结束之后,斯大林对中国抗战地位和作用评价有所上升,但在战争进行期间,其总体评价是比较低的。斯大林认为中国“在整个第二次大战中的作用,表现得相当或主要是消极的。”*[苏]尤·米·加列诺维奇:《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第184页。斯大林的这种评价在盟国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与丘吉尔一道,共同阻止中国抗战大国地位的确立。在开罗会议之后,拒绝中国继续参加大国领导人会议。后来在关于东方战场特别是战后国际格局的安排中,拿中国的利益进行交易,最终形成了与中国抗战代价和作用极不相称的雅尔塔体系。这种格局对于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地位与作用的评价及其历史记忆的形成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从结果倒推原因的逻辑:为什么战后中国利益得不到保证和体现,就是因为中国抗战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大英帝国的傲慢心态和欧亚战场之间矛盾及中英亚洲战场的行动分歧,丘吉尔对中国抗战的评价在三巨头中应该是最低的。虽然英国军队在西印度洋和中东战场遇到危机时,丘吉尔希望中国牵制日本军队,曾罕见地正面评价了中国军队几句。但危机过后,他对中国抗战的偏见便表现得十分明显。丘吉尔对罗斯福提高中国抗战地位的言论和行动十分不解,认为“把中国作为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12页。尖酸刻薄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曾告诉总统(罗斯福),我觉得美国舆论对中国能在全面战争中所能做出的贡献估计过高”,“把中国同英、美、俄等世界大国等同起来的说法是极不正确的”。*[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册,第607页。如果说罗斯福和斯大林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主要是基于各自国家的实质利益的话,那么,丘吉尔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则主要是基于即将没落大国对殖民地的一种拒绝与其平起平坐的傲慢与偏见。作为最早对中国进行殖民的大英帝国,看到中国领导人坐在自己对面,共同商讨战后国际战略格局,内心的失落是必然存在的。所以,他对中国的情绪有时几乎到了失态的地步:“中国的重要性将超过法国或波兰,或者将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哪怕是超过最小的,但古老而又历史悠久的盟国,如荷兰、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等——这种说法根本不屑一顾。”*[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册,第607—608页。尽管法国此时已经完全投降并帮助希特勒在欧洲、北非进攻盟国,但丘吉尔仍然认为中国没有法国重要,如果不是观念与心态,那就很难合理解释他的言论产生的原因、思维与表达逻辑了。作为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丘吉尔的这些评价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欧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是战后70年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的重要思想基础。
从以上的叙述与讨论中可以明确看出,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是他者的记忆,是以自我为中心与主体地位的欧美主要战胜国对于被其视为边缘与附属地位的中国之记忆。中国抗战客观存在的真实状况并没有完全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印象中,只是与他们自身利益有关的部分进入了他们的记忆,其它部分,则都被他们有意识、潜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过滤了。
二、主体转换与视角调整:重构中国抗战记忆的必要性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已经70周年,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仍然维持以欧美为中心的框架,停留在冷战的观念下。这种集体记忆已经越来越显现出与外在的矛盾和内在逻辑缺陷:一是客观事实的不断呈现,与原有记忆的叙事内容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差异;二是评价标准的全面与公正呼声的不断增强,使原有集体记忆中的价值判断的说服力有所下降。*赵文亮:《20 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 年第3 期。在今天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上,在世界利益关系的新格局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意识到,为了更好铭记这段历史,为人类持久和平提供记忆支持,就必须重新建构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
(一)记忆主体必须转换
影响集体记忆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记忆的主体,即谁主导了集体记忆;二是记忆的叙事,记忆中讲故事的方式与修辞;三是记忆的判断,即记忆价值结论。显然,在这三方面中,记忆的主体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主要的功能。*参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7页。怎么讲故事,如何做结论,都是由记忆主体来决定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的传统形态,其记忆主体是欧美主要战胜国,他们主导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所以,要重构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首先就是要对集体记忆的主体进行转换,将记忆建构的主导权从欧美主要战胜国的手中,转换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手中。
由于复杂的原因,70余年来,中国作为抗战的主体,却在国际社会关于抗战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不仅没有发挥主导作用,甚至连辅助作用都没有体现。中国抗战记忆的话语权基本上掌握在欧美主要战胜国的手中。这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在建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中国主体地位的表达缺失。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故事都是由欧美主要战胜国来讲的,评判的结论都是他们给出的。他们讲故事的过程中,从数量上极大压缩了中国抗战故事的数量,大量讲述的是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甚至北非战场的故事,而对于中国抗战故事则少讲、略讲甚至不讲。*这种现象在国际上公认权威的几本关于二战的历史著作中体现得较为突出。如:[英]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法]亨利·米歇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苏]A·A·格列奇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等。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著作和文章的数量非常惊人,而其中中国人著述数量的比例却非常低微。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版的英文著作多达数千部。然而,英文著作里关于二战期间中国作用的研究却少得可怜,这是不公平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中国在抗击日本侵略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的功绩不应该被尘封。”*《中国抗战功绩巨大而独特——访牛津大学历史教授拉纳·米特》,《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第3版。没有表达的数量,自己不讲故事,别人就不会讲你的故事。没有故事,就没有记忆。不仅表达的数量少,而且中国人对中国抗战的叙事,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很低,转化成为国际社会集体记忆的内容更少。这既有语言的障碍,又有欧美社会的心理障碍,无论欧美学术界还是民间社会,主观上接受中国人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的意愿都不是很强。这与近代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实际地位有一定的关联度:近代中国落后、软弱、分裂的状况,影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叙述故事、表达判断的自信心,而没有自信心,故事就讲不好,结论谈不透,别人就不接受;国际社会轻视近代中国,也不会认真聆听和理解中国人所讲的故事。正是这些多重的原因,70年来,中国国内关于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和作用的事实叙述与价值评估上虽然也有一些质量较高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国际社会中就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应。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记忆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欧美主要战胜国的手上。
其次,在强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中国主体地位的表现落后。所谓集体记忆的强化,就是记忆主体通过一系列的空间仪式和符号象征,将初步建构起来的集体记忆反复再现,不断巩固。巩固和强化记忆的最主要形式就是纪念活动,通过周期性的纪念活动,让记忆主体置身于与记忆内容相关的空间仪式之中,最大限度地接触和感觉与记忆内容相关的符号象征,多次定向重复,记忆的内容就由外部的信息转化为记忆主体的意识,沉淀为记忆主体的潜意识,渗入为记忆主体的无意识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余年来,各国特别是欧美主要战胜国对于纪念活动是高度重视的,投入了大量资金资源,周期性的重复与循环,并将纪念活动的影响推送到国际社会,成为巩固和强化国际社会关于这一战争集体记忆的重要因素。*如美国在1993年由克林顿总统签署授权,决定斥巨资在华盛顿中心地段的林肯纪念堂对面建立了二战纪念园(National World War II Memorial);参见张旗:《世界著名军事博物馆之旅系列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园National wwll Memorial》,《国际展望》2005年第6期。从现实效果来看,这些国家的策划和行动应该说是基本成功的,巩固和强化了他们建构的国际社会集体记忆。在欧洲,凡是二战重大事件,如敦克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攻占柏林、德国投降,都会举行国际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多国政要与社会代表参与,舆论媒体广泛报道。*参见:《NEW YORK TIMES》,2004.06.06.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几乎每年的5月8日卫国战争胜利日都要举行盛大的阅兵活动,参与的国际政要数量非常多。在美国,几乎每年的12月8日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太平洋战争爆发活动。*《美国隆重纪念“珍珠港事件”70周年》,《人民日报》2011年12月9日,第22版。而70余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改革开放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中国抗战纪念活动的规模、层次与内容都远远不如欧美大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意识到纪念活动在建构中国抗战记忆中的重要作用,抗战纪念活动的形式与内容都在发生一定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在抗战纪念活动国际化进程上做了很多工作,但这还是刚刚开始,对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的影响还比较微弱。
再次,关于中国抗战和二战记忆的艺术表达上,中国主体地位的声音弱小。文艺作品能够在表达与再现中强化和巩固集体记忆。70余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主要战胜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艺术表达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在国际社会的集体记忆中,实现了他们的话语权,体现了他们的主体地位和愿望。就关于世界反法西斯的电影作品来说,可以说层出不穷,从早期的《卡萨布兰卡》《桂河大桥》到近期的《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二战题材几乎成为欧美电影产业的灵感来源与票房保证。仅仅一个诺曼底登陆,就有很多部电影反复呈现。*刘庆华:《诺曼底登陆70周年祭——重观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电影评介》2014年第8期。通过先进的电影制作理念与技术,加上符合市场规律的运作机制,使得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的二战大片,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在取得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也获得不可估量的回报。*翟一南:《影像中的诺曼底登陆》,《新民周刊》2014年第22期。英国人还以其严谨理性的风格,以记录片的特有形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集体记忆进行再现与表达。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World War II)。其副标题直接点出了作品的目的:That have shaped our standing of world war II(建构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从作品的影响来看,应该说基本达到了制作者的目的。在苏联和俄罗斯,也曾推出过具有重要影响的卫国战争影视作品,如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卫国战争三部曲》等。一些中小国家,也产生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二战题材文艺作品,如南斯拉夫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均在世界电影艺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关于欧美二战的影视作品的详细介绍,参见王大骐:《影视里的二战硝烟》,《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11期。著名电影理论家马克·费罗说“电视图像在一个消费了它的社会,将充当历史文献和历史代言人。”*[法]马克·费罗:《电影和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而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视作品,无论是本身的质量还是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都无法与欧美大国相提并论。从艺术角度对国际社会集体记忆的影响,中国人讲故事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曲春景:《中国二战电影与反思二战的距离有多远》,《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资料的展示,越来越显示出了中国抗战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正如拉纳·米特教授所指出的,“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是未被讲述的二战伟大故事之一。尽管中国是首个与轴心国交战的同盟国,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相比,中国在太平洋战局中的作用未得到正确认识。”*《中国抗战功绩巨大而独特——访牛津大学历史教授拉纳·米特》,《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第3版。被还原的历史事实,被重估的历史价值,与长期形成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焦点,是集体记忆主体结构中,中国主体地位的缺失。所以,要将被扭曲的集体记忆纠正过来,首先就是要进行记忆主体结构的重构,提高中国人讲故事、做结论的数量和质量。
(二)记忆视角必须调整
如前所述,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建构的框架,是以中国抗战与欧美盟国战场的次主关系定位的,而不是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为局部和整体关系定位的。在欧美盟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记忆逻辑框架进行了置换,即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记忆框架,变成了中国抗战与欧美盟国战场的记忆框架。完成这种逻辑框架的置换之后,记忆的视角就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角,变成了欧美盟国战场的视角,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之间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变成了中国抗战与欧美盟国战场之间的外围与中心关系。在这种框架和视角下,进行事实叙述和价值评判,必然就会出现叙述的失真和评价的失衡。
正是在这一视角和框架下,国际社会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放在了德国入侵波兰的1939年,而不是中国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更不是中国开始局部抗战的1931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早有外国学者提出过倾向于以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为二战起点的观点。如费正清指出:“日本于1937年7月7日首先在北平附近,8月8日在上海发动的全面侵略实际上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见[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第491页;国内学者对此也有较多的研究和讨论,如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时间在欧洲是1945年5月8日,在亚洲是1945年8月15日,而不是日本向中国政府正式投降的1945年9月3日。如果将中国抗战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就应视作整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局部的结束,整体也应视作结束。事实是,早在欧战爆发之前,中国人民在非常孤立的国际环境下,在美日、苏德进行秘密谈判、签订和平条约的形势下,在欧美大国策动东方慕尼黑的艰难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抗战。但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取得的综合效果,都不能进入集体记忆之中,因为这些行动、牺牲和效果与欧美大国没有关系。费正清写道:“到1941年12月8日为止的头四年里,自由中国孤军奋战,而孤立主义的美国直到1941年中期仍带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负罪感向日本战争机器出售必不可少的石油和钢铁。”*[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 第491页。从历史的客观事实来看,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孤立抗战,不仅非常难能可贵,而且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之前中国孤独艰苦抗战,后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进程,都会发生极大的改变。无论是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还是中东战场,这些战场也都只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组成部分,同中国抗战一样,共同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整体,不存在哪个战场是中心,那个战场是外围与边缘的问题。要说中心,包括中国抗战在内的亚洲大陆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和中东北非战场都是整体的多元中心之一。
在欧美中心与中国外围的视角和框架下,中国抗战就被定位于牵制日军与配合盟国作战的功能上,而且不是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体需要的牵制和配合,只是对欧美盟国的配合。在1939年之前,中国的抗战是没有功能的,因为欧美盟国还没有参战,中国抗战没有配合的中心,所以中国的抗战在国际社会的记忆中是无需存在的。这种思维模式在战争进程中就已经形成,在后来的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不断强化。也就是在这一逻辑框架下,中国抗战的地位在欧美盟国心目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由低到高、然后再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在苏德战争和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欧美盟国战场的压力非常之大,希望中国配合与牵制的迫切性非常之高,只要中国战场一放松,处在气势峰值时期的日军北上或南下,对已经处在非常危急时刻的盟国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甚至中东北非战场都是致命的。中国的抗战确实也达到盟国这一期望,就像罗斯福对他儿子所说的一番话:“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美]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上海: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第49页。所以,以开罗会议为标志,中国被给予了较高的待遇,甚至列入四大国的行列,中国领导人被邀请与三巨头平起平坐开会。然而,到了1944年,在中国抗战牵制和配合下,欧美盟国逐渐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取得主动权,中国抗战的牵制和配合作用下降了。所以,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整体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下降了,中国再也不是四大国了,一些重要的甚至直接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会议,也不需要中国人参加了,从德黑兰会议到波茨坦会议,再也见不到中国人的踪影。特别是在决定战后利益分配的雅尔塔会议上,针对中国问题竟然重演了第一次世界结束后巴黎和会的一幕。欧美主要战胜国的思维逻辑及其行动,对于战后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记忆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70余年后的今天,欧美主要战胜国的这种思维逻辑与行动及其所导致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在事实上的不客观性,在结论上的不公正性,已经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正如著名二战史专家、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方德万所指出的:“很多欧美学者认为中国的抗战无足轻重,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切。对这个国家来说,没有一场战争比这场战争更重要。”*《〈剑桥战争史〉主编方德万谈中国抗战》,《南方周末》2015年4月10日,第6版。所以,今天要重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就必须从叙事和评价的视角上进行调整,真正从中国的抗战战场的视角,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整体关系的视角,而不是从中国抗战与欧美大国之间的视角,来建构和巩固集体记忆。
(三)记忆标准必须再造
传统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的事实失真与评价扭曲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评价标准的错位。这种错位一直以来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以欧美主要战胜国的利益而不是中国本身的利益对抗战中的政治、军事行动进行评价;二是用双重标准看待中国抗战,并在双重标准下建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
笔者以为,必须以中国综合利益为评价的最主要标准。中国抗战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整体战争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构成要素,与欧美盟国战场相比,这种时空的独立性显得更为明显。从时间上说,欧美盟国还没有参战的时候,中国就开始长达8年(1931—1939年)的单独抗战。从空间上说,在中国本土战场,基本上是中国军队在进行军事行动,除了盟国的少量军事(主要是空中力量)的支持外*关于外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从现有研究成果看,远远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大。拉纳. 米特说:“美国援助中国,固然对提升中国的军事装备水平很重要,但中国只得到了美国所有对外援助的1%到1.5%, 也就是说,99%的美国战时对外援助都流向了其他国家。中国几乎全凭自己的力量肩负起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任。”《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第3版。,所有的战役都是中国军队单独完成的。既然是相对独立的战场,那么,它就有自身军事发展规律。中国政府和军队也必须遵照这种规律来进行战场研判,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去采取行动。因此,对于中国抗战评价,必须从中国战场自身的成败得失为主,而不是以对其他战场牵制配合的成功与否为主要标准。只有中国战场自身能够维持并反败为胜,才是最为有意义的,也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发挥对盟国的配合与协同作用。即如苏德战争,苏联必须首先考虑本身战场的平衡与胜利,然后才能考虑如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军的配合。斯大林肯定不会首先考虑如何与中国抗战配合而制定苏德战场的战略战术。既然这样,也就不能要求中国抗战以配合欧美盟国战场作为第一要务。所以,也就不能以对欧美盟国配合与牵制的好坏来评价中国的抗战。中国早就制定了持久抗战和游击战的战略:在1938年之后,直至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改变之前,中国一般不主动与日本进行正面大规模的会战。因为中国已经研判到,只要中国持久地与日本消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中国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的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0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已经确立了两个基本理念:一是中国抗战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二是要取得战争胜利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在长期奋斗中改变中日力量的对比。如果按照这一思维逻辑和评价标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军事评价就必须重构。就拿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中印象很差的豫湘桂战役来说,中国政府当时从中国抗战所处的时空条件来说,采取的战略战术未必就是错误的,其结果从长远来看,未必就完全是负面的。当然,从欧美盟国来说,它是负面的,因为这加大了他们的战场压力。那么反过来问,为了减轻他们的战场压力,中国是不是就应该拿着自己准备与日本持久对抗的微弱军力,与日本疯狂冲向太平洋的军队进行最后一搏呢?中共对中国抗战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与欧美盟国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一直把独立的持久抗战作为最后胜利的最主要路径、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协同推进作为抗战胜利的外部条件、把与盟国的良好配合作为辅助手段。正因为如此,中共军队在持久战的总体原则下,不会在具体战役上与对手拚消耗。百团大战的实施与结局证明了这种指导思想的合理性。对百团大战的得失,费正清的研究结论是:“为了对抗日军的压力,中共军事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彭德怀发动了一次从1940年8月开始的号称‘百团大战’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整个华北铁路线不断被切断,碉堡群被粉碎,……中共显然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是后来日军实行武力报复”,因此对于军事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来说,“它是一次极大的灾难”。*[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然而,70余年来,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记忆都是以欧美盟国当时的军事利益得失为评价标准。在今天,必然要求将这种标准转换为中国抗战本身的得失标准,完成了这种转换,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必然也会发生根本的转变。
三、尘埃落定见真相:记忆重构的可能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余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结构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和平发展重要力量,海内外华人日益团结,原有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不仅存在重新建构的必要性,而且具备了重新建构的条件与环境,有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一)主体意识的觉醒:记忆主体重构的可能
今天,要重新建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最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在自身利益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角度,去叙述抗战这段历史,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从自身与人类共同利益的综合角度去评判好这一历史进程的成败得失。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今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自身的实际能力与主观素质,已经能够承担起重构自己的历史记忆,并向国际社会推介和宣传这种记忆的时代重任,近年来中国所采取的一些实际行动及其效果,已经证明这种可能性逐渐变成现实。
首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增强,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抗战集体记忆的主体提供最根本的条件。习近平指出:“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1版。如前所述,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之所以成为他者的记忆,中国人在记忆中之所以成为起相对映衬作用的他者,除了外部因素外,中国自身的话语表达能力的限制,对此有着重要的影响。1840年以后,中国长期处于被侵略、被压迫的地位,在抗战之前的大部分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降到了历史的谷底,感到一切不如人,自卑心理非常严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缺乏自己的话语,不敢讲因而也就讲不好自己的故事,更不能对自己的故事作公正的评价。既然自己不能讲,讲不好自己的故事,那么,别人讲的故事就成为主体内容,别人的结论就是历史的判定。如今,中国民族意识不断觉醒,自身能力日益增强,中国讲故事的主观积极性和客观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习近平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版。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民众采取的一些重大行动及其国际影响,证明了在民族自信心提升的前提下,建构并推介关于中国抗战记忆的极大可能性。例如,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了9月3日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在北京卢沟桥、南京建立了两个国家级的纪念馆,其他类型和层次的抗战纪念与记忆标志也正在建设之中。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
其次,国际社会冷战思维陷入困境,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大国中心主义意识弱化,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关于抗战历史记忆的建构主体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冷战格局瓦解,冷战思维下的大国中心主义意识呈下降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出现了一批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欧美大国利益立场上的政治家和学者,重新叙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抗战事实,评判中国抗战的地位。这些积极因素的出现,为国际社会重构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提供了外部可能,在推动中国人讲好自身的故事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时间洗砺现真形:记忆内容重构的可能
集体记忆的形成是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主观建构,其根本的前提还是在于历史客观事实。中国抗战的时空范围相当广泛,过程相当复杂,材料相当丰富,考察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集体记忆的形成与演进,我们可以找到其故事失真和结论失衡的重要原因。欧美大国仅仅从外部获得的一些零碎的历史材料,开始叙述中国抗战的故事,评价中国抗战的绩效,失真和失衡也就在所难免。正如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研究室主任尼基福罗夫所说,“在二战问题上,西方长期低估甚至忽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作用,忽视中国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和3500万军民的伤亡。”*《中国抗战功绩不可磨灭——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人民日报 》2015年5月9日,第3版。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余年后的今天,历史尘埃已经落定,很多反映当时客观事实的材料及其载体与介质,都逐渐浮现出来,一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背景下,中国人民抗战的客观画面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这些真实而客观的历史故事和画面,为国际社会重构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支撑。近年来,中国政府、学界、民间及海外华人都在这方面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海外华人中,也有一批学者搜集、整理和公布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数据和材料,如美籍华人学者张纯如关于日本在华暴行的数据统计和个案再现,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陈晓:《张纯如:书写数字背后“人”的历史》,《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46期。海外华人还成立了抗战历史材料的搜集与展陈的机构。国际社会也在这一进程中做了积极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大批关于美国政府、军方与中国抗战相关的档案材料正在整理研究之中*唐伯友,任竞:《美国国会图书馆抗战文献调查及其特点介绍》,《四川图书馆学报》2013年第4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也正在整理一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抗战史料*唐伯友:《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分类研究》,《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并开放了一批非常具有价值的有关抗战的档案。
(三)学术研究得结论:记忆形态重构的可能
不断呈现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和材料,也会给集体记忆的形成和演进带来新问题,即在这些海量的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和失真的事实和材料面前,怎样才能最大限度透过材料和事实所表达的信息,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历史材料,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评判这些事实与材料,从而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作出正确而公允的结论。除了亲身经历这一段历史的人自身体验的再现和感悟之外,大部分后来人的历史记忆需要基于学术研究上的各种成果的传播和强化。也就是说,后来人们的集体记忆是建立在教育、传播的基础之上的,而教育与传播历史记忆应以学术研究为前提。因此,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育传播内容,对记忆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今天,大量的客观反映抗战历史本来面目的研究成果已经问世,这些成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为国际社会重构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中国抗战及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研究,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研究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979—2008 年的30 年间大陆共出版二战图书1969 种,是1950—1978 年的29 年间出版总数的7.3 倍。*崔美:《建国以来中国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定量分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2005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论文就多达近600篇。*苏志明:《我国抗日战争研究现状分析——以2005-2014年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收录的核心或CSSCI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为依据》,《湘潮》2015年第12期。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如集中了中国大陆权威学者共同完成的九卷本《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中国与世界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被认为“代表了我国史学界关于二战时期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平。”*彭训厚:《一部把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的二战史巨著》,《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国际学术界也比较关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抗战问题,近年来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关于中国抗战问题的学术讨论甚至观点争论也比较活跃。除了传统的一些研究阵地如美国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之外,还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团队和学术机构。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传播,继续在国际学界发挥作用的同时,一批新的学者正在以他们的学术成果和研究能力,在国际学界关于中国抗战问题研究上,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国际学术界除了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继续拓展外,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学术导向与价值标准的调整。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及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的固有的观念和意识有所淡化,重新叙述中国抗战的历史事实和评估中国抗战的历史价值,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一批学者在这种共识的主导下,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因而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如拉纳·米特教授所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就是国际学术界以新的学术理念与价值导向研究中国抗战的力作,在国际学术界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赢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多家著名媒体的盛赞。*董文墨:《一部西方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力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党史博彩》2015年第1期。再如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方德万所著《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 1925—1945》,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近年来欧美学界涌现出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光新伟、刘本森、周进、乔克:《从东方战场寻找答案——中外学者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新进展、新观点》,《北京日报》2015年4月13日,第4版。类似这种新观念和新导向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随着这些成果的传播,必将对国际社会传统的关于中国抗战的认识和评价产生改变和转化作用,从而为国际社会重构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提供较大的可能性。
总之,70多年来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是建立在一种失衡和扭曲的中国观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一种不公正的集体记忆。今天已有学者看到这一问题的实质:“问题在于中国与西方透过几乎完全不同的镜头看待中国的角色。对西方同盟来说,中国是一个乞求者,一个双膝跪地、遭受重创的国家,静候英美国家将它从日本的手下拯救出来。而在蒋介石和许多中国人眼里,他们是轴心国的头号也是最为始终如一的对手。尽管有无数次从冲突中撤离的机会,中国却在外界援助似乎遥遥无期之时选择继续战斗,现在它被作为平等力量来对待,当之无愧。”*Rana Mitter,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1937—1945,pp.243—244.随着历史脚步的不断前行,国际社会关于重新建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集体记忆的必要性越来越清晰,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评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越来越明显。当然,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受到多重客观环境与主观认知因素的影响。在此进程中,中国学术界与理论工作者,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应该以积极的主体意识,严谨的学术作风,最大限度地还原再现中国抗战的历史过程,讲好中国抗战的历史故事,做好中国抗战的历史评判,并通过恰当的话语工具与表达路径,将中国人自己叙述的真实故事、研判的价值结论,传播和推送到国际社会之中去,为国际社会重构关于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
(责任编辑仲华)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Memory Reconstruction ——On the Place and Role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in the World War against Fascism
XieDibin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 major event in human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a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s Invasion was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War against Fascism, but its rightful place and role in this memory has not been properly represented.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factors. However, in today’s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hen China is becoming a major force for world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llective memory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has to be adjusted, the memory perspective should be shifted, and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must be modified. The Chinese people’s awaken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s growing awareness of national equality, plus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increasingly in-depth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and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are now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construct the collective memory concerning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rld War II;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ollective memory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44)
谢迪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K265; E296
A
1009-3451(2016)02-009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