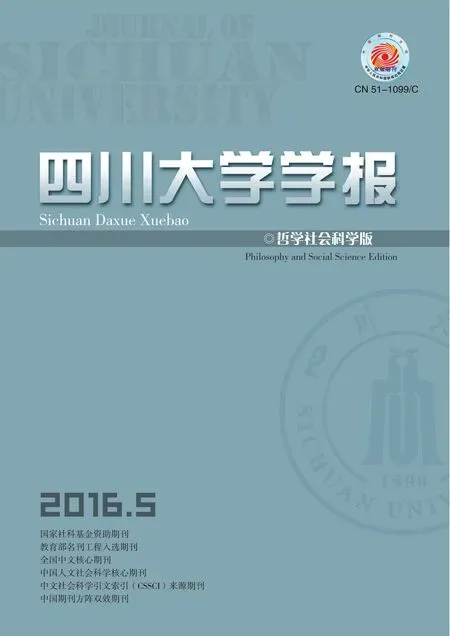“进乎技矣”:莱州寒同山道教石窟之建造及生态干预保护技术
姜 生,王 茹
§道教与中国文化研究§
“进乎技矣”:莱州寒同山道教石窟之建造及生态干预保护技术
姜生,王茹
以宋德方为代表的13世纪早期全真道石窟建筑开凿与保护技术探索实践群体,在莱州寒同山不仅开凿了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道教石窟群,而且在石窟山崖顶部留下了珍贵的古建保护技术遗产,体现了“道法自然”思想的实践结构,代表着道教建筑保护技术的最高水准,诚可谓“进乎技矣”。石窟群连同其依托的自然山体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保其坚固永久,其科技成就可总结为由“清、剔、破、通”等一系列具体方法构成的(一劳永逸式的、“自动化”的)“生态干预式石窟建筑自然保护技术”,且其系统至今正常运行,泽被千年。该石窟为研究道教的石窟建筑保护技术提供了典型例证,亦可为再现道教建筑及其保护方法之“法自然”思想提供新证。全真道的生态干预式石窟保护技术对于某些洞穴建筑遗产的保护以及当代建筑生态设计仍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其所蕴含“基于生态系统观念的科学技术”思想更与都江堰无异,而堪媲美焉。
道教建筑;全真道石窟;寒同山神仙洞;生态干预;古建保护技术
洞穴是最重要的传统道教建筑类型。古来道人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了道教特有的思想和实践,依以择山、开凿和保护洞窟,其中呈现的某些道门特有技术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全真七子丘处机、刘长生之弟子披云真人宋德方在山东莱州寒同山开凿的“神山长生万寿宫”全真道石窟群,即莱州神仙洞石窟群,便是一例。寒同山石窟群作为“道之建筑”,实乃“进乎技”而“几于道”而揭示“建筑之道”的珍贵科技遗产。
该石窟群坐落于莱州城东南方约8公里的柞村镇大台头村北一片弧形群山之抱,主峰海拔337米,北依大基山,西接云峰山,青龙白虎俱备。弧形口外南面,为一片常年积水的谷地(现有水库),其选址可谓典型的负阴而抱阳的传统风水宝地,且有青龙压白虎之势。该石窟群为全真道祖王重阳(1113—1170年)指点,出身莱州的弟子刘长生(1147—1203年)、宋德方(1183—1247年)师徒及其后继者开凿,是现存规模最为庞大的北方全真道石窟群。该石窟群无论在选址还是保护技术等方面,都体现了道教的“自然”思想。
莱州神仙洞石窟道场世代有王姓道士传承守护,祭祀不辍。每及三月三朝山日,八方善众蜂拥寒同山,虔奉香火,承其恩泽。
在连续多年对山东道教碑刻、遗迹和古建野外资料的调查收集中,作者与课题组成员数次踏访寒同山,收集研究石窟所存全真道史料,发现并提取了石窟群所在山崖顶部不为人知的一些技术信息。兹就初步研究结果报告如次。
一、神仙洞各石窟的厘定及开凿时间问题
寒同山神仙洞石窟群开凿于何时?目前的研究,多依山下公路边现存至元27年(1290年)所立元代石碑。碑阳题“神山无量洞天长生万寿宫碑”,碑阴题“本宫宗派之图”。据拓片及相关文献资料,综合识得碑文有关山上石窟开凿故事,内云:
莱城之南十里许,其山崛然而起,澄心首于东,塔峰角于西,大泽翼于南,浮游背于北,丹井洗手,云川濯足,高哉魏哉,赑屃硉矹,虽猿狖便捷,不可得而攀缘也。
其初,则缘于王重阳一日携弟子游历至此,指画未来。王重阳对弟子们说:“此乃无量洞天,有俟兴者”,并收刘长生(刘处玄)为弟子。不久师徒一同西游,后王重阳羽化。诸弟子为之安葬终南祖庭并守孝三年。其后,
明昌丙申岁,*按:丙申为丙辰(1196年)之误;明昌年号共使用7年(1190—1196年),而无丙申。长生自洛阳归,筑室于下,方开此山,为有司所遏,弗果所欲。谓披云曰:“此山外坚内虚,不为难事,留与后人结缘。开此山日,当与治城相际。”继而归真。逮至金季失鹿,大元开元壬寅(1242年)间,金紫光禄大夫王公,缮治莱城,披云感叹往言,以为果然。自太原西龙山昊天观、终南山重阳宫二处,将领徒众元至全、曲志全、石志温等三十余人来继其绪。首试所指之地,若合符矣。王公仍即押公据,以山前侧佗一带山间荒地,悉付本宫,裨助缘事。草创之端,众以劳筋苦骨,靡日费月,烟火肚肠,未能涤荡,意欲他适,离数十步,返首观望,彩云晻霭,神光炜煌,长生现其间。众相悔骇,幡然来复。既而五丁刻石,精卫衔木,铲凿之声,聒动天地。迨于十载,始毕乃功。……嗣教祁志诚以洞天事奏闻上皇帝,诏旨嘉其功,赐洞名曰“神山万寿宫”,追赠披云为“玄通弘教披云真人”。
从中可知,在寒同山,刘长生、宋德方师徒及其后续弟子前赴后继,积功十载乃竟其功。关于所开洞窟,碑文记述:

今考其迹,石窟群乃凿于一处相对独立之山崖,山之阳共6窟,坐北朝南,列上下二层,上层4窟,下层2窟,崖顶、周围、后坡俱为光秃裸岩。从下层所在平台计算,该山体相对高度约30米(见图1*本文图均属作者。所有图片均附于本刊封三前二页。)。
光绪19年(1893年)《掖县全志》记载,寒同山“俗名神山,有洞七,石像四十有九。山阴有姑洞,亦石像,元时皇姑学道之所。”现存雕像37尊,皆以莱州特有雪花白大理石雕造。
复依碑文及有关史料,可对6座洞窟之历史序列、各洞所祀神尊及有关历史信息整理如次(图2):
(1)三清洞:该窟体量最大,进深约7.4米,宽约5.8米。洞顶深浮雕二龙戏珠于云气中(图3上),天宫之象。主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为全真道所继承道门古来所奉神尊。
(2)五祖六真洞:按全真道尊奉王玄甫(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全真五祖,世谓“北五祖”。
山下元碑提到神仙洞所祀“五祖”和“六真”,所指为何,需要厘清。碑文在七洞名称中特别提到有供奉刘长生,如此则“六真洞”里似不应包括刘长生;然而4号窟额有题“长□(春)洞”,表明丘处机(1148—1227年)有独立的洞窟供奉。虑丘祖生前教门内外地位崇高(成吉思汗尊称其“神仙”)、西游万里跋涉之苦及披云事从至终之情,此窟为祀长春真人卧像应属实;乾隆《掖县志》收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庭芳诗“石洞春常在,仙真眠曲兮”句下注:“洞有丘长春卧石像。”*张思勉修,于始瞻纂:《掖县志》卷八“艺文”,乾隆二十三年刊本。据此,则实际上“六真洞”所祀恰应包括刘长生,而不含丘祖。推测山下碑文所言或源于宋德方凿窟特祀其师之类孝行传说,而刘长生、丘长春皆先后为其师;今观长春洞额中间一字笔画紊乱,似春似生,或即后人据传说干扰所致。同时,此处“五祖”乃指包括王重阳在内的全真道“北五祖”,因此神仙洞6个窟中,王重阳独祀一窟*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以《陕西通志》“三曰卧龙龛,内卧像一尊,传为披云子卧化之所”的记载为误传,认为龙山第3窟卧像“应为全真教主王重阳可能比较合情理”,然无据。根据神仙洞4号窟额题“长春洞”的情况,可判断龙山3号窟卧像亦当为长春真人丘处机。之猜无从成立;“灵官”亦未宜推测为“灵宫”。*景安宁:《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8页。户县祖庵镇重阳成道宫元代《终南山圆明真人李练师道行碑》记当时李志源(1176—1246年)主持该观亦建有“灵官堂”等五堂。需要说明的是,灵官系道门最为崇奉的护法神尊,镇守宫观;灵官之设属道教宫观传统配置。
关于“六真”问题尚需澄清。按早期全真道“七真”之称形成相当早,唯其构成或有不同。Pierre Marsone和Louis Komjathy等人的研究表明,就目前已知资料,1214年全真道碑刻中首见包括王重阳但不含孙不二的“七真”之称,1219年全真道碑文中始见包括孙不二的“七真”之称,但1271年以前“七真”所指尚有摇摆不定,其后则趋于稳定。*Pierre Marsone, “Account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Quanzhen Movement: A Hagiographic Treatment of History,”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Vol.29, 2001, pp.95-110. Louis Komjathy, Cultivating Perfection: Mysticism and Self-transformation in Early Quanzhen Daoism, Leiden: Brill, 2007, pp.48-49. Also see Loius Komjathy, The Way of Complete Perfection: A Quanzhen Daoist Anth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pp.217-224.
由上可见,神仙洞山下碑文中的“六真”非指全真道早期曾有之“六真”名称*全真道史上本有“六真”概念,是由后来所谓“七真”之中不含孙不二的六位王重阳弟子构成。(雍正)《河南通志》卷50寺观:“六真观,在修武县城北二十里六真山,世传‘六真’邱、刘、谭、王、郝、马讲道之所。唐天成间创建,明洪武间修置道会司于其内。”王士俊修:《河南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或者说,此六真非彼六真——而是由于神仙洞道场将“七真”(马钰、谭处端、刘长生、丘处机、王玉阳、郝大通、孙不二)之中有特殊政治地位的长春真人拆出单独供奉,遂将其余“六真”与五祖共一洞而祀。同为宋德方主持开凿的太原龙山石窟,第7窟的主室(后室)“玄门列祖洞”则奉祀七真,*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第39-45页。堪为之证。
(3)虚皇洞:此洞宏大幽深,洞顶深浮雕一龙翔于云气中,天宫之象。洞中大理石雕像11尊,各具神态。此洞之开凿时间,下文将予讨论。
(4)长春洞:此洞体量虽然不大,但其内配置最为特别,缘其与洞内北面石壁连体凿成一尊着衣、戴冠、覆被的全身卧睡石像(图3下),为六窟之中仅存的一尊完整原始雕像。
(5)灵官洞:为道教宫观道场之典型配置,按传统应系供奉宫观保护神王灵官。
(6)披云洞:此洞最小,应为奉祀主持凿洞的披云真人而设。
(7)女仙洞:即所谓皇姑洞,指有道姑背景之洞窟;在六窟所在山崖的阴面。
洞窟的竣工时间,有些尚可考知。三清洞内石壁摩崖题刻较多,东壁有“本州冶坊会首朱守贯同妻汤妙清,管镌打此洞人衣粮了毕,乞保合家清洁如意者”(摩刻区域高约0.52米、宽约0.36米),顶部有“宣差莱登州官民长官金紫光禄大夫山东淮南总管都元帅神山洞功德主王”(摩刻区域长约3.09米、宽约0.19米)、“时岁次丁未(1247年)仲夏工毕”(摩刻区域长约1.28米、宽约0.16米),应指1247年夏完成三清洞之开凿(该年宋德方飞升)。五祖洞内壁顶部有摩崖“岁次庚戌(1250年)五月朔,神山洞功德主,奉国上将军元帅左监军定海军同知节度使兼莱州管内观察使高”(摩刻区域长约3.24米、宽约0.16米),表明最迟在1250年农历五月已完成五祖洞之开凿。
复按蒙古乃马真后四年(乙巳即1245年)正月给付披云真人之圣旨:“今者幸有披云真人糺领道众,虔心开凿仙洞,创修三清五真圣像,中间所费功力甚大……”*《神仙洞给付碑》。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84页。陈垣注:在掖县。所谓“五真”即“五祖”。*有关讨论见景安宁:《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第279页。细观圣旨内容,可知其时已开三清、五祖二洞,但并未表明是否已完工,——摩崖题刻显示三清洞1247年乃竣工。这应是寒同山开凿较早的两个洞窟。
按上引碑文说法:明昌丙申(辰)岁即1196年,刘长生返回莱州,试图凿窟而受阻。然而需要特别注意且令人困惑的一处摩崖,见于三清洞门内南壁,其文曰:“明昌甲寅(1194年)九月晦日,继游者广饶程孝达□山□弟”(摩刻区域高约0.8米、宽约0.28米~0.4米)。这表明,最迟至1194年即刘长生返回莱州之前2年,三清洞事实上已处于开凿状态,唯其可能尚未完工,乃有广饶士人游观留题而去。
据此判断,神仙洞石窟群的初始期,尚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史:即,其开凿应在1194年以前已经开始;1196年刘长生因再启凿洞而受阻(或与明昌元年即1190年金章宗禁罢全真道有关);时隔46年后的1242年,其弟子宋德方乃始其大规模开凿,数年一窟,师徒相继,十载乃成。
这里不免一问:宋德方何以46年后方继其师遗愿重启开凿?厘其史迹,刘长生羽化后,宋德方改事全真领袖丘处机。1220年丘处机受成吉思汗诏请西行,宋德方在随行18弟子之列,归则随师驻燕京长春宫任教门提点。丘处机羽化后,宋德方往山西平阳玄都观主持刊刻《玄都道藏》,继而率弟子秦志安、李志全在太原龙山开凿全真道石窟群,龙山9窟之中7窟为宋德方师徒于元太宗六年至十一年(1234—1239年)间主持开凿。*相关研究见张明远:《太原龙山道教石窟艺术研究》,第86、98-103页。其后不久,宋德方携众转往其故里莱州重启开凿之事。
从1194年之前始开三清洞,到1290年山下大碑之撰作,前后百年,神仙洞石窟群的开凿史显然并未得到准确记录、清理和描述,刘长生初期启动开凿的历史已被遗忘,而碑文作者并未身临其境仔细了解石窟群各窟所祀及具体开凿历史,背景资料的提供者亦未能认真核证,遂至山下碑文信息混乱,与山上摩崖所记不符。加之寒同山去莱城较远,当年三清洞初启开凿的实际情况及先期进展,恐亦不传,遂致窟群之功悉归披云。
石窟群东侧山坡上有古真武殿遗迹(图4);复其东另有古道观遗址,尚存明清重修道观碑记。
二、石窟崖顶生态干预保护技术之发现及其构成分析
在神仙洞所处的弧形连绵群山中,从南面山下远远望去可以发现,只有石窟群所在的一片山崖上,山骨整体裸露,没有植被,犹如光鲜的童子头独现于绿色母体怀抱,特征突出,非常引人注目(图5)。何独此山崖头无植被?
经过对山崖的仔细观察,以及文化遗存的搜寻,作者在神仙洞石窟崖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科技秘密:以宋德方为代表的早期全真道技术群体,在崖顶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石窟建筑保护技术遗产,在建筑领域,其科学价值至今不失其“科学性”和“先进性”。
莱州地处山东半岛西北部,属胶东丘陵带,地势东南高、西北低,西临渤海莱州湾。据今官方数据,其年均降水量809毫米(2001年甚至达905毫米*李振兰等:《莱州市近40年降水变化特征分析》,《现代农业科技》2016年第2期。),年均气温12.5℃,四季分明,属北温带东亚季风区大陆性气候。据当地人士介绍及作者感受,此处光照强烈,昼夜、雨阳温差大,多大雨、大雪、大风。在这种自然环境下,要利用天然山崖——尤其是寒同山夹杂石英的砂砾岩质——开凿洞窟建筑,必须考虑如何应对自然风化和草木生长带来的不断扩张的生物侵蚀、如何实现长期有效保护这一难题。宋德方出身莱州,了解当地气候条件,有丰富的山石知识和高超的技术保障,其技术设计显然已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威胁问题。
神仙洞所在山崖的“光头”现象,恰为其证,也是宋德方群体开凿全真道石窟群的一大特点:将石窟群和其所在的小山体作为一个整体,同群山独立出来,或者说将整个小山体作为一栋建筑来处理它同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
仔细研究其团队治理、保护崖顶之技术成就,可以发现,他们主要对崖顶实施了“清、剔、破、通”四种技术,同时因应和利用(而非抗拒)风、雨等自然力量,来保证其坚固永久。其技术构成主要体现为(参看图6):
(1)“清”。首先须清除山崖表面所有林木植被,以及千万年风化和树木、杂草等生物植被枯荣形成的大量泥土,目的是去除一切能够涵养水分、生长植被的条件,变其生态,令山崖彻底“露骨”。关于山体、山骨,古来道教积累了非常深刻而丰富的地学成果。如南宋道士陈田夫撰《南岳总胜集》卷中所收西晋时期南岳衡岳观道士尹道全的传记,保存有一段很珍贵的道教山地学资料:“一者五岳山符……。二者五岳山蹠,神仙倒景,俯视山川之蹠,写其曲折蟠薄在地之势也。三者五岳山形,取其峰峦、洞室之所在,神芝、灵草之所生,高下丈尺等级之数,东西南北里舍之限也。四者五岳山骨,取其骨体之所像,枝干之所分,上法星文,下主人事之所起也。五者五岳山水穴贯(窦)*引者按:“貫”(贯)为“竇”(窦)误。(元)脱脱等《宋史》卷205“艺文志”著录的神仙类著作,有“《山水穴窦图》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02页),即是此类著作。而郑樵《通志》卷72,图谱略第1“记有”部分著录的道家《山水穴实图》(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39页)及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10“道家类著录”:“《山水穴实图》一卷”(长沙: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1939年,第306页),其中“實”(实)字皆“竇”(窦)字之误。有关研究见姜生:《东岳真形图的地图学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之图,取其泉液之所出,金宝之所藏,地脉之所通,而为之图也。”*陈田夫撰:《南岳总胜集》卷中尹道全传,阮元《宛委别藏》抄明影宋本。《道藏》本无此内容。其中后四条都是重要的道教山地知识。此亦证明,古道人并非如世人想象的唯擅堪舆,其所握地学成就往往不为人知。
(2)“剔”。接着,整个山头上包括大小石块和风化层在内的所有不坚固、可涵水的附着物,悉为剔除,山骨被彻底剔净清洗暴露出来。并且其山崖各处均被打磨光滑、玲珑可握。
(3)“破”。进而,大雨之后登顶观察,可看出山上所有能够容纳、储蓄土壤和水分的盆状凼坑,然后至少从两个方向上凿破所有这类凹坑,并打磨光滑。将这些盆状凼坑凿破、打磨改造成为开放型的目的,首先是使这些凹坑无法蓄水,其次是使坑内可能积存的土壤,以及通过风雨等因素传播过来的树木、植物种子,能够快速流失,无法驻留。在崖顶现场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多处较大的凼坑——多为历史上树木生长侵蚀而成——均被凿破,形成外流之势。
(4)“通”。基于对山体上水流的观察,在山顶、山腰、山跖各处开凿出系列水道,令山表水流有所去、有所循,达到水畅其流且有所向之目的。
在顶部东侧一条较深的水道内,在磨治光滑的槽底,我们还发现了一处“山庵”二字题刻(摩刻区域约长0.54米、宽0.32米),亦为人工开凿水道之证(图7)。
神仙洞崖顶的这项技术遗存,至今未被发现,盖其水槽虽深,而崖顶到处凹凸起伏、磨治甚工,水槽只是略显细致而已,且槽内石色在强光之下与周边无异,故难为人所感知。作者也是在一次仔细观察山表形态过程中,兀然旁及,广而看出整个崖顶所凿多条水道。
开凿水道的目的之一是分水,把原本任意流动(甚至产生激扬效果)的水流,通过水道,引导形成若干股水流,最终按照水槽引导的方向流向石窟分布区域的山体两侧。这样一来,不仅使山上来水对下面平台的冲击势力大为减弱,而且使六大石窟及其所在平台上的修道生活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得以体面地进行,洞窟外设厦檐亦可避免朽坏。从接近各洞口平台的山体上水槽的导流趋向,可为证明(实测结果见图8)。
略为分析即可看出,开凿这些水道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使山体上汇集的雨水形成若干股冲击流,使每次较大的雨水过后,山体上各处盆状凹坑内所积存的土和草木种子,均被冲洗带走,从而保持了山体的无植被无土壤状态。
而去除土壤和植被的一个重要目的,则是避免土壤和植被长期生长的生物作用和蓄水作用使山体逐渐崩裂甚至构成滑坡。因为此类山石,虽易于开凿,却也比较脆弱,易于风化,加之生物作用,岁月积久,难免自然毁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宋德方和他的开凿团队,为整个山体设计实施了这种基于生态干预的自动清理和预防性保护措施。于是,对于石窟保护来说本属威胁因素的大风大雨,在这里恰恰被转化利用为清除一切土壤和种籽的自然力量,且自然运行,不假人工。此般神思,唯有道者能之,不可谓不妙矣!
以自然之力自动清除崖顶,人所要做的所剩无几,只需偶尔登顶查看、把握山表情况。这一点也有文化遗存可证:考察中作者发现,山体上多处可见一组组明显为人工开凿、仅容一足的L形踏脚槽(图9),即是为道士登顶查看山体情况而设计。
所有这些技术措施的目的,都指向石窟建筑的保护及其寿命之延长。其四种工序构成的保护方法,可谓全真道在生态建筑设计方面的独有特色。课题组成员专程考查发现,这种“山庵”开凿和保护技术,此前在同为宋德方主持建设的龙山道教石窟已有应用,至今有效运行(图10);只是龙山石窟顶部已被文物保护施工覆盖,难知其旧,而神仙洞所见保护技术之施用,明显强于龙山。
正如山下大碑所言,“夫成此非常之事,乃非常之人。”自古莱州人工于山石,至今其地石业犹盛。文献显示,王重阳本人及其在胶州半岛吸纳的一些当地徒众,如马钰、刘长生、宋德方等俱谙山石之道。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一“马钰”:
师在文登七宝庵,门人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师乃示洞中仙词云:穿凿须加二尺深,甘泉自有应清吟。凿之一尺八寸,泉自涌出。*《道藏》第5册,第420页。
王重阳还曾现场指导洞窟的开凿。全真道文献《甘水仙源录》卷1《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记载:
(大定)八年三月凿洞于昆嵛山,于岭上采石为用,不意有巨石飞落,人皆悚栗,真人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间樵苏者惧呼作礼,远近服其神变。*《道藏》第19册,第724页。
此处所述即1168年王重阳携马丹阳、谭处端等弟子在昆嵛山开凿烟霞洞事。师徒所长,于此山石间,尽得其用,觅仙于山崖顽石,视其“外坚内虚”而“不为难事”(山下元碑局部,见图11),亦可谓以技证道乎。
三、结 论
作为一种要求出家住庵的禁欲主义宗教,全真道不仅把山庵洞窟作为苦修的地方,而且在本质上继承了传统道教对山中洞穴之神仙转化功能的信仰。洞穴代表的乃是仙家时空(如王质烂柯神话),故谓“洞府”。为此世代道门中人形成和传递了用以择地、造窟和保护的理论与技术。由于此类道教石窟建筑保存较少且多隐于深山,其中蕴含的科技价值长期受到忽视。即使在古人编纂的诸如《艺文类聚》《古今图书集成》之类的类书中,亦未将“洞窟”单列一类;《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山居部”也大多将其归于别墅(院)一类。这或许是其建筑类型长期为建筑学界所忽视的原因之一。
显然,道教石窟建筑研究对于深入理解道教信仰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修道者对山中洞室的酷爱和追求,其原因决不仅在于去离人烟、禁欲修道的欲望控制,更重要的是借神真所居“洞天”达其“通天”成仙之宗旨。正是这种内在的信仰动力,驱使宋德方之徒为之竭力尽心,从而在石窟建筑的开凿保护领域取得了卓越的科技成就。
更重要的是与这些技术相表里的道家思想:了悟“自然”之道、使人的行为与天地的运行相偕一致,才能得其长久。《道德经》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人类行为(文明张设)达到与天地运行相默契,才能进入“几于道”“同于道”的境界。
世谓道教神秘,而“道教与生态科技”更可谓扑朔迷离。《老子》所谓“同于道”者,言之易,行之难;难在引人走向体悟的出路与方法,然而真道也正是隐藏在此中。实质上,四川都江堰、山东神仙洞,为世人提供了绝好的理解通道。只是这些沉积着道家思想精髓的宝贵文化资源,隐乎山水千年,以技术的甚至艺术的面目出现,今人更难握其思想本真。
与都江堰系统所内含的“道法自然”思想一样,莱州神仙洞的生态干预式建筑自动保护技术,充分体现了老子“同于道”、庄子“庖丁解牛”所示的因乎自然而遂人愿的伟大思想,二者同属“道法自然”思想的顶峰之作。这些“几于道”的科学技术成就对于今人探索“基于生态观念的科学技术”,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支持与“教材”意义。
以宋德方为代表的13世纪全真道石窟建筑开凿与保护技术探索实践群体,在莱州神仙洞石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洞穴建筑保护技术遗产,体现了“道法自然”思想的实践结构,代表着道教建筑保护技术的最高水准。我们根据科学考察和研究,将其科技成就总结为由“清、剔、破、通”等一系列具体方法构成的“生态干预式石窟建筑自然保护技术”;这种技术的实施,使洞窟顶部的保护具有了一劳永逸的或曰“自动化”的性质。
生态干预式石窟建筑自然保护技术,始于自然生态之调整,“依乎天理”,而终之以文明设施与自然环境形成老子所谓“不争”的关系,达到“人之道”与“天之道”密切吻合、互相为用的状态;干预处理后的这片山崖,进入了一种稳定运行的新生态。
从道教的角度,宋德方之徒可谓得“道”之高者、无愧真人之称,恰如庖丁所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李冰、披云,可谓以技证道者。《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目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17-124页。从科学的角度,这种“自然”思想对于某些洞穴建筑遗产的保护,以及当代建筑之生态设计乃具重要借鉴意义,直可谓建筑生态学之境界标帜。
神仙洞与都江堰,造作相去千年,却蕴含相同的自然生态科技思想,且其系统至今亦皆运行正常、泽被后世,虽贡献领域不同(物质与精神)而思想所本无异,可谓同臻至道、堪与媲美焉。
(责任编辑:曹玉华)
“Beyond Skill”: The Construction of Mt. Hantongshan Daoist Grottoes in Laizhou and Its Eco-Interveni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Jiang Sheng, Wang Ru
Mt. Hantongshan Grottos in Laizhou, Shandong, the highest representative of Daoist construction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biggest Daoist grottos in north China, were done by a group of early Quanzhen Sect Daoists led by Song Defang in the 13th century. “Beyond skill” (as Zhuangzi says), and a perfect performance of the thought that “Dao follows naturalness” (as Laozi says), the grottos are an invaluable treasur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grottos and the rocky top were taken together as a whole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tection; the technology in this protection can be summed up as “eco-intervention technology for natural protection of rock grottos,” including at least four demensions, i.e., clearance, removing, breaking, and dredging. With climate factors (sunlight, wind and rain) converted into protecting forces, the system is still operating today, providing an ideal sample for the designing of eco-buildings and ancient rock grottos protection. Considering the thought of eco-technology, the Mt. Hantongshan grottos protection system rivals the Dujiangyan irrigation system.
Daoist construction, grottoes of the Quanzhen Sect, Immortal Caves in Mt. Hantongshan, eco-intervention technology, ancient construction protection technology
姜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二级教授(成都610065);王茹,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济南37010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宋元明清道教与科学技术研究”(13&ZD078)
B958,K878.6
A
1006-0766(2016)05-00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