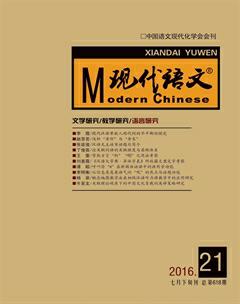常熟方言“则”“嘚”之用法考察

摘 要:常熟方言中,“则”“嘚”是两个基本的完成(实现)体标记词。“则”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有“了1”和“了2”两种用法,分别表示完成和已然义;“嘚”的用法有:于动词后充任现实体标记,相当于“了1”;在话语中,凸显现实事件对于听话人的未知性;用于“V+嘚+处所词”的存现句式,表人或物存在于某位置或处所的事件,相对于参照时间已经实现。
关键词:“则” “嘚” 体标记 未知性 处所词 变体
一、引言
常熟方言属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与北吴其他方言如苏州话、上海话等基本能互通。它与苏州话渊源深厚,属于广义上苏州话的一种,但又与苏州话存在系统性的差别,是一种较为独特而又颇具代表性的吴语次方言。
以往针对常熟方言的研究甚少,关于此方言中体标记的分析更是寥寥无几。出于地理优势考虑,一般研究吴语尤其是北部吴语语法的文章多以苏州话或上海话为对象,最早可见赵元任(1979)的研究,他提出吴语中的“仔”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1”,“哉”相当于“了2”;汪平(1984)指出“仔”和“了1”,“哉”和“了2”有共通之处,但非一对一的简单对应;刘丹青(1996)、陶寰(1996)对吴语尤其是苏州话的体标记做了细致的概括和描写;梅祖麟(1980)提出吴语的“仔”有两种用法,一为完成貌词尾,二为持续貌,相当于“着”,并列举了“着”(著)在不同吴方言点的发音,其中提及了常熟方言的情况。专门针对常熟方言体标记的研究文章只有两篇,且都以“V+开”为研究对象(王建,2008;袁丹,2011)。研究者普遍认为,常熟话的体标记基本等同于苏州话和上海话,常熟市区话的实现体标记与苏州话一致,都为“仔”。
二、常熟方言“则”“嘚”的句法分布和语法意义
常熟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与苏沪方言接近,因此持常熟方言者能与苏沪地区的人互相沟通。但是,除了有类似苏沪方言的用法外,常熟方言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比如它的体标记系统。李如龙(1996)提出用4条标准来界定体标记:1.意义的虚化;2.结构关系的黏着;3.功能上的专用;4.语音的弱化。在常熟话中,与普通话体标记“了”相关的典型的体标记词有:“则”“嘚”“哉”“开”“好”等。以往在常熟方言的研究中,对“则”的描述不够全面,而对“嘚”的情况基本没有涉及,因此,本文对常熟话中的“则”[ts?]“嘚”[t??]这两个完成(实现)相关的体标记词进行考察,结合语料分析其句法结构和语义特征,并与普通话中“了”的相关用法相对照,分析两者的内在关联及前者异于普通话的特殊用法。
普通话中,“了”在语义上表示事态的变化、已然,即表示某一动作、行为、情况和状态的实现和完成。“了”有两种用法:动态助词“了1”,附于各类动词后,表明谓词和其他谓语形式的词义所指处于事实的状态之下;语气助词“了2”,附于句尾,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则”(仔)的用法近于“了”,相当于“了1”和“了2”;“嘚”与“了1”相通,但其用法与普通话并非简单对应。以下对这两个体标记在常熟方言中的具体用法分别进行描述及分析。
(一)“则”的分布和意义
“则”与普通话的“了”最为接近。以往研究者将其用法等同于苏州话的“仔”,其实,“则”与“仔”的用法有一定的差异。“仔”的用法相当于“了1”,而“则”却有“了1”和“了2”两种用法,分别表示完成和已然义。“则”可出现于以下几种语法结构之中:
1.“则”后附动词
1)“V”+则+“O”(带宾语)
(1)姆妈买则一只西瓜。(妈妈买了一个西瓜。)
(2)我汰则一件衣裳。(我洗了一件衣服。)
2)“V”+则+时量补语
(3)我等则三刻钟,门还分开。(我等了三刻钟,门还没开。)
(4)小王跑则两个钟头,一个人也分看见。(小王走了两个钟头,一个人也没看见。)
3)“V”+则+动量补语
(5)我讲则两趟,小王总算听清爽则。(我说了两次,小王总算听清楚了。)
4)“V1”+则+“O”+“V2”(连续动作)
(6)你契则饭再看电视。(你吃了饭再看电视。)
5)“V”+补+则+(“O”)(动补)
(7)我契坏则肚皮。(我吃坏了肚子。)
(8)小王要气杀则。(小王要气死了。)
6)“V”+则+(“O”)+补
(9)小王跑则出去。(小王走了出去。)
(10)旧年我到则北京去。(去年我到了北京去。)
7)“V”+则+“O1”+“O2”(双宾语)
(11)舅舅给则我两千块钞票。(舅舅给了我两千块钱。)
8)“V1”+则+“O”+“V2”(兼语式)
(12)昨天我爸请则王老师契饭。(昨天我爸请了王老师吃饭。)
根据调查,“则”可出现于以上8类句法结构中。这几类句式的共同特征是:“则”紧密依附于动词之后,表示动作已经实现或事件成为现实。句式5)中,尽管“则”处于动词和补语之后,但如“契坏”“气杀”这样的黏合式述补结构可视为一个复合动词,因此,在上述结构中,“则”无一例外地后接于动词,成为一个虚化程度较彻底的现实体标记,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1”。另外,“则”不具有现实相关性,只表明“则”所关涉的事件相对于参照时间已成为现实,这与“了1”的用法相一致。如例(6)中,“契则饭”对于“看电视”的时间来说是已经发生了,但对于说话者现在的时间而言是未然的,因此“则”也可用于表述未发生的将来的事件。
2.“则”位于句尾
1)“V”+“O”+则
(13)小王去北京则。(小王去北京了。)
(14)我买水果则,快来契点。(我买水果了,快来吃点。)
(15)契饭则!(吃饭了!)
“则”亦可出现于动词和宾语之后,表示在说话时,事件出现了新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如例(13)中,对说话人来说,“小王去北京”是新的事件,小王所处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又如例(15),句末用“则”表示饭已经做好了,催促听话者来执行吃饭这一动作。吃饭的事件即将发生,听话者的状态即将出现新变化。此时,“则”一般位于句尾,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2”。
2)“V”+则(无宾语)
(16)雨停则。(雨停了。)
(17)我晓得则。(我知道了。)
(18)小王笑则。(小王笑了。)
这种格式无宾语,即“谓词+则”出现在句末,此时,“则”既可表示一种变化已经实现,也可表示新情况的出现,相当于“了1+2”偶合的形式。如:例(18)中,小王笑的行为,既可理解为“笑”这一事件已成为现实,也可理解为小王原来没笑,现在出现了“笑”的新情况,且这一动作可能持续下去。
3.“则”的其他用法
1)Adj.+则+……(形容词谓语)
(19)老王哩两年老则较关。(老王这两年老了很多。)
(20)哩件衣裳大则点。(这个衣服大了点。)
“则”也可出现于形容词作谓语的结构中,紧跟于形容词后,表示这个句子中的情状已成为现实。如例(19)中,“老王老很多”这一情况相对于参照时间已成为现实,“则”相当于“了1”。另外,在这种结构中,“则”后需加入其他成分,如表示程度、范围的补语,补充说明形容词所描述的情状,若“则”出现于句末,例如“老王哩两年老则”“哩件衣裳大则”,总有语焉未详之嫌。普通话中“了”的使用不受此限制,如“老王这两年老了”“这件衣服太大了”。
2)“N”+则
(21)春天则,花全开则。(春天了,花都开了。)
“则”也可直接出现于时间名词后,表已然义,如例(21)中,“春天则”,表示春天已经到来。
3)“S”+“V”+则+“O”+则
(22)小王去则北京则。(小王去了北京了。)
常熟方言中,一个句子中出现两个“则”是很常见的情况,如例(22),前一个“则”位于动词后,相当于“了1”,后一个“则”位于句末,相当于“了2”。而在普通话中,这样的句子出现的频率较低,“了”在同一句中重复出现的可能性较小。
与普通话相一致,常熟方言的“则”不能出现于否定句中,即“则”无法用来否定现实已然的情况。常熟方言中对现实情况的否定形式如下,“分+V+……”
(23)上礼拜我分去上海。(上礼拜我没去上海。)
4)应+“V”+“O”+则?(疑问句)
(24)恁应去上海则?(你去上海了吗?)
“则”还可用于疑问句中,表示对句中事件是否实现的提问,形式与普通话有所差异,疑问词“应”不在句末,而附于动词前。
无论是从“则”出现的句法结构还是表达的语法意义来看,它都与普通话中的“了”相一致,且具有“了1”和“了2”两方面的用法,这与苏州话中的“仔”只具有“了1”的用法是截然不同的。
(二)“嘚”的分布和意义
王建(2008)提出,“嘚(得)”是常熟练塘话(练塘为常熟郊区乡镇)的现实体标记,常熟市区话的现实体标记同于苏州话,为“仔”。“嘚”的用法与苏州话中的“仔”,即普通话中的“了1”相同。然而,根据常熟话的语言事实,“嘚”不仅是练塘话的体标记,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常熟市区及郊区乡镇的方言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另外,“嘚”除了能作为现实体标记使用外,还能出现在一些特殊的句法结构中,表达特殊的语法意义,体现出异于普通话“了1”的特点。以下对“嘚”的语法结构和语义一一分析:
1.“嘚”相当于“了1”的用法
1)“V”+嘚+(数量词)+“O”(带宾语)
(25)我夜里契嘚两碗饭。(我晚上吃了两碗饭。)
(26)小王去嘚北京。(小王去了北京。)
(27)我打翻嘚一杯茶。(我打翻了一杯茶。)
这一句式是“嘚”出现频率最高的情况。除了专名,宾语前一般会有数量词,构成数量名结构。这一句式中,“嘚”的用法等同于“了1”。另外,例(27)中,“打翻”作为一个黏合式述补结构,动作“打”和结果“翻”之间关系密切,可视为复合动词。
2)“V”+嘚+(“O”)+时量补语/动量补语
(28)我等嘚(小王)三个钟头。(我等了(小王)三个钟头。)
(29)我看嘚两遍,你呢?(我看了两遍,你呢?)
3)“V1”+嘚+“O”+“V2”(连续动作)
(30)好公契嘚早饭去买报纸。(外公吃了早饭去买报纸。)
4)“V”+嘚+(“O”)+趋向补语
(31)小王昏嘚过去。(小王昏了过去。)
(32)昨日头我领嘚点钞票出来。(昨天我领了点钱出来。)
5)“V”+嘚+“O1”+“O2”(双宾语)
(33)小王送嘚我一双鞋子。(小王送了我一双鞋子)
6)“V1”+嘚+“O”+“V2”(兼语式)
(34)小王喊嘚朋友帮忙修电视机。(小王叫了朋友帮他修电视机。)
7)Adj.+嘚+……(形容词作谓语)
(35)我挨嘚点,不好意思。(我晚了点,不好意思。)
“嘚”出现于以上7类句法结构中,必须紧跟动词,依附于动词之后,表示句中事件的现实性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1”。“则”也有以上的用法,但“则”还能置于句末,表示新情况的出现,“嘚”没有此类用法。也就是说,“则”有普通话中的“了1”和“了2”两种用法,而“嘚”只有“了1”的用法,它只能出现在动词后,不能置于句尾的位置。
2.“嘚”凸显话语的未知性
以上句式中的“嘚”可以与“则”互换,意义基本不变。然而,在下面的句子中,“嘚”不能用“则”代替:
(36)a.囡囡,妈妈回家了,我买嘚巧克力,阿想吃?(宝宝,妈妈回家了,我买了巧克力,想吃吗?)
b.* 囡囡,妈妈回家了,我买则巧克力,阿想吃?
(37)a.甲:恁去嘚阿浪?(你去了哪里?)
乙:我买嘚蛋糕、牛奶、火腿肠。(我买了蛋糕、牛奶、火腿肠。)
b.*甲:恁去则阿浪?
乙:我买嘚蛋糕、牛奶、火腿肠。
c.甲:恁买则啥物事?(你买了什么东西。)
乙:我买则蛋糕、牛奶、火腿肠。
例(36)中,在妈妈回家时,宝宝完全不知道妈妈会买东西这一事件,例(37)a中,问话人也完全不了解答话人去做了什么,在话语中,需凸显事件对于听话人的未知性时,用“嘚”而非“则”。例(37)c中,问话人已知听话人买了东西,因此,答话人可以用“则”来表示买了具体食物的现实。
3.“V”+嘚+处所词的特殊句式
“嘚”除了用于动词后,充任现实体标记外,还能出现在下面的句式中。如:
(38)恁格书放嘚台子浪。(你的书放了桌子上。)
(39)小猫困嘚门口头。(小猫睡了门口。)
(40)恁住嘚阿浪?我想寻恁白相。(你住了哪里?我想找你玩。)
以上格式中,“嘚”后出现的成分为处所词,即动词+“嘚”+处所词构成存现句。此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句中的“嘚”进行分析:
1)不能与“了”互换。
如果用“了”来替换“嘚”,就会出现像“我住了北京”“他睡了床上”这类在普通话中接受度极低的句子。如果把处所词和主语交换位置,构成如“处所词+V+‘嘚+O”的句式,部分句子的“嘚”可以替换为“了”且意义基本不变。如:
(41)桌子上放了(一本)书。
(42)门口睡了(一只)小猫。
然而,体标记“了”以“处所词+V+了+(数量词)+O”的句式出现,表达处所、位置相关的事件对于参照时间的现实性,这一语法意义看似与上述“嘚”的用法相同,但实质上却大相径庭。其一,“处所词+V+了(嘚)+(数量词)+O”的句式,强调某个处所存在着某物,“O”为焦点信息,而“V+嘚+处所词”的句式,则强调某物存在于某处,处所为焦点信息。其二,不是所有的句子都能转变为普通话“处所词+V+了(嘚)+(数量词)+O”的句式,如“北京住了我”这样的句子仍是不可接受的。
2)语义上接近于普通话中的“在”,与存在义相关,但不等同于“在”。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话中也有类似的“de”(写作“的”),构成“V+de+处所词”的句式。龙果夫(1958)提出,在河北方言里(北京和河间府),当主语是由加上语尾的“的”构成的时候,带有后置词的名词和地名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单独作谓语。例如:
(43)别睡的地下。(“别睡的”——主语,“地下”——谓语)
(44)你住的哪儿?——我住的北京。
(45)扔的水里去啦。
赵元任(1979)认为,这个“de”(写作“得”)是“在”和“到”的混合物,“在”和“到”在口语里都可以说成“得”。如:
(46)别就那么坐de那儿!
(47)他搬de哪儿去了?
林焘(1962)指出,在北京土话中,“住在北京”中的“在”有几种不同的读法:住/dai/北京、住/dou/北京。从/zai/到/de/,是“在”因连续语流中的弱读而引起的音变。刘丹青(2008)把“V+de+方所宾语”中的“de”看作附缀(clitic),即在句法上具有词的地位、在韵律上失去独立性而必须依附在另一音节上的单位。总之,北方话中的“de(的)”被研究者视为“在”的语流音变的变体。
在常熟方言中,相当于普通话的“在”的词语有“勒浪、勒嘿、勒得”等,它们可构成“S+勒浪+处所词”“V+勒浪+处所词”“勒浪+处所词、小句”等句式。而“嘚”只能出现在“V+嘚+处所词”中,因此“嘚”出现的句法位置与“勒浪(在)”不同。另外,“V+勒浪(在)+处所词”,表示一种静态的存在义,而“嘚”具有动态色彩,语义上也与“勒浪(在)”有明显区别。这类格式中的“嘚”,与普通话中的“了1”的时体意义相同,表示事件的现实性。如例(38)中,“你的书放在桌子上”这一事件相对于参照时间来说是已实现的,例(39)中,“小猫睡在门口”这一事件也是已经存在的,且可能持续下去。而对这样的句子稍加变化:
(48)a.刚刚恁格书放嘚台子浪,现在哪能不见脱则?(刚才你的书放在桌子上,现在怎么不见了?)
b.恁看,恁格书放嘚台浪呀。(你看,你的书放在桌子上呀。)
c.*明朝,我弄恁格书放嘚台浪。(明天,我把你的书放在桌子上。)
d.明朝,我一定弄恁格书放嘚台浪再出门。(明天,我一定把你的书放在桌子上以后再出门。)
以上4个句子,a、b、d都是可接受的,c则不成立。“书放桌子上”这一事件,在a和b中对参照时间来说都已成为现实。d句,虽然整句表示的时间为将来(明天),但书放桌子上的参照时间为出门,因此,对于出门来说,这一事件是现实性的,句子可以成立。c句,书放桌子上的事件对于参照时间明天,还未实现,句子不成立。
综上所述,常熟方言中的“嘚”是一个独立的现实体标记,不同于普通话中的“了”,也绝非“在”的变体。与北方方言中的“de”相比,它具有完整的时体意义,处于“V+嘚+处所词”句式时,其标记意义为:人或物存在于某位置或处所的事件,相对于参照时间来说已经实现。“嘚”所依附的动词有两种:一为持续性动词,表示动作的状态在参照时间已经存在且可能会持续下去,如例(40)中的“住嘚”;二为非持续性动词,表示动作发生所引起的结果在参照时间内已经存在且会持续下去,如例(38)中的“放嘚”。
4.“坐仔(嘚)比立仔(嘚)适意”的特殊用法
赵元任曾提出吴语中“仔”的用法的著名例子:
(49)坐仔(嘚)比立仔(嘚)适意。
(50)骑仔(嘚)马寻马。
(51)墙头浪挂仔(嘚)一只钟。
赵元任(1956)认为,这里的“仔”不能等同于普通话中的“了”,而应相当于“着”。梅祖麟(1980)从语音演变的角度提出“仔”来源于“着”,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而汪平(1984)则从共时的平面提出,这里的“仔”并不是“着”,而是“了1”。
然而,常熟话中的“嘚”也可以出现在这样的例句中,以上研究者的解释就值得商榷了。首先,“嘚”不太可能是“着”,两者的语音差异太大,用梅祖麟的语音演变理论无法解释从“着”到“嘚”的转变过程。其次,汪平认为,吴语中没有一个相当于普通话中“着”的表示持续貌的后缀,而且以上例句中的动词,既可理解为持续的状态,也可理解成一个瞬时的变动,表完成貌。因此,这里的“仔”并不是“着”,而是“了”。汪平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不够严密。例(50)理解为“骑了马找马”是可行的,表示先发生骑上马这个动作,再进行找马这一事件;例(51)中,“墙上挂着一个钟”和“墙上挂了一个钟”在普通话中都是可接受的,且意义相近,因此,无法用此句式来判断“仔(嘚)”是普通话中的“着”还是“了”;但例(49)难以解释,汪平也承认“坐了比站了舒服”这样的句子可接受度极低,因为“舒服”是表持续性的状态,“坐”和“站”这两个动词无法理解为完成义。他最终的解释是:例(49)在方言中也不太自然,更通行的说法是“坐勒浪比立勒浪适意”。这一解释未免过于牵强,在常熟话中,“坐嘚比立嘚适意”是很常用很自然的说法,在这样的句式中,动词仅限于“坐、立、站、睡”等动词,“嘚”还可被替换为“勒浪”“勒嘿”等表存在义的词语。因此,“坐嘚比立嘚适意”其实是“‘坐嘚+处所词比‘立嘚+处所词适意”的省略形式,“嘚”后的处所为大家所知,不需特别指明,因此省略。“嘚”的这一用法正体现了其存在义现实体标记的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常熟方言中,“则”和“嘚”是两个被广泛使用的现实体标记词。它们的用法如下表所示:
“则”相当于普通话的“了”,与苏州话“仔”的用法有一定的差异。“仔”的用法相当于“了1”,而“则”却兼具“了1”和“了2”的用法,分别表完成和已然义。“嘚”用于动词后,充任现实体标记,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在话语中,需凸显事件对于听话人的未知性时,用“嘚”而非“则”;另外,“嘚”还能出现于“V+嘚+处所词”的句式中,表示人或物存在于某位置或处所的事件,相对于参照时间来说已经实现。北方方言中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得”,构成“V+de+处所词”的结构,以往研究者将其视为“在”的语流音变。南北这两个“de”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其他方言中是否还存在“de”的这类用法,考察各种方言的结果是否能为“de”的来源和演变提供新的佐证,这些问题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解决。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及方言中的否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AY0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汪平.苏州方言的“仔、哉、勒”[J].语言研究,1984,(2).
[3]刘丹青.苏州方言的体貌范畴与半虚化体标记[A].胡明扬等主编.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4]陶寰.论吴语的时间标记[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
[5]梅祖麟.吴语情貌词“仔”的语源[J].当代语言学,1980,(3).
[6]王健.江苏常熟练塘话的准体标记“开”——附论“得、过、脱、好”[J].方言,2008,(4).
[7]袁丹.从语法化和类型学看吴语常熟话“V开”的功能[J].汉语史学报(第11辑),2011.
[8]龙果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9]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M].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1928.
[10]刘丹青.从普通语言学看虚词的性质和汉语虚词的分类[R].
第三届全国现代汉语虚词与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上海),2008.
(王蕾 上海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00433)